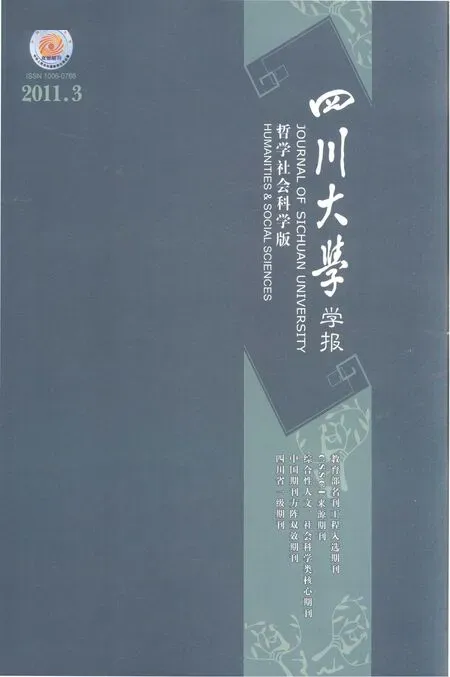莎剧中的性别意识与性政治
查日新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其作品充满人文主义思想,但在两性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出为谬见所污染的性别等级意识。在两性方面,西方性别等级意识被认为与男权主宰的性政治相关。若干莎士比亚戏剧承袭了西方普遍的性政治模式,即男权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把性别关系定义为权力关系。莎剧中的性别等级意识表现为对女性的否定,视女性为身体和精神有“缺陷”的性别,认同两性关系上的统治逻辑,且在剧中让女性内化为自我否定的因素,甚至表面的赞誉也实为本质上的否定;另外也表现在认同自然性别被强加的文化意涵,即由此形成的一种自然性别之外的性别状态,以及据此建立的压迫性的两性秩序、用来维护男权统治特权的种种律令和规范。这种性别等级意识的形成在于其个人意识背后的性政治立场,莎剧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性别意识的认同、甚至是张扬,可视为性政治的文学表达。
一、“男权神授”与莎剧中的性别统治
在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中,性别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物属性。在性别这个特殊的场域里围绕性别产生出权力话语,其表现形式之一是以霸权的方式对女性的性别身份进行规定。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统治、支配、等级秩序等概念构成了男性与女性之关系的基础。这一压迫性的男女关系在西方的思想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归结到西方的传统思想文化及基督教。
奥林匹斯诸神的谱系体现了最早的家长式等级秩序,其权力结构的核心就是男权统治。古希腊人以神话方式表现的神界秩序,创立了最早的“男权神授”模式,成为西方性别统治的原型。文艺复兴尽管很好地诠释了古希腊哲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者理直气壮地张扬人性,把人推到崇高的位置,在与中世纪教会统治的角逐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自由,但女性并没有因此改变传统的性别格局,现实状况依然是“男人是女人的尺度”。在莎剧中,男权意志时常被作为衡量和否定女性的“尺度”。批评家发现当时“有许多种方式让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妇女和莎剧中的女性角色被贬低、被魔化、被压制”[1]51,如莎剧中所书写的“男性厌女症和女性顺从”的故事[1]54。宗教方面,伴随上帝创世纪形成的“等级观念……实已深入基督教的骨髓”[2]。上帝设立了两个范畴的统治关系:一是人对自然的统治;二是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两者皆见于《圣经·旧约·创世纪》,且都为后现代文化批评所垢病。首先,上帝特许人以统治权:“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第二种统治关系见之于上帝创造女人的方式,“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并命令女人“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实际上是男人按自己的需要创造了“妇女的形象”,故“男权制让上帝站到了自己一边”[3]70-78。上帝创造的女人从最初就被置于从属的地位,全然是男权创世神话的产物。女性的身体源自男性的肋骨说明女性的身体不具有独立的完整性,因此,她的“缺陷”就是天命之规定。上帝创造女人的方式为男权话语把女性视为“低劣”的性别提供了思想本源,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以“男权神授”确定了男性的主宰地位,这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性政治图式高度一致。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其中不少女性角色看似不同于传统女性,甚至带有女性解放的意味。但这只是表象,细观可以看到她们仍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很多情况下,爱情、幸福的获得不是因为她们挑战父权成功,而是对父权的妥协。“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惯例”[3]40。有一种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可看作与一种压迫性的性别意识形态形成了同谋关系,并在戏剧的世界中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1]54。能纳入这种批评视角的莎剧颇多,如《哈姆雷特》、 《李尔王》、《奥赛罗》、《训悍记》、《错误的喜剧》、《第十二夜》、 《无事生非》、 《爱的徒劳》等。另外,研究者还发现莎剧中若干与基督教贬斥女性相似的表达,但本文并不倾向将此做完全的对应,而是认为作为文学的莎剧浸染了西方文化普遍的性政治要素,与之形成某种契合,承袭并强化了这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在戏剧文本中建立起男性主宰的空间。在《错误的喜剧》中,露西安娜认同“人类是控制陆地和海洋的主人”,超越一切“走兽飞禽”,而同时自然界中“雌”对“雄”的遵从成了她眼中女性的角色原型:“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你应该温恭谦顺侍候他的旨意。”[4]13-14显然,在人与自然、雄与雌的二元关系中,前者被奉为当然的统治者。她的言说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意识体系,特别是基督教“现在 (或过去一直)明确地灌输一种被父系制度价值统治的家庭主义道德,尤其是女人天生低等的信条”[5]119。这种表述与《创世纪》篇的主旨在不同语境下形成“互文”,既契合又以类比扩增了新的意涵。而这类女性角色只是莎剧中众多男权制下的女性人物之一,表明莎士比亚认可并在戏剧文本中再现性别等级秩序的统治:一切受制于等级秩序,此乃宇宙的法则;而女人受男人统治恰恰是源于宇宙的法则,是人类社会建立的秩序的根本依据,也是造物的意志的体现,因而女人对男人的服从扩展为普世准则和道德律令。显然莎氏的立场既表达了基督教的性别立场,也彰显了西方文化自古以来普遍的“性别集体无意识”。西方思想文化中的男权意识为基督教对男女的差异定位所强化,并产生出普遍的权力话语,成为形塑个体的工具。男权统治不仅为男性所利用以维护自身的特权,甚至也为女性所接受或被迫接受,使女性在自觉不自觉中成为压迫者的同谋,或者说被女性内化为自我遵从、自我否定的信条。露西安娜预设婚后生活的原则是“出嫁从夫”, “安心忍耐”[4]14。《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把父亲当作“家长和严君”,奥赛罗为“夫主”。此外,《驯悍记》中可以看到男权统治得以重建并取得最后胜利。《皆大欢喜》中看似自由的女性还是逃不出男权的控制并最终回归。总之,男人就是宙斯式的大家长,女性对自身,或在更广的意义上对女人的理解就是怎样尽到女人的“名份”,她们生活的轨迹就是从一个父亲走向另一个“父亲”。
性政治另一种伪装的统治手段是把女性美誉化。对女性的赞美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文化传统的体现,但实质是男性成为超越的性别后获得的一项特权,暗示男权的中心性,因此是一种隐蔽的暴力,它与贬斥女性在思想上同源。“骑士的举止只是主人集团将依附对象抬到偶像地位加以崇拜的游戏,……它们还模糊了西方文化的男权实质,并且通过向女性交付难于实现的美德,让女性局限一个狭窄的、往往被无偿征用的行为范畴”[3]56。莎剧对此的呈现就是把温柔、善良、贞淑等理想化的美德投射到女性身上,让女性成为良善品质的载体,但实际意义是男性把美好的品质置放到女性身上构成了对女性的禁锢,一旦成为某种男性理想品质的象征,女性便在被奴役的状态下更难以自拔,并受之评判、定义和规范。剧中通常表现遵从者受到赞誉,违反者必受惩罚。招致惩罚或悲剧的“过失”只是原因之一,重要的是她们被认为违背了男权的意志。而这种以“爱”的名义实行的统治在西方思想文化中长期存在,其核心是用服务于男权利益的“美德”迫使女性成为“利他”的存在,在赞美中失去自己。
二、身体的否定与女性的否定
性政治作为一种以男权为基础的性别意识形态,其立场必然表现为对男权统治的认同及对其合法性的维护。在西方思想文化中,性别意识的范畴是一个各种力量纷纷介入的社会的场域、政治的,通常以否定女性来证明性别统治的合理,而否定的路径一般由对女性身体的否定开始。
确实,莎剧中有大量的表述对女性身体纠缠不休。这可能不只是当时的社会风尚粗俗所能解释。女性主义批评家指责莎氏的女性观沿袭了西方思想文化的传统,把女性看作是有“缺陷”的性别。这个所谓的“缺陷”为莎士比亚通过男性视角的书写来彰显女性的“低下”和强调女性的“他者性”,并对女性实行双重否定提供了基础:以暗示女性身体的“缺陷”为先导;继之以张扬女性心智、精神的“缺陷”。西沃尔特等学者发现,女性在男权话语的呈现中消失或失语,但对女性“缺陷”的表述却从未缺失。她注意到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的一段对话,最后的一个双关语“nothing”暗示奥菲利娅的女性“缺陷”[6]617。
表面上,“nothing”的词义简单明了,就是“没有什么”,但西沃尔特明确指出“nothing”隐匿的意义远大于表面的意义,故不能只理解为“没有什么”,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俚语中,“nothing”还是一个“指称女性性器官的词语”[6]617。西沃尔特认为哈姆雷特隐含的主旨藏在“没有什么”的表面意思之下,他真正想说的是“位于姑娘的大腿中间什么也没有”[6]617-18。所以,他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双重表达,用“nothing”来完成一个彰显语言暴力的陈述——“女人→缺陷→低劣→无价值”。用“nothing”来指称女性的性器官,绝不仅仅是对女性身体的生物性描述,其中包含着自然性别差异并因此而导致优劣高下之分的文化观念,重心在于强调女性性器官相对于男性性器官在视觉上的“缺失”或“没有”,并试图通过男性的“有”和女性的“没有”来说明女性在身体上有先天的“缺陷”。为此,西沃尔特赞同伊丽格瑞的观点,认为在男性主导的呈现系统中,女性的“无”、“不可视见”导向否定的阐释[6]618。伊丽格瑞在 《非“一”之性》中认为,“她的性器官并不是一种性器官,只能说不是性器官。它只是阴茎这个惟一看得见的有形可指的性器官的否定之物,对立之物”[7]。莎氏对“无”的强调关系到西方文化的羡阳传统,即从“生态形式”方面对女性的否定,亦可看作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否定策略。
所以“nothing”集中体现了西方在女性观方面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可以说在哈姆雷特的意识背后,乃至莎氏的女性观背后,还有一个更庞大而强势的权力话语体系。用“nothing”来指称女性的性器官,绝不仅仅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一个陋词,“无”与“有”的模式沿袭了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但对立的双方并非在同一个层面上,而是被纳入一个统治和被统治、中心与边缘、“我”与“他者”的结构,其重心在于把男女自然性别的差异赋予自然差异之外的文化意涵,形成性别的逻各斯,使原本只是性别的自然差异因为二元思维的介入而形成性别观念上的高低优劣,并使观念的性别超越自然的性别成为性别等级秩序的思想基础。所以,“无”作为女性身体的“缺陷”被当作贬低女性的“事实”依据,并被用来铺垫下一步的否定:对女性心智、精神及主体性的否定。
在权力话语对身体的建构中,语言很难说是清白的。通过解构的视角,批评者发现“现有的语言交流模式只能被看作是以父亲的名义,以霸权的父权话语实施的压迫性统治”[8]。在西方的权力话语中,男性以“中心—我”的身份控制着性别规范的制定,同时也控制了语言。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莎剧中许多指涉女性性器官的词语皆具有男性视角,并折射出男性主体权力对女性的统治。哈姆雷特通过对词语的主宰达到对言说的控制,最后用“nothing”完成对女性身体的否定。此外,莎剧中其他的贬斥女性身体的词语也不少见,这些词语都可看作是承载男权意识的节点。如《圣经》所述,人类通过对自然存在物进行命名获得了对自然界的统治权;同样,男性以占有类似的“命名权”实施对女性的统治。莎剧中若干指涉女性身体的词语都具有类似强制“命名”的色彩,如:“the O,the pit,ring,casket,the subtle hole,her C’s,U’s and T’s,the lake,pond,swallowing tomb”[9]等等。“O”是一个男性视角下的指涉女性性器官的符号,如果作为词汇来解读,“O”与“nothing”可视为同义词,都表达否定的贬义:无、空、没有、等于零;另外一个词“ring”在词义上可作“圆、圈、环状物”来解释,因此与“O”、“nothing”也是同义的。另外如“her C’s,U’s,T’s”也是对女性性器官的色情化描述,虽不具有像“nothing”一样明显的否定,但由于其过于色情化的视角而带有贬斥女性的意图。这些词汇的重心在于通过男性视角把女性性器官妖魔化,甚至将之贬斥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其意象是强调“黑暗”、“不可见”、“坠落”、“空”、“无”等,故这些词语都是带有典型“男权隐喻”的表达[9]。首先,女性的身体在男性凝视下被强加了性别的政治标签,已不是单纯的生物意义上的身体,她们的身体在男性权力意识的作用下被重构,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意涵,使原本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身体”失去了其本来的规定性。外在于身体的因素将其置于男权主宰的政治空间(作为财产,作为被统治对象),各种力量卷入其中,目的皆在于让女性身体服务于除其本身之外的其他利益。
把女性身体罪恶化也是西方性政治的重要手段。李尔王因女儿的忘恩负义而在激愤中说出的一个词语“火坑”,卡罗尔指出它是将女性身体器官等同“地狱”的诸多“厌女症”表述之一[9]。但李尔王的诅咒扩大为针对所有的女性:“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儿是地狱,那儿是黑暗,那儿是火坑,吐着熊熊的烈焰,发出熏人的恶臭,把一切烧成了灰。”[10]从李尔王的这段话可以还原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经典”女性形象:魔鬼和罪恶,要么诱人下地狱,要么就是地狱的化身。原文中的“sulphurous”的词义是“含硫磺的”,用来表示地狱里的烈火。连续的几个词, “地狱”、“黑暗”、“火坑”秉承西方文化观念对女性身体的否定传统,其意图很明显,就是说女性的身体是罪恶的,它本身是堕落的,还导致他人的堕落。在西方的“经典”女性形象中,夏娃禁不住诱惑堕落,继而以身体诱惑亚当,结果触怒上帝,同被逐出了伊甸园;潘多拉打开盒子,结果给人类和大地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西方思想文化对女性的否定既可见于早期的神话传说,也见之于基督教关于人类起源的宗教书写,“堕落”或“罪恶”是其固定的标签。“将女人、性和罪孽联系在一起,成了西方男权制思想的根本格局”[3]82。所以,对女性身体的否定是西方从文化源头开始就已形成的一种书写策略,其在莎剧中的重现不过是重申一个观点,那就是认为女性存在的价值仅在于证明自身的否定性。即便是像鲍西娅(《威尼斯商人》)那样以“强者”形象示人的女性,她选择丈夫的个人意愿仍在遵从“父亲意志”的前提之下,所以她是“掌握自己命运时保持了父权的形式”[11]。她必须在女人的身体之外套上男人的衣服才能在专属男性的空间里获得言说的权力。也就是说,她必须首先“易装”变成“伪装的男人”才能进入男权的体系,所以她的意志表达对个人来说是胜利,但放在社会语境下,恰恰是对女性的否定,因为她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关于男人的概念,暗示理性、智慧、意志属于男性,因而契合了女性之理性、智慧“低劣”的传统观念,结果并没有颠覆男权,却以特定的方式强化了男权。
三、主体的缺失与女性的否定
审视西方的思维范式,对女性身体的贬斥只是否定女性的思想链条中的一环,其终极目标旨在由否定物质性的身体导向对女性精神的否定。身体的“属下”特质被用来说明女性“他者”身份的合理。其中的霸权逻辑昭然:女性不能以自己为“目的”,不是拥有个人意志的主体,而只能以男性为“目的”,成为无个人面目的女性群属。
有女性批评学者曾激进地想重建奥菲利娅的“故事”,但失望地发现,她在《哈姆雷特》一剧中没有自己的故事,自出场到溺水死去,她都是从属于一个中心角色——哈姆雷特[6]617。西沃尔特指出,不仅戏剧结构上奥菲利娅被边缘化,许多关于奥菲利娅的诠释 (心理分析、文学评论等)不断强化着奥菲利娅的边缘性,使之沦为男性“欲望的客体”[6]616-617。
疯颠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是文学艺术青睐的对象,常被用作探索个体精神领域的契机。但奥菲利娅的疯颠相对于哈姆雷特的疯颠也是一种陪衬的客体化产物,她的疯颠没有关乎到个人精神价值,在她疯颠的言语和行为中没有产生出“意义”。奥菲利娅的疯颠塑造仍未摆脱西方传统的“疯女人”的戏剧形象:白衣白裙、披头散发、头戴野花、精神错乱等[6]621。她的疯颠是一个女人为情所伤的,纯属个人的悲剧,丝毫没有哈姆雷特之“疯颠”的“形而上”色彩,因为他思考的是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12]63,其核心是拷问存在的意义。该命题使哈姆雷特不堪重压而“疯颠”,但无论他的“疯颠”是真是假,他已经将个人的痛苦上升到了终极关怀的高度,因而“疯颠”的哈姆雷特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新人”,而疯颠的奥菲利娅仅是一个传统的“疯女人”而已,重演了一次惯常的女人情殇的故事。
因此在《哈姆雷特》中,被否定的重心不只是疯颠的女人,而更在于对“女性疯颠”(一种特定的女性精神气质)的否定。此外,其他范畴的女性气质也被认为是欠缺的。在男权话语中,男性被赋予优越的气质:理性、勇敢、坚定,而感性、柔弱则被认为属于女人。理性虽说不是完全与女性无缘,但往往是要让位于感性的。“智慧和感情在这么娇嫩的身体里交战,十之八九感情会得到胜利的”[13]。当男性表现出柔弱,他往往把对自身柔弱的厌恶,投射到女性身上,以为女性是柔弱气质的天然宿主,认为本不属于他的东西“移位”到了他的身上。“‘女性气质’总是被说成欠缺的或萎缩的,是独自垄断了价值的那个性别即男性的另一面”[7]223。哈姆雷特把“脆弱”与“女人”等同起来[12]15;雷欧提斯把 “眼泪”归为 “妇人之仁”[12]118。可见,无论是关注真理和正义的哈姆雷特,还是权欲熏心的雷欧提斯都把“脆弱”和“眼泪”看作是女性的专属特质,且视之为否定女性的因素。这里所谓被否定的女性气质和被赞赏的诸如温柔、顺从的气质,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物的两面,皆出自男权的自利性立场,本质上都是对女性的否定。伊丽格瑞认为:“那种‘女人味’是男性的再现系统强加于女人们的一种角色,一种形象,一种价值。在这副女人味的面具下,女人失去了自我,为了女人味而失去了自我。”[14]在此种女性气质的规范下,女性被抽离了主体性,剩下的仅是客体化的纯粹肉体,但男权话语的介入又使肉体被强加了诸多“意义”,使女性不能以内在于自己性别范畴的因素建构自己的主体,相反却要被外在于自己的东西所僭越。
失去主体性的结果必然是女性的物化。在西方传统意识中,女性被要求看护好自己的身体,女性的价值之一是以贞操为标志,所谓的贞操是来自男权话语的律令,要求女性坚守,但终极是为了供男性所拥有。贞操作为尺度把女性打上了“物品”的印记,类似标明商品的等级、品相。奥菲利娅父兄要求她与哈姆雷特交往时看好自己的“童贞”,在交易中待价而沽。他们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女人,而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一件有价值的“商品”。莎氏的许多剧作充斥着对童贞的喋喋不休,绝非仅是当时风俗的粗陋,而是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物化,并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在我们的社会秩序里,女人们是男人们使用和交换的‘产品’。她们的地位与商品无异,‘商品’——这种使用和交易的物品怎么能要求言说和普遍地参与交换的权力呢?……那个秩序从来就没有把她们看作‘主体’”[14]。奥赛罗视妻子的贞操为他的私人财产,他对妻子的爱具象化为“肉体、美貌和温柔”。不可否认,此种视角使女性身体“被色情化和被妓女化”[7]。妻子被丈夫宠爱的前提是以女德和美貌装饰他的荣耀。但是若她不能贡献出符合要求的角色,这块婚姻拼图就破裂了。苔丝狄蒙娜不得不死的原因是“失贞”抽掉了男权视角下“好妻子”的最重要的支撑。“失贞”引起了社会惩罚力量的介入。作为“堕落”的女人,她只能被男权审查、处置,而没有辩白的权利。社会惩罚体制旨在维护性别的权力关系,对失贞的惩罚从来是放在男权架构的道德座标上来审视,男权作为背后的“道德”裁定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执行者”。
主体的缺失使女性成为不自由的附庸,不能成为有明确自我疆界的个体,结果只能被群属价值标准评判。当女性个人被群体淹没,她便不能以自身为目的,只能堕入为“他人”的境地,成为服务于“他人”的手段,甚或任由“他人”对自己的占用。莎氏认可了男权话语的谬见,并在书写中强化了性政治的暴力表达。这一点反映了莎氏思想中为男权意识所污染的一面。
结语
近年来,文化批评学者致力于消解性政治范畴下的权力意识,“不管目前人类在这方面保持何等一致的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3]38-39。在男权话语的主导下,女性不能拥有自己的主体身份,结果被“他者化”,被“物化”,成为有“缺陷”的性别就是几千年来的文化“宿命”。无论是对女性身体的“定义”,还是对女性形象的规制,女性本身都是排除在“言说”之外的,话语权归属到男性。围绕女性的“政治性”显然表现为对权力关系的维护,因而在性政治导引下产生的种种律令和规范也必然为权力所污染。
莎剧对这种性别意识的认同,甚至是张扬,表明该意识已变为普遍接受的知识文本,并成为形塑个体和社会的权力话语,使人们丧失对它的认知力和对其“暴力性”的批判。所以,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的研究来揭示西方文化思想中倍受偏见污染的性别意识,并对西方性政治中存在的谬见进行揭露应具有文化上的批判意义。
[1]Phyllis Rackin.Dated and Outdated:The Present Tense of Femin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M]∥Evelyn Gajowski.Presentism.Gender,and Sexuality in Shakespear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
[2]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07-109.
[3]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M]∥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6]Elaine Showalter.Representing Ophelia:Women,Madness,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M]∥Charles Kaplan,William D.Anderson.Criticism:Major Statements.Boston and 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0.
[7]露丝·伊丽格瑞.非“一”之性[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16.
[8]Anne K.Mellor.On Romanticism and Feminism[M]∥Anne K.Mellor.Romanticism and Feminism.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6.
[9]William Carroll.Language and Sexuality in Shakespeare[M]∥Catherine M.S.Alexander,Stanley Wells.Shakespeare and Sexu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8.
[10]莎士比亚.李尔王[M]//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47.
[11]David K.Nichols.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hakespeare’s Comedies[M]∥John A.Murley,Sean D.Sutton.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in Shakespeare.Lanham:Lexington Books.2006:52.
[12]莎士比亚.哈姆雷特[M]//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13]莎士比亚.无事生非[M]//莎士比亚全集:第二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2.
[14]露丝·伊丽格瑞.话语的权力与女性的从属 (访谈)[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