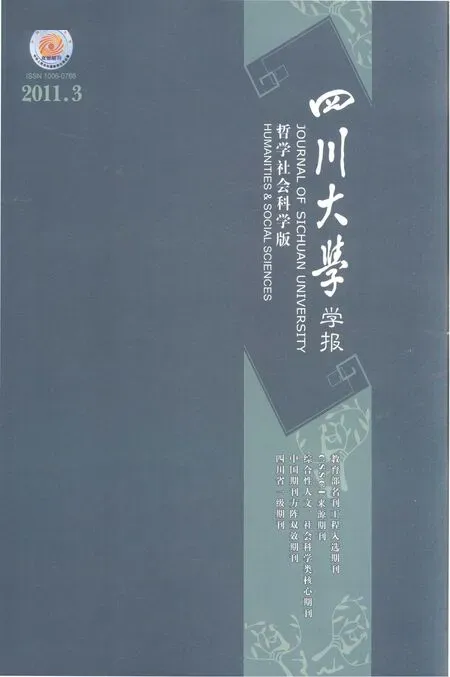五四时期 “中国特殊性”的建构及其特征——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
彭膺昊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国特殊性”问题产生于近代以来东西方全面接触的政治实践。在近代思想话语中,“中国特殊性”是与西方一系列特征的对比下形成的自我描述的总和。这种通过与外部文明的对比而形成的自我描述,不是一种单纯的文明概括,而是在自我认同基础上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核心方面,也是实现政治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中西特征进行对比的方式可上溯至道咸之间,后经洋务、戊戌乃至辛亥以后,以西方为标准展开对“中国”的叙述越来越成为思想界的主题。至五四时期,知识界对“中国特殊性”的叙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更加紧密。这一时期形成的对“中国特殊性”的内容界定、分析框架和价值判断,均构成了1930年代民族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置于从五四到抗战这样一个历史脉络中来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实质。本文将简要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叙述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作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基础。
一、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叙述的内容及其价值取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思想革新和社会改造的主题,知识界存在革新、保守和折中等三种主要倾向。各思想派别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虽然分歧很大,但在同一历史语境下具有共同的现实指向,即首先概括“中国”及其“特殊性”,然后以之作为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运动的知识基础。这个时期,这个主题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由于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例如,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形成、报刊杂志等传媒体系的空前发展、更加专业化的西方知识的大规模引介、新的概念体系虽然内涵模糊却被广泛使用。这些现象的出现为五四以来的知识界搭建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即使是守旧派也不得不受其影响,开始转而使用新的话语体系参与讨论。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叙述,并不能专指《新青年》等知识群体的观点,而是这一时期各主要思想派别共同建构的文化形象。
无论是何种派别,这一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描述基本等同于对“中国”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形成的,它以二元对比和高度化约为方法论特征,从而在内容上也表现为一系列对比特征的总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被归约为动与静、精神与物质、人治与法治、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帝国与民族国家等二元关系。只有在这种对比关系中,“中国”及其“特殊性”才获得了自身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或“中国特殊性”是在中西碰撞中产生的近代概念。
在价值判断方面,中国的“特殊性”对于实现民族独立和追求现代性的历史目标来说,到底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还是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一价值判断贯穿于近代以来的思想辩论和政治实践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继洋务、戊戌以来又一次集中对“中国特殊性”进行检视的关键时期,新兴思想对“中国特殊性”的态度主要表现为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在这里,“传统文化”也同样是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相对比而建构起来的近代概念—— “中国”被视为一个需要全面舍弃或改造的文化——政治实体。
在近代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历史观的推动下,源自西方历史实践的经验被系统地表述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从而,西方与东方的上述二元关系转换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这种认知框架下,“中国”作为某种“普遍规律”宰制下的特殊地区,其“特殊性”被相对地建构起来。在普遍主义的指导下,对这种“特殊性”的改造被赋予了历史合法性。然后,五四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叙述,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决定论和一种独特的普遍主义观点,这两个特征指导了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方向。
二、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叙述的文化决定论特征:以文化推动现实
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反对中国当局接受巴黎和会协议的政治事件引发,其产生的后果却是一场持久的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由对政治现实的焦虑导致对文化本质的追问,林毓生将这种思想方法称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①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罗志田也认为之所以民初的读书人往往惯于从“物质”看到“文明”,是由“政教相连的中国传统对‘学’的强调”所致。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页。。关于这一思想方法影响最广的表述,是梁启超晚至1923年才明确总结出来的“器物—制度—文化”的层进结构[1]。这一结构既阐述了一条“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演进过程,又鲜明地展现出文化决定论的认知方法。这种认知方法正是五四时期各派所共享的思想前提。
所谓“文化”问题在五四时期成为各派聚讼的中心场域,对“中国”之为“中国”的描述、对中国与西方之间区别的描述、对中国自身的特点或特殊性的描述等等,均在所谓“文化”的层面上展开。例如,严复早在1898年的《拟上皇帝书》中就区分了“外部改革”和“根本改革”,前者是指军政制度的变革,后者则是指“精神之改造”[2]。康有为在1913年草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时,坚持认为,作为文化表征的孔教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的灵魂②康有为在争论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以孔教的文化性来定义为“中国”的核心,所以他说“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康有为全集》(第10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陈独秀在1916年列出一条西洋文明输入以来的次第顺序,即“学术—政治—伦理”,几乎就是梁启超层进结构的雏形,并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瞿秋白在1920年也认为社会改造的第一步是文化运动③瞿秋白认为:“真正能做改造社会——创立新社会的——第一步,只有真正有实力的‘文化运动’。”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1920年3月6日),原载《新社会》旬刊第十五号 (1920年3月21日),收入《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0页。。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基于文化分类学比较中国、西方和印度的各自特点,并说:“现在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拙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4]力主“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在1928年的文章中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为“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强调了精神的决定性④陈序经说:“良以把文化来分做物质精神两方面,乃是我们为了便利研究起见而发生的主观的观念,并非文化本身上有物质精神之分,因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是不能分开,所以物质文化的演化是随着精神文化的演化。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物质的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现。”陈序经:《东西文化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1928年11月17日。。胡适在方法论上援引杜威的实证主义,肯定乾嘉学者的功夫,推动“整理国故”运动,实践了后人余英时所谓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但这仍是“文化”内部的重心转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所竭力推动的社会改造,主要涉及礼教批判、儒学批判、白话文推广、妇女解放、文学与戏剧革命等,都是在“文化”层面对“中国”进行自我认识和改良。
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或“中国特殊性”的认识,几可等同于对“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一认识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对“固有文化”的静态认识。“固有”一词是当时知识界共用的概念①关于“固有文化”及其一系列的衍生的“固有文明”、 “固有道德”等名词见于当时的各种名流中。早在1916年,杜亚泉在评论中西文化观的时候就说:“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见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916年10月),许纪霖等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38页。梁启超在“一战”之后访游欧洲,重估中西文明的价值,重新注意中国自身的特性,但这时他已经被认为转向保守了,1920年他也说:“吾认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申报》,1920年3月14日。何键在1929年针对兴孔说:“总理在三民主义内主张恢复我国固有道德,恢复我国固有文化,以树立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主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要发扬民族主义,便要遵照总理的遗教努力。这也是我们纪念孔子的一点意思。”见何键:《孔子诞辰纪念演讲》(1929年8月27日),《何键言论集》,第27页。于右任评价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时说:“承继总理复兴民族的遗教,为了提高民族精神,发扬民族历史、文化和恢复民族固有美德。……发起新生活运动,以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四维,做新生活运动的中心!”见于右任:《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21页。学衡派的梅光迪也说:“被引进的学说必须适用于中国,即与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见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学衡》1922年第8期。汪叔潜在评价当时的五四运动中新旧之争时,简明扼要地定义新旧:“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见汪叔潜:《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所谓“固有”,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传统文化视为静态而无发展的文化教条,在客观上造成了将传统文化对象化的结果。在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表现出自觉意识,追溯其来源,确认其内容的方式,正好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对文化的典型态度。
第二,“文化”的整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文化的把握来认识“中国”的特点,包含两个方面的整体论。一是“文化”自身的整体性。即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描述时,往往采取高度抽象和化约的方式来归纳整体特征。这种方式并不基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也尽量忽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因而,这种文化整体论并不必然与民族国家的自我建构相重叠,对内部文化多样性的忽略致使这种整体论很难获得坚实的现实基础;二是文化与政治现实的整体性关系,即认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现实必然与其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观念同样导致将中国现实与其文化特点相关联,成为各种“文化革命”的逻辑基础。如力倡“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说:“我们可以知道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但是因为有了密切的关系,而致一方面的波动,常常影响到他方面,而且文化成分的分析,除了是我们为便利研究起见,他本身上是一个整个的东西……其实文化是完全的整个,没能分解的。”[5]林毓生将这种思想表述为“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但认为当时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不能解释这种全盘性,其根源“必须从深入人心的历史力量和当时政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寻求”[6]。包含了“文化”自身的整体性、文化与政治现实的整体关联这两个层次的文化整体论,成为晚清以降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它蕴含了巨大的激进色彩,对“中国特殊性”的改造上也体现出这种激进主义倾向。
第三,以价值判断为主。这种整体观念导致了对中国及其特征的描述被落实到对中国文化的描述上去。不论辩论各方的倾向如何,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而不是结构分析,构成了当时论辩的核心问题。经历了洋务和维新之后的五四时期,对“固有文化”的否定性判断极为一致,汪晖称之为“态度的同一性”[7]。
第四,精英论色彩。可以看到,传统主义者对文化的描述比激进主义者更加高悬于实际生活,二者对“文化”的侧重点并不一样。在激进主义者那里,文化改造绝不是纯粹的精英文化内部的变革,而是社会改造运动。通过对大众的社会改造而达成文化革命,从而培育出良好的政治革命的基础。社会改造的前提承接了维新时代由梁启超等人倡言的“民”或“群”的概念。“民”和“群”是严复以来的知识分子在中西对比中最先发现的概念之一。梁启超通过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将大众纳入了历史视野。这个概念为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所继承,他们对文化的强调与传统主义者相比,最具历史意义的特征就是将大众纳入视野,作为文化的主体之一。
然而,只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包含了这个逻辑倾向,但并未充分展开,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论辩对象——传统主义者——往往固步于文化本身的讨论,极少涉及文化与大众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中西对比的认识论框架不可避免地要求化约性的描述。从而导致对“中国”及其特征的描述往往流于形而上的文化描述,诸如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等看似具体的描述本身实际上只是一种描述文化特征的概念,而很难说是对现实的结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作品对礼教及日常生活的辛辣刻画,恰恰比大多数理论研究更深刻地实践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正是他最直接而真实地触摸到了这场社会的文化改造运动的对象。而在这个话语下,对阿Q、血馒头中的麻木不仁者、祥林嫂等形形色色的大众却是作为负面存在来看待,对裹足、贞操等问题的讨论的确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无论如何大众都是与传统文化的丑陋方面绑定在一起的,是一个有待改造的对象而不是能动的创造历史的主体。
上述几个逻辑递进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描述主要等同于对静态的“固有文化”的描述,而这种文化是基于激进的整体论而建立起来的,知识界对于这种整体文化的判断主要以价值判断为主而不是知识整理,实质上是一种精英论。
三、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叙述的普遍主义特征:价值性与地方性
五四时期对“中国特殊性”的叙述是以某种普遍主义原则为标准而展开的,对普遍主义的价值肯定,也正是对“特殊性”进行改造的合法性依据和动力。这一时期所确认的普遍主义包含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特定价值体系普遍真理性的肯定,而不是对某种历史规律普遍适用性的论证。五四时期形成的最重要的普遍价值概念是“科学”。“科学”的世界观替代“伦理”的世界观而成为支持一切其他“普遍价值”的合法性基础。基于“科学”而形成的价值体系之所以得以成立,是以自身的合理性或先进性为根据,而并不依赖于历史或传统。在这一点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观极为相似,都蕴含了对某种价值体系的普遍真理性的诉求,正如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对欧洲启蒙运动的评论那样,是“唯理论的和反历史的”[8]。五四时期以“科学”为价值展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如前所述,传统文化被视为一系列价值主张和精神教条,因而五四时期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正是以“科学”为依托,新价值体系对旧价值体系的瓦解过程。对普遍主义的追求被具体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逐步成为运动的中心。郭颖颐(D.W.Kwok)在分析唯科学主义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时,认为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氛围中,很容易将“精神性”与“科学性”相对立,这也是导致以“科学”相标榜的新知识分子为什么普遍反对传统文化的“精神性”,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原因[9]。
然而,这种以对价值体系普遍真理性的追求为核心的普遍主义,是以文化决定论为基础的知识改良,而未能形成可以切实指导政治实践的系统理论。换言之,从高悬的价值设定到具体的革命策略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与之前的康有为相比,他结合近代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进一步发挥传统儒学命题中的公羊三世说,构建出一套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其蕴含的历史普遍主义色彩极为浓厚。而五四时期则转向对价值普遍性的肯定,以及对“中国特殊性”的否定,从而在客观上强化了对一系列现代民族主义命题的关注,弱化了对具体历史发展进程的探寻。而之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理论和线性演进观点则展示出一条清晰的历史发展轨迹,以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理论特色,也蕴含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巨大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含了社会发展的价值,而且提供了相对具体的革命策略。从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主要追寻的是价值体系的普遍主义,而对普遍历史发展规律的构建则相对较弱。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崛起的一个思想背景。
第二,是对某种地方性知识普遍适用性的肯定,而不是对具有先验色彩普遍规律的有效性论证。五四时期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通过对西方价值体系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辩论而展开,在这里,“科学”或“民主”都紧密地与“西方”这个地理名词相联系,西方价值体系首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例如,在“西化/欧化”与“本土文化”的论争中,孟德斯鸠式的地理决定论往往成为论辩双方所共享的理论前提,虽然决定辩论立场的关键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但具体表现则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可移植性的赞同或否定。再如,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区分,以及魏特夫 (K.Wittfogel)对中国“治水社会”的论断等,在五四时期也影响极大。这些学说都是从“地方性”的角度入手进行东西方的比较研究。总之,新兴知识分子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从经验主义出发,认为西方价值具有普遍的可移植性;后者则否定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但是,双方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将西方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有意识地消除这种“地方性”。
马克思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对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处理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论证一种“人类社会普遍规律”,这种普遍主义强化了自身的内在合理性,而不是其他外在的影响因素。在时间观念上,它历史地看待一切事物,从而弱化了历史与传统对于普遍主义的约束;在空间观念上,它虽然也重视地区性的具体情况,但更加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性。通过劳动、生产力、阶级等社会分析概念,消解了地区间的表面差别,克服了异质文明之间兼容性问题。正因如此,它实际上为“西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命题清除了障碍,跨过要不要“西化”或“中国化”的问题,直接引向具体如何“西化”或如何“中国化”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方式,在客观上遮蔽了某种价值体系的地方性知识的性质,致力于建构利奥塔(J.F.Lyotard)所批评的“元叙事” (meta narration),不可避免地带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观色彩,但的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合法性论证的框架,也促进了20世纪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进程。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反观五四时期的普遍主义追求,那种对地方性知识的普遍适用性论证的特点就被凸显出来。如果将国民党以文化保守主义来对抗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纳入视野,将中共内部关于教条主义的斗争纳入视野,那么“地方性”普遍主义问题的意义则更加明显了。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中国特殊性”叙述是在中西对比的二元框架下形成的自我描述,它包含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共享了对“中国”的文化性描述,坚持了文化决定论;二是在对普遍主义进行论证时,各派均围绕某种地方性知识的普遍适用性 (西化论),而不是某种普遍规律运用于具体区域的有效性问题 (唯物史观),这恰是两种内在结构并不相同的普遍主义模式。总的来说,“文化”的观念和特定的普遍主义观念共同塑造了五四话语下“中国特殊性”的内容及其价值,这正是全面抗战以后对“中国特殊性”的理解逐步走向具体化和民族化的思想前提,这也是在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大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背景。
[1]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833-834.
[2]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2.
[3]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新青年,1916,:6.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 (卷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62.
[5]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J].文化月刊,1934,1:7.
[6]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16.
[7]汪晖.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07.
[8]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9.
[9]郭颍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1900-1950)[M].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