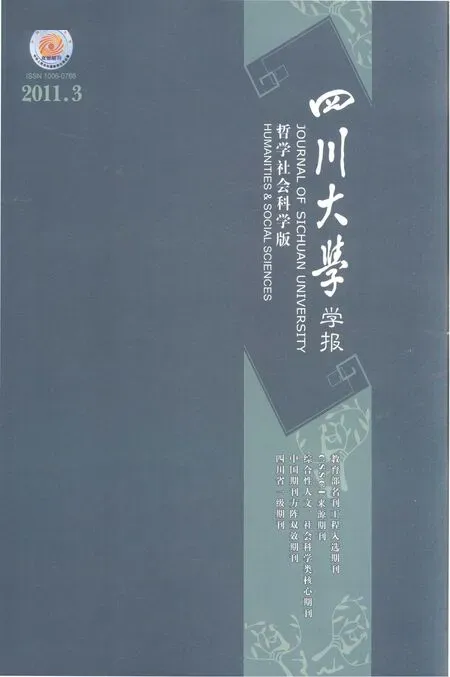从国有企业的救灾安置看单位制的变迁
王 薇,陈彩霞
(1.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培训中心,四川成都610072; 2.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作为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单位制在建国以来起到了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等作用。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这样的单位制组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单位多元化功能的收缩,单位对国家、员工对单位的组织性依附减弱等。有人认为单位制已经解体,或者在变革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单位制”的组织特征;也有人认为,虽然单位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发生了变化,但依然沿袭了传统单位制的政治功能和行政化特征。本文通过对两个地震灾区的国有企业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的调查分析,试图从中发现变迁中的国有企业特征在哪些方面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及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的举措给变迁中的国有企业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单位制及其变迁的研究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一)单位制研究的缘起。“单位制”理论作为分析中国城市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视角,起自美国学者 Andrew G.Walder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里提出的单位依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自国家,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这和市场经济下员工和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有根本不同。这个观点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认同,李路路和李汉林的研究指出,人们与单位依赖关系的保持,是由于人们可以通过这种依赖从单位组织中获取他们期望得到各种资源,单位组织所提供的资源远远超出了收入的范围[1]。对一个单位成员来讲,单位不仅是工作的场所,还是几乎一切必需的生活资源来源,有的大型国有企业“除了殡仪馆什么都有”。“企业办社会”就是单位全能性的写照[2]。企业通过向员工分配资源,贯彻了国家的政治意图,强化了职工对企业的依附。这种单位制特征也使员工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工作、衣食住行和娱乐,都和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如霍夫曼所说的“完全性组织”[3]。
(二)对单位制变迁的研究。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为主线的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也就是单位制发生改变的过程[4]。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国家不再是单位资源的唯一提供者,市场也为单位成员提供了获取资源的其他途径,国家—单位—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人们对改变的程度和未来的方向还存在不同认识。
孙立平等人认为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单位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单位角色职能化、单位利益独立化、单位责任具体化等,单位体制甚至已经开始解体[5]。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市场化的进程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从整个社会的统治形式和权力结构的角度看,再分配体制的特征仍然被基本保持着,单位特征因而也仍然保持着,原有单位体制的某些特点在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甚至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6]。Barry Naughton的研究指出,由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国家对企业控制的减弱,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有的单位内部还在实行子女可顶替退休直系亲属岗位的政策,使单位对个人仍旧具有极大的意义[7]。通过对三个城市的比较分析,谢宇和吴晓刚认为,单位的效益是决定员工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单位仍旧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8]。边燕杰等人对2003年全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单位仍是再分配体制下的两大结构壁垒之一,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深刻的、持续性的[9]。
(三)研究方法。为了调查汶川地震对国企员工的社会影响,作者深入到一个“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对企业在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中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是单位制企业发挥组织功能的重要时刻,也是重要的资源分配过程。通过对这个过程的观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典型的单位制国企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延续了原来的设置和功能,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又在哪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单位制国企的变迁。
本项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企业中上层干部和不同部门的普通员工。深度访谈围绕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进行,依访谈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对中上层干部的访谈主要集中在地震对企业造成的影响,企业在地震中的组织行为,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对普通员工的访谈集中在员工个体在地震中的经历,参与救助的情况,对企业救灾安置工作的感受和评价等几个方面。共访谈23人,其中企业领导3位,中层干部5位,普通员工15位。
二、被调查企业在地震后的救灾安置和重建情况
被调查企业是一个处于地震震中的某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的两个全资子企业——A企业和B企业。这两个企业在地震中均遭到毁灭性打击,员工伤亡182人,占员工总数的15.4%,其中遇难126人,受伤56人。生产设备全部摧毁,部分办公大楼受损,10%的员工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或亲戚,32%的员工失去了熟悉的同事,46.67%的员工住房遭到严重破坏。
(一)紧急救助。在国家对灾区进行救援之前,企业就已经组织开展了有效的人员和设备抢救工作。B企业一个生产部门负责人在访谈中指出:“我们在5月12号2点30分,中层干部就自觉集中到机关大楼开会,4点钟,厂长就带领几个人上映秀。后来干部就开始组织突击队,分批次向映秀运水和吃的,大家都是走上去的。是早在部队前面的。可以说我们主要还是靠自救。我们不仅救了我们厂的人还救了其他单位的人。在都江堰,我们当晚就对职工进行了安置,把老的小的安排到大汽车和帐篷里,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不停搭帐篷。”
上级部门也很快拨出人、财、物支持救援工作。“14号上级部门调来100多人,主要是两个兄弟单位的员工,一个负责运输,另一个帮我们救援”。 “省公司安排了14个冲锋舟,输送物资,接送职工。当时说需要什么救人设备,比如电锯,就由总公司送来。” “后勤物资保障难是难,但不是问题,因为我们背后有省公司,有兄弟单位,我们背后有这么雄厚的企业能不支持咱们吗”(A企业中层干部)?
党务部门和党员在紧急救助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第一批进灾区的突击队构成中,“第一是男性,第二是党员干部优先”。“党员在这次地震中表现了很强的责任心。这些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在地震发生后几天,单位就组织人上来检查厂房,还有那个闸门,是最危险的。是党员先上,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没有怨言”(某部门员工)。
就这样,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企业在上级单位的支持下,很自然地形成了“自己救自己”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也贯彻到了灾后的安置和重建过程中。
(二)安置和安抚。在将震区的员工迅速撤离危险地区后,企业在上级部门的支援下,很快组织了食物、饮用水、药品、彩条布、帐篷、被褥等救灾物资,搭建了临时住所,让受灾员工不致挨饿受冻。有女工评论道:“单位在地震中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反映迅速,我们的吃、住都不成问题,几车几车的运水、食物,满足大家的需要。单位在工作分配、安排这些方面都非常全面,也很细。对于那些有轻生念头的人,单位还专门请了心理医生进行辅导,而且效果非常好。”
受伤的员工被迅速送往系统内外的各家医院,所有的费用,包括陪护人员的报酬都由单位承担。房屋受损的员工被安排进了企业花费巨资统一搭建或购买的板房,调查时尚有392户住在这里。在地震后企业全面停产的情况下,省公司依然保持了全体员工收入跟地震前持平,被员工看作是“最大的安抚”。
对遇难员工家属的安抚是灾后最重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具体的工作包括上门慰问遇难职工家属,由企业出资帮助家属办理DNA鉴定和理赔,请法律顾问来为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对家属进行经济上的帮助和抚慰,帮助家属解决具体生活困难等。具体处理善后问题的中层干部说:“遇难职工的善后工作是这样的,先去家里了解情况,一家家跑,前前后后跑了4趟,看房子的情况,看家庭是否困难。抚恤金等全部按国家政策办,事情很多,比如有工伤保险,有几个月的工资,甚至有报销的车票等等,一家家送去。安置中的困难主要是家属的问题,死去的人常常是家里的顶梁柱,有的家属没有工作,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人不在了,这个家庭一下子就由小康跌入贫困。有些家属向公司提出,希望能解决家属就业问题,但实际上不可能。”但企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帮助家属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比如联合当地政府解决就业、养老等问题,在企业内部发起助学、捐赠等活动。有位遇难职工的家属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单位专门联系心理医生进行治疗,并承担全部的费用。
(三)灾后重建。A、B两个企业在地震时遭到毁灭性打击,设备严重损坏,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可以这么说,遇到了灭顶之灾。用这个词一点都不过。当时三个生产厂房全部被掩埋” (A公司党委书记)。地震发生后,两企业恢复生产的难度极大。
但企业很快就开始重建工作。首先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企业重建由国资委立项,省公司注资。由于有资金和设备的注入,从抢修被损毁的设备开始,企业的重建工作进展迅速。在地震后半年的12月份,A企业就有部分设施开始恢复正常工作。2009年5月8号,A企业的三台机组就全部恢复生产。
市场也对企业的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地震后有些方面受了影响,有些方面反而增加了机会,我们是可以面向市场的,地震后合同还比原来多了”(A企业中层干部)。地震前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内部的多种经营部门对外提供技术服务,这是创收的来源之一。地震一个月后就派人到外地去“打工赚钱”。尽管条件艰苦,但职工踊跃报名,“觉得单位对我们这么好,应该为单位做点什么啊”(某部门员工)。但企业领导和职工都认为创收只是提高了员工的收入水平,真正对重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上级部门的支持。
三、地震前单位制企业已经发生的变迁
在地震发生之前,被访企业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即面向市场。虽然生产、销售仍然是由上级部门统一指挥,不受市场风险的影响,但企业还是产生了危机意识,并尽早做出了反应。他们将自己的技术部门推向市场,利用自己的技术和设备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以此为目的的多种经营部门已经成为企业创收的重要来源,也成为震后重建时企业内部的重要力量。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企业还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契约性关系增强。在很长时间内,国有企业承担着吸收社会就业的职能,有的企业建立了“内部顶班”、 “内部招考”等招工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福利解决员工子女就业问题。A企业就有顶班、内部招考等制度,调查发现,71.58%的员工有家人或亲属在同一个企业工作过,平均每个人有2.04个,最多的有14个亲属在同一个企业或本系统内工作。在这些亲属关系中,除配偶外,最多的就是父母和兄弟姐妹。这反映出员工结构与企业实际需求两者脱节的招工制度弊端。
这种制度在1990年代宣告结束。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企业出于自身营利的需求,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市场的劳动用工人事制度。如今的A、B企业招工,已经建立了严格的用工制度,如对学历的要求、面试和实习经历等,亲属关系已经不能超越制度在招工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在B企业尤其明显,作为新建企业,其正式员工几乎全由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组成,招工程序也更加规范。已进入企业的员工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范着员工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全体员工都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合同规定了工作内容、所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权利。企业为员工购买各种保险,不再为员工直接提供医疗、养老等服务。
主要表现为契约性关系的人事制度变迁已非常牢固,不可逆转。即使大地震这样特殊的事件也不会使之发生改变。“有些遇难员工配偶提出捐赠款都可以不要,只要安排她进厂工作就可以,有的遇难员工父母也说可以不要钱,但要安排员工的兄弟姐妹进厂工作。但这都不可能了。当然如果你符合条件的,你可以通过省公司的一些政策、考试来就业,来给你解决,都是社会公考的,要社会公示的”(某部门中层干部)。
(二)政治功能弱化
1.行政特征和政治功能依旧保持。在经历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后,虽然内部结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传统的体制,承担着国家和政府的各种政治任务,具有除市场组织之外的行政设置和政治功能。
A、B两个企业所属的是国家授权投资机构并由国家控股、其领导班子由中央管理、资产管理及有关财务关系由财政部负责的特大央企。虽然经历了在产权关系不变更前提下的国有资产经营方式的改革,但仍然具备完善的在行政级别基础之上的单位等级体制。A、B两个企业的直接上级企业——四川省分公司领导由总公司任命,A、B两个企业的负责人由省公司选拔任命,吸纳新成员也必须上级人事部门批准,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在组织机构上并存着生产和政党组织两个平行的系统,从纵向上政党组织深入到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从横向上与生产系统行政级别相同。政党组织仍然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人事工作,传递和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干部的考核、晋升、调动等管理工作。在调查前期,公司刚刚进行了科学发展观的学习。说明除开生产任务之外,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把国家制定的政策、所倡导的价值观传递给员工的政治功能,对员工价值观和行为进行控制和整合。
企业还承担着一些常规性的政治任务,比如吸纳退伍军人就业的政治任务。A企业车队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高达4.5%,究其原因,车队主要成员是退伍军人。安置退伍军人就业是政府分下来的政治任务,单位无权拒绝。“我们现在进个人的门槛是越来越高了,以前中专生都能进,后来必须是本科毕业了,现在还要211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才能进来了。但对退伍军人是没办法的,不想要都不行”(党委工作部主任)。
2.行政特征和政治功能的弱化。在面向市场的经营中,营利越来越成为企业的第一目标。在此过程中,政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发生了重大改变,行政性特征不断弱化。首先,在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上,压缩了党务人员的比例。两个企业原来属于党务部门的人员如宣传、组织、共青团等部门的人员已经减少,尤其在B企业,这些部门的工作由一个人负责,“一个人干了14个人的活”。在党务部门和生产部门的领导安排上,强调党委书记的生产背景。“党要领导,对生产肯定要熟,否则怎么去领导”?在厂里,厂长而不是书记是第一把手。基层党支部书记和生产负责人已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都既能管生产,也抓党务工作,甚至是轮流担任。其次,党务部门的重心也转移到生产上,保证和配合生产经营成为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还有,为了适应企业的发展,党委领导下的人事工作引入了现代管理模式,员工升迁中政治表现和党员身份的因素下降,而技术技能成为最重要的考评指标。对这样的改变,员工的体会是“党员身份对工作岗位的升迁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关系不大”。并举身边的例子说“我们的值长在提拔的时候就不是党员,他是当了值长后再入的党。遇到生产中的问题要有技术才能解决,而不是说是个党员就可以解决的” (基层生产部门员工)。虽然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但这个经验材料明显和边燕杰所论证的“在国企和非国企,党员身份会显著地增加个人成为管理精英的机会”不同,至少在基层是如此[9]。
(三)功能多元化改观。“单位办社会”是传统单位制企业的重要特征,企业的功能多元化在客观上深化了员工对单位的依赖。在单位制度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最早进行的就是将非生产性职能从单位中剥离出去并逐步实现社会化。
1990年代初,A企业建在山区,办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等,1997年前后陆续撤销,只在原厂区和新办公区分别设了医疗点,为员工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各种管理工作。B企业由于建立的时间较晚,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些福利安排。
住房是单位为其成员提供的最重要的基本福利品,也是单位控制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伴随着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A企业也在1990年代末逐步将福利分房制度改变为职工个人买房的住房商品化制度。 “它一开始叫集资建房,分两次交。一共三万多。在当时也不便宜。当然后来就把它 (指房屋产权)买断了。97、98年是最后一批,后来的就完全是商品房。很多年轻人因为没分到房子还多大的意见呢”(某生产部门党支部书记)。
住房制度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这在灾后重建中也表现出来。员工最大的财产损失是住房受损,46.67%的员工其住房都遭到严重破坏,20%的员工房子需要进行维修。受灾员工在短期内难以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修复、重建或重新购买商品房,所以他们希望单位能给予帮助。但由于房屋倒塌是私人财产损失,企业已没有义务修建公房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
四、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对企业的影响
(一)强化了依附性。地震后A、B两个企业的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主要依靠系统内部尤其是上级部门的资源。除了被深埋人员救援、部分伤员医疗、因灾死亡人员的家庭按每位遇难者5000元的标准发放抚慰金及遇难家庭子女得到政府三个月的生活费补助外,两企业几乎没有得到其他种类的来自政府的正式援助。虽然震后多种经营公司的对外创收也部分地有利于企业的恢复和员工收入的增加,但和上级部门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如果不是有上级企业的强力支持和巨大投入,以此次地震损失的严重,企业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重建,也不可能给员工提供细致全面的远高于普通民众的救灾和安置水平。虽然国企的资金来源是国有资产,但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员工都把救援和重建的工作归功于本系统上级部门,因为几乎所有的救灾和重建资源都来源于省公司。这一主要依靠上级部门的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过程强化了企业对上级部门的依赖。
同时,由于员工的救援和物资帮助几乎全部依靠单位,救灾安置和重建过程也加深了员工对单位的依附性。在地震的生死关头和灾后人心惶惶的时候,企业不但给员工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如组织救援、提供生活用品、提供临时住房、安抚遇难员工家属、稳定的收入等的全方位的庇护,同时也给员工提供了家庭式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抚慰,表现出单位与成员间不仅是“契约关系”,而是“准伦理关系”。单位的这些做法提高了员工对单位的归属感,一位在震中值班的员工说:“和那些没有单位的人相比,有一个好的组织,感觉很幸福。有关怀,有单位,就感觉生活有了保障,给你很大的支持。有单位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省公司一直这样照顾,我们都习惯了。然后这次地震,有了一个对比,体会更加深刻了。”
(二)凸显了政治功能。在市场化的变革中,虽然国有企业依然承担着贯彻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政策的政治任务,但生产性企业的利润化导向已经让行政性特征和政治功能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地震这一突发事件和随后的救灾安置和灾后重建使政治性功能又得到了加强。
首先,在救灾过程中,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除了主动承担起本企业的救灾安置工作外,在社会需要时,也无私进行援助。A企业首批进山营救的员工把救援物品让给当地的村民,认为这是国企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地震发生后不久,由于救灾的需要,国家要求尽快抢修线路。虽然刚刚经受了员工遇难和设备损毁,但B企业还是毫不犹豫,不计成本,及时派出员工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社会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在安抚工作中贯彻“稳定高于一切”的政治要求。地震使两个企业人员伤亡惨重,企业的安抚工作内容极其广泛,也是工作压力最大、最难的部分。企业领导除了进入每个遇难员工家里进行哀悼慰问,还要分门别类解决家属的困难和要求,甚至介入家庭内部,调解由于财产分割带来的家庭矛盾。之所以排除种种困难做这些“不是企业份内应该做的事”,企业领导表示一是出于感情,二是“国有企业的职责除了为国家创造财富外,还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现在的社会就是要和谐,要稳定”(B企业党委书记)。其中一个企业领导在谈到工作成绩时也表示他们稳定了家属,工作得到上级肯定。“我们没一个家属到省公司去闹,到我们这儿反映问题都处理下来了”。
再次,党务部门在灾时发挥核心作用,其地位得以强化。在救灾中党务部门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党员的参与度要明显高于普通员工。紧急救援结束后,生产各部门在厂长的带领下开始重建工作,党务部门除了配合灾后救援,还要分管宣传、遇难员工家属安抚和职工住房重建、心理健康,工作量空前增加,党务部门的影响力增强。有三名员工在地震中火线入党。
除了依赖性结构的加强和政治功能的凸显,地震对企业影响的另一方面是服务性功能得到部分恢复,尤其是地震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又开始了新时期的“企业办社会”。比如为受伤员工提供医疗服务和工伤鉴定服务,全方位安抚受难员工家属,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法律问题甚至心理问题。由于部分员工住房受损严重,上级单位花费巨资自行修建和购买板房用于安置员工。由于板房离市区太远,为了方便生活,企业专门开通买菜班车等等。但这些功能的恢复应该是临时性的,将随着地震影响的减弱和生活的正常化而结束。
五、讨 论
从198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化转型、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单位制国有企业也发生了不容忽视的改变,从典型的单位制组织逐步转变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部分面向市场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在本研究调查的企业,单位已经有了除上级部门以外的由市场带来的创收渠道,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契约性关系增加,国有企业行政性特征开始弱化,功能多元化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单位已不再是一个“完全性组织”。这些改变昭示着单位所能分配的资源已经减少,比如原来的再分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住房分配已经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一去不复返了,子女教育和医疗问题也都不再依赖单位,而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源。人事制度也已全面改革,顶替和内部招工让位于公开招聘。单位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向着现代企业的契约性关系发展。
根据依附关系理论,在资源完全由上级或单位控制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单位对上级、员工对单位的组织性依赖应该随着上级或单位所控制资源的减少而减弱,但本文的研究发现,单位内部的依赖性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某些方面还有加强的趋势。
首先是单位对上级的依赖。被调查企业作为国企系统的一部分,其资金设备、人员任命等重要资源直接来源于上级,尤其是在遭受地震灭顶之灾后依然得到国家强有力的庇护,极为迅速地重建并恢复生产。因为有上级或国家做后盾,大大减轻了地震带来的损失,地震这一灾难加深了单位对上级的依赖。其次,在个人和单位的关系上,相对于全面面向市场的现代企业,国企保留了传统的单位制企业的特征,如对员工的父爱主义庇护和准伦理关系等。在平时,这种特征表现为单位工作的稳定性,如不随便裁员、保持工资收入的平稳增长,以及相较于其他企业较好的福利等。在特殊时期比如地震时,国企工作意味着可以得到全方位的保护,得到比社会受灾人士更好的安置,这一点在此次地震中表现得相当充分。这一特征也使员工和单位的关系虽然在市场化大潮下向契约化方向发展,但对单位的依赖性反而得到加强。
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单位制的变迁不可逆转,但一旦遇到突发性事件,单位在应急的过程中表现出行为上强烈的路径依赖:向上级单位索取资源,上级单位尽力满足其需求;单位主动为员工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员工认为理所当然,遇难员工家属甚至要求单位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一切生活困难,而单位也最大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在地震这一突发事件中,虽然国企又扮演了全能社会的功能,但大体可以肯定这是个暂时性的现象,国企的多元化功能会进一步压缩。但另外一些趋势不甚明朗,国企的依赖性结构将延续下去还是会随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地震后生产生活的常态化而减弱?已经弱化的行政性特征和政治功能在地震后得到了加强,这种加强会是持续性的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社会学研究,1999,(4).
[4]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式[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香港),1993,(5).
[5]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1994,(2).
[6]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J].社会,2008,(3).
[7]Naughton Barry.Danwei: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a Unique Institution[M]∥Danwei: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Xiaobo Lu&Elizabeth J.Perry.Armonk,NY:M.E.Shurpe.1997.
[8]YU Xie,Xiaogang Wu.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J].China Quarterly,2008,(195):558-581.
[9]边燕杰,舒晓玲,罗根.共产党党员身份与中国的变迁[M]∥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