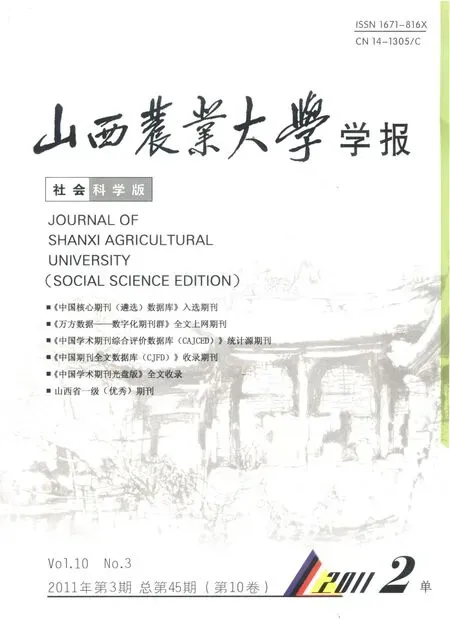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
闫志敏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近年来,在乡村社会广泛开展的村民自治制度给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巨大变化,然而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模式,要想在乡村社会真正扎根,还需培育作为主体参与者—— “农民”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公民意识,使其内化为农民内在心理的一种自发诉求,从而自愿的、积极的、理性的参与到村级基层治理中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也明确提出要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由此可见,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对于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型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公民意识的阐释及其培育的必要性
关于公民意识这一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众说纷纭。主流的学术观点一般认为,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现代意识,是人们对 “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1]在当前具体表现为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主要标志,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一种自我认识。
一直以来,作为一个以传统的农耕方式为主的国家,我国农民的公民意识一直难以产生,表现在经济上受制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以村落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产业形式,难以构筑起因普遍的经济联系和共同利益而交往的公共领域,无法生成农民公民意识的经济土壤;[2]政治上,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集权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滋长了大众的个体依附性;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纲常的浸染,限制了个体意识的发展,造就了普遍的集体无意识。直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逐步实施及其所蕴含的竞争、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的渗透才渐渐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客观上促使农民以一个市场主体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政治体制领域所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亦是如此,其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理念同样要求其参与者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一个理性人的身份自主的、积极的参与到村级政务管理中来。由此看来,要消除传统价值观念对农民公民意识的束缚,形成适合当前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所要求的现代意识,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对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势在必行。
二、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公民意识缺失的表现
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地区普遍推行的以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自治治理模式的实施,通过各个环节农民的广泛参与,逐步培养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了农民参与的知识和技能。但是鉴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发展的历程较短,还存在诸如选举形式化、拉票贿选、村两委矛盾、宗族势力的阻扰等多种因素以及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低等的限制,我国农民的公民意识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民公民意识的 “分散化”状态
公民意识是一种系统的现代化意识,它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的一种自我定位,体现于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的广泛参与,但当前我国农民的公民意识呈现出来的多是一种 “支离破碎”的状态,只分散的体现在某些单一领域。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只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例如,宅基地的划分、村民选举时竞选者的经济承诺等,简单的停留在追求劳动报酬权的平等上,而对于村庄长远发展的事项以及相关制度的完善方面大都抱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从众心理,缺乏参与热情,有时甚至表现为一定范围的政治冷漠或消极抵抗。
(二)法治观念的淡薄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农业法》、《土地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出台在客观上增强了农民的法律意识,为农民在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中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传统的“权大于法”的旧观念依旧深刻影响着农民在处理问题上的思想和行为,包括村级公共权力的掌权者和普通村民。在一些基层政府行政人员的潜意识里仍旧认为村委会是乡政府的“腿”,还是按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村民自治,习惯于随意性的摊派一些工作,而村民们也习惯于接受“上级”的领导,对于侵犯了自身政治权利的一些行政违法行为,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表示不满,如围攻上访等。当然,一方面源于农民的法律认知程度低,另一方面就是农民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独立人格的缺失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虽然结束了长期以来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但由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发展的有限性以及尚未根除的农民依附性心理,导致大部分农民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不能积极而正确的利用国家赋予自己的权利来捍卫自身的利益,以至于当自身利益受损时,认为自己“人微言轻”,要么选择忍受不公,要么采取非法手段。[3]如近年来各地频繁上演的上访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就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现代化的公民意识要求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既要维护公民正当权利,也要公民承担相应的义务,但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一味的争取权利,却很少去尽一个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
三、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途径
英格尔斯认为:“完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只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心理上、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4]也就是说,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社会取得实效,不仅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参与型政治文化为导向,更需要作为主体参与者的广大农民心理上的一个调适,逐步培育农民顺应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即我们说的公民意识。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人的观念、意识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既深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又饱受多元文化冲击的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而言,决定了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必须积极调动各方力量,有效、长久的贯彻下去。
(一)农村市场经济的壮大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民意识是上层建筑范畴内的概念,在现阶段表现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意识。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包含的开拓创新、自由竞争、公平公正等价值内涵以及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利益分化和利益觉醒有助于农民克服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封闭性,有利于农民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法治意识的养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引导农民自觉地遵循市场规律,自觉自愿的参与到市场中,通过自身的参与逐步培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公民意识。所以,要鼓励和支持农民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其提供政策上和组织上的条件,将其培育成市场经济主体。
(二)村级民主实践的扎实推进
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和深化村民自治制度,细化、规范化、程序化农村基层选举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民 “一事一议”制度,使村民逐步的熟悉进而习惯于民主的规范操作,锻炼农民民主管理的能力,提高农民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趋势表明,对于任何公民而言,仅有参与的意愿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公民必须在组织化的参与活动中提高参与能力。[5]因此,需要强化农村合法性社团组织建设,通过健全和规范社团组织活动,引导社团组织成员有序规范的参与农村各项生活,通过农村经济合作社、农民协会等组织鼓励村民参与社会事务,在此过程中了解组织权力的运作过程,从而提高合法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的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民组织性、凝聚力的提高,加强农民与政府间的沟通,扩大农民在相关涉农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
(三)乡村政治文化精神的重塑
基层民主政治的运作一定要处理好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改造传统的政治文化。否则,再好的制度也是不中用的摆设。[6]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小农意识还普遍植根于部分农民的思想中,表现为一些地区农民集体观念、民主法制观念淡薄,封建迷信盛行,宗族势力抬头,教条主义横行,道德水准下降等,严重阻碍了农民公民意识的成长。因此,迫切需要重塑新的乡村政治文化精神,营造良好的民主文化氛围。一方面,要通过传统的家庭教育来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如勤俭节约、诚信友爱、重情重义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使得农民参与政治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也日渐增多,地方政府要以一个开放的心态积极引导和疏通,结合农村的实际,通过多种方式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培育农民成为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
(四)农村公民教育的深入开展
村民自治最终是要实现村民的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三位一体的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公民教育的实施。所谓的公民教育是指通过对公民意识所施加的教育影响,使公民觉悟到自己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而不再需要外在的强制性,从而达到理性自觉的境界。[7]主要包括公民的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只有通过对其多方面的教育才能提高农民的素质,培育出适合现代化社会所需的具有民主主体意识、法治意识、权利和责任意识的理性的现代化公民。
[1]王国胜.农民公民意识及其增强[J].理论探索,2010(1):98.
[2]邱国良,段艳丰.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路径选择理论研究 [J].2008(4):44.
[3]朱宁峰.农民的公民意识及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4(9):39.
[4]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5]丰存斌.民间组织在促进公民参与中的作用分析 [J].理论探索,2008(6):130.
[6]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7.
[7]陈春燕,赵继伦.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J].理论研究,2009(2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