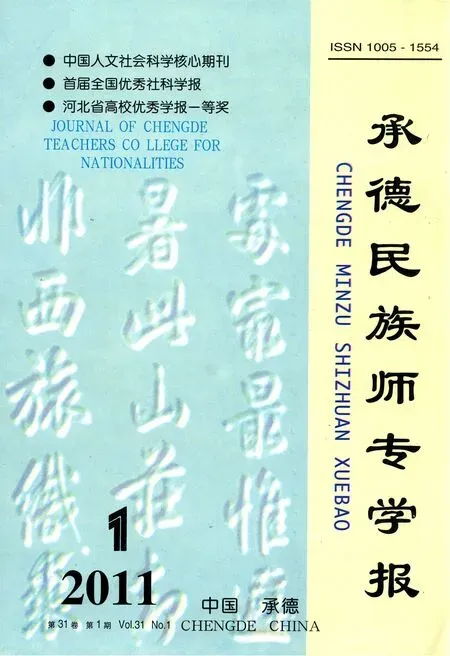《霍小玉传》别解
杨秋红
(北京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霍小玉传》别解
杨秋红
(北京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
作者从三个角度对唐传奇《霍小玉传》进行了新的诠释:男主人公李益不是一个绝情的负心汉,也不是简单的负约不负心,而是一个尚有余情的负心汉。女主人公霍小玉并不痴情,更没有爱到至情,是一个理智清醒的多情女。造成二人爱情悲剧的原因不能忽视唐代的门第观念与婚姻制度,亦不排除李益草率、懦弱、不敢担当的性格,但李益为仕宦前途而负心的道德问题更值得重视。悲剧主人公的境遇是超越时空的,小说的思想意蕴也值得现代人深思。
李益;负心;霍小玉;多情;道德悲剧
《霍小玉传》是唐代爱情传奇的压卷之作,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痴情女子负心汉”题材。书生李益和妓女霍小玉相爱,得官之后另娶豪门之女卢氏,霍小玉郁郁而终,在霍小玉鬼魂的搅扰下,李益再也没有得到幸福。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悲剧意蕴,众说纷纭。传统上认为李益是一个典型的负心汉,是他的负心造成了霍小玉的惨死,小说呈现了一个道德悲剧。现代研究者也有人为他辩护,说李益只是负约,并未负心,李益负约的根源在于唐代世族豪门权势影响下的门第婚姻观,和道德无关。与李益形象相对,霍小玉一般被看作一个痴情女子,她的爱之深、怨之切、反抗之烈,受到极高的评价,甚至被提升到至情的高度。似乎李益的品质越好,霍小玉的感情境界越高,小说的悲剧价值就越大。传统的读解和近来的新解各执一端,传统读解中难免道德图解的惯性,而所谓的新解又时露性别的偏见和勉强求新的拧巴。本文的“别解”,实为求公允之意。
李益:尚有余情的负心汉
我们先来讨论令人纠结的李益。李益到底有没有负心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先明了什么是负心。负心就是背叛爱情。仅从字面上看,李益似乎没有负心,因为李益始终不曾忘情。他失约赴霍小玉,是迫于母亲的威严,母亲 “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而“太夫人素严毅”,所以他“不敢辞让”。失约之初,“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其望,遥托亲故,不遗漏言”,李益故意隐瞒消息,是不忍直言,希望霍小玉自己放弃。进京就亲之时,李益“自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沈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此番李益虽然没有前去探望,但愧疚之情愈重,心如刀割。被黄衫客挟持走向霍小玉宅邸时,李益“神情恍惚”。目睹霍小玉饮恨而终后,“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下葬后,“生至墓所,尽哀而返”。后虽娶卢氏,但“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小说对李益负约后灵魂之痛的描写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痛从何来?表面看来是因难以忘情而痛,但更深的根由是必须抛弃和不忍抛弃两种感情相纠缠之痛。小说不仅写到李益之痛,还写到李益之愧。愧从何来?因为他选择了抛弃,没有背叛,又何来羞愧?
是否背叛感情,不仅要看内心是否忘情,还要看在行动上是否赋予感情以相应的形式。抽离了形式的感情,其分量是大打折扣的。和霍小玉定情之夜,李益主动提出“请以素缣,著之盟约”,这就是一种形式。李益授官离别之际,感于霍小玉提出的不要婚姻只要八年的短愿,又主动发誓:
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
这也是一种证明爱的形式。李益的两番誓言都是以特定的形式向霍小玉证明自己的情之真、爱之久。李益的第一番誓言只是定情,第二番誓言相当于向霍小玉承诺了婚姻之约,这个约定的分量重比泰山。李益迎娶卢氏,逃避霍小玉,负约本身就是负心。负心汉有两个等级:最不耻的负心汉是彻底忘情,稍好一些的会受到良心的折磨。李益属于后者,是他给了霍小玉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又亲手毁了它。李益刚听说母亲为他定亲时,曾经“逡巡”,这说明他内心是有过挣扎的,但后来李益不但负约,而且封锁消息,这种行为说明他在理智上认可母亲的选择,只是在情感上自觉愧对霍小玉,因此迟迟不肯直面现实。他表面上是在躲避霍小玉,实际上是在躲避自己的良心。我们不能因为李益有愧疚之心,就否认他负心的事实。
最有资格评价李益的人是霍小玉,霍小玉临死之前对李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在霍小玉心中,李益是一个负心人无疑。但霍小玉也看到了李益的愧疚是真诚的,因而鬼魂托梦说:“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可李益之情也仅仅是“余情”而已,因此霍小玉的鬼魂依然没有放过他。李益既没有彻底忘情,也不是简单的负约而不负心,而是一个良心未泯、尚有余情的负心汉。
霍小玉:理智清醒的多情女
如果说李益负心,那么霍小玉自然属于弃妇。对此,有的研究者提出质疑。关四平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弃妇形象自《诗经》中的《氓》、《谷风》以降,代不乏人,但若这样评价霍小玉,未免降低了霍小玉形象的审美层次,削弱了其认识价值。”[1]P91其实,霍小玉是否弃妇和评价她的爱情质量没有关系。李益结亲卢氏,逾期不就,希望霍小玉自断其望,这不是抛弃又是什么呢?说霍小玉是一个弃妇,应没有问题。霍小玉“怀忧抱恨”、“羸卧空闺”,“日夜涕泣,都忘寝食”的表现,和《氓》、《谷风》中弃妇的自伤自怜一脉相承,只不过霍小玉身上体现出一种执着的精神和积极探寻的努力,她“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她“遍请亲朋,多方召致”。这一点和霍小玉的处境有关。《氓》、《谷风》中的两位女子是明明白白被抛弃的,而霍小玉是不明不白被抛弃的,所以她一直希望和李生相见,问个明白,她的执着有一探究竟的目的。李益越躲,霍小玉就越想找到他,这也是人之常情。
霍小玉死前之恨也是“弃妇说”被颠覆的常见理由。小说中写道:
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传统的弃妇是哀怨的、柔弱的,只敢爱,不敢恨,而霍小玉敢爱又敢恨,这是她与众不同之处。霍小玉的仇恨之切和复仇之烈也和她独特的经历有关。《诗经》中的弃妇是良家女子,从恋爱走向婚姻,又目睹丈夫移情别恋,所以被抛弃时的感受是心碎。而霍小玉是一个风尘女子,情正浓时忽然离别,婚姻誓言成为浮沤,李生也不见踪影,极大的情感落差把霍小玉推到死亡边缘。再次相逢之时,不是团圆,而是死别。李生沉默了,被弃的猜想惨然成真,她把毕生的爱恨凝聚在一刻,爆发成一个复仇女神,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激情闪烁的霍小玉并不能改变她弃妇的身份,只能说她是空前的“这一个”。
那么,“弃妇”霍小玉是一个痴情女还是一个至情女呢?
本文认为,霍小玉没有爱到痴情。何谓痴情?《词源》释“痴心”曰:“痴迷不舍之情。”对一个人的感情达到痴心的程度,甚至不顾一切,呈现出病态。在和李益相遇之前,霍小玉是多情的,她“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和《李娃传》中结交贵戚豪族、“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的李娃相比,她对爱情保有梦想。李益“才调风流”,“仪容雅秀”,霍小玉对这位才子早已“终日念想”,后一见即钟情,定情之夜即为情而哭,担心“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秋扇见捐”。但霍小玉之情是否达到了痴情的高度呢?霍小玉之所以中宵流涕,正因为她曾是霍王之女,经历过世间人情冷暖,比常人多了一分敏感和清醒,既懂得真情难遇,又知道美梦易碎。在李益赴任离别之际,霍小玉已经意识到爱情的末日即将到来,“盟约之言,徒虚语耳”,遂提出“八年短愿”之说:
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
这说明霍小玉是清醒的,她并没有爱到不顾一切。自己不过是一个妓女,而李益门族清华。她没有妄想和李益一生相伴,更不敢妄想和李益走进婚姻。霍小玉非常懂得进退,既多情又理智,正是这一点让李益“且愧且感,不觉涕流”。霍小玉有情,但不痴情。霍小玉之死也不是痴情而死,而是愤恨而死。李益一去不归之后,霍小玉开始是“想望不移”,后来“冤愤益深”,最后“饮恨而终”。
霍小玉更不是一个至情女子。至情女子必如杜丽娘那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2]P1153关四平先生认为,霍小玉“是一个千古少有的‘至情’女子形象。其美主要在爱情上的全身心投入,以致超越了婚姻,超越了生死,最后为至情付出了生命。这是光耀千古的闪光点,具有超时空的审美价值。”[1]P91细思之,霍小玉对李益之情并非全身心投入,而是时刻保持着警惕,八年短愿就是她以理智经营情感的最好证明。霍小玉之情也没有超越婚姻,尽管她曾提出八年短愿,但李益发誓“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暗许婚姻之时,霍小玉还是深以为望的。如果霍小玉真的无意于婚姻,那么当她看到李益因顾及前途而无奈背弃盟约、又被惭愧之心折磨之时,或许会悄然放手,随缘而去。霍小玉之情也没有超越生死,虽然在生死之际她已经看到李益“尚有余情”,但还是实施了复仇计划,让李益生不如死,甚至搭上了很多无辜者的性命。霍小玉不是一个爱到至情的女神,而是一个执着于爱情梦想不能解脱的凡人。杜丽娘的至情不仅指爱情,还包含个性解放的内涵,起于天性,一发不可收拾,惊梦、寻梦之痴,生生死死之寻,皆为至情,而霍小玉之情仅为爱情,而且没有达到痴迷的程度。杜丽娘的至情来去无踪,“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霍小玉之情有迹可循。杜丽娘是寻情而死,死是一种解脱,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人性的自由,“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3]P281;霍小玉是怨恨而死,带着无尽的遗憾,所以鬼魂还会找李益复仇。尽管霍小玉没有生在一个产生至情女子的时代,但在她的时代,她对爱情的梦幻、对爱情的执着,也表现出罕有的力度,昭示出一种属于未来的方向。霍小玉情感梦幻的毁灭,依然具有动人心魄的悲剧价值。
悲剧根源:社会、道德、性格的多重悲剧
关于李、霍爱情悲剧的产生的原因,传统上认为“李益个人应负主要责任”。[4]P161关四平新论认为李益应该负次要责任,唐代婚恋观念、门第观念与婚姻制度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李益负约属于性格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李益是一个有错误的好人,而不是一个有优点的坏人。[1]P94-99本文认为,社会原因应该重视,但完全回避李益的道德问题也是不妥当的。
虽然唐代已经不似六朝时期门阀制度那么森严,但世族的权势仍然显赫。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这五姓是第一流高门世族,加上姓氏同而郡望异的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为五姓七族。这五姓七族为了保持贵族的血统,不愿与他族通婚,互相结为婚姻。即使皇权干预,也不能更改这一根深蒂固的风气。为将来仕途发展考虑,士林也争相与五姓七族通婚。此风之下,因和豪门攀亲的问题,恼羞成怒者有之,放弃尊严者有之,抛弃发妻者有之,杀死旧好者有之。《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正是唐代位于五姓之首的陇西李氏,又以二十岁的风华高中进士,正俟试于天官,前途一片光明。但“生家素贫”,并不显赫,故结一门什么样的亲对李益的前程尤为重要。李益之母为他聘“甲族”卢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李家为攀高枝,还要四处告贷。李益母亲的做法是为他的前途着想,无可厚非。而李益本人最初访求名妓,只不过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不料遇到“资质秾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的霍小玉,一下沉入温柔乡中,情浓之际许下誓言,甚至许以婚姻。但当他回到母亲身边,激情退却,现实摆在面前,一个风尘女子怎可与卢氏相比,年轻的李益或许此时才为自己的草率和冲动后悔不已。考虑到仕宦前途,放弃和一个妓女的恋情成了李益权衡利弊之后的最终选择。即使没有严毅的母亲为他订婚,李益从温柔乡中醒来之后,能否坚守诺言也是一个问题。
李益的选择,放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等级观念、家族的利益、个人的前途,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李益放弃了爱情。诚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婚姻要“权衡厉害”、“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5]P586李益的个人意愿终于倒向了家世的利益。但外部压迫力量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李益没有责任,一个人可以服从家世的利益,也可以坚持个人的意愿,关键在于当事人心目中何者为重。在唐代门第婚姻盛行的社会背景下,依然有不负心的人,在唐传奇中也有反映,如黄璞《欧阳詹》中,太原妓因欧阳詹失约而死,后欧阳詹为她“一恸而卒”。再如裴《裴航》中,书生裴航为平民之女云英放弃了科举考试和所谓的锦绣前程。和这些钟情之人比,李益的品格并不高尚,他更爱自己的前程。当然,和元稹《莺莺传》中始乱终弃还要自称“善补过者”的张生比,李益并不是最差的,但不能因此就抹煞李益的道德问题。
李益负心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宋元戏文《王魁》、《赵贞女》、《张协状元》、《陈叔文三负心》、《李勉》,元代杂剧《潇湘雨》,明代拟话本 《王娇鸾百年长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作品中,哪一个负心汉没有负心的理由呢?哪一个负心汉在负心之际没有经历过一番情与利的博弈呢?哪一个负心汉不希望负心之后那个多情女子自动人间蒸发呢?李益也是如此。他的特点不过在于千躲万躲终于没有躲过,被拉到濒死的霍小玉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试想,如果霍小玉至死都不能和李益相见,霍小玉死了,李益或许还会暗自庆幸,终于可以解脱了,从此不必再担心道德的追剿。被霍小玉质问时李益的沉默不语,还有霍小玉死后李益的诚心哀悼,都不能成为回避李益道德污点的理由。如果负心汉有愧疚之心,我们就说他是一个有错误的好人,那岂不屈杀千百年来被抛弃的多情女子!哪一个年代的爱情都会遭遇个人意愿和社会观念、家族利益的冲突,而我们对一个人是否负心的判断不能没有底线。对李益负心的社会原因可以理解,但对李益负心的道德判断不能含糊。本文认为,《霍小玉传》主要是一个道德悲剧,其次才是社会悲剧,李益应该负主要责任。
关四平先生文中还谈到了李益的性格问题,他认为:李益失约之后,故意封锁消息是出于善意,回复也只能让小玉失望,就不如不令其知,未成想造成了小玉的更大悲剧,可谓是好心办了坏事。在李益入长安就亲时,“潜卜静居,不令人知”,这与前次封锁消息的思路是一致的。这是性格问题,不能完全从道德层面评价其优劣。[1]P90-91本文认为,李益三番两次躲闪,并不是从霍小玉的立场替她着想,也不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害怕承担负心的责任,害怕面对负心的后果,这仍然主要是道德问题。李、霍爱情悲剧也不是没有李益性格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草率、懦弱、不敢担当。李益沉溺于温柔乡时,没有认真想过未来,草率盟誓。真正面对现实时,又缺乏担当责任的勇气。李益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良心不得安宁,休妻杀妾,也失去了幸福。
《霍小玉传》作为较早写“痴情女子负心汉”题材的作品,其价值就在于赋予了男女主人公以独特的风貌:一个尚有余情的负心汉,一个理智清醒的多情女。人物形象是丰富的、立体的、真实的,小说所揭示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又是道德悲剧、性格悲剧。悲剧主人公的境遇是超越时空的,小说的思想意蕴也值得现代人深思。
[1]关四平.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J].文学遗产,2005(4).
[2]汤显祖.牡丹亭·题词[A].徐朔方.汤显祖全集[C].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3]汤显祖.牡丹亭·寻梦[A].钱南扬.汤显祖戏曲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程毅中.唐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恩格斯.致斐·拉萨尔[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I206
A
1005-1554(2011)01-0024-04
2010-01-05
杨秋红(1974-),女,河北徐水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