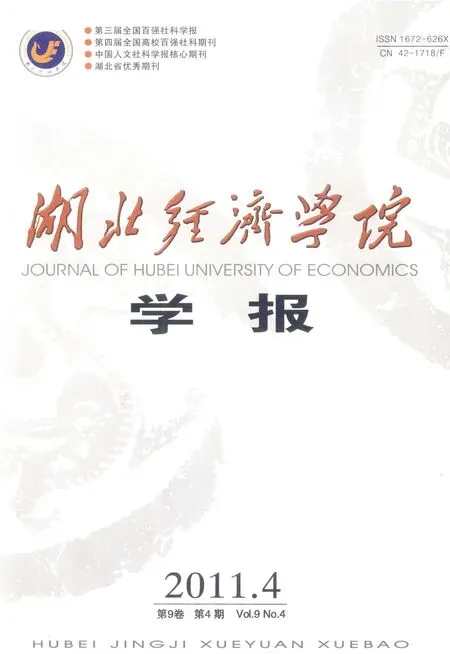肯定前的否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民主思想辨析
闫帅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基本道理的普及与推广,经历了重重磨难与挫折。换而言之,民主在得到肯定之前,遭受了一系列的否定。人们常说,古代希腊文明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滥觞。毋庸置疑,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当回望古雅典,溯流而上寻找民主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距离民主的源头越近,对它的质疑与批评之声也就越剧烈,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就是这些否定者的重要代表。他们首先对“何谓民主”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对民主进行了否定性批判。与此同时,他们也用短小的篇幅与微弱的语言给予了民主一定的肯定与承认。因此,本文努力的方向恰在于探索那些“肯定前的否定”以及“否定中的肯定”。
一、从民主的定义出发
无可否认,在民主得到首肯之前,众多政治学者都对其持一种否定态度,而本文只选择了其中的三位,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以下简称古典政治学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取舍与限制是因为作为人类社会基本价值之一的民主,其内涵与外延之博大难以数计,对其任何一个侧面或者一个微观细节的研究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在此只好尽量缩小研究范围,同时,以上三位在生活年代上接近,主要为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而这恰为民主的起源期,他们三位都有其代表著作传世,便于我们深入研究。除此之外,他们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也有着极其相似的一致性,即基本上持一种否定态度,特别是在对民主的论述上,有着相互承继的关系,这就便于归纳整理。
自苏格拉底始,关于民主的理论讨论就不绝于耳,由于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著,我们无法直接获得他对民主的基本态度,但我们可以从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来窥视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态度。苏格拉底认为民主制是有缺陷的,政治需要智慧,抽签制致使外行治国,是“非常愚蠢”。[1](P9)然而,苏格拉底批评仅限于民主制的缺陷,其并不反对民主制本身,反而对民主的生活充满了信心。[1](P15-18)当我们所要着重探讨的对象——柏拉图出场时,古希腊民主体制已经进入了衰败期,民主制的各种弊端日益彰显,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而惨死于民主制度下的事实,更是让他对民主体制怒不可遏。这些不堪的社会现实在输入柏拉图的头脑后,输出的必然为激烈的否定态度。作为政治学的伟大先行者之一,特别是作为对民主进行开先河之论的政治学家,柏拉图关于民主的阐述与讨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居于主宰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来者,继其之后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虽然对民主的阐述更为详细,但他们依然没有突破柏拉图最初设定的态度,并形成了一种代代继承的关系,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种 “路径依赖”和“惯性”。
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民主这个词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谓 “今非昔比”。所以,在阐述三位古典政治学者对于民主的基本态度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归民主概念本身,了解他们对于民主的界定。概括而言,他们关于民主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内涵上,民主是一种政体。现代社会将民主当作一种政治价值,在古代,民主只是众多政体中的一种。柏拉图认为,在古希腊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共存在过五种政体,其依次为王政、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其中民主政体是由寡头政体蜕变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政体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政体,即指“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公民团体凭这个制度分配公职时,或以受职人员的权能为依据,或以所有受职人员之间的某种平等原则为依据”。[2](P185)同时,他还依据人数与建邦宗旨将政体主要分为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两大类,前者主要包含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后者主要包含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并与前者的三种政体一一对应。而其中的民主政体即由多数贫民进行统治,只关注贫民的利益而忽略城邦的公共利益。
第二,在形式上,民主实行直接统治。由于人数的激增与治理区域的扩大,现代社会普遍实行“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选举代表来代表自己表达意见、维护权益、进行统治,而古代社会则实行直接民主。所谓直接民主即指人民直接参与、主导政府治理,而古希腊就是这样,他们通过公民大会让全体公民参与治理,官员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政敌由全体公民通过瓦片放逐法来驱赶,人们还可以通过抓阄的方式当选为执政官进而实行治理,而这种直接民主的模式在古希腊那种“小国寡民”的时代是可行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种直接民主的形式都有过阐述。
第三,在主体上,民主的主体为贫民。现代社会民主的主体为不分出身、性别、贵贱与信仰的一切合格公民,而古代的民主主体却设有重重关卡与限制,它的主体是那些排除女性、奴隶、外邦人的公民中的在人数上居于多数、在财产上居于贫穷的群体。这在三位古典政治学者的著作中都有过描述,在柏拉图看来,寡头政制是少数人的统治,而“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反对的”。[3](P313)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他认为民主制是由无产的贫民(群众)们执掌最高治权,实行多数人的统治,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的统治模式,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民主政体的贫民属性,认为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区别不在人数的多寡,两者在原则上的区别应该为贫富。“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财阀)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平民 (民主)政体”。[3](P135)而在西塞罗看来,所谓民众(民主)政府,即为“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4](P36)尽管他们在对民主的表述上多种多样,但他们无疑都将民主与在数量上居于多数、在财产上占有少数的贫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四,在价值上,民主推崇自由与平等。柏拉图指出:“自由是民主政体最大的优点和它赖以建立的基础。”[5](P340)同样,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民主政体以“自由为旗帜”,[3](P135)同时,他还对此展开了说明,在民主政体中,一切都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一切都归人民掌管,一切都处于人民的权力之下,一切事情均由人民讨论和决定,民众享受到自由。自由,民主所欲也,平等,亦民主所欲也。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5](P331)而关于民主与平等,亚里士多德表述为,他们(平民)会因为一方面的平等而要求所有方面的平等。
二、肯定前的否定
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对于民主的基本界定与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古代政治界关于民主的主流思想。而在此界定的基础上,他们表现了对于民主的否定态度,之所以否定民主,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民主主体——贫民的否定性批判。无论是苏格拉底所强调的“知识即美德”,还是柏拉图所孜孜以求的“哲学王”,他们都共同认为治国乃是一项技艺,并非任何人都能驾驭。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具有知识与品德,而在那个时代,教育是贵族才能拥有的奢侈品,普通公民对此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只有那些获得教育、拥有美好品德的君主、贵族也才有能力、有技艺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因为大自然已规定那些在品德和精神上更优越的人应该统治弱者,而且规定了弱者会情愿服从强者。这也才有西塞罗的那句反问:“有什么能够比依据品德来治理国家更为高贵呢?”[5](P41)而贫民的素质低下,眼界狭小,他们只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而忽略了全邦的幸福与正义。在民主的体制下,国家将其统治者的选举留给或然性,而这就会像一条其领航员是通过抽签从旅客中产生的船,注定是要很快倾覆的。不仅如此,品德低下的人民并无法正确地使用他们所推崇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而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享用着他们不熟悉的自由。也正是在民主体制下,一些无辜的人被流放,许多公民的财产被抢劫,引进了每年改选执政官制,人民眼前有了一束棒,不论什么样的诉求都获得了许可,平民中发生了分裂。
第二,对民主价值——自由与平等的否定性批判。作为民主所倡导的“自由”价值,人们一旦获得便会毫无保留地使用它,使它不受控制。人们也可以在民主体制下为所欲为,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如果有什么法令阻止你得到行政的或审判的职位,只要机缘凑巧,你也一样可以得到它们。而这种不顾后果而对自由的过分追求最终产生了三种恶果:首先,社会价值与是非被颠覆,极端的自由导致社会价值秩序的颠覆,傲慢为无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其次,社会现有秩序被破坏,取而代之的则为无政府主义,在对自由的过分追求中,秩序散失了,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而这种无政府主义还“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里去”,甚至“渗透到动物身上去”,在家庭中长幼不再有序,父亲开始惧怕儿子,走到大街上,人们必须给牲畜让道;再次,导致极权政治的产生,柏拉图就指出,自由是民主政体最大的优点和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但民主城邦如果“不顾一切过分地追求自由”,也会破坏民主政体存在的社会基础,并导致极权政治的产生。[3](P340)对于平等的批评主要表现如下:西塞罗之所以认为民主政体是三类政体中最有缺陷的一种,就在于其认为社会中人有智有愚、有强有弱、有贤有不肖,他们之间的地位和法权不应是平等的。德性和智慧超群的杰出公民应享有与他们的智慧和德性相称的等级地位和法权,否则,如果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众生平等,公平本身就是(对贤者的)不公平,所谓平等实际上是(对贵族的)不平等。亚里士多德也借荷马的诗句“良莠不齐兮贤愚同列”隐晦地反对名位的过分“平等”。
第三,对民主后果——暴民政治的否定性批判。前面已经论述了贫民的智力低下,缺乏理性,易为情感所左右。所以,在民主体制下,他们极易为一些政客所蛊惑。三位古典政治学者对此都有具体的说明,柏拉图认为:“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领导人,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3](P340)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独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治权,他们就代表了群众的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站上了左右国政的地位。”[2](P191)同样,西塞罗也有类似的表述,在他看来,“人民也是这样,在和平时期以及处理国内事务时,他们执掌大权,甚至威胁他们的地方行政官,拒绝服从他们,向这人那人或向人民呼吁,可是,在战时他们就会像服从君主那样顺从他们的统治者;因为安全超越人性。的确,在情况更为严重的战时,我们的人民都宁可把一切权力授予一个人,而且他无需同事。这个人的称号就说明了他的权力的特点;虽然他通常被称为 ‘独裁官’,出自他被‘任命’这一事实,但是,……他被称为‘人民的主人’”。[5](P49)而他们这些思想已经有了“民粹主义”和“多数人暴政”的基本想法,其意义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前承后继、一脉相通地对民主观念提出了极为挑剔、极端与刻薄的否定。与此同时,我们也无可否认,他们的批评是恰当深刻与切中要害的,是让民主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不得不正视以及在民主的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加以警惕的。
三、否定中的肯定
虽然在这三位古典政治学者的文章中否定的文字占据了较大的篇幅,但我们仍能从那些微少的字里行间读出肯定的语言,换而言之,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给予了肯定,尽管这些肯定是微弱的,但它却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以后发展开来。这些微弱的肯定即本文所论述的“否定中的肯定”。
在这三位古典政治学者中,亚里士多德对于民主的态度是相对全面与中庸的,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否定了民主,而在《雅典政制》一书中却又肯定了民主,而且多次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欣赏:“平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平民当权的公民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平民手里了。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对的,因为少数人总比多数人更容易受金钱或权势的影响而腐化。”[4](P16)即使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还是对民主给予了部分肯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强调人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城邦中大群的穷人被摈于公职之外,这就等于在城邦内保留着许多敌人”,[2](P144)现代民主就旨在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化解矛盾,把众多拥有不同意见与利益诉求的人民吸纳到体制中来,通过谈判、参与以及协商等诸多途径来解决,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对现代民主中强调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其次,肯定人民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亚里士多德认为,“似乎把治权寄托于少数好人(贤良),毋宁交给多数平民,这里虽存在着一些疑难,其中也包含某些真理,看来这是比较可取的制度。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相似地,如果许多人(共同议事)人人贡献一分意见和一分思虑;集合于一个会场的群众就好像一个具有许多手足、许多耳目的异人一样,他还具有许多性格、许多聪明。”[2](P144)西塞罗在其《国家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在他们(平民)看来,当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充满了一种和谐精神,并依据他们自身的安全与自由来检验每种措施时,没有其他政府形式会比它更少变化或更为稳定。他们坚持认为,在所有人的利益都相同时,和谐是非常容易获得的,因为利益冲突产生不和,这时不同措施有利于不同的公民。”[5](P39)
与其他政治价值不同,自民主诞生之日起,伴随而来的就是不断的质疑与猛烈的攻击,民主能够发展到今天,得到世人的肯定与政治家的推崇,恰恰是它对质疑与批评不断回应,对自身不断完善与修正的结果。而对这些肯定前的否定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理解与把握民主,在推崇民主时,不忘用那些肯定前的否定来警惕民主的丑恶一面,进而使民主在鞭笞下不断走向优质。后来民主的发展恰恰吸取了前人的这些批评,其表现为:在现代民主的发展中,积极倡导良好的公民素质与发育完善的公民社会,以此来回应古典政治学者对于民主主体——贫民的批评;民主与自由确实是相伴而行的,然而过多的自由反而会让人失去自由,即所谓“自由悖论”。因此,现代民主倡导与推崇受到法律约束的、有限度的消极自由,而非那种过度强调自我与放纵的积极自由,以此来回应古典政治学者对于民主价值——自由的批评;同样民主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和不良后果,这既包括托克维尔所指摘的“多数人的暴政”,也包括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的“民粹主义”,所以现代民主开始强调协商民主、共和观念与精英民主等主张,以此来回应古典政治学者对于民主后果——暴民政治的批评。总之,无论是“肯定前的否定”还是“否定中的肯定”,这些都为民主的前行与运转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这些源头的探索与研究,无疑能够更好地“使民主运转起来”。
[1]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日知(林志纯),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M].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