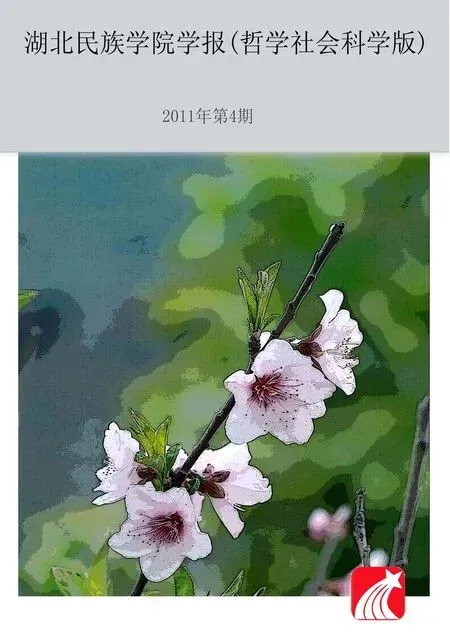李三瘦之三“瘦”英译的美学视角
余双玲,顾正阳
(1上海大学 英语系,上海 200444;2.宁波工程学院 英语系,宁波 315211)
李清照有诸多雅称,如易安居士、婉约宗主、李三瘦等。此“三瘦”即指李清照三个因“瘦”而名传千古的动人词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新来瘦”和“人比黄花瘦”。作为宋代婉约派词人的代表,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夏日绝句》等风格独特,脍炙人口,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历来有诸多学者探讨原文本的美学价值,如刘晓峰的《论李清照词的美学成就》、姚红的《李清照词的美学价值》等,他们从李词的语言、意象及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带领读者从文学的深层次体悟李词的各种美。更有甚者,不少学者总结出李清照词的最大美学特征是“瘦”字的使用,如崔际银就从多用“瘦”字、多绘“瘦”形、多构“瘦”境[1]等方面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译学探索与美学联姻,是我国译论的突出特色。”[2]远者如严复 “信达雅”的“雅”,近者如林语堂《论翻译》中的“忠实,通顺,美”中的“美”。现代学者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毛荣贵的《翻译美学》都将美学与翻译紧紧相连。诗歌是最美的语言,对于其翻译,美学是指导此过程的第一原则。诗歌翻译大家许渊冲的“三美”论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译诗,不仅要译其义,更要译其美。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李三瘦之三“瘦”字时,译其美形,得其美意,可谓译界典范。笔者试从美学视角分析之。
一、“瘦”译显语言美
“翻译又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在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管怎样,在两种文化的竞赛中,想要青胜于蓝,一定要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3]许先生强调翻译时使用语言的重要性。对于本来语言就炉火纯青、超凡脱俗的李词更是如此。试看“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之朴实清丽,试看“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之匠心独运,试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急徐有致,无一处不彰显词人语言之鬼斧神工。下面是一“瘦”原文: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这是李清照早期“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词人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令人玩味不已。春夜里一场狂风暴雨之后,残醉未消的词人睡眼惺忪。翌日清晨她急切地向卷帘的姑娘询问室外有何变化,粗心的卷帘姑娘却答之以“海棠依旧”——海棠花依然完好无损。对此,词人禁不住连用两个“知否”与一个“应是”来纠正其观察之粗疏。她说,风雨之后,该是绿叶茂盛,红花稀少!“绿肥红瘦”一句,形象地反映出作者对春天将逝的惋惜之情。“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本词的传神之笔,“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处。这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赋予词作高度的审美价值。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此语甚新。”《草堂诗余别录》评:“结句尤为委曲精工,含蓄无穷意焉。”皆非虚誉。许渊冲在其译文中也较好地保留了这种美学价值:
Last night the wind was strong and rain was fine;
Sound sleep did not dispel the taste of wine.
I ask the maid who’s rolling up the screen.
“The same crab-apple tree,” she says, “is seen.”
“But don’t you know,
Oh, don’t you know,
The red should languish and the green must grow?”[4]316
译文末句的意思是: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应该是红花凋零,绿叶繁茂。原词中的“绿”指绿叶,“红”代替红花,乃两种颜色的对比;“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份充足而茂盛肥大,“瘦”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打击而凋谢零落,乃两种状态的对比。译文没有直接以瘦译瘦,而是很好地把握了原文的意思,极大地发挥译语的优势并保留了原文的两组对比:the red(红色的东西) 和the green(绿色的东西), languish(消失)和grow(生长)。这两组对比的使用,贴切原文的意思,让译文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创造语言美的同时传达了原词的意思。
二、“瘦”译显形象美
形象的本义是指人物或事物的形体外貌,有声、有色、有形状……别林斯基曾经说:“诗歌用形象诉于灵魂,而这些形象就是那永恒的美的表现,它的原型闪耀在宇宙万物中,在自然的一切局部现象和形式中。”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翻译就是对原诗审美特征和艺术魅力的再现。因此,译诗必须要译出原诗中的形象美。在翻译诗歌时,要运用形象化思维,仔细揣摩作者思想情感,尽力译出原诗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形象,使译文读者进入原文的艺术境界,从而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形象体会和美感体验。[5]这一点极为重要,许钧先生曾说过:“翻译一部作品,领悟原作的美学特征,体会原作的旨趣意境,捕捉原作的形象,是非常关键的。”(许钧等,2001)李清照的词多绘“瘦”形,对象包括花和人。在翻译时应尽量用译语构筑“瘦”形,以在传达原文形象方面起到异曲同工之效果。请看《凤凰台上忆吹箫》之二“瘦”: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
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李清照的词,前期多书悠闲生活,后期多写悲叹身世。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便“ 负笈远游”,深闺寂寞,她深深思念着远方的丈夫。这首词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情挂念。炉中香消烟冷,无心再焚;床上锦被乱陈,无心折叠;髻鬟蓬松,无心梳理;宝镜尘满,无心拂拭;日上三竿,犹然未觉光阴催人。词人一连串“慵态”的描写,塑造了一个极其慵懒的形象,为何?“生怕离怀别苦”也。“多少事,欲说还休”,一腔哀怨,万般愁情,本想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只“执手相看泪眼”罢,难怪她会“慵怠无力”而 “新来瘦”了,而不是常人的“日日花前常病酒”,抑或“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个“瘦”字描绘出一位因伤离惜别而日渐消瘦的女子,具有无限的美感。上阕末句译文如下:
Recently I’ve grown thin,
Not that I’m sick with wine,
Nor that for autumn sad I pine.[4]320
译文的意思是:最近,我变瘦了,不是因为饮酒过度病倒,也不是因为秋天而悲伤。我国翻译家谢云才认为:“文学翻译是由把一种语言塑造的艺术形象用另一种语言再重新塑造起来。”[6]译文以thin(瘦)译瘦,用第一人称I(我),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并且再次描绘了一位心灰意懒、欲语还休的女子,她因为不舍与丈夫的别离而近来消瘦了。第一人称的使用使得这位形容憔悴、愁情满腹的女子的形象更可信、更感人了。
三、“瘦”译显意境美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中国诗人、词人在诗歌创作时历来重视构建一个或豪迈奔放的、或婉转凄凉的、或抑郁悲愤的、或意气风发的意境,甚至,有时,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靠读者去想象。德国接受美学理论代表人物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7]说的即是读者对文本的“空白”进行填补的过程。对于译者而言,在其翻译过程中可以有效地引导读者填补空白的过程,以使译语读者得到跟源语读者最接近的享受。请看三“瘦”《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同样作于李清照婚后,创作背景同于二“瘦”,表达重阳佳节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全词开篇言“愁”,结尾说“瘦”。 “瘦”因“愁”而起,“愁”因“瘦”而更“愁”。在上片中,出现三个时间词——“永昼”、“一夜”和“重阳”,贯穿其中的是“愁”,是“凉”。“每逢佳节倍思亲”,词人渴望在这重阳佳节与丈夫团圆,渴望与他共饮菊花酒,可是现实中还是孤身一人。看到曾与夫君共用的“玉枕纱厨”,触景生情,顿觉时间漫长而无聊。瑟瑟西风送来菊花的阵阵幽香,真让她柔肠寸断。此情此景,让词人发出“人比黄花瘦”的千古绝唱。思妇与菊花,谁更凄惨?菊花至少有人把酒相对,而思妇,只能独自一人品尝幽幽愁情。请看译文:
Say not my soul
Is not consumed. Should western wind uproll
The curtain of my bower,
I would show a thinner face than yellow flower.[4]324
译文的意思是:不要说我没有为此情此景肝肠寸断。西风卷起我闺房的帘子,比那些风中的黄花还要瘦弱、憔悴的脸。译文的精妙之处在于补译了一个face(脸)。自古花与美人总是相提并论,美人恰若“梨花一枝春带雨”,恰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她“闲静似娇花照水”,她“行动如弱柳扶风”,更有美女能“羞花”。 译文没有完全按照原文将“人”与“黄花”对比,而是发挥创造性地将美人的脸(face)与黄花(yellow flower)对比,可谓“创造性叛逆”。许钧在《翻译论》中说,“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我们重新思考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本质与任务提供了新的视角。[8]
李清照词中的“瘦”字升华了诗词的内容,创造出无限的意境,带来极大的审美空间,历来被学者所重视、所探讨。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基于对原文情境的透彻理解,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展现了“瘦”字在不同词中的不同韵味,带领读者领略了中华诗词别样美的意境。
[1] 崔际银.“瘦”,李清照词的美学特征[J].芳林漫步,2001(3):68-72.
[2] 赵秀明.中国翻译美学初探[J].福建外语,1998(2):36.
[3]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120.
[4] 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5] 顾正阳.古诗词曲英译美学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279-280.
[6] 谢云才.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辽宁大学学报,2000(6).
[7] (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6.
[8] 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