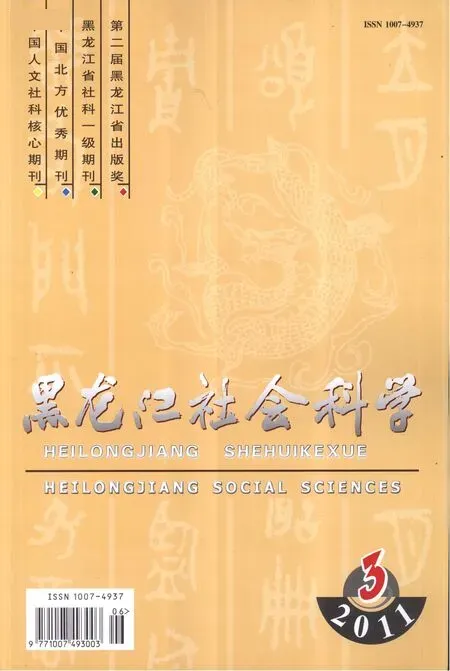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论休闲
陆 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亚里士多德论休闲
陆 扬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休闲在今日全球化市场态势中,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格外看好的巨大产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体育产业,都隶属休闲产业,并构成其麾下的三大支柱产业。这样一种大休闲概念的阐释,其理论基础是,工作之外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休闲的天下。说此种理论并非空穴来风,通过梳理分析亚里士多德对休闲概念的辨析,不敢说正本清源,唯愿可望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廓出休闲这一概念的原初认知模态。如果此研究能够对今日方兴未艾的休闲经济有所启示,它当可显示哲学缘出生活摆脱生计劳顿的闲暇,终而复归日常生活的这一希腊理念并非无稽之谈。
休闲;亚里士多德;幸福;休闲哲学
一
从历史上看,人类有闲阶级的出现与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但是休闲未必是有闲阶级的专利,一认知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发现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休闲肯定不是无所事事,抑或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妨说,休闲是在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中孕育着思想和创意。回顾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这一份珍贵的休闲哲学遗产,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当仁不让是这一休闲哲学的代表人物。
休闲意味着什么,休闲又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本人对此有清楚的说明。这些说明如果不能显示别的,至少可以显示休闲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且至少在一点上,它相似于柏拉图《理想国》中有如太阳高高照耀,那个至高无上的“善”的理念,因为它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十第七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的基础有赖于休闲,我们忙忙碌碌,目的要是为了有暇休闲。这和为了和平而战斗是一样的道理。可见,休闲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成任何其他目的的途径。
亚里士多德就休闲和其他人类活动作了比较,他举的例子是当时希腊最为显赫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对此,他分析说,政治和军事行动,那都是实践德性的行为,是同休闲不相干的。特别是战争行为,战争本身肯定不是目的,没有人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要是有人纯粹为了杀戮而与友为敌,开启战端,那人必是十足的杀人狂。同样,政客们的行为也无涉休闲,因为政治行为本身也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权势和荣誉,以及政客本人及其追随者们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说,权势与荣誉也好,幸福生活也好,它们同政治行为本身不是一回事,而是后者的目的之所在。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在所有德性行为中,哪怕是政治和军事这两种最是高贵而伟大,也是最为显赫的行为,同休闲也了无干系,因为它们别有目的,我们不是为了政治而政治,为了军事而军事。但是休闲的性质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一种理性活动:“理性活动则需要休闲,它是思辨性质的,无论在于认真价值和以自身为目的方面,都较政治和军事活动更高一筹,它有自在自为的快感 (这快感又深化了此种活动),有着人所能有的自足、闲适,让人乐此不疲,其他一切这个至福中人享有的属性,也同这一活动明显相关。故此,一个人如若能够终生都这样生活,这就是人生的完美幸福,因为幸福的属性无一不是完满的。”[1]
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可视为给予休闲的一个哲学定位。它将休闲定位在理性活动层面,判定休闲具有思辨性质,以自身为其目的。即便是最为显赫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对它也是望尘莫及。这是希腊哲学的传统,它要说明的是,哲学诞生于休闲,而唯有休闲的人生方是完美幸福的人生。
休闲由是观之,它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充满睿智的古代先哲的人生境界。它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断不可相提并论。与休闲对举的是形形色色的“德性活动”,一如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和军事活动定位为最为显赫的两种德性活动。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得出:只有工作,没有休闲,将不是完美的人生;而哲学和一应知识,说到底,都是诞生在休闲的人生之中。这可视为希腊哲学诞生的基本背景。对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有一个描述,他说,在被发现的越来越多的知识中,有一些是为生活所必需,有一些则供消磨时间。两者比较,人们普遍认为后一种知识更见智慧,因为这些知识并不是为了实用。故此:“只有当所有的实用发明已经具备,那些既不是旨在提供快乐,也不是为满足生活必需的知识,才能得以发现,而它们首先是见于人们开始拥有闲暇的国度。这也是为什么数学类知识是在埃及奠立,因为在那里允许僧侣阶层休闲自得”[2]。
可见,休闲是超越了日常生活之必需的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类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切思辨科学和数理科学得以确立的前提所在。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数学知识发端于埃及,是因为埃及出现了可以休闲自得的僧侣阶级。这样来看休闲,不失为启蒙的先导。
二
休闲是一种人生的至高境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就是人生的最终目标所在。对此,他在《政治学》卷八第三章中比较集中地做了论述。在鼎力推广音乐欣赏的语境中,他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自然本身,诚如人经常说,要求我们不光能够胜任劳作,同样能够善于休闲。因为,我必须再次强调,人类所有活动的第一原理,就是休闲。劳作和休闲两者皆为必须,但是休闲要胜于劳作,而且是为劳作的目的所在。”[3]
这是不是古今中外吾人所见给予休闲的最高评价?休闲高于劳动,休闲是一切人文、经济、军事活动的第一要领,换言之,它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夸张?但毋庸置疑,它们大体上正是古希腊哲学的共识。如上所言,既然这样一种至高境界不是先天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所成,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休闲,在休闲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正好也是亚里士多德思考的问题。他的解答是,休闲中我们要做的不应当是娱乐,因为假如休闲就是娱乐,那么娱乐就成了人生的目的。事实上,辛勤劳作当中更需要娱乐,因为娱乐使人放松,可以解除辛劳。考虑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娱乐,这样它可以成为解除疲劳的良药,由此得到快感。但是休闲不同,对此亚里士多德强调说,休闲本身就给人生带来快乐、幸福和享受,而消受此种快乐、幸福和享受的,不是疲于奔命的忙碌之辈,而是拥有闲暇心境的人。这里面的逻辑,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因为忙碌之辈总是紧盯住某个没有达到的目的,而休闲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它与幸福一样,令所有的人都觉得与之相伴的是快乐而不是痛苦。问题是,此种快乐因人而异,根据各人习性的不同而不同;最好的人快乐也最高,因为它缘出最高尚的资源。这些最高尚的资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其一就是在自由的时间里,以休闲的心境,来欣赏音乐。在这里音乐不光是一种教育、一种娱乐,严格地说,它没有任何功利目的,近似后来尼采推崇备至的狄俄尼索斯精神,是以生命的内在节奏,演绎以自身为其目的的休闲之歌。
反过来看,休闲既然是一种后天习得的人生至高境界,那么这个习得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学习?从这一理路来看,休闲和知识的获得,是难以区分二者是否同为一路。从词源上看,“休闲”(leisure)一词的希腊语是 skole,它同样是“学堂”一语的词根,一如对译“学堂”一语,英语中的 school、法语中的 école、德语中的 Schule,都可见 skole词根的影子。由此可见,要是说“休闲”这个词语在古代希腊的语境中意味着在自由的、非强制的氛围中学习,当不是言过其实。因此,亚里士多德推举音乐当是意味深长。它意味着我们的一切创意就是在休闲中得到酝酿,没有休闲就没有真正的创意。
休闲作为一种人生的境界,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中产阶级必备的一种禀赋,其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从其根本上说,有赖于中产阶级的休闲境界。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闲暇或者说休闲人生,并非自然而然可以获得,换言之,它不是天生的,而是习得的一种人生禀赋。
三
从政治学方面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担忧小人得志,尤其担忧心胸自私狭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底层人物主政城邦。柏拉图的这一担忧在《理想国》中多有陈述。对此,他提出的对策是尊哲学家为王:哲学家禀赋过人,洞烛幽微,受过良好教育,有足够的理性,而不是出于权力欲望来为国家服务。如在《理想国》卷七中他说,“理想国应当由’真正富有的人在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又说,“政治权力应当由那些不迷权力的人来掌握。”[4]可见,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是有一种超越世俗纠葛的休闲人生态度,一旦当政,自会处事公道,不偏不斜。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柏拉图同样推崇休闲的人生态度,肯定休闲是追求真理的基础。唯独在休闲之中,人得以沉思和反思,得以发展他的思辨能力,对周围的世界有更为深切的认知。换言之,休闲中有求知,更有创意,这就是希腊哲学的休闲理念。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休闲并不是有闲阶级的特权,它是一种禀赋,需要后天的培育,通过禀赋的培育,展示人生的幸福和智慧之路。因此,休闲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对此《政治学》卷二第十一章中有一个说明,亚里士多德在介绍迦太基政体时指出,迦太基的政体偏离了贵族政体的传统,偏向于寡头政治。这一倾向自有其公共舆论的基础,即说人们普遍认为,遴选行政人员,德才不应是唯一的标准,同样还要兼顾他们的财产,大众会说,穷人不大适宜执政,因为他们没有闲暇。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闲暇”,显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概念。我们设想一个穷人当政,必有薪水和适当收入,不至于依然操持旧业养家糊口。所以不奇怪亚里士多德对迦太基的根据财产多寡来遴选当政者抱批评态度。他指出,无论对于重财产的寡头政体,还是重德才的贵族政体,休闲的人生态度在其中都是举足轻重:“对于这个最高层的阶级,无论是他们在职时期,还是不在职时期,第一要领是他们须得拥有闲暇,不至于屈尊从事任何其他贱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即便这里必须考虑进财产,以便保证闲暇,可是假如最高的职位诸如国王和将军,都可以钱财贿得,那就非常糟糕了”[3]31-36。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或者说休闲的人生态度,并不是富人阶级的专利。它并不意味着有了财产就有了休闲的境界,更不意味着可以买官卖官,一旦当政便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此,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要是以为诚实的穷人会投身于逐利行业,一个生性鄙俗的人一旦遭遇不测之需,却不如法炮制,那才是荒唐透顶。他的建议是,当政终究还是德才为上,即便一个城邦的首脑对于那些比较优良的公民,无法给予终身供养,至少也应当让他们在职期间能够拥有闲暇。很显然,拥有闲暇在这里的意义,更多是一种高远的禀赋,让人不必斤斤计较于日常生活中的利弊得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它显然是为清明政治之必须。
休闲和平民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卷四第四章中有一个侧面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在比较分析平民和寡头两种政体时,将平民大体分为六种类型:第一种是从事农作的。第二种是以工艺和制作为业。第三种是经营买卖的商人。第四种是海上作业阶级。第五种是“日日劳作,以及家境欠佳,不得休闲的人。”[3]25-26第六种是父母双方都不是自由民,换言之,系奴隶出身。当然还有其他。至于贵族阶级,亚里士多德认为则是以财富、出身、德才、教育以及其他相似尺度来加以分类。这个分类也足以说明,休闲并不是贵族阶级的专利,平民阶级一样拥有休闲的权利。以上是亚里士多德将平民分为六种类型,只有以“不得休闲”来描述第五种人,即为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例子。
正因为平民同样可以拥有闲暇,所以平民政体并非不可思议。但即便如此,亚里士多德依然将能否休闲或者说拥有闲暇视为决定政体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农民阶级和家道小康的人执政,其民主体制的政府,必推崇法治。这是因为苦于生计的公民没有休闲,一旦执政,便倾向于求诸法律的权威。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门第出身无可指责,但即便如此,也须得拥有闲暇,方能真正出而从政,并且同样一切求诸法律,因为城邦没有经费来补贴公民。那么,反过来,假如城邦富庶,足以补贴公民,政体又当何论?对此亚里士多德的答复是,我们今天城市已经大大扩张,税收也与日俱增,故而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政治,比如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由此获取津贴。有了津贴就有了闲暇,有了闲暇就可以从政。
我们可以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念:高尚的人休闲,并不仅仅是紧张工作之余,放松一下身心,休闲本身就是幸福,就是目的。而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的人生至高境界,它意味着没有休闲就没有真正的创意。至于此,本文也可以尝试给休闲下一个哲学定义:休闲是人类在自由时间中,自得自足的非强制性活动。它自身就是目的,它或者利用主体自己的能力,或者利用外部的资源来满足休闲主体的身心愉悦,并且在此种愉悦中自然而然地求知和孕育创意,由此展示人类幸福和创造的必由之路。
[1]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M].Translated With H.Rackha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1177b,5-26.
[2] Aristotle.Metaphysics[M].Translated With Introd.Harmondswarth:Penguin Classics,981b,20-27.
[3] Aristotle.Politics[M].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337b.
[4] Plato.Republic[M].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td,1999:521b.
B6;D0
A
1007-4937(2011)03-0038-03
2011-03-06
陆扬 (1953-),男,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王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