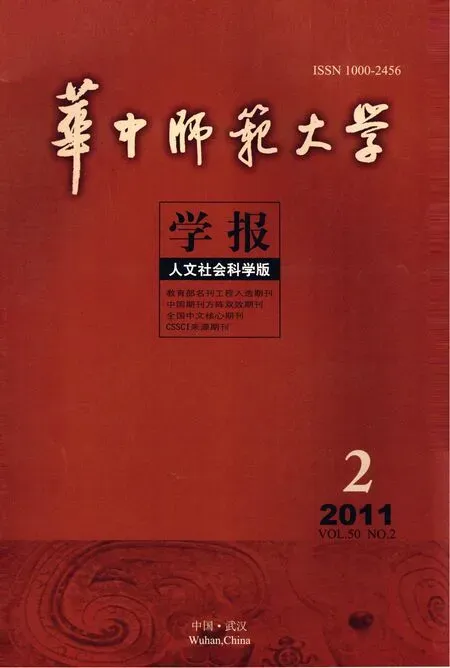“中国近代第一城”兴衰的文化阐释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中国近代第一城”兴衰的文化阐释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在中国现代城市群落中,南通曾有“近代第一城”的美誉。张謇最伟大的功绩在于社会建设,使南通一变而成为中国当时最现代的城市。正是张謇个人的思想、智慧和现实努力,才使南通避免了“先城市化,再花园化”(或“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陷阱。花园城的最大问题是以行政手段限制了城市扩张,这既在硬件上直接压缩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城市社会对人口与资源的容量与吸引力。对均衡与协调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城市结构的封闭,因而张謇的南通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型城市,从未真正具备过现代大都市的开放性与竞争力,尽管在文明形态、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上水平很高,但由于建立在对现代文明感性需要与冲动压抑与限制的基础上,因而其既无法吸引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同时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质,这是南通只能在群雄逐鹿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黯然退场的重要原因。
南通;城市化;花园城;文化
在中国现代城市群落中,南通曾有“近代第一城”的美誉。而今看来,其往昔的荣光无疑早已风流云散。在思考南通百年兴衰与沉浮时,我总是会想到儿时熟悉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下联是“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当时仅是觉得这幅对联格外高明,但以今观之,却可以发现其中竟暗示着南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荣辱与命运。无论是北方天子脚下的通州,还是地处东南江海交汇处的南通,它们曾经的兴盛实际上都与“通南北”的天时地利密切相关,因为几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是以南北为轴心而存在的。但随着时世推移与气运变化,现代世界的战略重心早已从本土的南北关系转换为全球性的东西问题。这是南北通州在现代化进程中每况愈下的根源之一。由此可知,南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盛极而衰,也许从一开始就已命中注定。而随着城市曾经集聚的资源与人气不断流失和衰竭,昔日的风华与辉煌也必然化为南柯一梦。古语云“一语成谶”,对于南通而言,这无疑就是“南北通州通南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这一切皆非人的智力与努力所能改变,但由于诗人所说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下,理智地探究一下南通这座“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得失成败,其意义可以说是远远超越于“发思古之幽情”之上的。
一
在文明时代中,个体的力量与智慧逐渐退居二线,没有办法同庞大的国家机器、复杂的社会组织相抗衡,于是在历史文献中,我们会经常看到怀才不遇者的悲哀与感慨。当然也有例外,有很多伟大而辉煌的事业与成功,其实就完全是个体凭借一己之力所创造的。这样的事件与记忆是必要的,它们让机械的人类历史变得情节生动曲折,也使普通的凡间生活富于魅力和光彩。
在城市建设方面,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锡南(Sinan,1489~1588),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从1538年被宫廷聘用,并很快成为苏丹苏莱曼一世的宫廷建筑总监,前后40多年,锡南共设计和督建了79座清真寺、34座宫殿、55所学校、19座陵墓、33所公共浴室、16幢住宅、7所伊斯兰教经学院、12家商队客栈和18个殡仪馆,此外还建有谷仓、军械库、桥梁、喷泉、医院和大型渠道等。其中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城金角湾西岸的苏莱曼清真寺,号称奥斯曼帝国建筑“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①。在融合了罗马建筑、波斯建筑和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之后,锡南创造出属于土耳其的基本建筑模式,并通过辛勤的设计与督造使整个帝国空间拥有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后来人对此只能望洋兴叹,他们关于城市的伟大设计与奇思妙想,往往只能尘封在资料室里或记忆深处。
在中国城市史上,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座城市,那很可能只有张謇和他的南通。尽管张謇涉及的空间范围不如锡南那样广阔,但就对城市物质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影响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像古代运气很好的读书人一样,张謇在他生命最成熟的盛年高中状元,为实现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环境。但处身于晚清帝国大树飘零的末世,特别是受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感召与震撼,张謇本人却意念别移。他毅然放弃了士大夫世代向往的汉宫魏阙,抱着“建设一流新世界雏形”的梦想回到故乡南通,从此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有关研究表明,从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到港闸工业区和南通城南文教商贸区建成,在前后约30年的时光里,南通的城建总量超过了此前937年(从南通后周显德五年即公元958年建城到1895年)的总和②。由此可知张謇对现代南通城市的影响之大,特别是他以大建筑师的风范所缔造的“一城三镇”,在空间资源利用上的集约、优化与深谋远虑,至今可以说仍是城市规划与更新的最佳范本之一。
建筑只是城市的躯壳,文化与精神才是灵魂。就此而言,张謇最伟大的功绩在于社会建设,使南通一变而成为中国当时最现代的城市。以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新型教育为例,从1902年捐资创建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始,张謇陆续创办了女子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同时还开设法政讲习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监狱学传习所、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等实业教育,通过提升市民素质而推动了城市的现代转型。张謇还大力从事福利社会体系和新型慈善事业的建设,创办有新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等,使当时的南通成为“一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抚、病有所医的社会”③。他的城市建设还涉及到新闻出版、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园、新式剧场等软实力层面,“民众的休闲、娱乐生活也开启了新风尚。1913、1922年第一、二公共体育场建立。1915年至1918年间,北、中、西、南、东五座公园先后落成,为公众提供了球类、器械、竞技等现代体育项目。至1919年,更俗剧场落成,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近代一流的新式剧场,剧场管理上以现代文明都市人的标准来约束看戏的市民,演出剧目上则是传统戏剧与现代话剧艺术并存,既有丰厚的传统,也有时代所赋予的新意,从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丰富了南通的戏剧舞台”④。由此可知,就其为南通市民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今天的许多大城市都不能企及的。
事实也确乎如此,作为中国古代城市向现代转型的典范,张謇的南通从一开始就受到多方面的赞美。1921年底,时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戈登·洛德,在其向英国政府提交的《1912—1921年海关十年报告》中曾这样写到:“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⑤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则把南通誉为“中国的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⑥。关于张謇对现代南通城市的重要贡献,史学家章开沅曾这样感慨:“在近代中国,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并且对全国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⑦茅家琦同样给予高度评价:“他的业绩为今天南通地区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⑧
以上这些方面,是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主要原因。南通在很多方面为当时的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不及。以交通为例,“1905至1913年间,修建了港闸路、城闸路、城山路、城港路,总长34公里,形成了‘一城三镇’的公路网络。1920年由张謇制定了全面的公路规划与修筑规划,确定了三条干线五条支线,从县城始,至垦牧区为东干线,至海门县境为南干线,将城闸路延长至如皋县境为北干线。在石港、四扬、三余、吕四等镇之间设立了五条支线与干线连接。到民国十年筑路计划全部实现,至此,南通已有公路288.4公里,为江苏全省总里程的66.5%。在那时,内地有五百多里的马路,一百多部汽车,非但江苏没有,恐怕全国也没有第二个地方。”⑨但今天重新认识上海与南通,一般人的心情就很难平静。原来的基础与发展一路领先,而今却只能以“上海大都市圈北翼的江海门户”为荣。或者说,本来都具备发展成国际大都市的地理条件,南通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甚至还曾抢得先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南通一下子被甩到后面?南通的兴起本就与张謇这样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密切相关,随着这位有教父般地位的人物“哲人其萎”,南通直接丧失了用以集聚资源与人气,以及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危机的核心,因而其衰败自在情理之中。但实际上,城市的兴衰往往有更复杂的机制与因果,而不可能仅限于一人一事之上。进一步说,即使是智力与能力过人的张謇和他精心营构的南通,在本质上也不能摆脱现代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入手,不仅可以为苦恼的南通理解其现代命运提供一个合理的说法,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城市兴衰的机理。而后一点,才是直接面向未来的。
二
城市是空间的产物,芒福德曾把城市的功能之一形象地称作“容器”。在现代南通的空间生产上,张謇规划建设的“一城三镇”广受好评。如吴良镛说:“张謇将工业区选在城西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狼山作为花园私宅及风景区,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6公里,并建有道路相通,构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一城三镇’的空间格局,城镇相互对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多镇,分片布局的模式极有创意。”⑩如凌振荣指出:“张謇在经营南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南通旧城为中心,以唐闸、天生港和狼山镇为纽带,以农村为基础,城乡相间,形成一个功能不同、互有分工的城镇组群。这种布局的优点是:首先,一城三镇各自的功能不同、互有分工。城镇间的农村,是今后城市发展预留地,避免了点式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大带来的交通阻塞等弊病。第二,在主城区外的隙地和农田设置文化、教育、金融等机构,不仅有利于古城保护,同时,也避免了利用古城土地而增加拆迁费。第三,一城三镇卫星城镇的布局,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各自功能的优势,也有利于同类功能机构的互补。第四,工业区在距古城较远的地方,避免了因工业污染给主城区带来的危害。同时,招收工业镇附近的农民工,能节约市政建设费。”(1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謇巧妙地避开了现代城市的发展陷阱,即由于盲目扩张而导致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居住密度加大、社会治安混乱等“城市病”。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可以将南通等同于英国城市规划理论家霍华德的“花园城”的原因。尽管从理论渊源上看,两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张謇的南通城市建设始于1895年,而霍华德提出“花园城”的时间是在1898年。他们面临的城市问题也有很大区别,霍华德面对的是西方工业城市的“城市化过度”,他相信治愈的方法是回到小规模的、开放的、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的社区,因而提出“花园城”理想,并在一些地区进行实践。具体说来,“一个花园城占地一千亩,城市周围是绿地,或农村地带,由农场、露天牧场、收容所和公共土地所组成。城外有一条主要线路把花园城和其他城市联结起来,它的环城部分有助于城内交通。在城市中心大约五英亩到六英亩的面积是公共建筑和市政中心。市政中心外面是主要商店、宽阔的中心公园、住宅区和花园,在环城地带有一些主要工厂。花园城人口限制在三万人左右”(12)。而张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南通推进现代化。如他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中所说:“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指甲午中日战争)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以个人私利而贬,庶原可达而守不丧。”(13)尽管时代背景与现实问题的差别很大,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样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特别是如何扬长避短,即在获得西方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其“城市病”,是包括张謇在内的当时许多中国先觉者共同关心与探索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张謇对南通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与西方城市社会学强调的区分生活区、商业区、工业区和公共场所等主张(14)不谋而合。正是张謇个人的思想、智慧和现实努力,使南通避免了“先城市化,再花园化”(或“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陷阱,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感到庆幸的。
但正如很多年以后,中国学者在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另一共识,即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只想要“好的西方文明”而拒绝“坏的西方文明”,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对于南通也是如此。花园城固然有诸多好处,但也存在着致命的问题。花园城在规划理念上有明显的复古特点,有悖于19世纪以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城市的繁荣依赖于人口与资源的大规模集聚,这是现代城市纷纷拆掉城墙、大量吞噬农业资源的根源。而花园城的最大问题是以行政手段限制了城市扩张,这既在硬件上直接压缩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城市社会对人口与资源的容量与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城市发展中无法两全的二律悖反。一方面,由于任何“容器”都是有限的,因而无限扩张必然导致“城市化过度”与“城市危机”,就此而言当然要对城市规模加以理性的限制。但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的本性是一种永不息止的“浮士德精神”,一旦其追逐和扩张的需要受到制约或打击,又会直接影响城市向更高水平的演化与发展,直至在激烈的现代城市竞争中败下阵来。关于这一点,在相关的研究中也已被注意到。如“张謇已经决定性地进入了资产阶级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他的思想、言论与行动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断绝与原先隶属的士人群体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多场合,他作为绅士的自我意识甚至还要大于作为资本家的自我意识”(15)。如“张謇试图把南通封闭起来,在封闭的环境下进行他的乌托邦实验,而不顾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做法,势必会影响南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发展只有拥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才能获得各种文化和精神,才能持续、快速地发展。比如就是汇集了世界各国、各肤色人种的智慧,才变得如此强大,如此充满活力,中国的上海亦是如此”(16)。
把南通与一江之隔的上海相比,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作为人工与理性的辉煌成果,南通城市形态的最大优点是秩序井然。这是张謇地方自治理念在城市规划上的感性体现,其特点有二:一是在城市空间上强调统筹规划;二是把城市看作相对封闭的社会系统,要求实业、教育、慈善等协调发展(17)。但反过来说,对均衡与协调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城市结构的封闭,因而张謇的南通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型城市,从未真正具备过现代大都市的开放性与竞争力,尽管其中包含有发达的现代工业和以新型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与之相比,上海现代城市形态主要是自然演化、无序竞争和各种势力相互比拼的结果,尽管其空间形态的混乱与无序使人深感厌恶,但由于在最根本处暗合了“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有益于人力资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源的高度集聚与优化配置,因而在开埠以后迅速发展为远东第一大都市(18)。而拥有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并一度成为联系上海、苏北航运枢纽的南通,则由于城市形态本身的约束与局限,抬升了竞争与发展的成本,因而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在中国现代城市前沿中很快失踪了。
三
除了城市形态,还有文化问题。与“宁静如太古”或“亘古不变”的大自然与乡村相比,城市社会如同“一口煮开的大锅”,高度异质化的人口与文化、滚滚而来的财富与机遇,包括在高速聚集中产生的激烈碰撞及由此裂变出的冲动、激情与创造力,是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此而言,张謇努力建设的南通,尽管在文明形态、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上水平很高,但由于建立在对现代文明感性需要与冲动压抑与限制的基础上,因而既无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同时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质,这是南通只能在群雄逐鹿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黯然退场的另一重要原因。
首先,这可以从南通城市社会的异质化程度来了解。异质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在古希腊时代已如此,如芒福德曾指出:“陌生人、外来者、流浪汉、商人、逃难者、奴隶,是的,甚至是入侵之敌,在城市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曾有过特殊贡献。”(19)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更是如此,每一个成功的大都市,其基本特征都是杂乱无章甚至是人无法忍受的。以洛杉矶为例,“在洛杉矶,人们不仅可以找到硅谷高技术的工业综合企业和休斯敦不稳定的阳光地带经济,而且还可以看到锈迹斑斑的底特律或克利夫兰影响深远的工业衰微和彻底失败的城市相近地区……洛杉矶如此逼真地展现出各种城市重构过程的这种结合性组装和衔接,或许没有任何其他的城市区域可与之匹敌。”(20)尽管在学习西方技术、开办工厂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张謇都是积极开放并领时代风气的,但在对现代城市社会的理解与建设上,这位晚清状元又表现出相当保守和封闭的另一面,如“为防止地方利益和资金的外流,他甚至反对外地人在南通‘谋利’”(21)。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却直接降低了城市社会的开放度和异质化水平,其后果一是影响了南通对更多资源与更优秀人力的吸引力,二是在很大程度上也严重束缚了城市的竞争力与发展活力。与上海相比,南通这一弱点十分明显。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高度异质化社会,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地方政府,也包括青红帮和其他社会组织,谁也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就决定上海的命运。尽管这给人的感觉是“世丧道也”,但由于只有这样才能为“乱世英雄起四方”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激烈而残酷的自然竞争与野蛮比拼,既有助于资本与资源的迅速集聚,又能培养城市居民处理复杂问题与局面的头脑和生存竞争能力,因而不是井然有序的南通,相反却是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才是一个现代大都市最好的摇篮。正如1904年有人在蔡元培主编的《警钟日报》上发表文章评价上海:“腐朽所蒸,香草怒生焉,艰危交逼,人才崛起焉。”(22)而南通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最终被淘汰出局,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它作为古典城市的宿命。
其次,再从南通城市文化的多样性角度来了解。与都市社会的异质化相一致,都市文化的多样性是现代大都市的另一基本条件。南通城市文化主要是以张謇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文化与墨家的实用理性。前者最看重的是君子对大众的教化,这集中体现在张謇对教育的重视上。在《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上,他曾这样慷慨陈辞:“须知张謇若不为地方自治,不为教育慈善公益,即专制朝廷之高位重禄,且不足动我,而顾腐心下气为人牛马耶?又须知二十余年自己所得之公费红奖,大都用于教育慈善公益,有表可按,未一累股东,而慷他人之概也。”(23)而张謇对墨家实用主义的推行,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上。张謇一生节俭,认为这是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他的衣服一定穿坏了才换新的,每顿饭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殊客人不加菜。他常说:“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须节省。”(24)在“文革”期间,南通市造反派以为张謇墓中会藏有大量金银财宝,曾以“破四旧”之名掘开张謇墓穴,其中仅有礼帽一顶,眼镜一付,折扇一柄,另有一对金属小盒,内装墓主的胎发和牙齿(25)。中国传统文化以主体作为社会生产的核心,既以礼乐教化培养了良好的社会生态,又有效地减少了奢侈消费对资源的恶性损耗,可以维护人类的长远目的与根本利益。这是它好的一面。但由于“利害相生”的原理,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其相当浓郁和普遍的“逆城市化”思想,又与现代城市发展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张謇本人就很明显,一方面,他是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典范,并以现代工商业、交通和社会公共事业(如电话公司、电灯照明等)极大地推进了南通的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特别是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罪恶与道德败坏,他更希望运用传统文化把南通建设成现代世界的理想国。和以“十里洋场”为象征的海派文化相比,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生活方式,在南通就受到严重的抵制而很难扎根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文化积淀的深厚与张謇本人的文化价值谱系,在当时就已成为南通向现代大都市发展的沉重负担。这是个人与历史最深的悲剧。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市”,由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其在繁荣的同时就为衰亡埋下了伏笔。尽管这其中一定有后人无法了解的苦衷,但无论如何,传统文化负担过于沉重的南通,在其鼎盛的同时就已丧失了成为现代大都市的最佳机遇。尽管这属于历史的必然性,但也为中国现代城市化积累了一笔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研究和悉心领会的。
注释
①《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608页。
②凌振荣:《论张謇的建城思想》,《东南文化》2004年第2期。
③④⑥陈金屏:《近代南通城市的历史演进》,《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⑤⑧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张謇所创办事业概览》,2000年5月。
⑦转引自崔之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⑨梁炳泉:《南通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⑩吴良镛:《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城市规划》2003年第7期。
(11)凌振荣:《南通近代建筑的形成和城市规划》,《南通文化(“第一城”特刊)》2003年(总第14期),第29页。
(12)(14)霍华德:《城市社会学》,康少邦、张宁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第206页。
(13)(23)张謇:《张謇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6-117页。
(15)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页。
(16)刘远柱:《张謇及其南通现代化模式的失败原因》,《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7)于海漪:《南通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历史研究系列之四:张謇及其城市规划思想》,《华中建筑》2005年第4期。
(18)刘士林:《浦东开发与上海的再都市化》,《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9)刘易斯·芒福德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03-104页。
(20)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2-293页。
(21)大生系统企业史编写组:《大生系统企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8页。
(22)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24)石静:《张謇和张孝若的父子情》,《民国春秋》2000年第4期。
(25)陈漱渝:《张謇生前身后事》,《寻根》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梅莉
2010-03-14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899);上海交通大学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A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