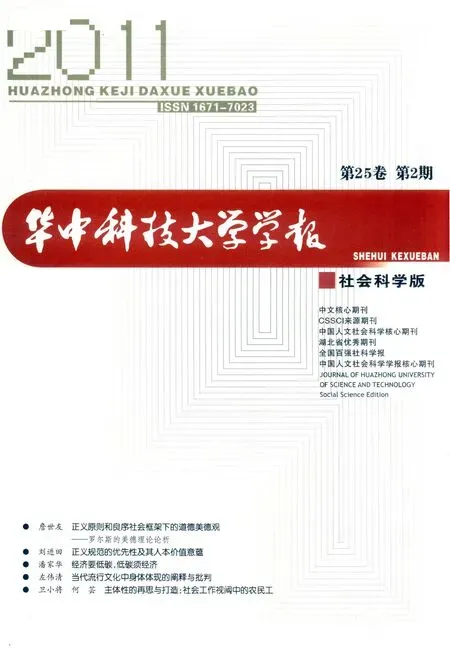民主法治国视野下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
——哈贝马斯商谈模式之程序建构路向的再思考
肖小芳,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民主法治国视野下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
——哈贝马斯商谈模式之程序建构路向的再思考
肖小芳,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哈贝马斯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集中阐释其交往维度与程序维度。在他看来,法律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本身,也不是来源于道德,而是直接来源于商谈的民主程序。哈贝马斯模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可接受性,我们可以尝试性地从一些修正方案中汲取“养分”,充分吸收哈特模式与德沃金模式的合理内核,从而使之更臻完善。
合法律性;合道德性;正当性;商谈的民主程序
一、商谈论视野中的程序论证模式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法律实证主义者不能解释正当性如何来源于纯粹的合法律性。就哈特而言,作为效力判准的承认规则本身缺乏合理的商谈验证,形式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需要考量。因此,哈贝马斯主张,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对于自然法学派而言,实证法的正当性直接源自一种更为高级的道德法,这样,法律隶属于道德。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后俗成的道德与法律从混合走向分离,它们是并列的、同源的,在作用方式、调节范围及规范有效性基础方面存在着差异,商谈原则分化为道德原则与民主原则更彰显它们的区别。于是,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法的道德论证是不可能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也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只有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证明水平合理论证法律的正当性,才能期盼公民尊崇法律。他断言,“对于现代的正当化问题而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证明水平已成为反身性的。证明的程序和假设前提本身就是正当化之有效性立于其上的正当性基础。一种认同的理念,即在作为自由的、平等的全体涉及者中间产生的认同,它决定着现代正当性的程序类型”[1]185。最终,哈贝马斯遵循从功能和规范层面进而深入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的理路,试图重新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复杂关系,诉诸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商谈的民主程序来论证正当之法如何产生及如何运用,在“民主法治国”框架内探讨基于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法律获得充分的规范意义,既不是通过其形式本身,也不是通过先天地既与的道德内容,而是通过立法的程序,正是这种程序产生了正当性。”[2]167商谈的民主程序成为法律正当性的唯一来源,商谈和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由法律来调控。一旦在法律上被建制化,商谈原则(D)就被转化为民主原则。D的最终表述有一种纯粹程序的意蕴,因为它并不关涉行动规范应该满足的其它条件,仅关涉行动规范是合理商谈的结果。只有商谈的理想的程序性条件得到满足,相关商谈参与者在经过理性论辩后才能确保商谈的结果具备合理可接受性。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程序是“指向意见和意志形成的、可以争辩法律内容之合道德性的‘无主体’的商谈程序”[3]17,他主张通过商谈或论辩来论证法律的正当性(规范有效性)。主体间遵循商谈的基本规则和程序规则,经自由、平等、充分、开放及持久的合理商谈,达成合理共识,因此,作为合理商谈之产物的法律理应是民主的,商谈过程是一种论证行动。在商谈的民主程序之中,公民的交往权力和政治参与权的运用与行使至关重要,法律的承受者同时作为法律的创制者。商谈的民主程序承担着全部的正当化重负,法律正当性来源于此程序。“民主程序确保合理结果的期待”[4]510,使得问题和提议、信息和理由之自由浮动成为可能,确保正式的公共领域之中的政治意志形成和非正式的自主公共领域之中的政治意志形成具有一种商谈的性质,并建立在这样一个可错主义的假设之上,即来源于适当的、合理的程序的结果几乎是具有合理可接受性的。因此,它本身是正当的,“仅仅从公民就为了他们的共同生活的规则达成一种理解的这种过程中获得其正当化力量”[5]36。在哈贝马斯视野中,本身具有正当性的商谈民主程序使法律正当化,正当之法与民主原则之间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们同源构成。同时,哈贝马斯又重视法律的道德维度,主张法律商谈加入了道德商谈的环节,道德通过正当程序可渗入商谈性立法和司法中。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现代法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正当化基础,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系统调节作用,依据交往理性来规整我们的行动和社会生活,实现人类解放的宏伟蓝图。因此,他遵循商谈程序的论证路向来解决“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之悖论。在哈贝马斯视野中,法律的正当性取决于所有相关商谈者基于相互理解之上的认可,主体间的自愿认可为法律正当化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商谈的民主程序之中,正当之法的产生与论证最终根植于公民的交往权力或交往理性的运用,公民的自主性与法律的正当性相互参照。哈贝马斯探究“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如何可能,其理论旨趣在于构建“民主法治国”(包括四个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保护的原则;行政部门必须服从法规、必须接受司法和议会对行政的监督;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原则),其中,法律与政治权力具有构成性关系,政治权力区分为交往权力和行政权力。交往权力具有立法的作用,立法依赖于这种交往权力的产生。民主地产生的交往权力通过正当地制定的法律转变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只有通过具有正当性的法律才能获得其约束力。法律是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的中介,既是行政权力的工具,也限制行政权力的运用。正当之法能够防止权力机构的“自我编程”,通过正当的行政权力获得制度性的支持,从而实现良性循环。经过法律建制化,货币与权力媒介都扎根于通过交往行动而得到社会性整合的生活世界秩序之中。以这种方式,现代法同社会整合的三种资源即团结、货币与权力链接起来了。通过它要求公民共同运用其交往自由的自决实践,法律归根结底从社会团结的源泉中获得了其社会整合力量。
二、程序论证模式的积极价值
从上述的论证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商谈论视野中的论证方案开拓了人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的新视野,更具吸引力和可接受性。
第一,哈贝马斯从立法和司法之程序性要求来寻求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深入考究法律正当性的理性基础,集中阐释法律正当性的交往维度和程序维度,继续考究商谈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并基于权利的双重性解读权利与法律正当性之相互参照的内在关联,澄清了“合法律性的正当性”这一悖论的循环性。
哈贝马斯充分认识到合法律性与正当性之间的张力,以程序主义途径重建法律正当性。商谈的民主程序本身是正当的,“民主程序应该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依据”[6]151。这样,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才有可能。“合法律性能够正当化法律,这是建立在商谈原则之上的。商谈原则要求受一个法律规范影响的所有相关者自愿的、主体间的认同该规范,这种自愿的、主体间的认同为其正当化提供了一个基础”[7]481。法律商谈将特定共同体中的所有的相关商谈者都纳入其内,商谈的民主程序不同于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形式程序,因为此程序本身是正当的,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平等性、透明性、公开性、公正性和民主性,其核心是把合理商谈的普遍语用学条件和交往的预设前提(如普遍的进入、平等的参与权利、机会的平等、以达成理解为取向、免于结构性的强制等)加以制度化。“民主程序通过运用各种交往形式而在商谈和谈判过程中被建制化,而那些交往形式则许诺所有按照该程序而得到的结果是合理的”[2]377。法律正当性也就是“理想的言说情境”下的合理可接受性,正当之法需接受交往理性的验证,它最终来源于公民的交往权力,这种交往权力与一种自由、平等、无主体、无强制的公共商谈理念密切相关,是一种源于公共自主的行使的权力,法律以作为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之中介的方式获得其权威性。哈贝马斯着重从理论上来描述理性法律商谈必须要满足的论证程序和假设性前提条件,因此,其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建构一个基础,用于对法律程序的合理性作理性分析这样一个事实”[8]71,它能够为观照现实的法律实践活动及探求正当的立法和司法判决提供一个理想化的指南和理性的可参照视域。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来源于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之悖论“必须通过确保公民政治自主之行使的权利得以解释”[6]83。哈贝马斯试图借助权利或自主观念来消除合法律性与正当性之间的隔阂,故他开宗明义地强调权利与正当之法的同源性。他主张,权利具有双重性(具有道德内涵,具有法律上的来源)和主体间特征(权利是关系,只能通过主体间相互承认和相互赋予),人权与人民主权同源共生。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有效行使须以私人自主为前提,人权提供了道德上中立的行为领域,确保人民主权以人权为前提。人权也必须通过人民主权之行使而创设的客观法来确立和捍卫。法律是作为确保人权与人民主权同时实现的工具而获得其正当性的。正当性根植于自主,即公民的普遍的合理自我立法。这种意义上的正当之法具备理性的基础,是立足于后俗成之论证阶段、依据程序类型合理论证的产物,是作为法律创制者的承受者之共同意志的体现。因此,公民有服从正当之法的道德义务和自愿认可的正当“理由”,他们出于共同接受的同一理由之上的合理共识自愿认可该法律的应有权威,法律的“合理可接受性”是基于“好理由”之上的“接受”,建基于论据的认知力量之上的合理共识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
第二,哈贝马斯区分道德有效性与法律有效性,强调法律的正当性来源于制度化的法律程序与服从自身程序合理性的道德商谈的相互交叉,突显了法律正当性与道德的内在关联。
在哈贝马斯理论中,有效性在D、道德原则和民主原则中分别表现为合理可接受性、公正性和正当性这三种形态[9]170。D表达了具有合理可接受性的规范所要满足的条件,道德原则表达了公正的(just)或依据道德理由进行辩护的规范所要满足的条件,民主原则表达的是正当的(legitimate)法律规范所要满足的条件。(道德的)正义(justice)概念区别于正当性(legitimacy)概念,法律规范通过民主原则或借助更为宽泛的理由(道德理由、伦理-政治理由、实用理由或来源于公正的妥协程序的理由)来辩护。这样,通过区分公正性与正当性和道德原则与民主原则,哈贝马斯避开了用合道德性论证正当性的做法,用程序正当性取代了实质标准。哈贝马斯“法律的道义论观念致力于确立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补充关系,确立道德进入立法过程的方式”[10]438。对于他而言,法律对道德保持“适当的”开放,法律的正当性来源于商谈的民主程序与道德商谈的相互交叉,“法律的道德向度被用程序术语加以阐述[11]258,法律的正当性与道德或与其公正性(impartiality)休戚相关,只有法律给予与之相关的每个人同等考虑时,普遍的同意才能实现。道德在正式的有组织的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与非正式的自主公共领域的意见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作用。道德理由可以渗入整个法律体系之中。
三、对哈贝马斯程序论证模式的修缮
哈贝马斯的论证向度遭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面临着一些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就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建树性的修正方案。例如,艾里克·沃茨[12]245-278(Eric W.Orts)创立“批判合法律性”和“系统正当性”概念,旨在综合哈特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彼得·巴尔[13]72-77意欲为哈贝马斯的纯粹程序法律正当性理论增添实质性的道德标准——人权。为了使哈贝马斯模式更臻完善,我们可以充分吸收哈特和德沃金模式的合理内核,借鉴上述的一些批判性修正方案,试着从以下方面努力。
第一,运用法律商谈论论证哈特视野中的承认规则的正当性,重视修订后的这一效力判准的作用。
在哈特理论体系中,承认规则是法律规则或法律体系的效力判准。它被作为判准用于断定法律效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这就表征着它的存在并具有权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正当性”这一有效性要求只能通过“理由”来兑现,主体间没有就承认规则的效力达成商谈共识,依据这种本身的效力都没有经过论证的判准进行司法判决也就无法确保司法的合理性。因此,他强调商议民主与正当之法的同源性,其法律商谈论的特质在于为论证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程序标准,商谈就是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和司法的合理性的一种检验。泮伟江在《民主的法律实证主义》中试图将“民主”与法律实证主义对接起来。经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商议民主的论证的承认规则本身也就具有了正当性。那么,经合理商谈予以论证的承认规则能否在哈贝马斯体系中发挥作用呢?在支振锋博士看来,人们不可能具有所有专门领域的知识并参与各种创造法律的商谈,因此须借助于专家或者专门机构,承认规则的桥梁也因此仍然是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商谈,影响甚至参与承认规则的创制,并利用它来识别与认可那些超出人们知识领域之外的法律规则,从而保证这些规则能够体现他们的利益与意愿[14]99。哈贝马斯本人也承认,只有那些接受过一定教育和训练的且具备一定批判能力的公民才有能力参与面对面的商谈进而引导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诚如沃兹所言,我们可以借助程序合理性这一标准来评价现代法律制度的系统正当性程度。只有当法律制定和法律运用的合理程序与作为法律承受者和制定者之合理期待和需求以及意志和利益相联系时,承认规则才是正当的。这样一来,承认规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事实存在,而是经过合理的商谈论证的、具备有效性的规则。哈特提供了一个形式标准将具备法律效力的、事实上存在的法律规则确认或识别出来。然而,他没有论证承认规则这一操作性的鉴别标准的正当性。经商修订后的承认规则,它的特点就是能够很好地区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和没有法律效力的规则,借助这种正当的承认规则,我们也就能够有效地鉴别那些超出人们知识领域之外的、已经存在的规则是否具有法律资格。
第二,重估法律的道德基础,将商谈论证的人权作为补充性的实质标准,以弥补哈贝马斯纯粹程序法律正当性理论的不足。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现代法的经济基础和道德基础都已过时,其基础只能是来自交往行动的“团结”。他主张正当之法应与道德相一致的理念决定他最终又得把道德视为法律的基础。“现代法律的总体仍旧需要正当化,法律之所以必须接受批判,主要在揭发它具有体系的特征,也就是批判法律声称对规范的正当性具有普泛的、寰宇的效力(有效性)。而正当的诉求都是道德追求的目标,所以现代法律正当性的检讨无法与道德的论述彻底割舍。”[15]261尽管哈贝马斯主张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对道德实践商谈保持开放,正当之法须与“正义”和“团结”这两个实质的道德原则相一致,但其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试图通过纯粹程序正义来确立法律的正当性,自始自终反对将道德视为现代法的基础。“作为哈贝马斯所倡议的民主程序现实化的制度担保(‘集体自由’)狭隘地集中于程序要求,却是以牺牲某些权利与原则的实质性诉求为代价的。”[13]13哈贝马斯建构的基本权利体系也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范畴,其视阈中的道德只是程序属性的道德。然而,纯粹的程序正义并不能保证实质的正义,商谈的民主程序不能与实质内容完全分割开来。这样一来,哈贝马斯的法律正当性理论需要实质有效性标准作为补充。
笔者认为,基于以下考虑,经法律商谈论改造过的人权可以作为道德标准的最适宜候选对象,哈贝马斯应将其普遍效力经过合理的商谈论证的人权作为补充性的实质标准:其一,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正当之法是正当的商谈民主程序的产物,同时也囊括了人权这一基本要素在内。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人权的有效性反映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的成分或体现可普遍化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人权带有一种普遍有效性要求。同时,它又需借助具体情境中的法律才能获得实证的形式,法律是作为保护人权与人民主权之共同实现的工具而具有正当性的。其二,在强调人权与人民主权之同源共生、互为前提的内在关系时,哈贝马斯已不自觉地把前者置于优先地位。在他看来,人权是道德自我决定的表达,人民主权是伦理自我实现的表达,法律的道德向度和伦理向度能够统一,道德优先于伦理,正义优先于善。这样一来,相对于人民主权而言,人权处于更为根本或更为基础的地位。德沃金恰巧注重实质道德,强调认真对待权利。尊重作为一个人所必需的权利,这就是对正当程序之理念所需的道德基础的强调,更能彰显商谈的民主程序在保障所有的相关商谈参与者的道德主体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依据哈贝马斯的理论,人权的普遍有效性依赖于主体间的相互授予和普遍认可,离不开实践商谈的合理论证。由此,他实现了人权正当性的普遍论证。用巴尔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依据人权的道德要求来引导法律中的道德商谈,在人权的道德要求中我们可以找到法律正当性的基本道德标准。如此,“哈贝马斯关于法律商谈程序的合理性在对法律的理解上也便具有了义务论成分(满足利益的可普遍化要求——引者注)”。[16]200正当之法不仅满足民主程序这一标准的要求,也将满足人权这一经合理商谈论证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实质标准的要求。
第三,诉诸正义而又合作的社会,为哈贝马斯的方案营造合理的社会基础。
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相关的商谈参与者就道德问题、伦理-政治问题和实用问题达成合理共识,将那些无法通过达成共识得以解决的问题置于商谈程序调控下达成妥协,这样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他假定在一个公共领域中把贫富差距和身份差别搁置起来进行商谈是可能的,强调“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平等“是‘单纯作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础上,论证权威(较好的论据就是权威——引者注)才能要求和最终做到压倒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17]41。可是,在当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基于性别、财产、地位及种族等之上的形式上的排斥。参与机会的平等对于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它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消除系统的社会不平等。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必须精确地拥有相同的收入,但是,它要求大致的平等,这种大致的平等与系统地产生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不一致”,“政治民主需要实质的社会平等”[18]121。要想公民有效的、平等的参与到民主的立法和司法中,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哈贝马斯认识到,要想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之中的无主体、无限制的交往之流不被截断,这就要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民主地构成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而这种公共领域本身,则必须以一种能够使平等的公民权利具有社会效力的社会作为它的基础。只有在一种从阶级限制的躯壳中生长出来、摆脱了千百年社会分层和剥削之桎梏的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一个没有拘束的文化多元性的潜力”[2]382。哈贝马斯承认公民平等地运用其权利需要以一定的实质条件为前提。排除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释放生活世界的交往潜能,用交往权力来引导社会权力,由理据说了算,推进彼此的合理商谈和理性合作,致力于理解这一目的,修复或维护“团结”与权力及货币间的平衡关系,这样的一个“正义而又合作”的社会基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是一种最好的情形。只有在这样的理想状态下,非正式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得以进行的未受扭曲的交往形式才有可能,这种交往形式能同时确保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之形成条件,因而与这种交往形式相关联的正当之法才有可能。同时,“只有参与者都恰巧把‘理性合作’视为是一种‘好的’、较其它互动形式更为可取的方式时,他们才会被充分地激发去不厌其烦地进入达成一种理解的商谈过程”[11]414。哈贝马斯心照不宣地寄希望于一个“正义”而又“合作”的社会,预设了相关的商谈参与者具备一定的理性商谈的能力,且愿意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商谈方式解决问题,以较好的论据为基准,达成合理共识。商谈参与者采取施为性态度,这就暗含着自由与平等个体的相互承认,也蕴含着包容他者的义务及团结的概念。
概言之,上述的修缮方案对于克服哈贝马斯模式面临的困境而言不无裨益,哈特视野中的承认规则予以合理商谈论证后,能够作为对哈贝马斯法律正当性理论的一种补充,将德沃金意义上的人权这一实质性的道德标准予以商谈论证后,可以引入哈贝马斯的纯粹程序法律正当性理论之中,诉诸一个正义而又合作的社会,则能够为哈贝马斯视阈中的法律商谈营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基础。
[1]Jürgen Habermas.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79.
[2]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比)范·胡克:《法律的沟通之维》,孙国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4]Christopher F.Zurn.“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Law and Philosophy,2002,21.
[5]James L.Marsh.Unjust Legality:A Critical of Habermas’s Philosophy of Law.Rown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1.
[6]Jü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6.
[7]Mark Modak-Truran.Habermas’s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Religion.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1997.
[8](荷)伊芙琳·T·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张其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9]Cristina Lafont.Procedural Justice.“Implications of the Rawls-Habermas Debate for Discourse Ethics”.Philosophy&Social Criticism,2003,Vol.29.No.2.
[10]Jeffrey Flynn.Habermas on Human Rights:“Law,Morality,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Jul.2003,Vol.29.No.3.
[11]Michel Rosenfeld and Andrew Arato(eds).Habermason Law and Democracy:Critical Exchang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2]Eric W.Orts.“Positive Law and Systemic Legitimacy: A Comment on Hart and Habermas.Ratio Juris,1993,Vol.6.Issue.3.
[13]Mathieu Delflem(ed.).Habermas,Modernity and Law.London;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6.
[14]支振锋:《哈特法律规则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7年。
[15]高鸿钧、马剑银:《社会理论之法:解读与评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刘建成:《第三种模式: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Craig Calhoun.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2.
责任编辑 吴兰丽
“The Legitimacy of Legality”under Law and Democracy——Rethinking Habermas's Procedural Constructive Approach of the Discursive Model
XIAO Xiao-fa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Habermas abides by the procedural approach of the discursive model to reconstruct law's legitimacy and interprets intensively the communicative and procedural dimensions of the law's legitimacy.In his view,the legitimacy of law neither originates from law itself nor morality,but rather originates directly from the discursively democratic procedure.Habermas's model has certain attractiveness and acceptability.We can draw“nutrients”from some modification schemes and absorb the rational cruxes of Hart's and Dworkin's model adequately,so as to make it perfect.
legality;morality;legitimacy;discursively democratic procedure
肖小芳(1980-),女,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YJC720050);2009年度浙江师范大学科研项目(SKQN200904)
2010-10-20
D0-02
A
1671-7023(2011)02-00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