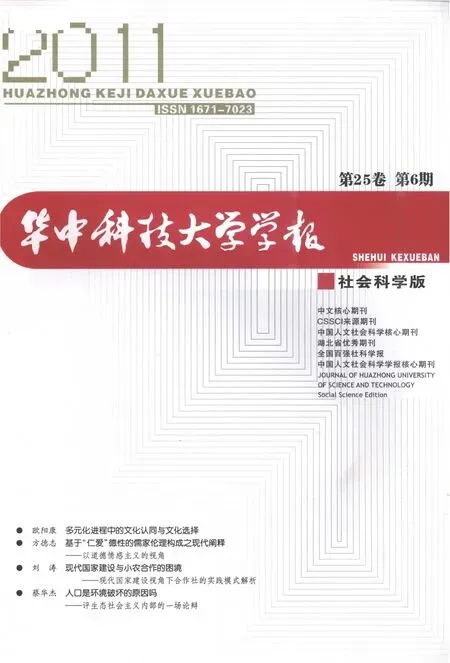基于“仁爱”德性的儒家伦理构成之现代阐释——以道德情感主义的视角
方德志,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基于“仁爱”德性的儒家伦理构成之现代阐释
——以道德情感主义的视角
方德志,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仁爱德性,作为一种好的行为动因和心理特质,是源于自然之“生生动力”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人之优秀的“品质结晶”,构成了儒家伦理的立论根基。基于仁爱德性的儒家伦理,根据体验论建制下的“天人同一”境界,旨在阐发和追求一种道德行为者本人与“他者”内在依存的、情感的人道主义生活理想。
儒家;仁爱;德性伦理;道德情感主义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复兴思潮正值“余音绕梁”,但德性伦理不是某一种文化语境下的“发明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原始遗产”。仁爱,作为人的一种道德行为动因或道德潜能,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构成的基础性概念,它旨在描述一种根据人之“此在”的“未完成状态”之生命的体验境界和开拓过程来筹划一种与“他者”内在相关的人际理想,呼应了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的情感主义一支。本文从道德情感主义的理论视角,通过“德性论”理解“仁爱”概念,试图对基于仁爱德性的儒家伦理之构成体系做一个“有机”的现代诠释,以期儒家伦理能以其自身的“德性论”语境来“言说”现代诸多伦理话题。
一、儒家的仁爱德性——自然生生力量的自我觉知
儒家伦理思想的创立者是孔子。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所言,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中的角色地位类似于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角色地位[1]48,49人类早期的哲学问题在他们那里都实现了一种属人的、伦理学的转向。前者把此前的天道(天命)论内化为一种属人的道德心理学知识,把“天道”内化为“仁道”,开创了一个能够集中表征中国文化特质的儒家仁学思想流派,后者则把此前的(自然)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内化为人的灵魂学说,以“聆听灵异之音”和“美德即知识”之命题定型了西方文化之道德认识论的特质。
孔子把“天道”内化为“仁道”,那么仁道必然承继了天道的精神。天道就是自然/本性之道,就是生生之道,那么仁道也必然承继了这种生生之道。进一步来说,天道在于生生不息,那么仁道也必然是生生不息。所以,在孔子这里,“仁”就是自然之“生生力量/能力”在人“心中”的一种“具体内化”,这就意味着“仁”是个动词,“仁”即是“生生动力”。正因如此,后来宋明理学家周敦颐把“仁”直接解释为“生”,朱熹则以春季万物复苏之态来表征“仁”之生命惊动,认为“生底意思是仁……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2]107,就“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2]113宋明理学家把孔子的“仁”追溯为生命之源,应该说这是符合“仁”的源始含义的。“仁”首先是“生(人)”,其次才是“爱人”。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即说明了“仁”道与“生”同在。
在孔子这里,“仁”与“爱”又是分不开的,所以樊迟问“仁”时,孔子曰“爱人”。从一般的自然性命来说,“仁”仅仅是一种生生秉性,有“仁”并不意味必然有“爱”。正如宋明理学家所言,万物与人都分有“一体之仁”。就此而言,“仁”也仅仅是一种生命活力动因而已。但是,在人这里,“仁”生成了对“仁”的自我意识,这就是“(仁)爱”。(仁)爱作为仁的一种“自我意识”,是对仁的一种留意,对仁的留意也就是对自然之“生生”的一种自我觉知。由“仁”生成“(仁)爱”,生命的创造从此就不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人成了自然性命中的唯一觉悟者和守护者,所以人不仅爱人,还能爱物。那么,“仁爱”,作为一种行为动因和德性潜能,就是指人的大德性或那种向善的生命动力,它内在地驱动着人能“由人及物”地泛爱开来,从中展现出人对自然之生生动力的一种饱涵和呵护。西方近代的道德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理论也是从一般的生命感知能力(sense①据此,笔者也将以英文“sense”来对译儒家之“仁”,以“sense-love”对译儒家之“仁爱”,以及后文也以“sense-beautify”来对译“仁美”,它们都是作为动词使用,旨在展现一般生命的敏感程度和明觉状态。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一般用“humanity”、“co-human”、“benevolence”等对译儒家的“仁(爱)”。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对译只是一种伦理学上的“对接”,并没有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对接”,揭示不了宋明新“仁”(儒)学的哲学意蕴。当然,我们以“sense”对译“仁”主要是基于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用法,而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用法,后者只是以前者为基础。“sense”一词来自于中世纪拉丁语“sensus”,表示感觉的层次,与古高地德语的“起程”或“旅行”意同。)发展而来的,它源于人这个敏感(sensitive)的生物对诸自然性命/众生(sentient beings)之鲜活的存在(well-being)有一种特别的敏锐性或敏感性。人一旦失去了这种敏感性,就会变得“麻木不仁”,由此那种反映关切他人之生命遭受状况的道德礼制也就会变为一种外在之物和强制规则。
孔子之后,孟子立志于孔子“仁”学的系统化建构,他援引自然的生生之“仁”入住于人的“良心”之中,以“心学”阐发“仁学”,创立了“天人合一”的生命互动机制。因此在孟子这里,人之为人的标志就是人能施“仁爱”德性(“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爱”作为一种关切生命的道德动因,积淀和凝聚了自然生生之仁的动力源泉和机理,潜藏于人的“良心(灵魂)”之中,它驱动着人去爱人惜物,去行“仁”道。人实施仁爱的过程,就是“良心”开始变得生动敏感和呈明的过程,就是其觉知自然之生生之仁的过程。故人能够做到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反向推之则不成立。“爱物,仁民,不亲”,“非仁也”。人连自己的亲近之人都不亲爱,何谈去亲爱其他人,即使有,也是私爱,不是“仁爱”;人连自己的亲近同胞都不爱,何谈爱物,即使有,也是私爱,不是“仁爱”。
孟子的“仁爱之心”经过佛老学理的穿梭洗练,在宋明新儒学那里已经变得“晶莹剔透”、“异常灵敏”,它已经超越了狭义的人际伦理范围,进入了天人同一的体验境界。在二程、朱熹那里,“仁”即为“天理”本体,人与万物“分有”了同一个“仁”(“一月印万川之月”),连石头树木都有“仁”。到陆象山、王阳明那里,“天理”回到了“心中”。“本心即理”,发明本心即呈天理。在王阳明看来,仁者具有“一体之仁”,人有虚灵不昧的仁爱之心,故能与鸟兽、草木、瓦石同为一体,不管是有知觉的动物、有生命的植物,还是如瓦石之类无生命的物体,当它们受到损害或破坏时,都会触动人的“仁爱之心”。人之所以对万物(甚至雨露飞尘)都心怀怜恤,这是因为通过深度的生命体验和历史洗炼,人之仁爱之心的生命节奏与诸自然性命的生命节奏已经走向了内在同一,开始觉悟到“仁”的“生生”本性。
仁学发展到了明末清初,随着主体性个体意识的增强,基于仁爱的礼制道德逐渐成了“杀人”的工具(“以理/礼杀人”)。历史学家会认为,“以理/礼杀人”是因为外在的封建专制加剧了,这只说对了一半。其实,从哲学概念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礼”还是那个“礼”,没有变,此时它之所以变成了“杀人”的礼,是因为那颗“仁爱之心”已经历炼得太敏锐了,太敏感。“纸包不住火”,那颗仁爱之心已经容不下家族宗法制语境下的礼制形式了,它已经觉悟到了普遍的爱人(类)意识。“仁者爱人,不爱礼制”。李贽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和曹雪芹以贾宝玉为代言传达的男女平等观念,以及黄宗羲提出早期民主宪政思想,等等,即是“仁爱之心”走向“民主/民生化”的一种“启蒙”写照。民主/民生意识原本就源自对一切人的生命以同等关怀,源自对生命深度的爱。这就要求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当做生命来对待。男女之所以不平等(男尊女卑),就是因为在父权家长制社会没有以同等生命来看待女性。没有对人之生命的深度的爱和深度的关怀,就没有实质的民主/民生意识。中国哲学史家萧箑父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历程原本也可以走出一条自身的启蒙之路,只是在明末至清,这种启蒙思想的萌芽遭到外在原因(外族和列强)的遏止,导致中国早期启蒙筹划的流产和夭折[3]11-36,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然,“启蒙”只相当于个体仁爱之心的觉知阶段(意味着仁爱之心从“抽象的普遍”回到了“生动的具体”),它需要通过“力行”来“见知”。觉知是难的,力行见知更难。仁爱的“力行”分为手段和尺度。合理性主义者认为“恶是社会的动力”,因为它合某种外在“绝对精神”的目的,人道的情感主义者会认为,善更是社会的动力,因为它是人之仁爱的外化手段(关于仁爱的外化手段这里暂不讨论)。仁爱的“力行”尺度即为“中庸之道”,它分为形而上层面的理解和人际伦理层面的理解。
二、儒家仁爱的实践尺度——中庸之道
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儒家的中庸之道是指一般自然性命的运行机理,“过”或“不及”都可能导致自然性命的衰竭或殒灭,所以《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即指符合生命生成的“中位”,诸生命只有“切中”自然性命的运行机理,才能成为生生之仁的据拥者,从而达成“和”的状态。“和”的状态也即自然生生之仁的外在“繁荣”和“优秀”状态。据此而言,《中庸》一书即是对孔子“仁”道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挺进和开拓,它把孔子基于日常生活的“中庸”方法上升到自然性命运行机理的高度,从而可与易经和道家的“道”论通约。
孔子在谈中庸时并没有诉诸于这种形而上的性命机理的追述,而是仅仅聚焦于人的日常行为的扼守“中道”。孔子之所以提倡人要中道的行为,其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复兴周礼,只有恢复礼制,人伦常态的生活世界才有望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标准至精至微,这套“心法”遗忘已久了。在孔子看来,狂狷之士虽各自道德高标,但行为都不切合中道,或过之或不及,因而必然违背常礼,不利于人伦常态的运行。孔子则把“允厥执中”(“道心”法则)直接内化为人心的“中庸”法则,以为礼制的恢复找到一种内在的心理尺度。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行为都能扼守中道,那么我们就不会违背常礼。当然,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其实质是指合情理的“仁(爱)”行为,中庸之道如果偏离了仁爱,就失去了“(仁)道”的意义。孔子反对那种貌似中道的“乡愿”行为。“乡愿”行为是仁爱德性泯灭、坏死的象征,产生的是一种道德(能力)假象。所以,孔子批判“乡愿”为“德之贼也”。这是价值立场和道德标准出了问题。
中庸之道作为“仁(爱)”的力行尺度和实践标准,也即意味着“仁爱”这种道德动因只有通达中庸才能完成它的“爱人”使命。人有一颗仁爱之心,那种“仁爱”潜在动因要投放出来,那么如何投放,这就需要思量考虑,它需要在它投放的诸对象之间寻求某种平衡,防止过犹不及。这就像一位家长关心自己的两个孩子一样,他对他们的仁爱之分配程度应该要达到某种平衡,否则的话,“良心”不会同意,会认为他不会运用“仁”道。同样,一个人在对待疏远之人和“泛爱众”的过程中,在他们之间也必须要适度地分配“仁爱”的分量,防止过犹不及。这即是一种“守中”行为,它是通过内心的“反思平衡”而达到一种恰当的“公正”行为。就此意义上说,“中庸”就是指人们在其生命实践中所达成的“适度”标准。“中”即“适时适地”意义上的“切中”和“适度”,它包括时间和空间的一同到场,造成一种好的/善的性命效果(“和”),故“中”既指空间方位上的“中位”,也指时间方位上的“中位”(“时中”)。
因此,在儒家这里,一个人要行仁爱之道,“踩觉”中庸是相当难的,他/她必须具备一种生命智慧和实践之真,使得“悟道”与“行道”同一。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被塑造出来的,他/她是在行“仁”道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这就离不开与他人的照面,与他人的“仁”发生互动。奉养父母不是给吃给喝就可以了,抚养孩子也不是用来随便处置就可以了,他们都是人,都有人/仁格,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他们的“仁”会起反应,会体验不到做“仁”的尊严和信心。或许正因为仁道难行,孔子认为自己一生中只有几次践履中庸。《中庸》里记载孔子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由此看来,“踩觉”中庸之道是何等之难。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伦理德性的时候,也讲到中道原则,他的中道与孔子的中道在机理上是相同的,都是指人在生活习惯中逐渐形成对生命机理的内在“切中”。不同的是,亚氏是在一种基于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语境下(即实践智慧,现在一般理解为实践理性)来描述人对生命机理的内在把握,他描述的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合理性的独立完满的“自我”所践行的中道原则,而孔子是在一个基于情感体悟的人道主义语境下来描述人对生命机理的内在把握,他描述的是一个非生物学的、与“他者”紧密相关的“自我”所践行的中道原则。王岳川先生说,“孔子‘中庸’的‘中’有很浓的人性仁爱意味……而亚里士多德‘中道’的‘中’表达出西方哲学智慧知性的对象化特征”[4]62,其实就是指中西中庸之道的文化语境不同,前者践行的是逻各斯/理性的中道(“适度”),后者践行的是仁爱的中道(“适度”),两者都是生命智慧的达“道”象征。
孔子践仁的中庸之道经过子思《中庸》形而上的拔高之后,中庸之道逐渐成了个人生命节奏与自然(天)性命节奏之间的对接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孔子提倡中庸之道的生活常用语境。孔子的中庸之道实质上暗示了“仁(爱)”在生活世界中的践行之难,暗示了我们要在人的生活世界中“适时适地”地投放一个人的“仁爱”,从而成就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仁人”。因此,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心法”,它不是一个精确的度量,而是通过一种内心反思的平衡从而达到仁爱的“适度”投放,而这个“适度”又必须伴随着投放者生命节奏的成长而逐渐变得“精确”和“适中”,故它是生命智慧,是仁爱之道。总之,在狭义的伦理学语境中,中庸——作为“仁爱”的力行尺度,其价值立场是“仁爱”,目的是“爱人”,效果是“与他者共生”,它与那种德性坏死、丧失“仁爱”立场的“乡愿”行为是有质的差别的。
三、儒家仁爱的社会化表象形式——家-国同构的“仁政”
传统的儒家“仁政”理念,作为人之“仁爱”动因的开发程度之社会化表征,是通过家-国同构的实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兼备了古代男权社会家长制和(圣)贤人政治的双重色彩。根据这种仁政理念,由于家、国结构是同一的,家庭伦理和公共政治秩序也必然是同一的,家庭伦理就是政治秩序,它们都可以看做是“仁爱”动因的外化形式。但是,家庭单位与国家实体之间在性质上毕竟是不同的,因为由各种血缘亲情集合的家庭之间在“自然倾向”上是相互排斥的。这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氏族)/家族出来组织政治,这就产生了家族政治,与这种家族政治相配套的是推广一种家长制的、圣贤明君式的“仁政”。随之,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就完全由圣贤明君这个人的“仁爱”的开发程度和推广程度来决定。相对于一个人的“仁爱之政”来说,是对大多数人的礼乐“教化”。“教化”的目的不是激活民众的“仁爱之心”,不是让他们都觉悟起来,直接感知做仁/人的资格和尊严,而是让他们学习和顺从既定的“礼制”,于是贤人政治就蜕变成了一种家长制下的“替代成功综合症(substitute success syndrome)”。因此,传统的儒家“仁政”是建立在一种一个人或少数人“觉悟”而大多数人“无知”的、“内圣外王”的贤人政治基础之上的。例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和“道之以德”(《论语·为政第二》),就是指“一个”合格的为政者要能够推行仁道,要能够以身作则,以自己至高的德性来配得至高的“职位”,从而为那些“无知”和“下愚”的人们垂范行为。在孟子看来,人人都有一颗先验的仁爱之心,那么君主可以照此来推行仁爱之政,就可以达到贤人政治的目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篇上》)这里的“先王”就是指“尧、舜、禹”这样的圣贤明君。
但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孔孟时代并不是圣贤明君的时代,而是家族僭主政治的时代,它只适合传统圣贤明君政治的变体(衰变)形式。两种政体的性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是为了僭主本人及其家族集团的利益,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是充当前者的手段,后者主要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照顾君主本人的利益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前者。因此,孔孟所提倡的“仁政”理念并不合时宜,他们指望通过标榜贤人政治和礼乐教化来体恤民众,试图以一个人的“仁爱之政”作为家、国贯通之系,从而使得家-国变成一个大写的“仁”字,这种美好愿望最终只能充当僭主政治“假仁政,行霸道”的手段而已。
其实,孔孟所设想的由一位“内圣外王”的“仁者”来推行“仁政”,使得家-国变成一个大写的“人(仁)”字,与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所设想的由哲学王来管理城邦,使得城邦变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二者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古代家长制下贤人政治理想的表现。在《国家篇》中,柏拉图为了勾画一个德性完满(即正义)之人的肖像而用国家各阶层之间的协调运作来做类比。国家各阶层之间的协调运作象征着一个人灵魂之理性(逻各斯)部分与非理性(反逻各斯)部分之间的协调运作。一个德性完满之人即是通过逻各斯(智慧)的绝对控制,使反逻各斯部分生成“勇敢”和“节制”的德性,从而使得灵魂实现其和谐的“正义”表象。哲学家是智慧的代表,是德性完满的象征,那么反推回来,哲学家应该当一国之君(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理解了,把理想国当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字,其实本来的思路是:“人”是一个“小写”的理想国)。但是,柏拉图基于哲学王的城邦政体设计,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亚氏看来,柏拉图的那种贤人政治理想只存在更久远的时代,它不仅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而且其国家阶层关系和社会角色的“硬性”规定也不能现实地有效运作。根据亚氏,政治学不仅要揭示理想政体,更在于找出符合现实要求的政体形式,所以他认为政体的实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层次,但是只有在现实中能够有效运行的才是最好的政体,即使是恶的、变态的政体形式(例如,他认为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民主政体即为现实有效的政体,即使它是一种衰变的政体)。除此之外,亚氏还对人的城邦性存在身份作了结构性的改造说明,他把城邦看做是人际交往的类存在形式,所以提出了“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这个独断论命题。在亚氏这里,哲学家的本职工作在于“沉思”神性之思,城邦的事务则是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所从事的崇高职业。通过实践智慧之人的协调,城邦人际活动得以开展,而实践智慧之人的智慧也是在“实践”中炼成的,它是逻各斯经过习俗积淀的产物,并受到习惯法的制约,不能随意作为。为此,亚氏指出了人之德性潜能实现的有限性。例如,意志薄弱和运气环境等要素都决定了个人德性实现的局限。这就意味着个人要进入交往领域——城邦由此生成,与此相适应的就产生了交往中的正义问题,这个正义问题就不仅仅是柏拉图所谓的“内在”正义问题,而是走向了外部人际交往领域,与之对应的也不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政治,而是民主政治。
中国儒家自孔孟提出家长制的贤人“仁政”理念之后,并没有受到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那种强烈的学理批判,而是经过荀子“法新王”的法礼化改造,就成了以韩非为家族僭主政治制定严格等级制的一种现成模板,从此家-国概念和律法秩序成了一个人的意志体现,“仁政”也蜕变成了一个人的任性表达,社会政治状况会随时因为僭主的任性和情绪变化而发生改变。孔孟所提倡的贤人仁政理想与当时僭主政治事实之间的内在不协调运作所招致的儒家“仁爱”德性的蜕变和被反利用,也使我们试图把古代儒家所追求的家-国同构的政治化形式与作为其形成动因的仁爱德性分离开来对待。例如,当代新儒学家杜维明先生就认为“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不代表儒家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是,在我们看来,伦理学与政治学是天然一体的,儒家的人文关怀精神与它的伦理实现形式——家-国政治秩序是不能分离的,即便它被冠上了封建社会“软刀子”的罪名。假如基于伦理学的政治学都是基于人之“今生”“此岸”问题的考量,它就不应该是一种停留于内心的情发机制形式,或是一种对“来生”“彼岸”的向往意象。基于仁爱的儒家伦理必须要走向基于仁爱的儒家政治。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儒家基于家-国同构的“仁爱”政治理念进行一种结构性的改造说明,特别是在现代民主语境下尤为必要。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质也就是要从逻辑上能够说明个人(个体)为什么要走向共同体。在孔孟(以及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理想中只能通过家长制来说明,由此也产生了人之等级和层次的划分,这是排斥民主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则是以上帝的“预定和谐说”来为现实(完满的单子)个体之共同体身份做逻辑上的预设(由此形成一种以抽象的、独立完满的个人权利为表征的对立互竞的现代契约论社会)。这是背离仁爱的,因为它没有突出德性在人际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主要贡献力。笔者这里则从个体(仁爱)德性实现的欠缺性角度来说明,试图从道德情感主义立场把仁爱伦理与民主政治衔接起来。我们先假定现实的人在德性实现上是欠缺的和不足的,这就能说明现实人际关系是一种内在依存性关系,而不是一种排他性的关系,由它构成了现代人际的“商谈”“平台”。这个过程也就是:由于个体德性的欠缺性导致了家庭的产生,由于家庭成员组成的共同体之德性实现的欠缺性导致了城邦或国家的产生,由于城邦或国家之德性实现的欠缺性导致了世界政府的产生,由于人际范围内结合的共同体之德性实现的欠缺性导致了理想的神性完满人格(德性)的产生。根据这种认知逻辑,孔孟所提倡的家-国作为一个大写的“仁”字就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仁爱)德性写照,而是作为“类”德性的写照。这个“类”德性只能借助于共时的和历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德性交往才可能实现。这样的话,家-国作为一个大写的“仁”字就是一个符合现代民主语境的历史范畴。
亚里士多德在解释个体与城邦的关系时,提出了“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这个独断论命题,认为城邦性是每个个体的存在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破解了柏拉图共和国中暗含的等级设计,为西方民主政治首开先河(当然,亚氏在文本中没有具体说明个体身份是如何走向城邦身份的:个体是以抽象完满状态的、外在互竞“分权”式的、“狼与狼”的方式走向共同体的呢?还是以现实欠缺和未完成状态的、内在依存性的方式走向共同体的呢?我们这里选择后者的解释方式或许更适合时代需要,或许更能清除传统儒家“仁政”中的家长制“遗风”)。通过承认个体的欠缺性,一方面,我们就排除了把每一个“他者”抽象地看做是一种“镜像化”的对象——由此招致个体之间的分离,以及最终导致个体自身(现象的我与本体的我)的分离悖论;另一方面,它可以将现实个体之欠缺性、未完成性这一人性事实充分暴露出来,进而以之作为人际“商谈”的一般人性前提①这里的个体之欠缺性不是基督教原理中所预设的“原罪”,而是一种人性事实,人只有承认人之“此在”的欠缺性,它才能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本真状态,才能本真地体验生命、关怀生命,敬畏生命。。
当然,承认现实个体德性实现的欠缺性和有限性及其未完成状态的身份,即意味着现实个体有时可能会违背“仁爱”的行为,进而可能危害或败坏德性共同体(例如,由于个人的觉悟不够、意志薄弱、运气等情况,都可能侵害或败坏其他诸性命的存在),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基于“仁爱”的法律,即“仁法”。“仁法”的一般程序是:通过公平公正的程序选拔立法人员,组成立法机构。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必须本着以全体公民的生命福祉为立法动机,制定相关的法律,使得法律能够反映出“仁爱”动因,这就保证了司法过程有“仁法”可依,接着是司法机制的严格执法(这个过程也相当于是程序正义②当代西方著名德性伦理学迈克尔·斯洛特在《源自动机的道德》一书(在“关怀的正义”一节)中就提出了一种基于关怀动机来构建立法、司法的律法方案,以便使内在的动机转化为外在的社会律法,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关怀德性的“社会正义论”,以替代柏拉图、罗尔斯的正义设计。这里笔者综合改造了其观点。参阅Slote,Michael(2001),Morals from Motive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92-109.。除此之外,政治共同体的经济活动要以“仁爱”为导向,而不是仅仅为了人的最大化福祉需要而发展经济。这就是说,“仁爱”使得人的经济活动变成了一种有目的的、仁爱的交往活动,而不是一种以破坏自然环境和危害其他自然诸性命为代价的、无目的的技术活动。经济发展和实业成就的最高界限是使人之性命与诸自然性命都能保持生生不败,是要把自然的生生之仁内化为人的一种现实的创生活动。因此,为了生命共处,为了泛爱众,人类必须选择“节制”。“节制”即是“仁爱”的内在要求(或其派生性德性),而制定消费法和生态环保法等则是仁爱的外在强制和“仁法”的具体运用。“仁法”不仅仅是维护人的生命福祉,它的最高目标是不违背自然的生生之仁,而是接近于自然必然性的“正义”。
在儒家这里,个人欠缺性的情发机制也恰恰体现在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或同情之心。人之所以同情他者,怜悯他者,是作为个体之欠缺性的一种心理暗示,它暗示了现实的人都是欠缺的,都是未完成、不完善的,都需要他人的协助。同时,我们的同情反应或体验也是对个体之作为类存在身份的一种情感感召(因为都分有生生之“仁”)。因此,可以说人的同情反应是人之仁爱动因实现不足的一种现实呼救。通过同情体验,每一个人才会体验到各自都是以类(“仁”)为目的而存在着,而不是孤立的、排他性的圆满单子(“满街都是圣人”不是政治学的人性事实)。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即是指人的同情心是仁的一种情发机制,是“仁(爱)”动因的发端口和情感表象。通过“恻隐之心”之体验,各个个体的“仁”被召集到一起,与“类”存在联系起来,同情即是一个人的欠缺性及其类意识的一种情感表现。完满的、自足的人不会有同情心,没有同情心的不是神,或者就是物,只有欠缺的人才有敏感的同情心。总之,通过预设人之“此在”状态德性实现之欠缺性,通过“仁法”作外在保障,传统的儒家“仁政”理念就能以一种情感主义路径实现了向现代民主语境的转变,它可以媲美于西方启蒙以来基于抽象理性算计的、排他性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
当然,只有人这个生物才能意识到自身的欠缺性,只有人才有这种敏感之心,从而使得人能穿越亲近之人,推及他人,并进而推及到万物,在仁的最高境界上发现人与万物原本是“一”“类”,这就进入了儒家的“仁美(sensebeautify)之境”。
四、儒家仁爱的美之象征/表象——生命的“同一”境界
儒家的“仁美之境”,作为人的生命体验之境界,不同于基于认识论范式上的“审美”,其实质是自然生生之“仁”(即生命)的“一同”“绽出”或“一类”“到场”,是“仁”之觉知的最高层次。“仁”的觉知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感觉层次(也可以称为“仁”的无意识层次),这是一般生命迹象的标志,它是指包括人与动物、植物在内的等一切生命元素的能动性和感知性特性。其次是伦理层次,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爱”层次。正如上述,“仁爱”就是指“仁者”对“仁”的一种“自我觉察”或“自我留意”,这里的“仁者”就是特指“人”这种生物,它有某种特殊的敏感官能——“仁爱之心”。所以,“仁爱”就是指人通过对生命之境的深度体验或深度开拓而返转回来对“仁”有了一种自觉守护。在此意义上来说,人萌动“仁爱之心”就标志着自然性命的一种自我觉醒。但是,“仁爱”只是仁的伦理层次,它揭示的还是人的“类”意识阶段,还没有进入人与自然万物“一”“类”的层次,所以,人在仁爱阶段要受道德秩序的制约,即“礼”的规约。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就是指“仁”进入人伦层次必须接受的道德规约,没有道德规约,不讲“礼制”,生生之“仁”会被败坏和殒灭。不过,在伦理阶段,人也会体验到一种生命的境界之美,这就是“孔颜乐处”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指颜回能在世俗生活保持着或体验着一种超功利的、非世俗的生命之乐。但是,这种境界之美仍然是以对“礼制”的践行为评价限度的。因此,“孔颜乐处”的境界更多体现了一种人之“克己复礼”的“生命力度”,一种合伦理又超伦理的“中和”生活品态。
“仁美之境”属于仁之觉知的第三个层次。这个层次在宋明理学中得以全面展开。经过佛老庄禅生命意境的穿梭和洗炼之后,宋明新儒学将“仁爱”之“仁”从人伦层次升腾到对诸自然性命的“同一观照”层次。所谓“同一观照”,就是指借助于人的生命觉悟,诸自然性命的生机活力“一同”“绽出”,其效果即是被人感受到的那种生机“美感”①这里把“仁美”与“美感”都对译为“sense–beautify”,旨在表达:美在(动态)美感之中,不在美感之外。美是不能用来“言说”的,它是诸生命本身同时绽出时的生机体验。用来“言说”的不是美本身,而是关于美的知识(例如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共同文化、语境、价值观等)。一个人“发现”某种东西是美的,那是他/她个人的生命体验,他/她也指望其他人也能“认为”它是美的,在于其他人也有相似的生命体验(康德认为是“共通感”)。他/她也可能意识到其他人不认为它是美的,那是因为那时他/她已把美当作了一种知识对象来传播。这就不是一种美感体验本身,而是先入为主地在“认识”美。。换言之,人之所以“发现”自然物是美的,是因为通过人的生命深度体验,人的性命机能与自然(万物)的性命机能达到了内在的“贯通”,从而产生一种生命的和谐共振,于是我们“发现”了“美”。因此,美的本源即是自然之生生力量的“一同”“绽出”,它借助于人的觉知。这就像我们在生命活泼、心情高兴时,看到自然万物是美的(无论是柔和之美还是壮穆之美)一样,那是因为人的性命机能与自然物的性命机能达到了内在的和谐。看到一棵杨柳或一座险峰是美的,会产生快乐,那是因为人的生命节奏(机能)与杨柳或那种自然力的生命节奏达成了内在的一致;反之,在人劳累困病的时候,自然万物似乎丧失了美的特性,原因在于,美是诸自然性命活跃时的和谐共振,而劳累困病正是生命败坏的象征。
“仁美之境”作为仁之觉知的最高层次,也是对“仁”的一种源始“回应”,它暗示了儒家之“仁”原本即是对自然之生生不息力量的一种哲学隐喻。当然,“仁美之境”必须是以“仁爱”(善)为递进平台,没有“仁爱”这个阶段,人就不能达到对诸自然性命之“同一观照”。因为“仁”只有在(人的)“仁爱”阶段,它才有了自我意识,它才觉醒了。仁/人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就会逐渐从人伦之“仁”的深度体验和礼制束缚中超脱出来,走向万物之“仁”的内在相通,并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万物的“一”“类”意识这个层次。就此而言,我们说儒家“仁美之境”即是“仁爱”德性的象征。美是快乐的,是好的/善的,因为人对生命的敏感关怀已经走出了有意识,已经走向对诸自然性命的泛爱和大爱①这也可以看作是“仁”的“呈明”状态,它超越了“启蒙”所自带的“蒙蔽”状态(例如,个体、人类中心主义),“呈现”的是一个没有“男尊女卑”、“人贵物贱”自然之仁的本真(真理)状态。。
康德说,“美是道德(能力)的象征”,这只是从理性目的论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在他看来,美是实践理性(道德目的)的情感显现,人之所为发现自然界是美的,原因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特质就是要求我们能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理由/原因/目的。在认知中,它要我们给出理由(世界的原因)——由此招致了不可知论;在行动/行为中,它也要我们给出理由(即行动/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人的理性决定了人的道德行为不是自然情感的产物,而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人是自由的,因为理性的终极目的就是自由,就是与它“自身同一”。而作为理性的人,只有在其实践行动中才能真正给出它的目的,这就是按照“道德律”地行动/行为。“道德律”就是理性的“自我同一律”对行动意志的要求,就是自由律。那么,自然界本身有没有目的/理由,我们并不知道,而是因为人有理性,人就要给自然界的有机体存在找出一个理由(目的)。这就是自然目的论。人因为具有理性,成了自然目的论的觉悟者,因此,自然界是向人生成的。据此康德认为,人之所以发现(借助于艺术鉴赏的过渡)自然界是美的,是有道德(即实践理性)之根据的,即是合目的的。合什么目的?合人的理性之目的(康德还从认识论上给出了美的“契机说”),也即合道德目的。但是,“合目的”并不是等于那个目的本身,它只是对该目的的一种暗示或象征,即美只是人之道德能力(意志自律)的一种暗示或象征。
很明显,在儒家“仁美之境”中,我们说“美是仁爱的象征”,即也在说“美是道德(能力)的象征”。但是,这里的“道德”与康德的“道德”在理路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从情感主义体验论立场出发的,后者是从理性主义认识论立场出发的。前者不分主客,通过人之生命的内在开拓和深度体验,把美看做是源自诸自然性命的和谐共振和一同“绽出”,在“审美”中“率先见证”了“人类”与“物类”之“类”存在状态,并进而暗示了人类发展的终极目的就在于揭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类存在状态。后者则是从主客对立的角度,把美看做是由人的理性“审视”出来的,在审美中,见证的不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一”“类”存在,而只见证了人类的目的要求,一种对抽象的、形式的道德王国之象征。
当然,说“美是道德(能力)的象征”,也即是指“美是德性的象征”。在康德那里,德性即指配得道德律的行为/行动的那种意志力量,即意志的战斗力[5]4-9。人丧失了德性力量或德性坏死,人就失去了道德能力和自由能力,道德律也就变成了一条空洞的法则。“仁爱”作为一种向善厚生的道德行为动因,也是人建制和力行礼制(道德)的德性能力。人一旦丧失了这种向善厚生的内在驱动力量,视生生现象为“不仁”,道德礼制也就变成一种空洞的说教。
西方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由来已久,其实,透视“德性复兴”,我们发现:人类的诸如仁爱、友爱、关怀、仁慈等这些(道德)德性品质是人类在其千百年的社会历史活动中积淀下来的那种好的行为动因——由它们构成了人际交往的基础性规范,人类须臾也离不开它们、贬值它们。现实之人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偶然和运气),而德性的互助弥补了我们作为个体所自带的欠缺,让我们共度难关,繁荣族类。如果“德性复兴”能够让当代人自觉地认识到德性品质曾经并将一直在人际交往中担当和发挥着基础性的角色和基本的贡献力,那应该就是当代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了。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萧箑父:《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
[4]王岳川:《<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5]苗力田:《德性就是力量》,载姜丕之等编:《康德黑格尔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A Modern Explanation to Confucian Eth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Virtue of“Sense-Love”——From Viewpoint of Moral Sentimentalism
FANG De-zh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325035,China)
“Sense-love”,as a good motivation of action or a good psychological trait,is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Strength's depositing to become human beings'“character crystal”through our long–term social practices,which compos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fucian ethics.From a standpoint of“unity of nature and man”derived from human beings'experienced sense,Confucian ethics has been talking about how to accomplish a good humane and emotional being,while inherently connected with the others.
confucian;virtue ethics;sense-love;sentimentalism
B82-055
A
1671-7023(2011)06-0043-09
方德志(1979-),男,安徽舒城人,哲学博士,温州大学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2011-02-22
责任编辑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