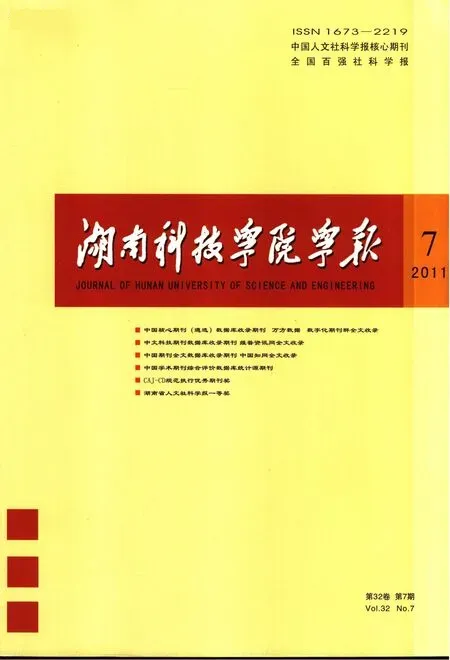从接受美学解读《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嬗变
黄泽英 刘雨琪
(湘南学院 大学英语部,湖南 郴州 423000)
从接受美学解读《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嬗变
黄泽英 刘雨琪
(湘南学院 大学英语部,湖南 郴州 423000)
《简·爱》出版一个多世纪之后,伯莎·梅森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发生了嬗变:疯女人形象蜕变为男权文化压制和迫害的女性代表和最有力的反抗者。文章试从接受美学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读者因受期待视野中历史及个人视界等因素的影响对伯莎产生了偏见,视之为疯女人;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读者的期待视野冲破了传统和历史的束缚,对伯莎有了新的认知能力并对其重新解读。
接受美学;《简·爱》;疯女人形象;偏见;女权主义运动;接受
一
19世纪中叶,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一文中不但创造了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至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积极进取态度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简爱,还塑造了另一个人尽皆知的怪异、凶狠、邪恶的“疯女人”形象——伯莎·梅森。前者一直以来被视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叛逆女性形象 之一,而后者在《简·爱》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都处于被忽视的境地,仅被看作是影响简爱幸福婚姻的绊脚石和导致罗切斯特人生悲剧的罪恶根源,是作者用来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工具,或视为女主人公简爱的闪光形象之陪衬。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伯莎的疯女人形象在读者心中开始发生变化。英籍女作家琼·里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桑菲尔德庄园顶楼囚禁伯莎的暗门,在其长篇小说《茫茫藻海》中改写了伯莎疯妻子的角色,从她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从此,伯莎的疯女人形象得以颠覆,更被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桑德拉·M·吉尔伯特( Sandra·M·Gibert )和苏珊·古芭( Susan Gubar )视为女主人公简爱“最真实最黑暗的重像(double),是女主人公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压抑的另一个凶悍的自我”[1]。受西方文学评论的影响,国内学者们也纷纷质疑伯莎是否真是一个“疯女人”,“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同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只不过小说所遵循的‘情节剧’三角关系的公式把她们摆在对立的地位”[2]。如今,在读者心中伯莎已从一疯女人蜕变为《简·爱》的另一个意象和象征——男权文化压制和迫害的女性代表和最有力的反抗者。为什么伯莎在读者心中会发生这一形象大衍变?读者的意识为何发生了变迁?笔者拟从接受美学文论出发、从读者接受角度来阐释这一嬗变。
二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以读者的文学接受为旨归,研究读者对作品接受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和规律的理论体系,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伊塞尔和尧斯。其中,尧斯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期待视野”是指“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时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包括伽达默尔的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两方面的内涵”,即文化修养、心理素质、个性气质、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审美情趣、鉴赏水平等。一方面,“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链上被充实和丰富”;另一方面,“读者以往的阅读记忆也积累了阅读经验;这两者的融合,便形成了一代代读者的期待视野”[3]。按照该理论,作品文本包含着被各种期待视野对象化的可能性。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文本的理解,总是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迁,会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阐释和评价产生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一代读者与前代文学作品发生“对话”,使读者自身的期待视野获得对象化。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是依据自己的期待视野使作品意义现实化。在读者接受方式上,尧斯将文学作品的接受分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前者具有历史性,它指在不同历史时期读者接受作品的状态。文本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就读者而言,其所处的传统和历史构成了其进入理解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合法的偏见”。正是这种偏见构成了解释者的“特殊视野”;后者具有共时性,它指同一时期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接受以及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共同接受。尧斯指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采取不同的接受方式不仅是因为期待视野发生了变化,作品“隐藏含义”的逐渐显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被认识的动态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又试图摆脱它以前所有历史时期的局限。这使得垂直接受能够不断地延伸。尧斯提出的读者“期待视野”以及对读者接受的共时性和历史性的分析凸显了影响读者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和规律,这为探讨《简.爱》的读者对其中疯女人这一形象认识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共时读者对“疯女人”的偏见
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把宪章运动不断推向高潮,成百万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积极投身到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中,劳动人民要平等,要独立。在这样的环境下,夏洛蒂创作了《简·爱》,通过简爱争取工作以至婚姻上独立自主、平等的奋斗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英国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悲惨地位,另一方面反映了英国妇女反压迫,抗歧视的斗争精神。然而,当时的宪章运动都尚未提出男女平权的思想,因此《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同时代的人并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4]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加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5]
其实,简爱对当时等级观念严重、男权至上的社会的反抗还是比较传统的。首先,简爱虽然追求独立,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得罗切斯特的爱。其次,简爱非常看重传统的婚姻形式,不管内涵如何,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在获悉罗切斯特的疯妻子仍然活着时,她没有勇气与他一起去挑战、冲破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第三,尽管简爱鄙视那种基于金钱和美貌上的婚姻,但她又不得不承认财富和美貌的重要。为了缩小她与罗切斯特之间的地位差距,她从马德拉的叔叔那获得了一点遗产、也获得了自信,才敢于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婚姻爱情。但是,当时的读者在其期待视野的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束缚下,视自尊、自立、自强的女主人公简爱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叛逆女性形象之一!对于想回归男权社会的简爱,当时的读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代表男权社会的罗切斯特采取一系列毁灭性报复行为的疯女人伯莎了。
在罗切斯特对着简爱述说他与伯莎悲惨与痛苦的婚姻中,读者听到的是粗俗、陈腐、蛮横无理、荒淫又酗酒的有着家族精神病史的伯莎,在她与罗切斯特不满四年的婚姻里“就已经把我(罗切斯特)折磨得够了。她的坏脾气蔓延滋长,快得惊人;她的邪恶日甚一日,又快又猛。”[6]而罗切斯特又不可能用任何合法的手续把她摆脱掉,因为医生已经诊断出伯莎疯了。在文中读者也可在多处看到她疯狂的行径:在一个火辣辣的西印度群岛的夜晚,她对罗切斯特大喊大叫地咒骂,让他感觉就像生活在地狱,甚至想用手枪自杀;罗切斯特眼中又狡猾又恶毒的疯女人趁看守她的人一时疏忽,悄悄藏起一把刀子,刺伤了她娘家唯一关心她、爱她的弟弟;她两次偷到阁楼的钥匙,夜里溜出来,第一回想图谋把罗切斯特烧死在床上,第二回魔鬼似地找上了简爱,奋力把象征婚姻的婚纱撕得粉碎;伯莎一把火烧掉了桑菲尔德庄园,并把囚禁她的罗切斯特烧残烧瞎!伯莎竭尽全力想毁灭代表英国父权制的罗切斯特并付诸疯狂行动,她的反抗相比温和的简爱更大胆、更直接、更决裂、简直无所顾忌。在维多利亚初期,宪章运动虽然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女性在经济上尚未独立,妇女作为一种虚弱、驯服的生物不得不屈从于男性、必须顺从于她的丈夫或父亲的老观念根深蒂固,这使得更多维多利亚人对妇女角色还是持有传统观念——男性是强壮、理性、有侵略性和优秀的家长,而女性是低等的因而必须依赖于男性。维多利亚社会女性的屈从地位使得当时读者期待视野中的历史、个人视界务必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制约,形成特定的思维定向和先在结构:罗切斯特是“家长”,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伯莎作为妻子必须屈从于他,哪怕疯了之后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当时读者的这种“特殊视野”和“偏见”使他们只看到了文中罗切斯特的男权地位一再受到伯莎疯狂的威胁、甚至是致命的报复,而未能跳出这一藩篱看到伯莎正是男权社会、家长奴役制度下的牺牲品这一实质。伯莎被当时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读者贴上“疯女人”的标签不可不为一种历史的偏见。
(二)历时读者对“疯女人”的接受
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在西方国家风起云涌,这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法律和造物者对人都是公平的,无论是男还是女,因此妇女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具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而伴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权主义批评方法也应运而生。批评家们从社会、文化、生理等各个方面对女性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研究,特别是从以往著名女作家创作的经典作品入手,重新解读她们的文本,并挖掘出许多新意,由此形成了许多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
女权运动提倡的男女平等思想使得新时期读者的女性意识不断得以加强:女性不再低人一等,不应被男性奴役,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应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对《简·爱》中一直处于简对立面的伯莎·梅森——被罗彻斯特禁闭在阁楼里面的疯女人进行全新的理解、阐释和评价。
伯莎为什么被冠以“疯女人”的称号?女权主义下的读者认为是罗切斯特称之为“疯女人”的。在他与简爱的婚礼被梅森打断后,他带着牧师等人回到桑菲尔德庄园,冲上阁楼,指着伯莎公然对众人呐喊:“伯莎·梅森是个疯子,她出身于疯子家庭,——三代都是白痴和疯人!”[6]而且,婚礼被取消后,在罗切斯特对简爱的述说中,他不断列举伯莎的恶行来论证她的“疯女人”形象。在桑菲尔德庄园,罗切斯特一人掌握着话语权,而伯莎没有任何话语权为自己辩解,甚至连人身自由的权利也早已被剥夺了。况且,桑菲尔德庄园里除罗切斯特之外的所有的人,包括管家菲尔费克斯太太、女仆莉莎、小女孩阿黛勒等,都没提过伯莎·梅森是“疯女人”。而对于文中伯莎先后针对两位男性——丈夫罗切斯特和娘家弟弟梅森的疯狂报复和伤害,女权主义下的读者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伯莎是男性压迫的直接受害者。伯莎在婚前就没有任何的自主权,父亲用三万英镑与罗切斯特作了一个金钱与地位的交换,就将其嫁给了罗切斯特,这奠定了伯莎·梅森婚姻的悲剧基调。而婚后,罗切斯特又以性格和伯莎格格不入为理由,拒绝与伯莎进行交流,这种夫妻双方感情沟通的缺乏,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使伯莎·梅森痛苦万分,在短短的四年内就由一位美丽的富家小姐沦为疯婆子,罗切斯特不愧为有家族病史的伯莎迅速变疯的推手。因此,伯莎在父权与夫权的双重压制下,哪怕在失去人身自由和话语权之后,仍没有放弃对代表男权的丈夫和弟弟进行奋力的反抗。终于,伯莎穿越了男性权威话语的重重阻隔,摆脱了以往读者眼中的“疯女人”形象,脱胎换骨以崭新的面貌走进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伯莎是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是一个受压制、受迫害的妇女形象,她的“疯狂”行为实际上对维多利亚时期父权社会的有力反抗。这也使得夏洛蒂深藏在《简·爱》中的“隐藏含义”在一百多年后得以彰显。
三
夏洛蒂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英国社会虽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没有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即使宪章运动,也没有完全解决男女平等问题,而对于男女婚姻上的平等,当今的女性仍在不断追求,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等因素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与束缚,使得与夏洛蒂同时期以及之后一百多年间《简.爱》的读者们对伯莎这一形象产生了历史的偏见,将其贴上了“疯女人”的标签。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以来,女性在社会和婚姻家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高,读者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鉴赏能力也在不断变化,期待视野得以提升,对“疯女人”有了崭新的认知能力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夏洛蒂塑造了简爱和伯莎两个对立的女性,前者早已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接受,后者经过一个多世纪之后也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并赋予新的理解与阐释,她的创作既关照了共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也预见了历时读者对其“隐藏含义”的解读能力,《简·爱》不愧为一部经典之作。
[1][美]吉尔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
[2]朱虹.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J].外国文学评论,1988,(1).
[3]Jauss,Hans Robert.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4]Anonymous.The last new novel [J].Mirror,1847,(2).
[5]Kappeler. Susanne ed. Teaching the Text[M].London: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
[6]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吴钧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7]徐菊.经典的嬗变《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Research on the Mad Woman in JANE EYR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Theory
HUANG Ze-ying, LIU Yu-qi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of Xiangnan University, Hunan Chenzhou 423000,China)
The image of the mad woman in the readers’ mind of JANE EYRE has been changed since it was published in 1847.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Theory and points out that readers regarded her as a mad one with prejudice for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in their horizon of expectation, and that they have a brand new attitude and knowledge on 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movement for the change in their horizon of expectation.
Reception Theory; JANE EYRE; the research on the mad woman; prejudice; reception
I106
A
1673-2219(2011)07-0046-03
2011-01-20
湘南学院青年课题“《简·爱》中疯女人伯莎.梅森形象研究”(项目编号07Y021)。
黄泽英(1974-),女,湖南郴州人,湘南学院大学英语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刘雨琪(1974-),女,湖南永州人,中教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法。
(责任编校: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