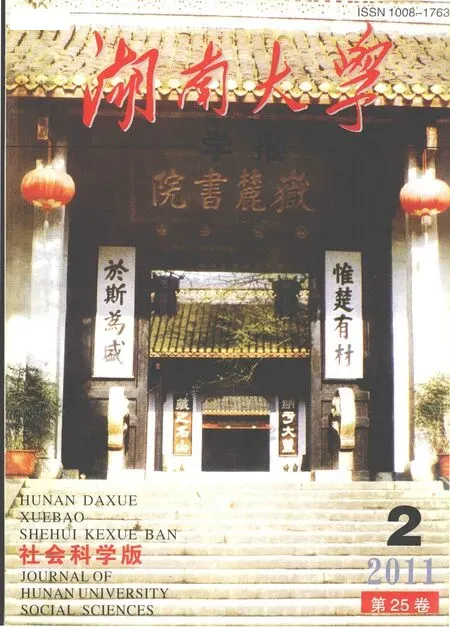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缺失*——巴赫金狂欢理论批判
阎 真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缺失*
——巴赫金狂欢理论批判
阎 真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一个建构在扭曲的史实性描述基础上的理论大厦,其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史结论如“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和“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等,都是建构在虚幻的史实性描述之上的理论想象。这种想象极大地歪曲了狂欢节的真实面貌和文化功能,虚构了狂欢节与官方文化宗教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对抗,在历史和逻辑双重意义上,都有着根本性缺失,是一个体系性的文化史虚构。
巴赫金;狂欢理论;文化史虚构
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世界性风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沼泽,它在中国的众多拥戴者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本文提出以下六个问题,并得出相应的结论,以对这一巨大的理论沼泽予以彻底清理。
第一个问题:巴赫金对狂欢节的史实性描述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
狂欢节是狂欢理论的史实性基础,狂欢理论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史实的描述是否客观真实,决定着狂欢理论能否合法建构。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迈出了错误的第一步。巴赫金用四个“范畴”来描述狂欢节:第一,“人们之间随便而亲昵地接触”,“在生活中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的人们,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地接触”,意义在于“取消的就是等级制”。第二,“插科打诨”,其意义在于“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级、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第三,“俯就”,“随便而亲昵的态度,应用于一切方面,无论是对待价值、思想、现象和事物”,其意义在于“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第四,“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作法”,意义在于“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摹仿讥讽等等”。另外,还有“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这是“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意义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1](P1175-178)巴赫金正是在这种描述和意义阐发的基础上,得出了“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的“可能性”等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史结论的。
如果我们不看别的文献,就会相信这是狂欢节真实客观的存在状态,就是史实,从而接受了巴赫金那一系列意义阐发和文化史结论。但如果我们又读了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就不可避免地对巴赫金描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产生疑虑,进而对那一系列重大结论产生质疑。
在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狂欢节是“以游行本身为主要特征的节日庆典”,而“凯旋车”是游行的主要仪式。布克哈特多次描述了这些游行的状况,其中有很多次有具体的年代和事件背景,如1491年罗马狂欢节、1500年罗马狂欢节、还有佛罗伦萨狂欢节,等等。除了游行,狂欢节的其他内容还有赛马、赛驴、有教皇保罗二世招待群众,等等。但没有对“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加冕和随后脱冕”等场面的描写,一个字都没有。[2](P397—420)
布克哈特描述与巴赫金的描述差距如此遥远,几乎没有重合之处。如果不是同在狂欢节这样一个题目之下,人们很难看出他们是在描述同一史实。这里特别要提出讨论的是两人对狂欢节的“主要的仪式”的不同理解,因为,主要仪式体现着事物的本质意义和内涵。巴赫金说:“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1](P177)而在布克哈特笔下,这个“主要的仪式”根本就没有出现,而对凯旋车游行的描述则达数十次之多。二者描述的反差实在太大了。谁更客观而真实地表现了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呢?
基本状态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内涵和文化功能。虽然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基本状态可能有不同的描述,但毕竟事实只有一个,基本状态只有一种,它不能因为视角的差异而随意描述,否则历史就没有客观性可言。历史学如果还是一门科学,那它就应该有自身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否则,任何人都可能从某个局部引发出自身所需要的不同的以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历史则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倾向于接受布克哈特的描述,原因有二:其一,他对每一个事件的描述都详尽地注明了史料的来源。史料的引证占了文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种史料的严谨性也是其著作历经一百多年仍被公认为学术经典的主要原因。其二,布克哈特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描述历史,并不是试图导向任何结论,即没有“使命感”,这也为其描述的客观性提供了保证。而巴赫金的描述第一没有注明任何资料来源,没有注明自己是从什么资料中概括出狂欢节的四个“范畴”以及“主要的仪式”,并将其当作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我在此郑重提请有关研究者特别关注,这种不注明任何史料依据的描述,在学理意义上,是一种学术性的硬伤,其客观性、全面性和公正性是没有任何保证的,而这正是整个狂欢理论大厦的基础工程。第二,巴赫金是为了自己的理论目的而进行描述的,为了把史实纳入自己的思维轨道,对狂欢节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扭曲性描述。这是一种极为明显的“使命性”描述。这种选择使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的存在状态与史实相去甚远,一些边缘性的非核心的东西被置于中心地位。最明显的,就是对“主要的仪式”的描述。
由此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巴赫金对狂欢节的史实性描述缺乏最起码的史料性支撑,是不真实不客观的。这种描述扭曲了狂欢节的真实状态和文化内涵。在一个错误的史实基础上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是狂欢理论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根本性缺失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狂欢节是否像巴赫金所描述的,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在对狂欢节史实状态进行了不真实的描述的基础上,巴赫金展开了又一个不真实的推论,这就是对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予以了极大的夸张,这种夸张,把狂欢节的文化史意义提到了一个与史实不相符合的高度。他说:
不妨说(当然在一定的前提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1](P184)
“狂欢节,这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3](P10)
在他的笔下,狂欢节被提到与“常规生活”并列的“第二种生活”的地位。这是一个为了达到特定理论目的而进行的不真实的描述。在中世纪,由狂欢节带来的“第二种生活”是根本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两种思维体系”,而只有一种生活和秩序,那就是宗教规定的生活秩序,也只有一种思维体系,那就是宗教的思维体系。狂欢节只是在这种生活秩序和思维体系制约下的节日庆典,而没有也决不会被允许有“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的文化意味。否则,它将与宗教产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而我们看到,在中世纪,这种冲突并没有发生。关于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我们看到,在布克哈特的著作中,狂欢节是与奇迹剧、俗世演出、哑剧和君主招待会、游行仪式和宗教上的凯旋式、赛船和水上游行等并列描述的,并不像巴赫金描述的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那样重大的以至核心的地位。美国文化史大家威尔·杜兰在其长达1l卷20多册的巨著《世界文明史》中,对狂欢节甚至是只字不提。著作对世界各个时期的文明状况的描写极其详备,服饰、乐器、沐浴方式、游乐方式等都细细描述,也相当详细地描述到了威尼斯等城市的节日庆典,却偏偏忽略了狂欢节。[4]在威尔·杜兰的价值视野中,看不见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当然就更谈不上如巴赫金论述的那样,“对整个文化的发展,其中包括文学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影响”。[1](P183)作为一个文明史大家,威尔·杜兰不可能不了解狂欢节;但他对狂欢节的重视程度,与巴赫金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还有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人1955年出版的《世界文明史》,《新编剑桥近代史》等权威著作,对狂欢节也是只字不提。
由此我得出第二个结论:狂欢节远不像巴赫金所描述的那样,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甚至核心的地位,因此也没有如他所表达的那么重大的文化史意义。巴赫金赖以做出重大文化史结论的史实基础是狭隘而贫弱的。这种狭隘和贫弱,与结论的重大与宏观,形成了极为巨大的反差。
第三个问题,狂欢节是否有反官方反教会的异端文化意义?
这是狂欢理论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巴赫金对狂欢节的状态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扭曲性论述,都是为了证明狂欢节是一种反抗和解构官方文化教会文化的异端文化,他关于狂欢节的四个“范畴”,“主要的仪式”,以及“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和“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的描述,都是为了论证其文化异端性。于是我们要问,狂欢节是否具有这种文化异端性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史实:第一,狂欢节起源于基督教的谢肉节,英文的“carnival”一词,就源自拉丁文“carne vale”(意为“与肉告别”)。这是狂欢节与宗教的文化渊源。第二,狂欢节有大量宗教内容,如“背负十字架的基督”,“教士们的化装游行”等,教皇本人更是最重要的参与者。[2](P397-420)这是一个宗教意味非常浓厚的节日,却被巴赫金描述为反宗教的节日。这是为了自身的理论建构而扭曲史实的典型案例。第三,在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狂欢节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宗教文化和平共处,没有产生激烈的价值对抗。第四,狂欢节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年复一年,却没有从中产生新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为历史的进步提供动力。
这些史实会不会让狂欢理论的崇奉者感到难堪?巴赫金说:“这种真正的节庆性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官方不得不予以容忍,甚至在节日的官方部分之外,部分地把它合法化,把民间广场让给它。”[5](P11)“容忍”一词暗示了狂欢节的文化异端性。但真实的情况是,教会不是“容忍”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为什么教会“容忍”并且参与狂欢节,还与之和谐相处千年而没有发生激烈的文化冲突?是因为狂欢节其实并没有文化上的异端性,还是因为教会没有意识到其异端性?这个问题简单明了而又尖锐,不存在把水搅浑,把问题复杂化,从而得出其他结论的可能性。这决定着我们对狂欢节文化品格的定性。如果狂欢节真如巴赫金所论述的那样,具有“第二种生活”、“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以至“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等如此重大的异端性文化功能的话,那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宗教内容?为什么僧侣和教皇也会参与?难道他们迟钝到上千年里都察觉不出狂欢节的文化异端性,或者察觉到了还要参与解构自己的活动?为什么狂欢节能与教会长期和平相处,是因为教会对异端文化的容忍吗?
史实如此清晰,逻辑如此简单。任何诡辩都改变不了基本的史实和简单的逻辑。史实证明了狂欢节的文化品质是平庸的、保守的、游戏的、非异端性的,它与宗教文化从来就不存在着如巴赫金所描述的那种价值对抗和文化冲突,也就是说,狂欢节并没有“第二种生活”,“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的文化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不但能够接受它,而且参与其中的原因。教会如果能够容忍“第二种生活”,“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以及“大型对话”,并参与具有这些文化内涵的活动,那教会岂不是很宽容、很仁慈,甚至在否定自身吗?而中世纪那么多对异端的迫害又怎么解释,难道中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年代?这是狂欢理论的崇奉者面临的理论困境,甚至可以说是绝境,要走出来实在是太艰难了。
由此我得出第三个结论:巴赫金关于狂欢节文化异端性的论述是文化史的虚构。既然狂欢节的文化异端性不能够得到史实的印证,那么,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内在逻辑就根本不能够成立,所谓“第二种生活”、“两种思维体系”,以至更高的理论升华“狂欢节世界观”和“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就处于一种理论断裂的状态,狂欢理论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个问题:文艺复兴为什么没有将狂欢节作为精神资源?
按照巴赫金的论述,狂欢节具有取消等级制、形成人们之间的新型关系,使神圣与粗俗接近,讥讽神圣文字、产生交替与变更精神,以感性的形式表现平等自由等文化内涵,而这也正是在欧洲持续了几百年的文艺复兴追求的基本目标。从最简单的形式逻辑来说,在那个上下求索,寻找思想资源的年代,当时的文化巨人应该将狂欢节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加以开掘,高举其旗帜,阐发其意义,挖掘其深度,使狂欢节的文化功能发扬光大,为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性文化转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可是,非常遗憾,这种辉煌的景象并没有产生。
还是让我们回到史实。无论在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乔叟等人的文学作品中,在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提香等人的绘画和雕塑中,还是在莫尔、蒙田等人的理论著作中,都看不到狂欢节的思想资源意义,也看不到狂欢节的踪影。拉伯雷的《巨人传》提及狂欢节,但不是正面论述,更没有任何举其为旗帜的意思。文艺复兴长达数百年,其中涌现出大批文化巨人。难道那么多文化巨人在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中集体性地失聪失明,对狂欢节的伟大文化意义和思想内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没有人对狂欢节表现出特别的重视,连拉伯雷也没有(他如重视就会正面大篇幅描写,而不会在一部长篇中仅仅只是侧面地提一句)。这种史实让狂欢理论的崇奉者和辩护者如此难堪。这究竟是因为狂欢节本身就不具有反等级、反教会自由平等的文化内涵,还是因为那些巨人们迟钝愚蠢而没有发现这种文化内涵呢?
由此我得出第四个结论:狂欢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平庸表现,确凿地证明了巴赫金对其伟大文化意义的论述是完全不能够成立的。这是狂欢理论及其拥戴者绕不过去的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绝境,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人能用什么方法走出这种绝境。
第五个问题:狂欢化到底有没有历史依据?
狂欢化是巴赫金创造的学术概念,在狂欢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是暖昧而模糊的,这种暧昧性和模糊性掩盖了其历史依据贫弱而文化能量被无限夸大之间令人震惊的反差。在这里,我想对这个概念进行透视梳理,以剥离附于其上的暖味性和模糊性,使其在学术的视野中变得通透明朗。
让我们从巴赫金的定义开始。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1](P175)这是它的定义。“狂欢化的渊源,就是狂欢节早身”。[1](P186)这是它的来源。“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1](P247)这是它的文化功能。
按照巴赫金的论述,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那么,只有那些渊源于狂欢节的文学作品,才符合狂欢化的定义。但是,当我们回到史实中,这种渊源于狂欢节的作品,即从“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又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之中,中世纪又有哪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体现了这种转化呢?按照巴赫金的说法:“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的潮流可以说打破了许多壁垒而闯入了常规生活和常规世界的许多领域。首先这股潮流就席卷了正宗文学的几乎一切体裁,并给它们带来了重要的变化。整个文学都实现了十分深刻而又无所不包的狂欢化。”[1](P185)这么说来,狂欢节功莫大焉,不但“打破”了壁垒,“席卷”了,一切文学体裁,还带来了“无所不包的狂欢化”。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第一,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解放的文艺潮流,跟狂欢节有什么关系?把这么大的历史功绩归于狂欢节,有什么历史依据?巴赫金根本就没有能够为这种描述提供任何史实性证据。一个看不到狂欢节踪影的文艺思潮,却被狂欢节的潮流“席卷”,这种强迫性的描述,按照怎样的逻辑才能够成立呢?第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用“狂欢化”来描述?按巴赫金的论述,只有渊源于“狂欢节本身”的文艺作品,才能被描述为“狂欢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哪一部作品,又是渊源于狂欢节呢?如果一部作品,连“狂欢节”三个字都没有,我们能说它渊源于狂欢节吗?即使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提及这三个字,也是一种极其细节性的描写,同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没有进入那些文化巨人的价值视野,更不用说举为旗帜,那狂欢化又从何说起呢?又怎么能够把那些伟大作品归于“狂欢化”的旗下?在那些文化巨人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塑和理论著作中,看不见狂欢节的踪影,却被认定为渊源于狂欢节的“狂欢化”,从最简单的逻辑上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只有在那种不讲史实的强迫性逻辑之中,才能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以至整个文艺复兴,归功于狂欢节名下。“狂欢节的潮流”“席卷了正宗文学的几乎一切体裁”,这一论述是对史实的公然扭曲,这种扭曲是如此地肆无忌惮,实在令人惊异、叹息,以至产生一种理论的愤怒。至于今天有人用“狂欢化”来描述当时的文艺思潮,那是另外一回事,根本就不意味着当时的文学思潮和作品与狂欢节有什么渊源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就会把历史的清澈之水搅浑。在巴赫金笔下,他自己定义的,源于狂欢节的“狂欢化”与文艺复兴时期“十分深刻而又无所不包的狂欢化”,已经不是同一个“狂欢化”,前者渊源于狂欢节,而后者与狂欢节没有关系,不符合他自己的定义。在这里,概念已经发生了偷换。偷换的理论功能,就是试图强行在狂欢节与文艺复兴之间建立起史实中并不存在的联系。这种意义的转移,是狂欢理论关键性的一环,却又是丧失了内在规定性和逻辑性的一环。
由此我得出的第五个结论是:狂欢化作为巴赫金创造的理论概念,既得不到史实的支撑,也缺乏最起码的内在逻辑的严谨性,更谈不上一种真实的文化史意义。巴赫金对史实的扭曲性强迫性描述在这里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给人带来的是无法扼制的学术性愤怒。
第六个问题:由狂欢化而来的“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吗?
巴赫金说:“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这里说的“对话”,按巴赫金本人的意思,是在“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与“独白意识”的对话。既然是在“高级领域”与“独白意识”的对话,而且是“大型对话”,它必然有相当的规模,有相当的对抗性,尽管形式可能多样化。
让我们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回到史实。首先,狂欢式转化为文学语言形成狂欢化,这一状态如我们前一节所论证,是缺乏文学史的史实支撑的,巴赫金也好,其理论的崇奉者也好,都无法在文学史中提供这种转化的例证,不论在中世纪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如此。因此,渊源于狂欢节的狂欢化,是一个精神能量非常有限几乎找不到史实支撑的词。这种极其有限的能量,能够建立起“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吗?而且,这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在中世纪没建立起来,也不可能被宗教文化允许建立起来。如果允许了,那就是多元化社会了,还谈什么“独白意识”呢?如果一种“可能性”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还没有转化为现实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一种没有任何史实支撑的纯理论的虚设。大型对话结构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步建立起来了,独白意识被打破了,但如前所述,这种建立的力量不是来自狂欢节,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狂欢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根本看不到狂欢节的踪影。狂欢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既不能说重要角色,更不能说决定性的角色,连小角色都不是。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归功于狂欢节及狂欢化呢?
由此得出的第六个结论是:由狂欢节产生狂欢化,进而建立“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是把虚设的“可能性”当作了史实,与历史的真实进程没有任何关系。巴赫金关于狂欢节和狂欢化的“大型对话”意义的描述,是对文化史的又一次虚幻性想象。
从以上六个问题及其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巴赫金狂欢理论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缺陷。在历史的层面,他将局部的甚至极为边缘化的史实描述为整体的核心的史实,把小树枝条当作钢筋水泥基石,以建构理论大厦。在逻辑层面,他利用人文科学语言难以量化的特征,以一种暖昧性的推理方式,从一种局部的边缘化的史实中,推论出整体的全局性的重大结论。在一种表面严谨的逻辑过程中,史实与结论的联系已经十分脆弱,以至完全断裂。这种断裂在对狂欢节“主要的仪式”的描述中,在“狂欢节——狂欢化——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这种推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狂欢理论来说,史料支撑系统性贫弱匮乏,不论是在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狂欢节文化功能的异端性方面,还是狂欢节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狂欢式转化为文学语言即狂欢化、狂欢化所具有的对话功能方面,史料都远远不足以建构一座理论大厦。这是方法论的缺失,是狂欢理论一系列缺失中最根本的缺失。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看出,我在对以上各个问题的论述中提供的史料,除了局部的准确性之外,还是一个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的整体,因而结论也具有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的整体性。这种从诸多方面导向同一结论的整体性揭示出,巴赫金史实描述的主观性、独断性和强迫性是令人惊异的,而建构在这种主观性,独断性和强迫性史实描述基础之上的理论升华是根本没有内在逻辑性的。狂欢理论各个局部、各个环节从史实描述到理论升华,其牵强性脆弱性也是相互印证的,其理论缺失是基于各个局部缺失之上的系统性、全局性缺失。令我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一个如此漏洞百出的体系不但建构起来,而且还在长达数十年的岁月中,得到国际和国内理论界的无条件拥戴。在今天,国际与国内学术界应该对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世界性理论失误,进行为时已晚的彻底反思。
[1] 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2]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5]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Double Lack of History and Logic——A Critical Analysis of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YAN Z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is constructed on the foundation of distorted historical description.A series of major conclusions of cultural history,like“two systems of life and thought”,“a carnival sense of the world”.and“the open structure of great dialogue”,are all imaginary theories based on insubstantially historical description.The imagination greatly distorts the real nature and cultural function of the carnival,and fabricates the cultural confliction and valu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carnival and official religious culture.As a systematic fabrication of cultural history,it lacks both historical and logical significance fundamentally.
Bakhtin;Carnival Theory;fabrication of cultural history
I0
A
1008—1763(2011)02—0078—05
2010-05-18
阎 真(1957—),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