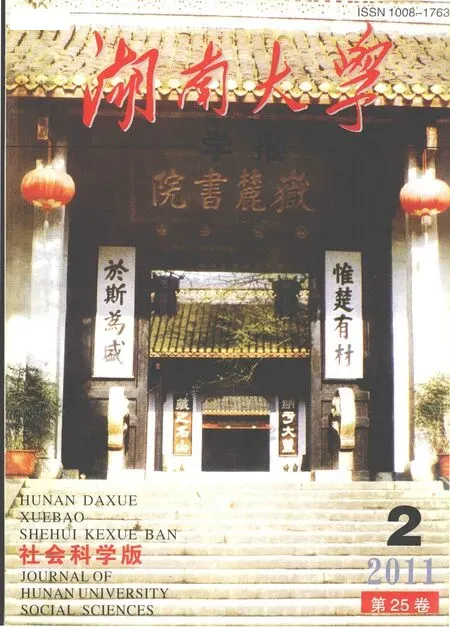六朝至唐志怪小说中符咒元素的思想内蕴与叙事功能*
李生龙,张辟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六朝至唐志怪小说中符咒元素的思想内蕴与叙事功能*
李生龙,张辟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志怪中的“符咒”的描写,不仅语涉怪异非常之事和神异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治病、袪灾、辟邪、镇宅,解决传统理性主义中鬼神妖异所引发的问题,成为六朝至唐志怪小说猎异好奇的重要题材,隐含着丰富的思想内蕴,而且有着直叙、连接情节、于悲喜交加之际使读者享受某种审美愉悦的叙事功能,体现了作者对符咒元素运用的巧妙娴熟,对后来志怪小说的进一步人情化、故事化有深远影响。
志怪小说;符咒;鬼神;思想内蕴;叙事功能
六朝至唐代的志怪小说不少涉及符咒叙事,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艺术内蕴。本文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希望研究者批评指正。
一 六朝至唐志怪小说所述符咒之作用
符与咒,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符”,原是刻在玉璧上的符号,可能兼有宗教与军事双重作用。2008年杭州市临平玉架山遗址曾发现一件直径达24.6厘米、上有两个刻符的大玉璧,距今四千多年,可能具有某种宗教意义②据中新网杭州12月14日电(记者龚读法)12月13日报导.。从军事角度说,符用作帝王发布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上面刻有文字或图案,一分为二,分则各执一权,合则验符为信。《史记·五帝本纪》载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又有“合符釜山”之说,《史记索隐》说是“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可见其符用玉制成。后符制可能有所变化。汉代兵符用铜,使符用竹。《史记·孝文本纪》就有“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之记载。《史记集解》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又引张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从简易也。”许慎《说文解字》说:“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 ,分二相合。”[1](P191)《史记索隐》解释道:“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说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颜云‘右留京师,左与之。’”可能到东汉许慎时代兵符与使符已兼用竹制。
总之,符既有某种宗教意义,又是一种权力象征。权力意识与宗教理念进一步纠合、滋乳的结果,符便被引入了鬼神世界。战国以来的方士将符作为驱神役鬼之方术,产生了所谓神符,东汉道教兴起,道教徒称之为道符。为了显示其神秘难测凡俗难晓,符的形制、书写也日渐变得五花八门。刘晓明说:“道符是道巫使用的一种神秘图形与文字,或称符文、符书、符术、符箓、符图、甲马,名称虽异,但指的都是同一种东西。”[2](P1)随着道教方术的丰富,符的作用也五花八门,不仅仅限于驱神役鬼。早期道教太平道、天师道皆为符箓道教。今传之道教早期典籍《太平经》有不少道符作用的记载,并存有符图,为我们了解道符提供了实证。
“咒是人们向神明表达的某种语言信息,这种语言信息集中反映了人们的某一愿望,并企图通过神明来实现这一愿望。和一般的语言不同,咒语不是人与人沟通的思想的手段,也不是梦中呓语和下意识的独白,它是一种有意识行为,其对象是神不是人,或者说,通过神再到人。”[2](P351)《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腊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是见于载籍的早期咒语,昭示着先民的法术意识。与“咒”相通的是“祝”,李远国认为:“咒的含义与祝相同,似当为祝的别体字。”又说:“道教凡作一切科仪、摄养修持、通神达灵,皆要使用咒
语。”[3](P47-54)
简言之,“符”、“咒”都是针对不可知或不可察见之神秘物事而设,潜藏着先民企图通过自身或外界之神秘力量来制服神秘物事的法术意识,是先民企图消弥灾眚、化解危难、缓和恐惧心理的方法之一。早期符与咒可能各自为用,但随着道术的丰富与发展,两者常成综合态势,符与咒或单独使用,或合在一起兼用,但兼用的情况可能更多。因为符中往往隐含着咒,故统称“符咒”。
历史积淀起来的符咒类别众多,功用不一,难以缕述。六朝至唐代的许多志怪小说如晋干宝《搜神记》、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唐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张读《宣室志》、戴孚《广异记》、薛渔思《河东记》、张 《耳目记》、杜光庭《录异记》等都涉及符咒叙事。这些小说中所呈现的符咒功用主要表现为治病、袪灾、辟邪、镇宅四个方面,有时四种功用可能互有交错,也有利用符咒为害的例子。
——治病。如《广异记》“燕凤祥”条载平阳儒士燕凤祥屡屡见“鬼”以致精神恍惚,初请巫祝祠祷无效,继而“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不久,凤祥梦见空中有一人朱衣墨帻,对他说“还汝魂魄”,精神病方得以痊愈。把因惊吓而导致的精神失常看成魂魄为鬼所夺,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用符咒驱鬼治病的方术活动也就成了志怪小说中常见的情节。
——袪灾。灾的种类很多,可分为自然灾害、植物灾害、动物灾害等多种。如《搜神记》第25条所记著名道士葛玄用符咒求雨来袪除旱灾(自然灾害):“(葛玄)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着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录异记》卷七记载葛玄用符袪除水蛭之灾(动物灾害):“庐山西南七十里,有涌泉观。昔太极仙公葛玄炼丹于此,感致泉水自石窦中涌出……其地旧多水蛭,农人患之。仙公刻符于洞门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处皆无水蛭之患,远近赖之。后人凿此符移于涌泉观中,但旧迹在耳,而灵验不改。”[4](P500)
——辟邪。所谓邪,一般指的是由鬼怪等异物引起的非正常态势。如《异苑》卷六记载:元嘉十四年,徐道饶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来捉弄他,他“就道士请符,悬著窗中,见便大笑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玄怪录》记王煌日渐形体削弱,道士猜测王煌所娶之妻为鬼魅,并取符箓验证,其妻立变为“耐重鬼”[5](P112)。以上均属于鬼物为邪。《广异记》“杨伯成”条记老野狐变作人形鱼幻惑等等,则属于妖怪为邪。
——镇宅。宅之所以需要镇,是因为某种不可知之神秘物事扰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如《异苑》卷六记载:“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方间桓徐州故宅。有怪称是天上仙人,在宅中掷秽污,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氎诵咒文,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于此都绝。”[6](P532)
符咒可以消灾解厄、除邪镇宅,也可以为害。如《广异记》记苏丕女之婢以巫符为害的故事,是古代巫惑之谬种流传。
二 六朝至唐志怪小说符咒所隐含之思想内蕴
如上所云,符咒源于早期巫术。巫术产生的土壤是人类抵御灾患能力的低下和科学知识的匮乏。正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抵御灾患的需要,人们转而相信神巫能够“通神”、“通天”,具有超人群、超自然的能力,能够解除普通人无法解除的灾厄。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巫术,只是表现形态各各不同而已。中国的巫术发展到战国时代,为方士们所吸纳,道教产生以后,巫术转化为道教法术,符咒成了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盛行以后,也带来了自己的法术,其中也有符咒。刘仲宇说:“中国的佛教、道教以及民间的巫师,都拥有大量的企图凭借超自然力量和各种神秘手段去支配鬼神、控制和改变外物自身或变化的秘术,……它有依赖于神灵又能部分地超越、制约神灵的特征。”[7](P2)这里说的是整个方术的特点与作用,自然也包括了符咒。
符咒法术针对的是神秘难知的鬼神或怪异物事,这些东西本来是无法解释的,然而古人却力图作出符合理性的解释。《礼记·祭义》记载:“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8](P1218)这是用气化论来解释鬼神。东汉王充则用气化论来解释一切怪异之事:“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9](P935)“故妖怪之动,象人之形,或象人之声为应,故其妖动不离人形。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9](P940)“天地之道,人将亡,凶亦出;国将亡,妖亦见。犹人且吉,吉祥至;国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应妖祥,其实一也。”[9](P941)这种理性主义对道教徒也有影响,如葛洪解释妖怪说:“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10](P900)
受传统理性主义的影响,志怪小说的作者也常对鬼神怪异之事作出符合理性的解释。例如干宝《搜神记》卷六论“妖怪”云:
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
卷十二则说:
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水浊则贪,土浊则顽,五气尽浊,民之下也。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本乎时者亲旁:各从其类也。……应变而动,是为顺常;苟错其方,则为妖眚。
这里综合运用了先秦以来的气化论、天人感应论和同类相感论,对鬼神妖怪的产生作了最系统的理性主义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不是要求人们回归理性,拒绝迷信鬼神妖异之事;而是企图引导人们坚信鬼神妖异实乃自然而然之事,不可不信。借助理性主义解释为宣扬怪异之事张本,是志怪小说鬼神妖异理念的一大特点,也是志怪小说之所以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①关于先秦以来鬼神怪异理念的阐释,可参看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第五章第一节《天人感应与神话、志怪》。长沙:岳麓书社,2009.
鬼神怪异是人们最感恐惧的物事,也是志怪小说着重渲染的重要内容。之所以要渲染恐怖气氛,实是为符咒之奇功异效张本。例如《宣室志》卷六记御史崔某职于广陵,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宏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锁闭累年。崔某自壮其胆说:“妖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向廉使请求入住其中。可入住以后却确实令人恐怖:“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另一则故事记梁璟从长沙到长安举孝廉,途经商山,舍于馆亭中,时适八月十五,月白风清,到半夜竟有三男子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前来同他饮宴赋诗,梁氏虽然胆大,最后因同萧中郎发生争执,“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亡见矣”,终于抵拒不了极度恐惧而“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这类因目睹鬼怪而惊怕甚至导致精神失常的情节在志怪小说中比比皆是。它无非是要告诉读者:鬼神怪异之事任常人多么心雄胆大,也不可不信;而且要解决问题最终只能依靠符咒。这些描写、渲染为我们理解符咒为什么盛行提供了基本背景。
志怪小说总是极力渲染符咒的神奇。道士为了自神其术,在符的书写方面费尽心力,使局外人一见便生诧异之心。一般说来,志怪小说对符咒形制、施用情况的描写都较为笼统,但有时也略加涉及。如《河东记》“李自良”条所述天符,“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广异记》“杨伯成”条记道士自荐前来驱魅,“书作三字,状如古篆”,尽管简单,却仍能给人以神秘之感。描写符咒施用情况的如《广异记》“赵州参军”叙卢参军之妻美貌,被阴司泰山三郎看上,暴病而卒。卢参军哭求颇善符咒的正谏大夫明崇俨解救,明氏给了他三道符。他连烧两符,泰山三郎都拒不放人。当烧到最后一道符时,竟卷起百余丈狂风,摧毁了泰山三郎的宫宇,甚至人物糜碎。三郎这才恐惧,卢妻得以复活。《广异记》记术士以符咒为害的情况尤为具体:苏丕女之婢“求术者行魇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彩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婢女死后,所埋七彩女还继续为害。符咒的作用之所以在小说中反复被强化,主要是人们寄希望于它们的神秘不可知的越自然、超人力的力量。
《抱朴子·道意》说:“任自然无方术者,未必不有终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横枉,大疫流行,则无以却之矣。”[10](P177)说方术可以却暴鬼之横枉、大疫之流行,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方术中包括医术,用医术解除大疫是有科学根据的;说它不对,是因为鬼由心生,用符咒之类的方术来驱除暴鬼、解除大疫,无异于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但符咒一类的方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它至少可以起到精神化解或心理缓解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道教徒用符咒治病、除邪其实也往往就行用了医术。盖建民说:“道教医学符咒治病术之所以会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并非像道书所宣扬的那样,是符咒本身所具有的神力,其实质是道门在施符念咒一套法术背后暗含着某些药物治疗或精神心理治疗的因素。”[11](P69-79)这讲的是符咒施行时的实际情况,一般志怪小说则未能深入描写符咒施用时兼用药物的细节。
其实,部分志怪小说中所写的某些人的精神变异,是可以推想其现实原因的。例如《广异记》“杨伯成”条记文辩无双的狐精吴南鹤向杨伯成请求与其女结为良缘,杨伯成认为女子当因媒而嫁,不肯允诺,吴南鹤竟“径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这行为颇为违礼,杨家人嗔责。可杨氏却很中意,对父亲说:“今嫁吴家,何因嗔责?”后其女为吴南鹤所“惑”,杨家人千方百计请道士施符,才让吴南鹤恢复狐形。家人庆幸,可杨女却大惑不解,惊云:“本在城中隔子裹,何得至此?”今天的人们一看便知,吴氏女虽因“狐媚”导致神魂颠倒,却并非真正的受害者;相反,她是颇受用这种“狐媚”的。这是因为在“狐媚”的“妖氛”之下,隐藏着她追求自由婚姻的理想。
《广异记》“长孙无忌”条叙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美人,美人因狐媚而持长刀斫刺无忌。崔参军行符,制服了狐,美人之疾遂愈。这故事其实都反映了当时女子对婢妾制度的不满。所谓道士施符消除狐媚,可理解为她承受不了压力而向现实屈服。符咒在此充当了替封建婢妾制度辩护和柔服人心的角色。
三 六朝至唐代志怪小说符咒元素之叙事功能
志怪小说对符咒的叙述一般有三种模式,其功能也各不相同:
第一种模式是直叙符咒故事。例如《搜神记》第26条直叙东晋著名道士吴猛三次施行符咒之事,《异苑》卷八第13条直叙武昌太守张春责成巫师以符咒消灭蛇、龟、鼍三物为祟之事,《广异记》直叙道士叶静能赠符与其弟子王苞迫使老狐精露形绝迹之事,它们的重心都放在符咒本身功用之描述,虽然偶尔也穿插一些形象描摹,但总体上流于简单。因多是直叙,淡化时空背景,立体感不强,故事铺展不开,情节较少曲折,篇幅自然也不长。这类故事,尚未脱离一般笔记的直叙手法。
第二种模式是以符咒作为连接情节的叙事元素。符咒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使情节变得生动曲折。例如《广异记》叙罗公远制服老狐的故事。首叙汧阳令(不知姓名)忽欲出家,见菩萨坐在狮子上,叮嘱他要坚持坐禅求福。汧阳令于是闭门不食者六七日,家人忧惧,恐其损寿。恰好著名道士罗公远经过,汧阳令之子向罗公远请教父亲的病情,罗公远道是天狐作祟,书符数道,宣称施符后汧阳令病情即可痊愈。汧阳令之子按叮嘱投符于井,父遂开门,子见父饿惫,逼父吞符。父亲于是明悟,不再言修道之事。故事到此似可终局。但接着作者又翻出波澜:数年后汧阳令罢官过家,居于郊外,有自称刘成的人带着十余骑前来,说汧阳令当年曾亲口将女儿赐与自己,如今女儿已十六岁,要同她成亲。汧阳令不允,刘成便“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汧阳令只得被迫应允。成亲后家人见其资产丰厚,也不嫌弃。此为皆大欢喜之结局,故事至此也可告一段落。然而汧阳令之子却又平地起浪:他远上长安求罗公远,罗公远说:“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箓,吾所不能及,奈何!”在汧阳令之子的苦苦求告下,罗公远才答应同刘成交战。罗与刘斗法,大战了数十回合,直到罗使出狡计,刘才被擒获,变成老狐,罗以袋装着他回京。罗既已获胜,故事自然也应该结束了。可是罗见唐玄宗后,说此狐乃是天狐,不可以杀,要求将它流放到东裔。于是罗书符将刘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所以“今新罗有刘成神,士人敬事之”。至此故事才以喜剧谢幕。这实际上是一个佛、道斗法的故事,老狐与罗公远难分胜负,暗示着佛道实力彼此相当,最后老狐虽遭流放,却成了东裔士人敬事之神,则隐示佛道仍能兼容,仍能分庭抗礼。故事始终以符咒作为叙事线索,一波三折,情节引人入胜。
第三种模式是先不提符咒,而是叙写主人公之遭际,极尽人情,待读者跟着人物悲悼嗟惜、引领望救之时,再引入符咒以解其艰厄,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于悲喜交加之际享受某种审美愉悦。从叙事视角看,这类故事当中也颇多转换之例:它们或用全知视角,或用限知视角,且多设悬念,能紧紧吊足读者胃口,抓住读者之心。
这类故事以唐代志怪小说为多。例如《广异记》叙仇嘉福故事。仇嘉福从京兆富平入洛应举,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相与交往,自称姓白,说仇氏命相与之有旧。数日后仇氏随白进入华岳庙,白氏一一阅视诸神,要求仇氏回避。仇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掀开帐幕,竟看见自己的妻子被悬头于庭树之上,细想妻子必死,于是心色俱坏。白氏事毕见仇氏脸色不好,问其故,仇氏以实对。白氏慨然为之解救,要他立即回富平,并安排神仆相送。仇氏“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故事至此虽可结束,但白氏究竟是何许人,他是用什么手段救活仇氏之妻的?前文都无交待,给读者留下悬念。作者接着叙述第二个故事:
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
原来白氏是先致钱二百千,再用符召岳神才救活崔氏之妻的。这一方法,自然也可用于救仇氏之妻。这样就在第二个故事中交待了第一个故事未交待的情节。以上都是用全知视角叙述。至于岳神怎样放回崔氏之妻的细节,就用限知视角,让崔氏之妻自己描述阴间所见所闻。直到最后才点出白氏的真正身份:原来他乃天宫之太一神。至此读者心中悬念才一一解除。此故事既写出了仇生对妻子的眷念,又写出了白氏(太一神)为人的侠义,还在不经意中写出了天宫也需贿赂与强权并行才能成事的情景。故事在充满人情味的气氛中展开,又在充满人情味的气氛中结束。符咒作为叙事元素在仇氏妻的故事中并未点出,而在崔氏妻的故事中才得到昭示。《宣室志》卷八叙陈岩遇白猿的故事,《广异记》叙杨伯成之女遭狐媚的故事等等,都能于曲折叙事之中曲尽人情,给读者以审美快感。
以上两类尤其是第三故事已属传奇,体现了作者对符咒元素运用的巧妙娴熟,对后来志怪小说的进一步人情化、故事化有深远影响。
[1] 许慎.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 刘晓明.中国符咒文化大观[M].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3] 李远国.道教咒术初探[J].宗教学研究,1999,(2):47-54.
[4]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第126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 牛僧儒.玄怪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2.
[6]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第1042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 刘仲宇.道教法术[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8]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祭义[M].沈啸环,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十二·订鬼[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登涉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盖建民.道教符咒治病术的理性批判[J].宗教研究,1999,(4):69-79.
Ideological Immanence and Narrative Function in the Mythical Stories of Six Dynasties to Tang Dynasty
L ISheng-long,ZHANGBi-bi
(College of Liberal A rts,Hunan No 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e destricrip tion of charm s in themythical stories not only includes very strange things and miraculous supernatural,w hich treats an illness,eradicates disaster,exo rcises evil spirits,and maintains a dwelling house so that it solves the p roblem s resulting from spiritson the traditional rationalism,becomes important different hunting curious materials in the ghost stories of Six Dynasties to Tang Dynasty,and imp lies p lentiful ideas,but also has narrative function that directly narrates stories,connects p lot,and makes readers enjoy a certain aesthetic p leasure,w hich show sw riters ingenious skill in the novel narrative that has deep ly influences on the follow ed mythical stories.
mythical sto ries;charm s;spirit;ideological immanence;narrative function
I206.2
A
1008—1763(2011)02—0073—05
2010-09-03
李生龙(1954—),男,湖南祁东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