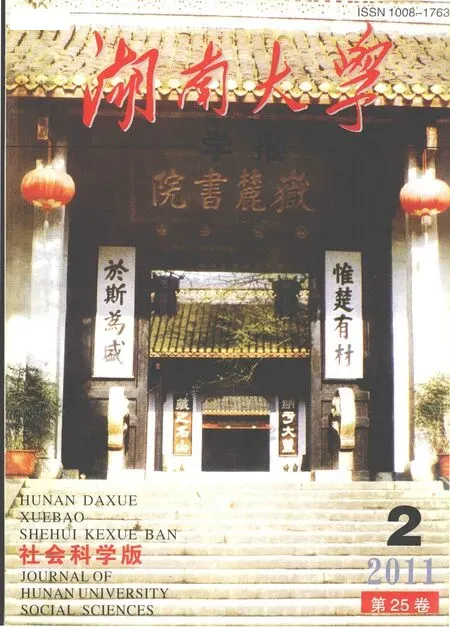论保证期间*
高晓莹,杨明刚
(1.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44; 2.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论保证期间*
高晓莹1,杨明刚2
(1.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44; 2.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我国司法解释及实践中,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在学说上存在较大争议,法律适用上也出现了逻辑矛盾、价值判断混乱等诸多问题。而将保证期间定性为诉讼时效,则既有理论支撑,更能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应根据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则对保证期间制度进行重构。
保证期间;除斥期间;诉讼时效
在我国学说、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保证期间是一个重要但歧见纷呈的问题。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保证期间性质的认识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保证期间属于诉讼时效,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二是认为,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因为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三是认为,保证期间属于特殊的除斥期间,因为保证期间具有除斥期间除权的主要特点,但《担保法》又规定保证期间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1](P132-133)四是认为保证期间在性质上为一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既非时效期间,也非除斥期间。[2]概括起来,核心的争论在于,保证期间是一种诉讼时效期间还是除斥期间。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对保证期间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对保证期间性质的不同确定,将直接影响债权人和保证人的利益平衡和分配,导致一系列不同的法律后果。现行立法对保证期间性质的规定是模糊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更有探讨的余地,需要在进一步检讨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保证期间制度。
一 保证期间与除斥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按照参与制定该司法解释人员的权威解释,该条的意义即在于确定了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的性质。其将保证期间性质界定为除斥期间主要有如下理由:一是,保证期间是保证合同的效力存续期间,保证期间届满即发生权利消灭的后果。《担保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保证人免除责任。上述规定即被认为是我国法律对保证期间届满后产生除权效果所作的规定;二是,《担保法》第25条规定,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换言之,在此之前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保证期间并非诉讼时效;三是,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期间,是从债权人的权利在客观上发生时起算,而《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遭受侵害之日起算,侧重债权人的主观状态。[3](P141-142),[1](P133)
司法解释明确将保证期间规定为除斥期间,消除了《担保法》在此问题上的模糊性,使保证期间的性质得到了明确确定,其司法实践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担保法》的原意,带有立法解释的性质。并且,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的理由并不充分,既缺乏现行立法的支持,在价值选择上也存在冲突,逻辑上欠妥当,更无理论上的依据。
(一)将保证期间认定为除斥期间,没有现行立法的充分支持
首先,《担保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在保证期间,债权人未按规定方式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有人据此认为这与诉讼时效不能消灭权利本身,仅能消灭胜诉权的特点有差异,而与除斥期间的规定性相吻合,这是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界定为除斥期间的最为核心,也最为关键之所在。
我们认为,《担保法》的上述规定本身并不意味着保证期间届满对债权人具有除权(权利消灭)的意义。因为所谓“除权”是从债权人角度讲的,是指债权人对保证人不再享有任何程序上和实体上的权利,即不仅丧失胜诉权,实体权利也予消灭。而《担保法》的规定是从保证人角度讲的,规定的是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即仅指其免受国家强制力的执行,并不能当然得出保证期间届满具有消灭债权人的实体权利的意思。相反,从我国民事制度整体而言,将《担保法》第25条、第26条的规定理解为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丧失胜诉权,制度上更为和谐,语义上也更为准确。在我国民法理论上,将债务和责任作了区分,对于债权的实现而言,债务人自愿履行其债务,属于债权的自然进行状态;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由债权人通过诉讼强制其履行,属于债权的不自然进行状态,此即现代所谓的民事责任。[4](P1-2)债务是法律或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当为的行为,民事责任是当事人不自愿履行义务,由国家去强制其履行。用国家强制力去保障义务得以履行是对原义务的替代,亦即民事责任是义务的转化形态,它比民事义务多包含了一层国家的强制性意义。保证责任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这里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与在其他责任类型中,因时效届满,原权利人丧失胜诉权,原责任人不再承担被强制执行的后果的表述并无差异,字面上应指免除了保证人受国家强制力而履行保证义务的风险。从债权人的角度则是排除了债权人通过诉讼获取国家通过强制力来确定和保障其债权实现的权利,债权人丧失的仅仅是胜诉权,其实体权利是否丧失,法律上并未规定,解释上应认为债权人仍享有实体权利。因此,我们认为,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法律规定,仅仅意味着保证人不再承受败诉的风险和强制执行的风险,在期间届满后,保证人自愿履行保证债务,应予准许,并应产生与一般自然债的履行相同的法律效果,保证人不能反悔要求返还。
其次,《担保法》第25条明确规定,“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直接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显然与法律的明确规定相抵触,有越权解释之嫌。同时,《担保法》还明确规定保证期间允许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连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法官都承认“这一规定与除斥期间的特点有一定的出入”。[1](P133)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作为除斥期间的另一项理由是,保证期间的起算是从债权人的权利在客观上发生时起,例如,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这与诉讼时效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的起算,从而侧重债权人的主观状态有异。我们认为,该项理由是难以成立的。《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这是对整个民事制度中诉讼时效起算作出的抽象概括。实践中,对各种具体的权利行使期间,尚需通过权利的具体情形来判定,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往往需要通过客观的事件来外在表现。就合同之债而言,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通常都是以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仍不履行这一客观事实的出现作为判断的标准,这并不仅仅是对保证债权的独特现象,而是对整个合同之债通行的判断方法。以保证期间是从债权人的权利在客观上受到损害起算,来否定保证期间的诉讼时效特性,显然缺乏说服力。另外,我国现行法上,不乏除斥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的规定。例如,《合同法》第55条第1款规定,撤销权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这里所规定的1年是典型的除斥期间。因此,不能因为《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期间是从债权人的权利在客观上发生时起计算就认为其起算与诉讼时效有别,从而将保证期间划归除斥期间之中。
(二)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价值判断上也相互矛盾
第一,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使得同一保证债权前后用不同的期间制度调整,存在逻辑冲突。在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的情况下,按其特性为固定期间,不得中断、中止或延长,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按法定方式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甚至向法院起诉均不发生期间中断的效果,而是使保证期间失去作用。但此时保证债权继续存在,仍需期间制度予以调整。为此,司法解释采用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连接的办法来加以克服和解决。“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人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同一项保证债权的行使期间,在债权人行使权利的前后,分别由具有不同价值的制度来调整,显然没有合理的理由予以支持。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尚未行使权利之前,该权利的行使由除斥期间进行调整,而在债权人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方式主张权利后,权利的行使期间则由诉讼时效制度进行调整。在债权人主张权利前后,其享有的权利均是针对保证人的请求权,在性质上并无本质变化,却需由两种不同性质的期间制度予以调整,这在逻辑上存在冲突,也人为地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造成理解和适用上的繁琐和困难。
第二,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增加了保证人的期间负担,导致了价值选择和判断的矛盾和混乱。一方面,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其目的之一是为了限制和减轻保证人的责任承担。由于保证责任不同于一般民事责任,保证人是为他人的债务承担责任,在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三者的关系中,保证人通常所承担的是单务的无偿的法律责任,并不享有要求对方对待给付的请求权。因此,法律有必要设定一段特殊的不变期间加以限制,以弥补适用诉讼时效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止保证人无限期的承担保证责任。[5]此即为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的价值考量上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后,由于保证债权的实现最终需要保证人的履行,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按规定方式主张权利后,保证债权不再属于作为除斥期间的保证期间的调整范围。此时对保证债权的行使期间,司法解释不得不采用与诉讼时效相连接的处理模式来解决,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保证人的责任承担。因为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内债权人依规定方式行使权利后,保证期间消灭,保证债权的行使期间由诉讼时效制度进行调整。其结果是,保证人承受了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双重期间负担,这无疑又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与上述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的价值选择本身是存在冲突的。
第三,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还将使保证人和主债务人在追偿问题上陷入困境。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债权的行使期间分别受到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制度的双重调整,这就意味着保证人在期间上的负担通常较主债务人更重,在主债务已过诉讼时效而保证债权仍在有效期(不管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期间)内的特定情形下,将出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能否向主债务人追偿的疑问。如果允许保证人在履行保证责任后仍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向主债务人追偿,则主债务人原本受到的诉讼时效规制就形同虚设;而若限制保证人的追偿权,保证人承担责任后不能再向债务人追偿,则对作为第二性义务承担者的保证人又难谓公平。由此可见,司法解释的上述安排,将使保证人在追偿问题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有人认为,保证期间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间,保证期间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责任免除期间,而不必要也不应该归入到现有的诉讼时效期间或者除斥期间之中,并由此得出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属于互相排斥、不能兼容的期间形态的结论。[6](P216),[2]持此观点者认为,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有诸多类似,但二者也存在区别,表现在:(1)保证期间首先是约定期间,其法定期间为任意性规定,在没有约定时适用法律的规定。而诉讼时效为强制性的法定期间。(2)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实体权利丧失,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债权人仅丧失胜诉权。据此得出了保证期间非为诉讼时效期间的结论。
我们认为,以上述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差异来否定保证期间属于诉讼时效期间,从而将保证期间作为一种特别的权利行使期间,值得商榷。保证期间具有诉讼时效的基本属性,用诉讼时效的规则来规范保证期间,在逻辑和价值衡量上都更具妥当性。
其一,保证期间可由当事人约定,但并不能简单地以此将其排除在诉讼时效的范畴之外。
保证期间确可由当事人约定,且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才由法定期间调整。这是否是将保证期间排除在诉讼时效之外的充分理由呢?此即涉及到诉讼时效是否均为强制性的,能否由当事人约定的问题。对此,立法、学说上有不同观点和做法。一种观点认为,时效期间的规定,系强制性规定,非有特别明文,不得加长或减短。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7条规定:“时效期间,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之。”《瑞士债务法》第129条亦采此说。第二种观点认为,长期时效期间不得加长,而短期时效期间在长期时效期间范围内可酌量加长。《俄罗斯民法典》第49条从此规定。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时效期间的加长,有害于公益,而减短时效期间,则与公益无碍,且不反于时效制度的精神,应认为其有效。[7](P381)德国民法中,对诉讼时效的约定问题明确持有限制肯定的态度。《德国民法典》第225条规定:“法律行为不得排除或加重时效。允许减轻时效,特别是缩短时效期间。”解释上认为,诉讼时效(消灭时效)具有法律警察的性质,要求债权人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但这仅说明诉讼时效法的一部分具有强行法的性质,第225条即规定了诉讼时效可以减轻,但不得排除或加重。[8](P93)亦即,在德国法上,对于排除或加重诉讼时效的规定为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作出的排除或加重诉讼时效的约定是无效的,但该法允许约定减轻诉讼时效。因此,是否可由当事人约定,并非诉讼时效的本质属性,诉讼时效是否完全由法律规定而具有强制特性,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立法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保证期间可由当事人约定显然并不是其不适用诉讼时效调整的充分理由。
我国通说认为,《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不得由当事人依自由意思予以排除,时效期间不得由当事人协议予以加长或缩短。当事人关于排除时效适用、变更时效期间或预先抛弃时效利益的约定,应为无效。[9](P236)我国司法实践也一直采取此种观点。从实然角度而言,诉讼时效期间在我国法律中具有强制性,不得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而保证期间可由当事人约定,因此显然不能由诉讼时效制度予以调整。但从应然角度看,我国现行立法和学说所持观点存在探讨的余地。法律上设诉讼时效制度来限制权利的行使期限,其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防止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长期持续存在,以稳定现存的法律秩序。亦即,诉讼时效制度系为公共利益而对权利人利益的限制,它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权利人及其相对人,而且还包括了以权利不行使事实状态为基础发生的种种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当然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排除或延长,否则即违背了时效制度设立的宗旨,将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但是,当事人约定缩短诉讼时效,这仅是受诉讼时效期间保护的权利人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自主选择,与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并不冲突,且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尽快稳定,对公共利益非但无损,而且有利,在立法政策上显然没有予以禁止的理由。因此,期间的法律强制性并非诉讼时效的本质规定性,诉讼时效是否均为强制性的,是否允许当事人约定减短时效期间,取决立法政策的选择。从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在合理性而言,允许当事人约定减短时效期间更为妥当。鉴于此,从应然角度看,在保证合同领域,以保证期间可以由当事人约定即简单地否定其不是诉讼时效期间,缺乏合理的理论支持。
其二,将保证期间界定为保证债权行使的诉讼时效期间,在理论上更符合保证债权的权利属性。
保证期间是债权人能有效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保证债权的期间,它具有诉讼时效的本质特性,即保证期间的调整客体为作为请求权的保证债权。在学说上,以权利作用为区分标准,可以将民事权利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四种类型。形成权的行使,由除斥期间制度调整,期间一经届满,形成权即告消灭,不需再对其提出抗辩。而请求权的行使期间,由诉讼时效制度调整,且诉讼时效适用于几乎所有的请求权,只有极少数的请求权,法律规定例外地不适用诉讼时效。[8](P89-91)因此,对请求权而言,学说上通常均将其作为诉讼时效的调整客体。“请求权消灭时效之原因与宗旨,乃使人勿去纠缠于陈年旧帐之请求权。……盖若权利人非于请求权之行使置若罔闻,消灭时效本无发生之由,故权利人于请求权内容之利益,实属微不足道,其因此付出之代价,亦难谓严酷也。”[8](P291)
在保证关系中,债权人对保证人享有的是保证债权,是请求保证人为保证义务的权利,在债权人按规定方式主张权利之前或之后,债权人主张的都是同一权利,无疑应归属请求权之列,同时,也并没有公共利益的要求或权利自身特殊性的要求使其例外的不受诉讼时效的调整。从比较法上进行考察,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对权利行使期间的一般性限制规定,除法律有例外规定时请求权的行使不受诉讼时效调整外,对一般请求权行使的期间,均通过诉讼时效制度来解决。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均将保证作为一种合同之债予以规定。概而言之,基于保证债权的权利属性,解释上将行使保证债权的期间归属诉讼时效的范畴,更为妥当。
其三,将保证期间确定为诉讼时效,可以与《物权法》对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新规定保持体系上的协调一致。
对于抵押权的行使期限是否为诉讼时效的问题,学说上存在分歧,有人将其归纳为三种不同认识:一是物权的存续不受诉讼时效的影响,诉讼时效仅约束债权,故抵押权的行使期限并非诉讼时效;二是认为物上请求权属于请求权的性质,应受诉讼时效的影响;三是主张物权的存续不受诉讼时效影响,但物权中与债权性质相同的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影响。[3](P89-90)而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抵押权的行使期间性质如何确定前后有较大变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权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二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据此,其对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行使期间采用了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挂钩的方法,将其确定为主债权的诉讼时效再加二年的不变时间,整体思路与该司法解释对保证期间的性质确定相同,是将抵押权的行使期间作为除斥期间进行处理。而《物权法》则对此作出了重大调整,该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虽然由于抵押权的物权属性,对上述法律规定的抵押权行使期间是否为诉讼时效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物权法》所规定的抵押权的行使期限已完全摆脱了司法解释将其确定为除斥期间的定位。并且,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从法律效果考量,物权法规定的抵押权司法保护期近似于抵押权的“诉讼时效”,因为其与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10](P275)因此,《物权法》对作为物权的抵押权行使期间,已按照诉讼时效的方式进行了规制,而保证债权为一种债权,将其司法保护期限确定为诉讼时效,既无理论上的障碍,更可与《物权法》新的立法精神相统一,从而在法律制度和规则的确立上更能保持体系协调。
其四,将保证期间确定为诉讼时效,更能实现债权人、主债务人、保证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合理解决相同或类似问题在规则适用上的不合理冲突。
在有担保的法律关系中,对债权人而言,主债务人、保证人均是其债务人,但由于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而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权利行使则受诉讼时效规则调整,导致了债权人对主债务人和保证人权利行使方面的冲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在期间届满后债务的“起死回生”问题上,我国司法解释对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不得不适用不同的规则。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第90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4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即同样是期间届满后在催款通知书上的签字行为,对主债务人和作为从债务人的保证人而言,将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显然欠缺正当性。而造成这种割裂的唯一原因,就是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如果将保证期间确定为诉讼时效,将保证债权与主债权的司法保护期间相统一,则可以很好解决上述矛盾和冲突。
三 我国保证期间制度的重构
如上所述,在我国,由于《担保法》对保证期间性质的规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担保法司法解释”则明确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不能中断、中止和延长,导致了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冲突。同时,司法解释通过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之间的连接关系,将保证债权的行使期限变得复杂化,产生了认识和适用上不必要的困难。而将保证期间在性质上确定为诉讼时效,或者至少参照诉讼时效制度来解决保证期间问题,既有理论支持,在制度价值上更具妥当性,逻辑上也更为周延,且在适用上较为简便易行。
在将保证期间确定为诉讼时效的框架下,需从如下几方面对我国的保证期间制度进行重构:
第一,在保证期间的确定上,可借鉴《物权法》对抵押权司法保护期间的规定,以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作为保证债权的行使期间。这样处理,避免了保证债权因时点不同而需不同期间制度调整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得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有效衔接,也能保持各方利益的基本平衡。同时,因保证人通常具有为他人无偿承担债务的特性,为保护保证人的利益,鼓励更多的民事主体担当保证人,可允许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但该约定只能缩短保证期间,不能延长保证期间。如此,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体现了通过保证期间保护保证人利益的价值选择。当然,将保证期间确定为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约定保证期间,这仍有待于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在是否有条件地允许当事人约定的问题上作出立法政策上的新选择。
第二,关于保证期间中断的适用。对一般保证,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保证期间中断。自裁决生效之日起①对于保证期间何时重新计算,尚有争议,如前述高圣平认为应从“保证债权可得行使时”重新计算。,按照法定或约定的保证期间予以重新计算。在新计算的保证期间内,还可因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或者保证人同意履行等,产生新的中断。对于连带保证,在保证期间内,因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或者保证人同意履行等,即发生保证期间中断。这样处理,与“担保法司法解释”的模式截然不同,而与现行《担保法》第25条第2款后项“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保持一致,并使得期间制度对同一债权调整上统一起来,在保证期间设立的价值取向保持了统一性。
第三,关于保证期间的中止的问题。中止是指在时效期间即将完成之际,有与权利人无关的事由使权利人无法行使其请求权,法律为保护权利人而使时效期间暂停计算,待中止事由消灭后继续计算。《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担保法》中未规定保证期间的中止。在债权人和保证人的关系中,法律需对二者利益进行平衡,在保护保证人利益的同时,也需对债权人的利益予以足够的关注,使债权人通过设定保证的方式保障债权实现的目的尽可能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交易安全,这也是法律创设保证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我们认为,保证期间也应适用中止的规定,在保证期间即将完成的一定期限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因债权人原因不能行使请求权的事由的,则保证期间中止,这可使得无过错的债权人利益得到妥当保护,对保证人而言也无不公平之虞。
第四,关于保证期间的延长问题。在诉讼时效中,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对20年的最长时效期间,遇有特殊情况的,可由人民法院决定延长诉讼时效期间。这里的特殊情况,是除不可抗力或一般客观障碍以外的情况。学者认为,我国立法规定20年诉讼时效期间的延长,针对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长期不统一的特殊情况,一旦两岸统一,使两岸同胞数十年不能行使的权利,可通过对20年时效期间的延长获得法律保护。[15](P249)这些多发生在因侵权产生的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领域,对于保证合同来说,诉讼时效的延长基本无适用的余地。
第五,关于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责任的承担。按照诉讼时效规则处理保证期间问题,与将保证期间确定为除斥期间会产生迥然有异的结果。保证期间届满后,债权人仅丧失了胜诉权,其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此时,如果保证人自愿履行的,并不存在不当得利问题,不能再事后反悔要求债权人返还。同时,在保证之债的“起死回生”问题上,只要保证人在催债通知上签字、盖章,即应视为其对保证债务的重新确认,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拘束力。这就与主债务人在催债通知书上签字、盖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二者之间可保持有机统一,在价值衡量上更具妥当性。
[1] 曹士兵.中国担保诸问题的解决与展望[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 孔祥俊.保证期间再探讨[J].法学,2001,(7):55-59.
[3] 李国光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4] 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5] 窦玉梅.探索于民法中最活跃的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奚小明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N].人民法院报,2000-12-15(03).
[6] 高圣平.担保法新问题判解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7]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8]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9]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10]曹士兵.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On Guarantee Period
GAO Xiao-ying1,YANGM ing-ga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2.Research Centre fo r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There is biggish controversy in w hich the nature of guarantee period is determined as scheduled period during judicial interp retation and p ractice.There are also logic contradiction and value judgment confusions in legal app lication of it.Provided that the nature of guarantee period is determined as the p rescrip tive period,w hich ha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hall realize the interest balance among creditors,debto rs and guaranto rs.Therefo re,guarantee period shall be reconstructed acco rding to the relevant rules on the p rescrip tive period.
guarantee period;scheduled period;the p rescrip tive period
D924
A
1008—1763(2011)02—0130—06
2010-11-12
高晓莹(197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交通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