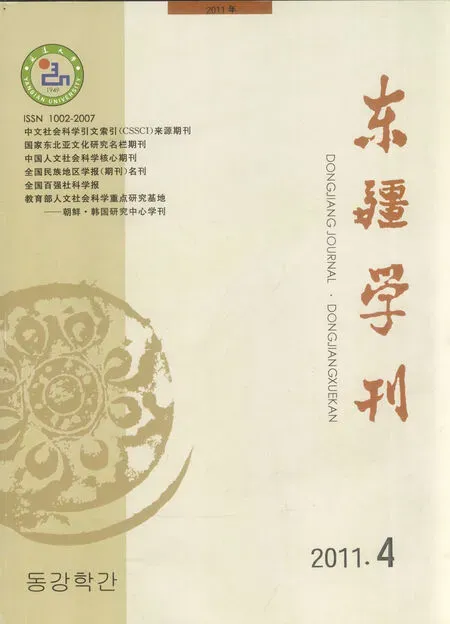试论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
徐东日
试论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
徐东日
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满族认识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即18世纪上半叶之前,朝鲜朝燕行使臣由于受到“华夷观”的影响,将满族人视为“蛮夷之族”,言语中多有蔑视之意;他们也描述了清军野蛮的暴行,揭露其人性残忍的一面。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的所见所闻,对满族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改变。在他们笔下,满族人的形象开始具有正面色彩,这集中体现在满族人的强壮、具有顽强生命力以及长于骑射、崇尚武功等方面。
朝鲜朝燕行使臣;满族人形象;负面;正面
在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清代中国“形象”①比较文学形象学所指的“形象”是指“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和异国人的体貌特征以及人种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研究这种看法是如何文学化,同时又是如何社会化的。”转引自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页。的描述文字中,对满族人形象的塑造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满族是清王朝的统治民族,他们在清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满族人的形象就代表着清代中国的主要形象。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不少朝鲜人(尤其是朝鲜朝士大夫)出于以“礼”为文明基准的“华夷观念”,认为满族人是不懂得“礼”的野蛮的“夷狄”,而朝鲜是继承了孔子之“礼法”的“小中华”,所以,他们在朝鲜朝初期一直将满族人视作是一种负面的形象。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满族人称作“胡”。
一、“胡”的辞源与朝鲜朝语境中“胡人”形象的生成
(一)“胡”字是在将自我与他者分为“华”②“华”, 在古文献中也称作“华夏”、“诸夏”, 其主体为汉族。和“夷”③西周前,“夷”特指东方少数民族,《说文》:“夷, 东方之人也, 从大从弓”。春秋战国时, 始以夷总称四周少数民族, 如《谷梁传序》:“四夷交侵, 华戎同贯。”疏:“四夷者,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夷”作为一种蔑称, 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如“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君”(《论语·八俏》)。清代人撰写的《说文通训定声》解释此话的意思是“夷狄之俗, 非如华夏之民有礼义文章之美也”。即, 将“夷”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周围的少数民族的总称。这两种文化程度不同的民族的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在《说文》中,徐锴指出:
牛颔下垂皮也。
即“胡”字形声。从肉,古声。本义:牛脖子下的垂肉。
《诗·豳风·狼跋》:
狼跋其胡。
《汉书·郊祀志上》:
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
颜师古注曰:“胡,谓颈下垂肉也。”又如:胡髯朗(羊的别名。胡,颈下垂肉;髯,须);胡皱(牛颔下松弛有皱纹的皮);胡袋(某些鸟类颌下的皮囊,也称喉囊)。这样,“胡”一词后来泛指鸟兽颔下的垂肉或皮囊。
由此可见,“胡”一词起初是泛指非人的动物,即是指鸟兽颔下的垂肉或皮囊。所以,这种“胡”的含义,明显带有一种很浓重的贬义色彩。究其缘由,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人种学、人类学的层面上:由于古代生活在中国北方或西方的其他民族在相貌、体态以及举止行为上显现出比较“怪异”或“丑陋”的特征,这使得生活在中原的汉族人从心理上产生了某种恐惧感和拒斥力。
二是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由于古代生活在中国北方或西方的其他民族长期以狩猎为生、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手段,所以其文明程度较低,而生活在中原的民族(主要是汉族)早已处在农耕生产的文明阶段。因而,大概从夏代开始,中原就产生了儒家的“华夷观”,即强调厚华薄夷以及华夷之间的尊卑、亲疏关系,尤其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与国际间关系时,强调“华夷之辨”。
三是在世界观、政治理念的层面上: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模式形成了浓厚的“我族中心主义”倾向的文化思维模式,以后渐渐演化成“天朝模型”的世界观。其突出特征是以朝贡制度为媒介,使中国与周边民族或国家的封建宗藩关系得到空前的强化,并由此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种“天朝模型”的世界观,使中国人较少去了解异民族。而当他们与异民族相交往时,又往往给予不平等的待遇;对异邦之来中国通商则一律视之为向中国朝贡。这种文化心理实际上助长了中国最上层统治者、一般官僚甚至不少一般百姓虚骄自满、傲慢自大的习性,使自己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
(二)朝鲜在历史上也曾被中国称之为“东夷”,但朝鲜民族是一个勤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在自己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师法中国,广泛汲取中国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的文化营养,并和朝鲜固有的文化习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逐渐成长为礼仪之邦,这种文化上的不断进步,最后终于使得朝鲜民族充满了自信,并骄傲地以“小中华”自居。其结果,古代朝鲜人不仅已经“知文教”、“通王化”了,而且与周边那些尚未“知文教”、“通王化”的“四夷”①宋代学者石介在《中国论》中提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相比较,其文明程度都要高出许多,所以到了后来,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朝鲜已经与“华夏”几无二致,从而不断进行民族身份的重新认同,这使得朝鲜民族将自己划分在蛮夷之外,认为朝鲜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分支。这种观念,长期以来逐渐渗透到朝鲜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并进而形成一种稳定的文化“深层结构”,它又与朝鲜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相辅相成,从而具有与汉民族几近相同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价值判断标准。
正因为如此,当朝鲜民族面对比自己的文明程度低下的满族时,就会以一个文明人俯视野蛮人的姿态对其加以妖魔化的文学描写,指称他们是“胡人”。这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套话”②“套话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 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转引自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 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12 页。“此词原指印刷业中使用的‘铅板’, 后来被转借到思想领域, 指称那些一成不变的旧框框、老俗套。在符号学研究中, 人们再次借用了这个词。按照以色列符号学家吕特·阿莫希所下的定义,‘套话’就是人们‘思想的现成套装’, 亦即人们对各类人物的先入之见”。转引自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 载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185 页。,其符指意义就在于说明满族人是一个不曾开化的野蛮人。这些本来都是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谓,在此朝鲜却都依旧照搬了过来。此前,朝鲜人指称女真人的套话还有“小丑”、“野人”、“酋胡”等。这些词语,浓缩了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人对满洲人(或清朝)的社会总体想像。
实际上,朝鲜民族对满洲人(或清朝)的这种社会总体想像,是此前朝鲜民族对女真族形象描述的延续。而作为朝鲜朝语境中的女真人形象的源头,又当属朝鲜朝官修史书《高丽史》③《高丽史》是郑麟趾等人于1451 年(朝鲜朝文宗元年) 编撰完成的朝鲜有史以来最完备的一部断代体史书。。在此,我们不妨看看两则有关女真族的记述:
(1)《高丽史》太祖十四年(公元931年)“辛
卯条”载:
是岁诏有司曰:“北蕃之人,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忘耻。今虽服事,向背无常,宜令所过州镇筑馆城外待之”。
(2)《高丽史》“列传卷第七·李子渊条”载:
女真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
在以上引文中,作者是把女真人当作完全有异于朝鲜人的“异类”和饥来饱去的“兽类”进行描述的,很明显,他们这时尚未真正文明“归化”,跟一般文明人相比,表现为“向背无常”、“见利忘耻”,既不讲信义,也毫无礼仪可言。
可以说,《高丽史》之后出现的“《燃藜室记述》与《建州纪程图记》所描述的女真人形象,基本上是《高丽史》对女真人形象描写的延续,哪怕它们的描述与《高丽史》的描述相左,那也是由《高丽史》的‘历史的文本性’的权威地位所决定的”[1](29)。而纵观他们对女真人形象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力求突现女真人“向背无常”、“见利忘耻”、“畏威贪利”的一面。下面例举一条引文证实这一点:
建贼之于我国,壤地相接,其狺然欲噬之心,曷尝须臾忘哉!十数年来,佯言通好,约束诸部…虽有积怨于明朝,畏威贪利,乍示臣顺。知我国素事明朝,故不反明朝,其势不得不先侵我国也。今者,吞灭忽温,威服诸种,凶势日强,无复顾忌。袭破抚顺,仇我大邦。知我国不可得而和也,故投书遥喝,胁之以分击,欲使我国帖然退伏,不敢为明朝之援,其为桀骜何如哉
以上是咸镜道节度使金宗瑞呈给朝鲜国王世宗的奏折。
由这个文本,我们可以窥见女真人野蛮、富有攻击性的“侵略者”的形象。而这些对女真人形象的描述,在女真人缺席的情况下,又往往被掌控着其“话语霸权”的朝鲜朝士大夫们以各种文化形式加以“文本化”,反过来,这种“文本化”又作用于朝鲜朝民众的“社会总体想像”,通过这两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描述女真人的固定模式。同时,描述女真人“饥来饱去”、“人面兽心”、“见利忘耻”等在特定历史时期及特定文化语境中被一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朝鲜士大夫所使用的语汇,也在这种“文本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其与女真人之间的特定符指关系,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包含着固定内涵的象征性语言、一种包含着价值判断意义的文化符号,即套话。
二、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李等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胡人”形象
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描写清初中国形象的“燕行录”作品较多,但其中的主要作品要数麟坪大君李的《燕途纪行》。
盖闻伊时,孤城事去,守将战死,戎伍末卒并效忠贞,无一降者,以故清人大肆屠戮,人无噍类。[4](25)
锦松虽陷,古塔誓死不降,及城陷,人皆死节。清人怒其久不降下,夷城三山,屠城锦州。[4](23)
在这里,“人无噍类”,就是城中没有活着的人的意思。由此可见,清军的残暴已达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3](127-128)
(二)在历史上,满族比起朝鲜民族,其生活环境要恶劣得多,资源也比较匮乏。为此,满族统治者就垂涎于朝鲜的物质财富,发动了无数次侵扰朝鲜半岛的事件,使朝鲜民族备遭兵燹之祸。而在这些掠夺朝鲜财富与人口的残酷战争中,也就充分暴露出其人性残忍的一面。
所经道路蓬蒿蔽野,荻花如雪,麋鹿成群,人民萧条,剪径恣行,不遵法纲,征客颇苦。[4](18)
从朝鲜人描述满洲人时开始出现“残暴”这一形象的时间来看,这一阐释系统形成的源头是在“丙子胡乱”之后。“丙子胡乱”迫使朝鲜仁祖大王臣服于清朝,清军在达到目的后就撤离朝鲜。在北撤途中,他们还对家财丰盈的朝鲜宗室及士大夫大肆进行劫掠,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女眷,从而使朝鲜民族蒙受了巨大的民族耻辱。正因为如此,这场“丙子胡乱”在朝鲜人心目中既有的女真形象上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即“残暴”。而这也正是李等燕行使臣在塑造满族统治者形象时频繁描述其残暴行径的根本原因。
三、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眼中的满族人形象
倘若说,到18世纪上半叶为止,朝鲜朝燕行使臣在描述满族人时,还带有一些贬斥色彩,即由于频繁使用“胡人”这一套话,使得我们始终隐约地感受到存在着一种肃杀、紧张的气氛。那么时值18世纪下半叶,在朴趾源等朝鲜朝北学派人士的笔下,朝鲜人言说满族人的“胡人”这一套话(沿用两百年左右)就明显地减少了,描述满族人形象时也不再出现“威胁”、“攻击”、“侵略”等词语。与此相反,他们反而更多地使用呈现一种强壮、有力量的阳刚之美的描述文字,譬如,满族人长于骑射,崇尚武功,具有骑射①所谓骑射,顾名思义,并非专指射箭,尚有骑马技艺。的长技。可以说,满族人骑术的高超是非常出众的。燕岩朴趾源就由衷地称赞满族人擅长骑射乃其“家法也”。另外,比朴趾源早一年(1779年)使清的冬至兼谢恩使、书状官洪明浩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凤城至山海关外,民俗蠢强,专尚弓马”。[5](4688)这句话虽短,但在满汉对比中突出了满族人淳朴勇武、“专尚弓马”的民族气质,代表着当时朝鲜朝大多数燕行使臣的思想意识。满族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自入关前开始,清廷就督促各牛录额真,令其属下不分老幼,“春夏秋三时,勤于骑射”,从皇帝到各级官吏不时稽察,“如有不能射者,必治牛录额真之罪”,以便坚持并发挥满族人所独有的“制胜之技”。[6](4-5)同时,在全民中加强军事教育,命令无论大武官、小武官都要认真读兵书。由于经常进行军事教育,上上下下的人都懂作战。因此,形成清朝初年重要的国俗之一,即具有骑射长技。
正因为如此,为了防范满族人(清朝以前称满洲人)的进攻,李民奂在呈送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提出了六条整顿军备以抗衡女真的建议。其中,第四条指出:
臣观边塞苦寒,风气强劲。所居之人,习性悍勇,驰骋畋猎,乃其常事。[7](48)
应该说,这是李民奂对建州女真人的一个总体印象。《建州闻见录》的篇幅虽然不长,只有廖廖数页,但作者却屡次提及女真人“习性悍勇”,即便不直接提及女真人的“习性悍勇”之处,但由于作者叙事的生动,女真人的“悍勇”之气亦扑面而来:
胡性能耐饥渴,行军出入,以米末少许调水而饮,六、七月间,不过吃四、五升。虽大风雨寒冽,达夜露处。马性则五、六昼夜绝不吃草,亦能驰走。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7](44)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此将女真的强悍与朝鲜的疲弱进行了比较,并简单分析了个中的原因,总结了一些具有经验性的东西,作为“备御六条”,“昧死投进”,“以备圣明采览事”。
客观地说,朴趾源等朝鲜朝北学派人士是怀抱着“富国强兵”、“富国裕民”的目的而使行中国的,因而对满族的“骑射”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看,朴趾源等朝鲜朝北学派人士之所以对满族的“骑射”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且推崇满族人的骑射技艺,实际上也是受到了麟坪大君的《燕途纪行》、老稼斋的《燕行日记》等“先辈”“前文本”的影响与制约。“我们都知道,制作一个异国‘形象’时,作者并未复制现实。他筛选出一定数目的特点,这些作家认为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异国描述的成份”。[8](138)而满族人的“骑射”就是大多数燕行使臣所认为的适用于“他”要进行的关于满族人的描述内容。因而,朴趾源等人是在“利用厚生”这一功利目的及“先辈”“前文本”的影响下,才真正开始了对满族人“骑射”生活的观察与描述:
十六日壬戌,晴。平明发行,到王家营中火。过黄铺岭,有少年贵人,年可二十余,帽戴红宝石,悬翠羽,骑骊马,翩翩而去。只一骑在前,而从者三十余骑,皆金鞍骏马,帽服鲜侈,或佩弓箭,或负鸟铳,或擎炉,驰骤如电而不除辟呵喝,但闻马蹄之声。询于从骑,曰皇帝亲侄号豫王者也。[9](636)
在此,朴趾源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位华衣骑射的皇侄的雄俊形象。豫王年仅二十余,穿戴华丽,身份高贵,但并非是纨绔之子,他不仅骑马翩翩而行,而且是勇于“只一骑在前”,“驰骤如电而不除辟呵喝,但闻马蹄之声”。可见,朴趾源对满族皇室及其子弟的围猎讲武的描写是比较赞许的。这实际上也是对乾隆帝等清帝“国语骑射”政策的一种肯定,即他认为,不论是哪个国家,加紧进行骑射训练以致精善,对实现其“富国强兵”都很重要。可以说,在力图维持八旗满洲的“国语骑射”能力方面,乾隆帝较之康熙、雍正都有更大的建树。
四、北学满族人:改良马种、改变养马方式
(一)回顾一下明清交替之际,明朝军队联合朝鲜军队与满洲军队交战,联军竟然无法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骑兵相抗衡。那么,明朝军队和朝鲜朝军队同样也有戎马之足,可为何打不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呢?朴趾源等北学派人士都认为,这里除了人的因素之外,满族人的马匹因素是满洲军队在与明、朝联军作战时取胜的一个法宝。满族人的马匹所具有的一个独特优点就是满洲马种比起朝鲜马种更加“体大良善”[10](723)。从文献记载可以得知,关东马应是以满洲马(即“胡马”)为主,而满洲马种有其固有的特色。[11](357)然而满洲马种并非纯种,有相当数量是与蒙古种杂交的混血种,或称蒙古种,所以康熙年间,认为“关西马皆产于蒙古”。或者是因为部分地淘汰了原有的马种,多从了蒙古马种,所以,有女真人多“从蒙古那里得到良马”之说。对此,《蓟山纪程》的作者指出:
李民奂也在《建州闻见录》中写道:
臣闻胡中之养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而放之……我国之养马异于是,寒冽则厚被之,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步……甲胄则不坚不密,重且龃龉。弓矢刀枪则歪弱钝弊,不堪射刺。炮铳则四五放,多有毁裂者。其它诸具,皆非着实可用之物……[7](47)
与满洲马或蒙古马相比,朝鲜马则是另一个品种,主要产地是朝鲜全罗道的济州,[13](26)它不是“体大性驯者”,而是在东方矮小马种中属于最小的品种。对此,朴趾源比较分析了朝鲜和中国在马匹繁殖及其品种改良方面的现状。他写道:
今中国,……马骡生而不骏且毛色不佳、性不驯调,则必攻去其睾子,令毋得易种,且独令特大而性易调良。我东监牧不此之思,惟以土产取种,弥出弥小,虽驮溷栽柴犹恐不堪,况堪为军国之需乎?此产非佳种者也。[14](633)
我东牧场惟耽罗最大,而马皆元世祖所放之种也,四五百年之间不易其种。[15](632)
于是,朴趾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从中国购买几十匹优良种马,放牧在草地,逐渐增加繁殖数量、改良其品种。即:
及今两国升平之日,诚求牝牡数十匹,大国必无爱此数十匹。若以外国求马私养为嫌,则岁价潜购,岂无其便?择郊甸水草之地,十年取字,渐移之耽罗及诸监牡,以易其种。其蕃孳之法,当以《周礼》及《月令》为率。[14](633)
满洲人畜牧业兴旺的原因,除了因为拥有自己的优良马种之外,还由于满洲人为发展自己的畜牧业、加强军事力量,常常利用自己善战、马匹优良的优势,以突袭的方法侵入朝鲜,掠夺朝鲜的马匹,以致使朝鲜马匹大量流向满洲地区。所以,朝鲜边官指出:“野人之强,莫盛于此时,兵强马良,非我国之利也”。[16](723)另外,满洲人也经常用自己的少数良马来换取朝鲜更多的马匹。譬如,明正德七年(1512年),朝鲜边将报告说:“以我牛、马七八头易胡马一匹,是以胡人马畜日繁。”[17](520)直到清代中、晚期为止,蒙古马仍然“倍价”于“高丽马”[11](357)。其结果,致使朝鲜朝马匹数量连年减少,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至嘉靖四十年(1563年)的短短半个世纪间,朝鲜朝北道农民相继出现了“无耕牛”或“驾马而耕”的现象,甚至出现“耕田之际,人代牛役”的惨痛局面。因为他们的牛、马“则尽归于野人”[18](652),即归于女真人。
正因为满洲马种比起朝鲜马种要“体大良善”,所以令朝鲜边防军羡慕不已。为了引进满洲马种,朝鲜国王曾经命令庆源、镜城的边官,以本国物产与建州猛哥帖木儿进行交易,将“体大雌雄种马”引进国内,以便“孳息”[19](370)。为了加强朝鲜北部边境的军事力量,咸镜道利用与女真杂居或近邻的便利条件,引进穆棱河马种,产马效果颇佳,即所谓“良马多产”。最后达到朴趾源所指出的“自内厩所养,至武将所骑,无土产,皆辽沈间所购,一岁中所出者不过四、五匹”[14](632)的良好效果。而这种严重依赖进口马匹的状况,则必然使人们滋生起“若辽沈路断,马何由来”[14](632)的担忧。
(二)导致满族人在与明、朝联军作战中取胜的原因,除了满族士兵善于骑射的因素与“体大良善”的马种因素之外,还因为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科学的养马方式。
其一是充分利用了满洲马的饮食习性。朝鲜朝边官在与之作战过程中发现:满族人的铁骑经常违背常规在夏季突然发动攻击。一般来说,出兵是在粮草丰盛的秋季,夏季出兵是人们难以想像的事情。即“且比贼好以盛夏雨水时,动兵犯抢”,对此,朝鲜朝边官和明朝军官只是猜测满族军队展开进攻“盖出其不意也”。[7](50)事实上,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是在四月,攻克开原是在六月,打下清河铁岭是在七月。透过满族军队频频展开的夏日攻势,朝鲜朝边官和明朝军官不会没有发现满族军队的这一战役规律。明朝户部给事中官应震就曾揭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即“建酋马喜食夏日河边柳英,递料其狂逞,不在秋而在夏也”。因为马吃了这种柳英后,“每一日食而三日饱,故建酋马独肥,而建酋兵独善用马。辽人习步不习马”,所以“建兵强,辽兵弱”[20](32)。由于辽东柳英遍地,随处可见,八旗军到了夏日,也就不必备足草料,即便只吃柳英也能做到“一日食三日饱”,从而提供更多、更便利的出战机会,这使得满族军队的战斗力变得极强。这种马性也构成了清军战胜明军与朝鲜军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二是充分利用满洲马耐劳的习性而加以驯养。李押在《燕行纪事》(1777)之“闻见杂记”中描述满族人畜牧马匹的的特点道:
马不牵辔,超乘驰骤,其捷如飞,即胡人之所长。虽值远行,路中不为喂饲,至宿处,脱鞍而后必待夜深,只给草饮水,行过七、八日,始喂熟太。[21](93)
满族人之所以这样驯养马匹,就是为了在饲养过程中顺适畜性。所谓畜性是在饲养环境中养成,即“胡中之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暂有卸鞍之暇,则脱而放之。栏内不蔽风雨寒暑,放牧于野,必人驱十马,马饲调习,不过如此”,[7](47)这种“驭马之道,盖与我国北路略同”。[21](93)而明朝和大部分朝鲜朝的马匹则在“寒冽则厚披之,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驰骋不过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夜无阙,是以暂有饥渴,不堪驰步,步遇险仄,不无颠蹶”,所以相对于满洲马耐劳的习性就显得“不合战阵”的需要[7](47)。对此,朴趾源以北学派思想家独到的眼光认为,“马政”问题不只关乎着朝鲜的“利用厚生”,而且还关乎着国家的安危,深刻影响着朝鲜的国防建设。
朴趾源还严厉地批评朝鲜朝士大夫不将“马政”视为一项强国之策反而“以为羞耻”进而不肯虚心向满族人学习牧马之术的做法。朴趾源甚至认为朝鲜的国力之所以贫弱,“盖由畜牧未得其道耳”。他恨不得自己躬身实践,探索出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来:
盖余之所取乎燕岩者,尝有意于畜牧也。燕岩之为区,在万山中,左右荒谷水草最善,足以养马牛羸驴数百。[14](632)
朴趾源以“燕岩”作为自己的号,就是为了体现自己立志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正因为作为北学派思想家的朴趾源致力于求索“利用厚生”的道路,以尽快改变朝鲜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他就赞美和夸大了满族人的畜牧能力,从而,他对满族人畜牧能力的描述也多少带有“理想化”的成份。朴趾源注意到中国放牧马、牛的方法:
余偶出门外,有马群数百匹过门而去,一牧童骑绝大马,持一蜀黍柄而随之。……于是闲行察之,则家家开门,驱出马驴牛羊,辄不下数十头。回看馆外所系我东鬣者,可谓寒心。[15](632)
朴趾源在亲眼看到中国放牧的现场后,分析人与动物都具有追求自由的自然属性,应该使它顺其自然,因而认为朝鲜驯马的方法很不正确、很不科学。他认为:
他还具体记述了马的生理特性、喂养方法及保健方法等:
何谓喂养失宜乎?曰渴之思水,有甚于饥食。吾东之马未尝饮冷,马之性最忌熟食,为其病热也。豆刍洒盐令咸,欲其饮水也;饮水,欲其利溲溺也;利溲溺,欲其泻热也;饮冷,欲其胫劲而蹄坚也。吾东之马,必烂豆烹粥,一日驰走已自病热,一站阙粥,平生虚劳,行旅迟顿,实缘熟喂,至于战马喂粥尤为非计,此其喂养失宜者也。[15](633)
就这样,朴趾源对朝鲜畜牧业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明确指出朝鲜的贫困与畜牧业的不振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尝试论之国俗所以贫者,盖由畜牧未得其道耳。”[14](632)
五、结语
归结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朝鲜朝燕行使臣对满族认识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即18世纪上半叶之前,朝鲜朝燕行使臣由于受到“华夷观”的影响,将满族人视为“蛮夷之族”。由于朝鲜民族具有这种“社会集体想像物”,所以,其使臣也不把满族人视为正族,言语中多有蔑视之意。与此同时,他还描述了清军野蛮的暴行,揭露其人性残忍的一面。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通过燕行的所见所闻,对满族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改变。这一时期,在他们笔下,满族人的形象开始具有阳刚之美的正面色彩。这集中体现在满族人的强壮、有顽强生命力以及长于骑射、崇尚武功等方面。他们认为:清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正是体现了满族先进的文化要素。
[1]刘广铭:《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2]李肯翊:《燃藜室记述选编》,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排印版,1980年。
[3]陈尚胜:《朝鲜王朝对华观的演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6]《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三。
[7]李民奂:《建州闻见录》,《清初史料丛刊(第九种),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排印版,1979年。
[8][法]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9]朴趾源:《热河日记》,“还燕道中录”,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5年。
[10]《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二九三。
[11]杨宾:《柳边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南清河王氏铸版,民国二十二年。
[12]佚名:《蓟山纪程》,《燕行录选集》(Ⅷ ),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7年。
[13]薛培容:《东藩纪要》(卷五),光绪八年(1822年)刊本。
[14]朴趾源:《热河日记》,“太学留馆录”,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4年。
[15]朴趾源:《热河日记》“马日汛随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4年。
[16]《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十六。
[17]《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卷。
[18]《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25。
[19]《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卷二五。
[21]李押:《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Ⅵ ) ,首尔: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89年。
On The Images of Manchu in the Eyes of 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Xu Dong ri
(School of Korean Studies,Yanbian University,Yanji,Jilin Province,133002)
It is long before 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changes the attitude towardsM anchu.Before the first half of 18th century,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regard Manchu as barbaria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ayiconcept.Therefore,the envoys do not consider Manchuria as an orthodox nation,but contempt for them.The envoys describes the violence of the Q ing’s T roop and expose their brutality.In the second half of 18th century,however,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change their attitude to Manchu according to what they observe and hear.The positive images of Manchu created by 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 show out Manchu’s power,strength,tenacious vitality,expert horsemanship and marksmanship,Kungfu and etc.
Choson Envoys to Yenching,Manchuria image,negative,positive
I312.6
A
1002-2007(2011)04-0001-08
2010-07-20
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项目:A KS-2009-MB-2001。吉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重点科研项目:“朝鲜《燕行录》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徐东日,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疆学刊》主编,研究方向为中朝比较文学。
[责任编辑 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