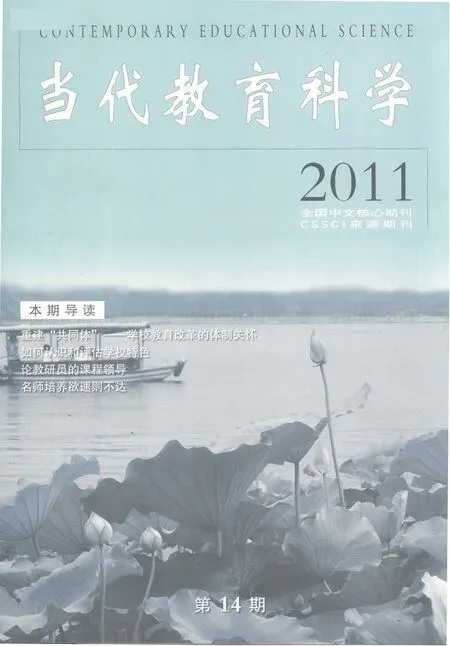校园安全事故问责制的思考
● 马宁奇
校园安全事故问责制的思考
● 马宁奇
校园安全工作成为学校管理的首要任务,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规范校园安全管理,但是在校园安全事故责任承担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问题,特别是事故处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还不完善。虽然《义务教育法》对教育问责制度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施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一、校园安全责任承担上存在的问题
(一)校园安全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
没有明确法律责任主体的法律是一部可操作性不强的法律。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对校园安全责任承担主体还不够明晰。其中,第八章专门规定了奖励与责任的制度,第61条规定:“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建设、交通、文化、卫生、工商、质检、新闻出版等部门,不依法履行学校安全监督与管理职责的,由上级部门给予批准;对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部门和所在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规定学校不履行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职责,对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等等。《办法》中囊括了所有校园安全的责任承担主体,但是没能根据校园安全的类别对责任主体具体化、明确化,这容易导致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后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在安全事故中找不出真正的责任人,无法问责。
(二)校园安全事故的归责原则不明晰
归责原则的不明晰直接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担责任,无过错无责任;同时也有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法律法规之间不统一。在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学校受到伤害的采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这就造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依据的法律不同审理结果就不同,责任的承担也不同。
(三)校园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不彻底
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是,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只追究直接当事人的责任,而忽略了与直接当事人相关的责任人的追究。责任追究往往不彻底,在校园安全事故的许多案例中,如教师体罚了学生就把该教师免职,学校倒塌事故就把校长撤职了等等,而没有追究校舍是谁建造的、是谁提供的、学校是谁举办的这些真正的原因,只是在表面上做到了对事故责任人的追究,不能真正追究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造成伤害的真正责任人。
二、校园安全事故处理中实行问责制的必要性
问责制通常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应承担他们行为的法律义务的机制。问责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及其官员因为违法或失职而受到惩罚,承担民事或刑事法律义务。二是政府及其官员要就其工作的绩效与结果承担责任。我国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问责制,第9条第2款是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规定:引咎辞职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次法律修订,是我国立法中第一次将“引咎辞职”写入法律规定,体现了国家保障和推进义务教育的态度和决心。本款规定的引咎辞职主体为“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之所以规定为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主要是因为实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责,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1]这是整个教育立法中最大的亮点。
(一)只有确立了校园安全事故的问责制才能真正落实校园安全责任的主体
责任的追究其实质就是追究事故责任主体的责任。在国外对校园安全的问责方面,普遍重视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教师和其他职员,对于学校的安全和学生权利的保障,负有重要的责任。如英国在对付肇事者方面特别强调学校与警察的合作,但是作为一个原则,其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学校而不是警察。因此,只有明确校园安全事故的问责的制度、归责的原则,才能准确的定位责任主体。也只有落实责任主体,才能把校园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二)校园安全事故问责制是归责原则得以正确执行的保障
问责制的核心就是责任主体在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管理范围内谁负责,谁的责任追究谁。特别是在学校安全管理中,《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学校负有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这涉及到学校对学生是否有监护责任上存在疑问,所以在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中更难以进行明确的归责。如果能够把责任清晰化,并明确规定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违反义务应承担什么后果等等,并事先建立切实可行的预案机制,就能保障归责原则的执行了。
(三)校园安全事故问责制是校园安全应急预案执行的保障基础
随着国内校园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都加大了校园安全预案工作的执行力度,建立了校园安全应急预警机制,设置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及其负责人,但是对未履行义务的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怎样追究责任很少规定,这就导致校园安全应急预案机制形同虚设,在真正发生校园安全事故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要使校园安全应急预案机制增加其执行力度,就要切实制定好校园安全事故问责机制。
三、完善校园安全事故问责制的对策
(一)厘清校园安全事故问责的主体
校园安全是指在学校职责范围内,不发生学生和教职工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校园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校园安全也不仅包括校内也包括校外,校园安全的责任不仅仅限于学校、教师和学生,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社会各团体等也担负着责任,凡属于与学校产生法律关系的单位和个人都可能是责任主体。所以,在制定问责制时,不能只考虑追究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要根据不同的校园安全事故类型,明确地规定可能涉及到的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才能有的放矢,准确迅速地根据其责任的大小追究其相应的责任,保护师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明确校园安全问责的范围
只有明确问责的范围才能落实责任主体的责任进而维护责任主体的权利,不然就会导致“谈问责色变”,不利于保护校园的安全。校园安全包括学校饮食卫生安全、交通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安全、消防安全、教学设施设备安全、网络安全、自然灾害、校园暴力与校园周边安全等等。这些安全事故涉及到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相关职能部门,只有明确问责的范围才能真正保护学生的利益不受损害,在众多的安全管理工作中难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和突发的安全事故,所以必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而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以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仅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适用于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如果存在过错,在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精细划分就可以使被问责者得以有的放矢地履行他的份内责任。
(三)校园安全事故问责的实施方式多元化
在校园安全应急预案中体现问责制。问责制其实不在于追究责任,而是要警示责任主体如有过失是会受惩戒的,是要求他们在平时认真而充分地履行职责。没有惩戒的问责制是难以执行的,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责令辞职,无论是赔偿损失还是降职降薪,只有问责的方式合适,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才能促使责任者认真地履行其职责。
校园安全事故问责的主体不仅包括直接责任人,还应追究与校园安全事故有关的主体的责任。众多案件判决表明,大多数都是对学校的直接负责人员进行了行政处分,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并没有根据事故的实际情况,追究其背后的真正责任者。如某小学厕所倒塌砸伤学生案。根据《学校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学校应当依法承担责任,但这是一个笼统的责任主体,必须要将其细化,落实到每个个体的责任人,即负责学校安全工作的教师或工作人员为第一责任人,其领导部门——该校的校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也有连带的责任,而最大的责任者是学校的举办者。
第三,校园安全的问责并不应仅仅是至上而下的责任追究,还应包括至下而上的问责,以及监督和反馈责任的承担情况。问责蕴涵着责任理念,实施问责制,必然要求政府树立向公众负责的行政理念。[2]在校园安全事故发生时,应该结合学校的主体,如学生、教师、学校工作人员等其他非当事人,接受他们的问责,接受他们对责任承担情况的监督与反馈,这样会对事故的处理更明晰,更有利于提高问责的效率和准确率。
[1]石连海.中小学校安全管理模式及其启示——以赣州市学校安全台帐管理为例[J].当代教育科学,2009,(24):50-52.
[2]李树峰,校长问责制的定义探析[J].教育科学,2006,(06):50-54.
马宁奇/河南省城建学院
(责任编辑:陈培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