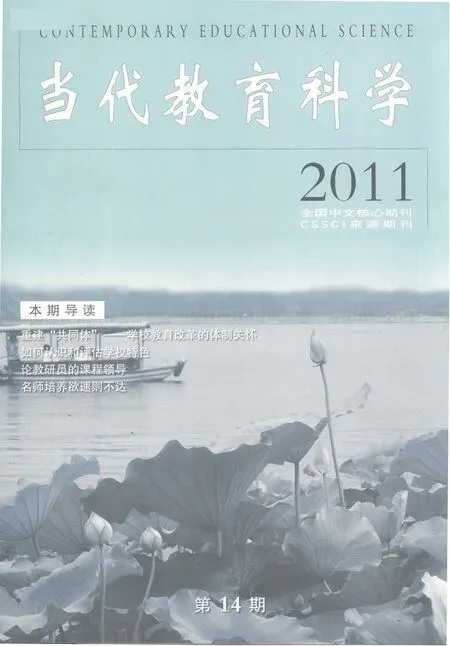小组学习“有序对话”的构建
● 陈银萍
小组学习“有序对话”的构建
● 陈银萍
小组学习被称为是“动车组”理论的迁移,是将原本由火车头(教师)拉动若干车厢(学生个体)的普通列车,转化为每节车厢(学习小组)都有动力支持的“动车组”。此理念可谓理想化了的判断,事实上,小组能够成为具有前进动力的动车组,也会在调控不力中成为具有反作用力的沉重负荷。这取决于小组内成员的交流与对话是否积极。
小组合作学习以及班级内的群体合作交流是一个“人—人”对话的场景,其秩序受制于其中的每一个人,建立良好的小组合作与交流机制,让有序对话得以实现并维持,是有效的合作学习和课堂教学的必由之路。
一、只有“责任”,没有“榜样”的关系
小组学习构成的机制和动因来自于互补、共享和提高,一般认为,小组合作学习应当是不同层次学生的有机搭配,即异质建构,而我们所谓的“异质”则主要看成绩之“差异”,最多是看能力之“差异”。由此而成的小组就聚合了处于不同学习层次上的学生,优良差均而有之,在整个班集体内则实现了小组间的“同质”,即均衡性。
对于整体的班级教学来说,如此划分的小组既有利于小组内的“结对”帮扶,又有利于小组间的对等评价,可谓是公平合理的划分。问题是,就某一个小组而言,这个小组中的学习生态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小组成员内部是否有一个良性发展的秩序。
这是一节初中历史课,小组学习的任务是讨论“官渡之战”中曹操胜利的原因,并对照分析“赤壁之战”中曹操失败的原因。教师要求每个小组内A同学(注:A是成绩最优者)分析原因,其他同学补充,并且由A同学选择小组成员进行展示。在接下来的小组合作中,A几乎具有了所有的话语权,而在选派上台展示的学生时,A派了D,因为按评分要求,在全班评价时,A对一题得一分,而D对一题则得四分。笔者发现,整个讨论过程中,完全由A控制了思考、探索,而D则只是机械记忆,上台复述,几乎没有动脑探索这一具有真实实效的学习过程。问之,D说:A学生说的会很完整,我再想也没有用,记住就行。
如此小组讨论,整个小组有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具有“榜样”的力量,大家亲之信之,然而在对话中却是领导者和等待者的角色。
其实,榜样的力量也是会极端化的,一方面会形成正向的引领力,在大家的信任中带领大家一起进步;另一方面,更会产生消极力,让身边的人变得暗淡,并使他们自我退缩,特别是对学生群体来说,还会产生依附性,从而不利于每个人的积极性的发挥。
小组内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既然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小组,每个人都应该公平地成为小组中的一员,也应该获得公正的对待,所以,维系小组内同学关系的应该是相互之间的责任感,而不是从属感。
建立责任感的途径在于分工负责,学习成绩有差异是现实的状态,但是小组成员在合作中的分工不应有差距,应该是各尽其能,并且不断实现角色变换,即便是小组长,也是轮换执行地好。
二、只有“对话”,没有“训话”的交流
对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坦诚,特别是对话双方能够畅所欲言,能够做到倾诉与倾听;而训话则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一方侵占另一方的话语领域,使双方都得不到正常的反馈,从而使得信息闭塞、情感阻滞,而学生对学生的训话则加剧了这种信息与情感交流的不畅。
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小组本来是一个合作共进的场所,然而因教学评价的需要,教师往往将其打造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荣誉共同体,从而使小组之间面临着分分相争的局面,对小组荣誉的渴望越大,则心态越容易失衡。有时候成年人都容易急功近利、贸然冒进,更何况是未成年的学生。特别是成绩好的学生对于成绩差的学生,帮助之心肯定会随之增加,但帮助过程中难免也会出现急切之情。
其实,小组中成员间的“训话”是一个常见的教育现象,在小学里较为普遍,甚至高中也有。如果不能调整学生的心态而让小组内的“训话”充斥,那么,学生的学习心态仍旧会以封闭的形式出现,至少不能够将自己真实的学习状态和认识全部展示出来。小组内的学习效果又怎能保障呢?
让对话成为小组内研究与交流的主流方式,需要的是教师的引导,需要教师首先具有一种宽容、包容的教学情怀,以此来调整学生的心态;进而要在小组内构建一种合作大于竞争的交流文化,让学生体会到共同解决一个问题、攻克一个难关是远远比获得一些分数、战胜一个相邻小组更快乐的;小组内的积极对话还源自于小组成员相互间的目标统一,大家在一致努力时,就能够多一些相互间的理解与关系,特别是在进行开放性的研究时,每个人的不同观点自然会得到尊重和关注。
让“对话”得到充分肯定,还在于小组成员内是一种立足于“说出”而不是“说教”的交流。“说出”即可,无须“说教”于人,这是教师构建小组内合作与交流的良性对话关系的立足点。
三、只有“需要”,没有“越位”的帮助
学习也是一种需要,而且是一种高级的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会从中获得知识,汲取成长的力量,而且也如马斯洛所说,会有“高峰体验”。而这种“高峰体验”只有在人的需要被充分满足,并达到极致的状态下才会产生,有了这种体验,学生才能充分地领略学习之美,才能投其全部身心于学习之中,学习过程便也成为生命中最美好的过程之一。这种体验所带来的是学生对更高的学习需要的追求。
但是,这种体验是在学生个体需要得到满足状态之下才产生的,如果没有“需要”,会有“高峰体验”吗?不会,甚至连“山脚体验”也没有。
如此一来,当同学之间的帮助不能建基于受助者的需要,不能理解受助者认知与情感深处的呼唤,一切帮助皆为徒劳。
事实却是,在教学过程中,在小组合作互助过程中,没有受助者说话的权利,没有受助者表达需要的空间,一切都在外力的约束与调控下进行。从知识到能力,甚至到道德因素,都会受到来自于其他同学的越位相助时,学生的心态已经偏离了正常的生命轨道,合作已经变异为施予和抵御的较力,帮者劳神,受者劳心,二者缺失了天然、内在的心灵沟通。
让每一个学生把自己的需要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学习与生命之中的兴奋点,求助是一种正常的学习心理与学习需要,满足的应当是“需要”,而不仅仅是学习。
四、只有“为什么”,没有“你错了”的评价
今天看来,仍有40%的中学生认为教师像领导,仅有30%左右的学生认为教师像朋友。[1]师生之间还不平等,仍有四成的学生感觉自己的学习是在一个权力场中进行,造成这种感觉的主因是他们在评价中的不平等感,大多数学生都会有随时接受惩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惊惧,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学生正常的人格成长,对于他们的学习质量与学习效率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惩罚是有两面性的,一则帮助学生改过自新,二则造成学生的封闭和逃避。正确运用评价策略,对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极为关键。
学生之间的惩罚除去“校园欺负”之类的极端现象,单就学习过程而言,强势学生与弱势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也能造成心理乃至精神上的惩罚,而这种惩罚的不确定性,以及“权力意志”下的“非权威性”造成的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相互之间的不够坦诚,都指向足够的交流与沟通的缺乏。
如果学生之间的评价更多的是“你错了”,那么,被评价者会努力向评价者证实自己的“非错”或“错之因”,而不是主动内省自己的“错之因”。错误既成隐私,又成缺陷,如此一来,“你错了”的评价,就会变成一种惩罚而使生生之间形成对立,教学乃至教育效果就已经大打折扣了。
其实,学生之间更加清楚对方的弱点与不足,在学习过程中也是如此,一个成功的亲历者,总是能看到同伴在亲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此时,明确地指出来是非常及时而重要的。
但是,面对“错误”而进行的指正,应当是能够促进“犯错者”或出现问题者产生反思与自我认知,能够进行积极主动地反思改进的。
什么样的指正与评价方式能达到这种效果呢?显然,让被评价者反思也是需要外力影响内力的,外力的加予应当是一种“为什么”的引领。学生毕竟是未成年人,其有意注意力是比较弱的,而一种“为什么”的评价引领,自然地生成了促进反思的力量,而且能够让学生在不受惩罚压力的状态下直面自己的问题或者错误,这便是良好评价的作用,也是在惩罚与人性向善之间寻找到的平衡点。
生生之间追问的“为什么”,超越了合作中的互助交流层次,而进入了一种相互的价值引领境界。如此,合作中真实的人性追寻何难呢?
[1]檀传宝等.中学师德建设调查十大发现[J].中国德育,2010,(4).
陈银萍/潍坊高新双语学校
(责任编辑:刘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