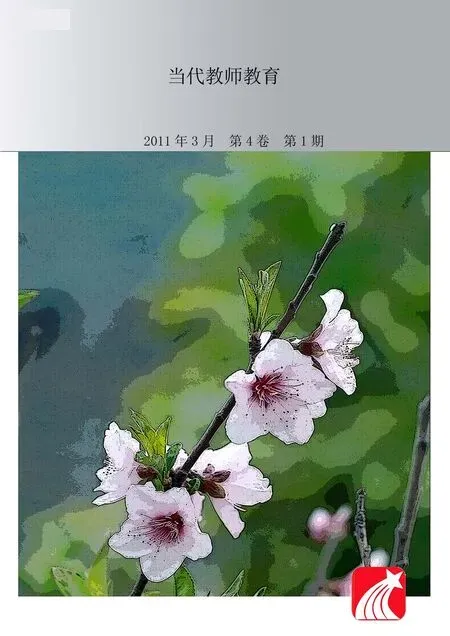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及启示
王 慧 英,李 天 鹰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一、不同历史时期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
(一)中世纪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
意大利是世界大学的发源地,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就位于意大利。中世纪的意大利大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教会中保留下来的研究机构,另一类是行会组织建立的教育机构。[1]行会是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产物,最初是通过限制不正当的竞争来以保证行业经营的稳定性,解决行会成员困难,保护本行业利益为目的的组织。随着意大利城市的繁荣,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行会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其中学生行会设立的教育机构奠定了意大利大学的根基,很多意大利大学都是基于学生行会组织成立的,其中就包括博洛尼亚大学。
中世纪,意大利大学的一切事物并不是由大学来负责,而是由其归属的教会和行会负责,教会与行会在授予大学教师教学资格上有着自己严格的标准,所有在大学中获得教学资格的教师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考核。首先,大学中的教师在身份上要是教会或行会的成员,或者是接受教会或行会委托的人。[2]其次,在获得教学资格之前,他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获得大学授予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当时的硕士、博士学位是大学教师资格的象征,在水平上没有高低之分。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后,申请者要经过个别考试、公开答辩和组织辩论三个程序的考核来决定其是否可以获得教学资格。首先申请者要向校方保证自己真正已经具备了申请的条件,然后在教堂聆听圣灵弥撒,准备资格评审委员会的供评注用文献,并在同一天宣读评注结果,接受资格评审委员会针对申请者个人的提问;个人考试通过以后,申请人将被引入大教堂发表学术演讲,面对听众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为自己进行辩护;通过公开答辩以后,申请者将以教师的角色组织一场公开的大学辩论会,经评审合格后,由资格评审委员会授予其大学授课许可证,方可在大学里从事教学活动。[3]由此可见,在中世纪,要想在大学中获得教学资格,必须要在其所属领域中有卓越的成就或者很深的学术造诣,否则面对资格评审委员会的提问和公开答辩时,很难游刃有余地应对。对教学资格申请者来说,能够获得学位和大学授课许可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既是对申请者过去学识的认可,也是其学术追求的崭新起点。
(二)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
随着意大利国家的逐步统一,意大利结束了大学的教会管理和行会管理,效仿法国,开始了对大学的统一管理。大学的经费开始由国家资助,大学开始归属国家教育系统,由意大利中央教育部统一管理,对大学教师的任用及教学资格的评审也开始由国家负责。
1925年墨索里尼确立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统治,随后迅速展开意大利教育制度的改革,意大利教育的法西斯化迅速得以实现。墨索里尼将大学视为“重新使意大利精神发扬光大”的阵地,十分重视对大学的控制,并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借口,把全国大学的数目减少到24所,其中国立大学仅10所。为了将法西斯主义渗入大学,使其具有“全新的和真正的法西斯主义革命的性质”,[4]在法西斯统治期间,政府以减员增薪为幌子,对意大利大学教师进行了大清洗,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教师进行一次全面甄别和筛选,借此把那些有反法西斯倾向的教师全部赶出了学校。在身份上,大学历史与哲学教师必须是法西斯党党员,所有大学教师在获得教学资格之前,必须在墨索里尼像前宣誓效忠领袖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事业。
在法西斯统治期间,意大利大学教师资格的授予成为了一种法西斯的政治工具,对意大利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三)20世纪60—90年代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
20世纪意大利的大学教师分为三个级别:研究员、副教授和教授,他们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专门的待遇。按照政府规定,教授和副教授具有直接从事教学活动的资格,大学的教学工作由教授和副教授承担;研究员不可以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和参与教授的项目研究工作,他们不具备直接从事教学活动的资格。大学教师在晋职后的三年中,要接受政府和大学在其科研和教学方面的评估,同时要求大学教师在一所学校工作三年后要调转到另一所大学工作,“流动”经历是意大利大学考核教师教学资格的重要指标。二十世纪,意大利的大学发展十分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法西斯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摧残和意大利大学的贵族化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大利经济的复苏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流动,促使人们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并且这种需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膨胀。迫于形势的压力,1969年意大利政府被迫实行了高等教育的开放政策,宣布取消大学招生名额限制和大学入学考试,规定凡是持有高中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力文凭的人,可以在任何大学的院系注册学习。这一改革后,大学的师生比迅速加大,出现了明显的教师短缺现象,政府被迫允许研究员直接授课。与此同时,政府绕过正常的人事管理制度,迅速提高教授和副教授的数量,在社会上大量招聘取得大学毕业证书的人从事研究员工作,聘请各个行业的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大学授课,迅速补充教师队伍。[5]由于学生入学前基础的差异和大学课程设置的原因,很多学生不能按照意大利大学的要求顺利毕业,同时,大学的招生却一直在扩大,使大学的教学任务依然严峻。尽管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大学人事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下降,但是这种被迫开放大学讲台的做法却为半个世纪后的意大利大学教学改革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审查的程序迫于形势压力基本消失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教学任务基本由研究员承担了,教授和副教授在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为了约束教师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政府提出了非全职工作的大学教师在薪水上要比全职工作的大学教师低40%的政策,但是其他社会组织随后颁布的对全职工作的大学教师参与社会活动的优惠,又为全职教师从事社会兼职提供了便利,也使政府的约束受到了挑战。
为了进一步规范对大学的管理,提高办学质量,意大利政府于1980年通过了382号法案,对大学进行改革。在该法案中,对意大利大学教师的教学资格和基本工作量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法案,意大利大学教师分为研究员、副教授和教授,大学教师可以选择全职在大学工作,也可以兼职在大学工作。全职在大学工作的教授和副教授,每学年的教学工作量不低于250小时,教授在管理工作方面的工作量不低于100小时。非全职在大学工作的教授和副教授,教学工作量每学年也不能低于250小时,教授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从事管理工作。研究员不能直接授课,他们间接参与教学工作的工作量每学年最多250小时。[6]在意大利大学中,教授通常是几门课程的主讲者,法案中规定了教授的最低工作量,于是教授们开始将法律规定工作量以外的教学任务进行了重新分配,大部分教授在完成最低工作量之后将大量的剩余精力投入到他的科学研究中,而把其最低工作量之外的教学任务委托给了副教授和研究员。尽管法律对研究员从事教学活动的资格和工作量做出了限制,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大约有1/5的研究员将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投入到了直接教学中。尽管在规定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但是基本上保证了大学的教学质量。这一时期,副教授是大学教学的骨干力量,因为他们既要完成自己的最低工作量,也要分担教授分配的工作量。
1998年7月,为了提高大学教学质量,意大利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对大学教师的招聘和教学资格授予的考核模式进行了改革,由先前的国家统一考试的间接考核模式转变为由大学、政府机构共同组成考核委员会的直接考核模式。在政府规定的两个招聘时期内,各个大学根据需要公布招聘信息并成立由该大学的成员、政府成员和其它大学的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考核委员会。考核委员会根据招聘对象的不同,调整其人员组成和考核内容。一般来说,考核研究员,考核委员会由一位政府人员、一到两位该大学人员和两位以内的其他大学教授或副教授组成;考核副教授时,考核委员会要分别增加两位其他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考核教授,要分别增加四位其他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所有考核委员会成员均为该领域内代表国家水平的人员。考核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对研究员的考核主要是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考核;对于副教授,在面试过程中要对其进行教学演示和科研讨论的考核;对于教授,要增加对其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的分析和评价。考核结束后,考核委员会将推荐三个合格人员,由大学来决定最后录用的人选,并授予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教学资格,另外两位可以在大学工作三年,三年后重新接受考核,考核通过后可以正式被大学录用。这种严格的考核程序和模式在日后的意大利大学改革中虽有改动,但是基本奠定了意大利大学选拔教师、授予教师教学资格的程序框架。
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意大利大学选拔教师程序是十分严格的,而且也看到了对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授予要求也是很高的。被授予教学资格的教师通常都拥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较高的教学技能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研究成果。他们不仅要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从事教学研究。因此,意大利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都比较大:大学教授的平均年龄在55岁,副教授在48岁,研究员在40岁。
(四)博洛尼亚进程中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
为了推动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实现高等教育的欧洲维度,1999年,来自欧盟的29个成员国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旨在加强欧洲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合作,建立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7]《博洛尼亚宣言》提出欧洲大学实行开放政策,欧洲高等教育区内的成员国要互相认可彼此的学分、资格和学历,确保学生和教师的流动和交流。
根据《博洛尼亚宣言》,意大利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意大利大学在欧洲的竞争力。在大学教师的教学资格授予上,政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2004年,意大利政府通过与大学助教和研究员缔结相关有限时期契约,对大学教师现状进行改革,大学教师分为助教、研究员、副教授和教授。政府对助教和研究员的教学任务进行了限定,规定每年350个小时的工作量中只有120小时可以从事教学。[8]同时,助教必须在完成一到两个五年期限的合约后才可以从事研究员工作。也就是说,目前,在意大利,大学教师在获得教学资格之前要进行3—4年的博士学习,获得学位,然后经过5-10年的科学研究体验,才可以获得每学年至多120小时的教学权利。在博洛尼亚进程中,意大利政府非常鼓励大学教师到其他欧盟国家的大学学习和工作,同时也积极聘请其他国家的知名学者来意大利大学授课和讲学,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流动机制。教师的“流动”经历也是考核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重要内容。[9]意大利大学主张不接收本校的毕业生留校从事教学工作,坚决杜绝由此引发的学术“近亲繁殖”。由此可见,意大利大学对教师获得教学资格的要求是高的,尽管在程序上偶尔会导致一部分教师将精力集中在科学研究和评审中,但是总的来说,这样的政策对意大利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
二、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评审的评述
(一)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评审是保证大学教学质量的根本
从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到今天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意大利大学,教学质量始终是意大利大学的生存之本。在意大利大学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严格的教师教学资格评审程序是保证意大利大学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20世纪60年代以后,意大利提高了对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评审标准,对各个层次的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做了严格的规定,对研究员和助教的教学资格及工作量做了明确的限定。登上大学讲台,获得教学资格的教师都是其所属领域中的学术精英,很多教授在其所属领域中的学术水平都代表着意大利的国家水平。同时,对于退休的教授,政府也明确规定其退休离开工作岗位五年后将不得从事教学活动。[10]因此,意大利对大学教师教学资格的严格审查对其大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功不可没。
(二)对教学能力的直接考核是意大利大学授予教师教学资格的重要评审内容
面试考核一直是意大利大学招聘教师的重要考核方式,从中世纪的公开答辩考核开始一直保持到今天。在面试考核中,意大利大学一直十分重视教学能力的考核,将教学技能和教学成果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中世纪时,被考核者要在公开答辩中充当教师角色,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进行辩护,答辩通过后方可被授予大学教师授课权。近代开始,意大利大学对研究员的教学资格进行了限定,原则上研究员不能直接参与教学。对副教授和教授的面试考核中增加了教学演示的考核,对教授的考核还明确规定了对以往教学成果的评审,面试通过者,方可授予其从事教学活动的权力。除此之外,在教师职称评定中,教学成果的考核也是重要的评审项目。因此,在意大利,大学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要十分注重对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增加对教学本身的研究。
(三)意大利大学通过授予各行业精英授课权来丰富大学教师队伍
在意大利大学教师教学资格演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意大利大学师生比例悬殊的阶段中,意大利大学把教学资格颁发给了各个行业的精英,非常鼓励他们来到大学中讲学。20世纪60年代以后,意大利大学教师人数逐渐增加,但是意大利大学仍然聘请各个行业的专家和精英,授予他们从事教学活动的权利,目的是使大学保持学术活力。在欧洲大学的博洛尼亚进程中,意大利大学将教学资格颁发给了国外大学中的优秀学者使其从事大学教学活动。[10]同时,意大利大学也非常支持本国的教师到国外学习和交流。另外,意大利大学主张不接受本校毕业生从事教学活动,以避免学术的“近亲繁殖”。由此可见,意大利大学的讲台是开放和充满活力的。
三、对我国大学教师教学资格评审的启示
(一)建立并规范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资格评审制度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国高校教师的来源渠道,丰富了我国高校教师的学缘结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高校的青年教师都是先上岗后办证,没有经过专门的教学技能学习和培训。很多高校青年教师的入职培训也缺乏教学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只是走形式而已。青年教师承担了大量的一线教学任务,有的高校青年教师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建立并规范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资格评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大学质量的提高,一流的教学水平是关键,因此,高校应该制定制度明确规定并适当提高教授和副教授从事本科教学的最低工作量,并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使教授和副教授真正成为高校教学力量的主体。我国高校的青年教师大多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具备比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应该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高校应该在青年教师入职的初期,积极挖掘他们的科研潜力,增加他们的教学体验,为他们制定学术职业发展规划,鼓励他们经常听课,间接参与教授和副教授的教学活动,经过严格的教学考核之后,方可从事教学工作。
(二)增加教学研究成果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的比重
在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中,对教师教学方面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其工作量的考核上,而对于研究成果的考核,大多集中在其专业学术领域内,评价导向重科研轻教学。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育人的社会服务功能,教学工作是高校教师重要的工作内容。因此,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要加大其教学资格的评审和教学成果的考察。当前,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中只对教师的基本教学工作量作了规定,而基本教学工作量的完成是对高校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最基本要求,职称的晋升应该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和对教学资格的新一轮审查,而教学成果则是二者的重要体现。因此,在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中,要平衡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的比例,加大教学成果的比重。同时,在教师职称评聘中,对那些多年没有教学成果的教师要建立切实有效的淘汰机制,取消其从事教学活动的资格,以此来保证和提高我国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
(三)将“流动”作为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资格评审的重要考核标准
一流的大学,其教师必定要来自五湖四海。我国很多高校将自己的毕业生留在了本校从事教学工作,在特定历史时期,这一举措的确缓解了我国高校教师队伍短缺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因此,在国家建设一流大学的今天,我们在考核教师教学资格的时候,应该对此问题予以重视。高校要建立积极的教师流动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中国大学的“博洛尼亚进程”,积极鼓励教师在高校间的流动,将流动经历作为高校教师从事教学活动的重要考核标准。同时,在高校教师教学资格授予上,我国应该借鉴意大利大学的经验,向全世界各个行业的精英及各个大学的优秀学者颁发从事高校教学工作的许可,对这个群体取消对其学历的约束和限制,开放高校的讲台,以此促进我国高校学术的繁荣和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 Stuart Woolf. On university reform in Italy: contradictions and power relations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J].Minerva,2003(41):347-363.
[2] Guido Martinotti, Alberto Giasanti. The rober baron: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Italian university[J] Higher Education,1977(6):189-207.
[3] 缪榕南.学者行会的成员资格——中世纪大学教师录用的历史考察[J].教师教育研究,2007(3):62-67.
[4] 陈祥超.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教育体制初探[J].世界历史,1994(1):30-37.
[5] 傅凰.意大利教师任用制度及改革述评[J].煤炭高等教育,2009(5):66-69.
[6] Roberto Moscati. Italian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 transition[J].Higher Education,2001(41):103-129.
[7] 刘宝存.博洛尼亚进程的最新进展与未来走向[J].比较教育研究,2009(4):1-6.
[8] 贾莉莉,编译. 意大利政府对大学教师进行新的教育变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4(4):92-93.
[9] 佛朝晖.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意大利高等教育体系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2008(2):74-78.
[10] Roberto Moscati.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ologna process in Italy.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M].Vol.26.Higher Education Dynamics, 2009: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