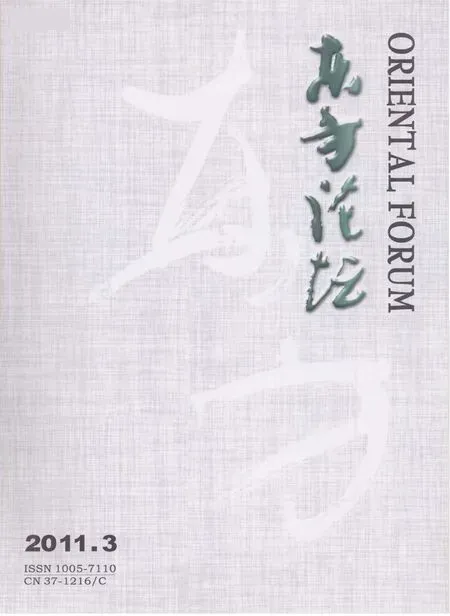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的教授派
吴 锦 旗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8)
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的教授派
吴 锦 旗
(金陵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38)
抗战时期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国家在非常时期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团结的组织工具,它是国内各党派和政治团体参与政治的一个场域,其中的教授派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教授派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他们凭借其惯习在国民参政会上鼓吹政治改革,试图推动战时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宪政民主。
国民参政会;教授派;自由主义;场域;惯习;
抗战期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为在野的各党派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规范的平台,国民参政会也成为国民政府容纳和团结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新型制度设置,教授派是国民参政会上一个特别的政治团体。
一、教授派的构成分析
邹韬奋曾打过这样的比方,“如果说国防参议会是小规模的‘请客’,那末国民参政会可以说是大规模的‘请客’”。[1](P28)他还对这些来宾依其政治属性做过细致的分类,构成国民参政会的在野党派有: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教授派。不过,邹韬奋所说的“教授派”只是对中国学术教育界的一种笼统而又模糊的泛称,“以前所谈过的党派,多少是有群众性的,即在他们的后面有群众;讲到所谓教授派,这一点是没有的,虽则他们各有他们所教的学生,但究竟是在散漫的状态,说不上什么党派的群众性,可是参政会中有十几位大学教授,尤其是来自昆明的教授居多数,他们因为平日往返比较地接近,对于政治多多少少有一些共同点或共同兴趣,于是在开会期间,他们每有他们的小组聚会,交换关于各种问题的意见,在提案中互为声援,形成教授派的力量。尤其显著是在第五次大会时,关于‘五五宪草’的修正意见。除救国会派及中共各有书面意见提出外,教授派也提出‘修正草案’,其中在国民大会停会期间应设‘国民大会议政会’一条,曾在会场上引起激烈的辩论,这一派的人物有罗隆基、罗文干、陶孟和、周炳琳、傅斯年、张奚若、杨振声、钱端升、任洪隽诸先生。”[1](P41-42)邹韬奋所说的“教授派”,很可能是特指国民参政会中的那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并且当时正在大学从教的学术精英(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因为他们彼此处于同学术圈中且在政治上志趣相投而被视为一个政治团体。
而实际上具有教授身份的参政员肯定不止这些人,即使以对政治的关心程度来说,这一派也应该包括胡适、周览、许德珩、张君劢、张申府、梁漱溟等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国民党党员或其他党派成员。关于国民参政会的组成人员,有研究者从党派归属来进行划分,据对第一届200名参政员的统计:国民党代表89人,占44.5%,无党派人士89人,占44.5%(其中相当一批倾向国民党),其他五个抗日政党仅有22人,只占11%(共产党7人,青年党7人,国社党6人,社民党1人,第三党1人)[2](P51),如果这样划分,教授的职业身份就被党派归属吸收了。但如果以曾在大学中任教或当时正在大学中任教及那些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人而言,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拥有教授的职衔,似乎也可以将他们都视为教授派的成员,这样一来,教授派所包含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实际上许多教授参政员的身份是多重的,既在高校中任教,也从事文化活动,有些还是社会活动家,有些还参加了不同的党派和政治社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一群教授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他们有着相近的政治信念和近似的价值认同,而正是这些左右和影响着教授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
教授派人数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却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国民参政会中的教授群体从年龄结构上看,大约涉及到了两代学人①按照许纪霖的观点,20世纪中国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即“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的学人。自1915年以后,是中国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如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他们大多出生在1880-1895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20世纪30-40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3](P83)
从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上看,前一代人“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上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通人,他们有扎实的传统文化的功底,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后一代学人与他们的前辈有所不同,“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3](P83)如傅斯年、罗隆基、钱端升等人,这一代人主要是以海外留学生为主,留学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欧、美、日,以欧美为主,这就使他们的思想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前一代人主要靠社会影响而闻名,是社会精英,而这一代人的名望则是局限于知识圈中,属于学术精英。
从政治归属来看,教授群体虽然依托于大学,但并不是将自己封闭于大学之中,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辗转于学术和政治之间,有些人成为在野党派的创立者和重要领导人,有些人则加入当时国内的一些党派,以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属于自由、独立的学者,潇洒地游走于政治与学术的两端,有些人还走出象牙塔,教而优则仕,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这些人自然就与原先的同事、同学、朋友之间有同气连枝的关联,拥有如此四通八达的关系网络,能够打通教授与掌权者之间沟通、交流和接触的管道,周旋于政府高官之间,即意味着占据独特的社会资本,以言论政,可以影响国策。
二、教授派中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光谱
教授派虽然人数比较多,而且彼此之间并不相互依附,但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而言,必然会有一个灵魂人物,他将起着号召和领导的作用,而这个人非胡适莫属。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从政治思想上看,胡适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鼓吹改良,慎言革命。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胡适心怀不满,但他是信奉实验主义的,希望用改良的方法来推动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921年,胡适提出了“好政府主义”的方略,即用一个好的政府来代替北洋军阀的坏政府,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形成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胡适也同样是从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致于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对胡适及其追随者进行文化上的围剿和人身上的迫害,后经人从中调解,才使国民党当局解除了对他的打击和压制,此后胡适个人也逐渐得到国民党高层如蒋介石等人的赏识,成为当权者的座上客。但是,胡适始终没有放弃他自由主义的理想,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他办 《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时,在他周围都聚集着一群信仰自由主义的教授。陈源在抗战期间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与一部分朋友至今仍认为你是蔡先生唯一的继承人,但又不愿意你在此时离开美国,所以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那一样。”[4](P465)因为胡适在国内学术精英中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邀请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后又被聘为国防参议会的参议员,再被遴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适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即受政府委派到美国进行游说以争取外援,不久即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所以抗战期间胡适并不在国内,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教授派的影响颇大,其政治理念一直是左右着教授们的行动。
如果说胡适是教授派中政治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和精神领袖,罗隆基则是一个具体实践者,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1912年罗隆基以江西考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他在这里一共生活了9年。五四运动时,他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他以学生领袖而闻名。早年的清华生活培养了罗隆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和才能,特别是在学潮中他受到了政治家最早的素质训练,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主攻政治学,这也许和他在清华时受到的影响有关。在美国期间,他与闻一多等留美学生成立了一个接近政治的组织大江会,倡导国家主义,1924年2月24日,罗隆基写信给他的清华同学施滉,介绍了“大江会”的组织和主张:“‘大江’的宗旨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持诚恳忠实的态度,取积极协作的办法,以谋国家的改造。’”[5](P225)1925年,罗隆基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去了英国,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他的导师就是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的思想对罗隆基影响很深。
1928年,罗隆基回国,不久结识了张君劢,在张君劢创办的上海吴淞政治大学任教授。罗隆基还参加了《新月》杂志社,担任编辑,与胡适、梁实秋一起发表关于人权的文章,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为此,罗隆基还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过,经胡适多方奔走才被营救出来。1931年,罗隆基与张君劢又一同组织再生社。此后,因罗隆基对政府的激烈批判而屡遭迫害。1936年,由再生社改组的国社党与民宪党要员伍宪子商谈两党合并问题,罗隆基、张君劢和张东荪等代表国社党在草约上签字。此时的罗隆基又是国社党的重要成员了。罗隆基虽然是国社党的发起人之一,但他一直是教授派的核心人物,他始终信守自由主义理念。战争爆发后,罗隆基离开天津南下,辗转到了武汉,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大敌当前,他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立场。抗战中的罗隆基成了现实政治旋涡中的一个重要人物。[6](P1-53)
教授派的政治光谱大多聚焦于自由主义之上,这与他们中的多数人留学欧美有很大的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倾向于维持社会现状,他们容易认识到现有社会的问题和不足,并对此会提出激烈的批评,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而是为了改革旧体制以获得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自由主义以各种重要手段寻求体制内的变革,但他们拒斥任何彻底改变体制的企图,因为他们支持体制的基本因素。”[7](P23)自由主义是教授派中的一种普照之光,即使其中有些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如梁漱溟等,他们其实也把政治民主化作为努力的方向,不赞成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拥有共同的自由主义理念是教授派成员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的思想基础。
三、教授派成员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场域和惯习
教授派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彼此之间是高度分化的原子式的存在,互不隶属,也不相互依附,我行我素,以独立、自由为基本价值取向,但有些教授或自己组织党派或加入其他的党派团体,彼此之间似乎在政治观念上出现了分歧,但党派的差异并不能排除他们在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能形成相似的看法,并因此相互协同行动,互为声援,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派实际上是形散而神不散,但是这个教授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教授之间是如何通过交往而结成关系网络的?国民参政会的教授派又是如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法国学者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分析框架①许纪霖曾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问题,本文中的分析亦受其启示。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8](P133-134)场域实际上就是一个关系网络的系统,在不同的场域中有不同的行为规则和可预测的结果。如果把国民参政会看成是抗战过程中的特定政治场域,它为当时国内的各党派和政治团体提供了一个彼此交往、沟通、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场所,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党派之间的交流、沟通,有助于实现战时国内的政治团结。参政员的位置也就意味着相对应权力的存在,按照1938年4月12号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第五条,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遇有紧急特殊情形,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依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不受本条第一、二项之限制。第六条,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第七条,国民参政会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劝。”[9](P7)即参政员有决议、建议和质询三种权力,对权力的运用过程也就是一个真实的参与过程和彼此相互竞争的过程,还是一个消除分歧、相互协商达到妥协的过程。
教授派参政员起初对国民参政会还是比较赞赏的,罗隆基说:“参政会在人选方面,我们不能说完全满足人民之意,但这是北伐以来,破天荒的一种新设施。社会各方面都有人士参加,这可以说是中国完成民主政治过程的一大进步。我们希望国民参政会的权限能够更提高一些,使许多参政员能够真正贡献出许多有利抗战的意见,以供政府采用。”[10](P88)教授派参政员确实希望利用参政会这样一个平台实现政治改革的目的,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作用,
行动者在政治场域中的争斗和博弈除了要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外,还和他们的惯习密切相关。布迪厄指出:“所谓‘理性的’(rational)惯习,或者更恰当地说,合情合理的(reasonable)惯习,确实是某种适当的经济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但它本身却是特定的经济条件的产物。要想真正觉察到并把握住那些形式上向所有开放的‘潜在机会’,你必须占有最低限度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正是这一条件限制着所谓‘理性的’惯习。”[8](P165-168)惯习是一种被明确了的立场,是一种被行动者明确建构、认同和遵循的行动方法和准则。由此,惯习是一个实践概念,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动态互动。[11](P306)教授群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不仅仅存在着职业、身份、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等方面的相似性,更为根本的是他们有着惯习上的一致性,“同一共同体内惯习的一致性,是这个共同体得以建构和维持的根本,同时也是构成社会里不同生活风格的基础。每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分享同一类型的惯习,集体行为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惯习造成的;共同体内每个人都只是这一阶级惯习的不同版本,相同的阶级惯习是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原因,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标志,惯习给这个共同体成员带上了只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家族徽章’。”[11](P406)
国民参政会上教授共同体基本一致的惯习同他们的教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在教育过程中才逐渐形塑其稳定的性情倾向,而这样的性情倾向又会在行为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出来,教授群体在行事中带有浓厚的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色彩,指望用和平、理性、民主、渐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运用其手中掌握的有限的权力去说服、劝导、引诱当权者进行自我革新,在原有的政治体制内通过政治改良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他们远不能理解和适应专制社会中政治场域的黑暗、无序、混乱和保守,以致于他们的主张和行为既不能见容于执政的国民党,同样也不讨喜于共产党,在两个大党的夹击中左右为难,茫然无所措,其政治努力有过程而无结果,只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或许就是其自身的惯习所带来的宿命。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一个政治舞台,而教授派则在这个舞台扮演着理念人的政治角色,他们开始从“谈政治”向“干政治”转变,国民参政会不过是为他们参与政治建构了一个新的场域,教授派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本,在特定惯习的支配下,努力推动战时中国的民主宪政发展。
[1]韬奋.抗战以来[M].上海:韬奋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年八月初版,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再版.
[2]周勇主编.国民参政会[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3]许纪霖.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A].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陈源.陈源致胡适[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闻黎明 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6]谢泳.罗隆基评传[A].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7][美]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
[8][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 李康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0]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Z].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11]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On the Professor Group in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WU Jin-qi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8, China)
The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was a tool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unity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It was a platform f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Among them, the Professor Group was a major force which, influenced by western liberalist political thoughts, habitually advocated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Professor Group; field; liberalism; habit
K265
A
1005-7110(2011)03-0015-04
2011-04-26
吴锦旗(1968-),男,江苏盐城人,法学博士,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侯德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