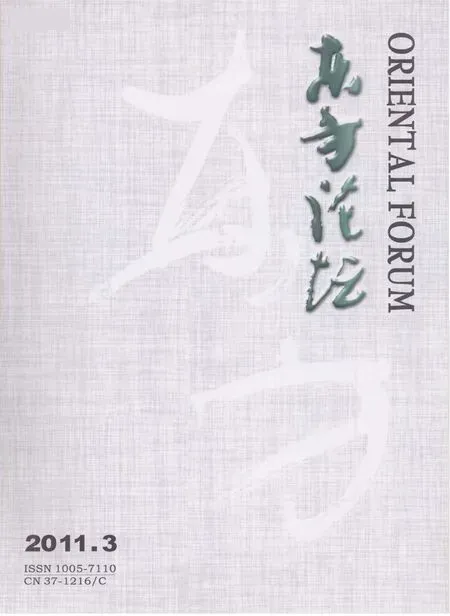遁入炼狱
——托马斯·曼的疗养院图式
黄河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北京 100089)
遁入炼狱
——托马斯·曼的疗养院图式
黄河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北京 100089)
死亡和疾病是贯穿托马斯·曼一生创作的主题,而疗养院则是这一主题的特殊舞台背景,作为疾病与健康、死亡与生命之间的混沌地带,它在曼式神话原型与宗教语言的转借处理下,处处打上了人间炼狱的烙印,成为世纪之交颓废派艺术的滋养土壤。
托马斯·曼;疗养院;炼狱;艺术;疾病
托马斯·曼(1875—1955)作为20世纪德语文学巨匠,年仅26岁便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并立刻引起轰动,成为德语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并凭借这部展现一个殷实家族没落的鸿篇巨制,于1929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从长篇小说处女作,到中篇佳作《死于威尼斯》,直至后期集大成之作《魔山》、《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以及《浮士德博士》,死亡和疾病都是托马斯·曼小说经常出现的主题。据笔者了解,国内外文学批评与研究对这一主题主要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性分析,因此从主题的重要舞台环境——疗养院——入手,似乎仍具有一定意义。疗养院(Sanatorium,拉丁语sanare,有治疗、治愈之意)在托马斯·曼生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用意义中,指为肺病患者在高山地域或者森林茂密的平原建立的康复机构。曼的两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魔山》和短篇小说《特里斯坦》——都发生在肺病疗养院里。
一
世纪之交,德国此类的疗养机构并不少见,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肺结核这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并在世纪之交达到了发病的最高峰,以至于几乎没有任何一家疗养院的适应症列表里没有涵盖这一病症。
由于亲友因肺结核或其他慢性肺病进入疗养院疗养,托马斯·曼有过多次疗养院经历,其中第一次有资料记载的就发生在1901年6月到8月,正值《特里斯坦》1901年上半年的完成与1903年正式出版间的修改期,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与之相吻合。曼接触到的第一个肺结核疗养院是达沃斯森林疗养院,他的夫人在1912年3月选择了这里疗养,曼于当年的5月15日至6月12日在这里看望妻子,并住在疗养院附属的别墅区里。但就餐时间,他可以进入疗养院的主建筑,感受到那里的气氛,并以此为原型创造了《魔山》中故事发生的地点——高山上与世隔绝、时光停滞的山庄国际疗养院。1909年6月,曼曾向他慕尼黑青年时期的好友Walter Opitz写信总结过他在苏黎世的疗养院经历:“我现在不得不万分夸赞的Bircher医生的疗养院里,那里人们只能吃到蔬菜、水果和坚果,必须在6点起床,9点熄灯,每天都只能在空气浴、日光浴、水疗和园艺劳动中度过。这太难了,在开始的时候,前5天我总是纠结地站在行李箱前,与想离开的固执念头做斗争……但几天后,我的消化不良开始好转了,以从没有过的惊人的速度,而且这种效果还在持续。此外,疗养院里友好的社交和优雅的环境也使这些变得容易了一些……”[1](P191)这些经历都在上述两部小说《特里斯坦》和《魔山》中得到了艺术的还原和再现。
二
肺结核虽然在世纪之交的文学舞台上时常被塑造的素材,但极少数文本将其背景定为疗养院。奥托尤利乌斯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笔下的布谷王子(Prinz Kuckuck)曾逃入日内瓦疗养院,但很快离开了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1917年克拉本德(Klabund)的中篇小说《病》(Die Krankheit)已经把故事发生地点设定为了——同《魔山》一样——达沃斯肺病疗养院。之后,克努特·汉姆生《最后一章》和黑塞《漫泉疗养者》都对疗养院的生活有一定的反映,但疗养院题材还是在托马斯曼的笔下尤为突出。曼的两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魔山》和短篇小说《特里斯坦》——都发生在肺病疗养院里,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把疗养院作为了自己的生存模式。
而这种生活模式有什么特征呢?这里的一部分人病得很严重,迫不得已来到疗养院,反而找到了家乡般的归属感。“只要来过这里的人,就将这里称为故乡”[2](P278),这里人们能同病友无拘无束地生活在一起,因为大家健康或者生命都受着同样的威胁。但山庄疗养院里也逗留着另外一些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要是有人问卡斯托普这里的情况,他很可能会先说起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根本没有病,只能以一些轻微的不适为托词,事实上只因为病人的生活模式对他们的口味,完全是为了娱乐而自愿地生活在这里。”[2](P413)例如施皮奈尔就向他爱慕的克莱特杨夫人透露,他呆在这里“是为了风格”,确切的说是“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时代的建筑……这种明朗和坚实,这种冷酷的朴实和拘谨的严肃,给我力量和尊严。夫人,毫无疑问,它最终会是我得到内心的清涤和复苏,使我在品格上有所提高”[3](P96)。
除了施皮奈尔和克莱特杨夫人,疗养院里逗留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害胃病的、害心脏病的老爷太太们,和中风的、害风湿病的,以及神经有各式各样毛病的人。有害糖尿病的将军,在这里消耗他的退休金,还有赫伦劳赫牧师生了19个孩子而完全丧失思维能力的妻子……,等等。这些人用医生主持列昂德的话来说,“那大都优柔寡断,既不能为自己制定一套规章制度,又不能自动遵守,便干脆让他做主,乐得去依赖他的严格管束”。
以卡斯托普为例,作为《魔山》中那个交织着神话色彩、也同时透着世俗感觉的病态世界的主人公,他一开始还保持着来自汉堡的传统,总是带着礼帽。但很快就以生病的表哥为模板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了熟悉、平稳、严格划分时间的所谓“横向”的生活,他就餐时不再坐直背,进入大厅时不再费劲关好身后的门,而是让它自己撞上;渐渐地也适应了这里主流的习俗,走路不再戴帽子。塞塔姆布理尼(Settembrini)劝诫他,长此以往卡斯托普为之而生的生活方式会轻易丧失,但他也并不在意。塞塔姆布理尼还告诉他,“最多半年,来到这里的年轻人脑子里除了调情和体温之外就不能再有别的想法,最多再过一年,他便再不能接受别的观点了,任何其他的想法他都会认为是残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错误和无知的”[2](P278)。这同样也不能引起他的重视。卡斯托普没有像詹姆斯叔叔(Onkel James)一样仓皇而逃,也没有像小弗兰茨(Franzchen Oberdank)一样,为能在山上多待一年而振臂高呼,但他留了下来。在对山庄国际疗养院病态世界的描写中,透露着饱食终日的社会中生命的消逝,这里不只是病患的落脚地,无论谁能支付代价,就可以在这里醉生梦死地屈从与无所事事堕落,沉溺在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双重诱惑中。疗养院的主治医师贝伦斯(Behrens)也认为自己是了解死亡的,是死神的雇员,他也曾说“我同意,肺结核是同一种特特殊的情欲结合在一起的”。
由卡斯托普的例子可见,疗养院的特征是它既含有病态的因素,又包含着治疗、痊愈的希望和作用,疗养院试图让人远离死亡的威胁,并带领人找回康健的生命。但事实上疗养院的患者却长期处于了久病不愈和康复的临界上,他们既不是健康人,又不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病人,疗养院的生存模式因而也类似于处于转变期的中间状态,是疾病和健康之间的模糊点,是地狱和天堂间的中转站——炼狱,赎罪的炼狱。根据西方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炼狱是亡灵的过渡性的停留所,之后他们坠入地狱或升入天堂,正如疗养院的病患也徘徊于生与死的灰色地带,从这里他们被死神掠走或者重回生命。但丁在《神曲》中就详细描写了炼狱这一特征,《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寓意人类由犯罪、受苦而失望——地狱;经由信心而涤罪——炼狱,而由爱而获救赎——天堂。知识、理性和智慧(由维吉尔代表),可到达幸福之门,唯有信心和爱(贝娅特丽丝代表,)引导人进入天堂。
在炼狱中,亡灵为了超脱,要根据以往所犯过错的恶劣程度而承受严酷程度相当的惩罚来赎罪,并根据罪孽的级别被分派到不同的赎罪地,因为亡灵能爬到山越高的位置,就越容易从山顶升入永乐的天国。同样疗养院安置病情的等级来运作,轻度患者或者快康复的人享有很多的自由,但重病号却必须远离一切组织的活动,日日夜夜困在床上,例如《特里斯坦》里的雪橇旅行,他们就不能参加。施皮奈尔和克莱特杨夫人都没有参加这次旅行,施皮奈尔趁机说服了自己的心上人弹奏钢琴曲,尽管这是医生严格禁止的。曼对这段音乐精湛的描写展现了听觉艺术音乐和视觉艺术文学天衣无缝、游刃有余的转换统一,而语言特色中的宗教色彩也让疗养院这一世俗的医疗健康概念和炼狱这一宗教概念更为贴近。在弹奏之前,施皮奈尔就营造了一种童话般的气氛,将少女时代的克莱特杨夫人描绘成泉水边7位女伴中的女王,还带着不可名状的皇冠。他用天使的名字来神化心仪的女子,当克莱特杨夫人讲述着自己如何嫁给成功的商人为妇,并生育了强壮健康的儿子的时候,施皮奈尔也借用了《圣经》的话语“跟他去了”。当演奏开始时,他像在神坛上一样,点燃了钢琴上的两支蜡烛,“她又细腻又虔诚地弹着,忠实地守卫者每个形象,恭顺地烘托出每个独立的细节,就像神父把最神圣的十字架举在头上那样。”[3](P108)在弹奏肖邦的夜曲时,描述都还是乐理性质的,“对不同的音色表现出一种过敏的感受,对有节奏的旋律流露出近乎痴迷的喜悦,指法坚实而轻柔”。叙述者对肖邦的曲子引用了完整的总谱名称:《降E大调夜曲,作品第九号之二》,与之相对比,瓦格纳的作品却长时间没有提及名称,在施皮奈尔“不可能!……不是真的!……然而我并没有弄错!……你知道是什么吗?”的惊呼里保持了神秘的色彩,直至这一桥段的末尾才提到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名字,但两人已经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在爱情的殉难里融为了一体,“两股力量,两股陶醉的生命,在悲痛和狂喜中,为了得到对方的挣扎;它们如痴如醉地渴望那永恒和绝对的东西,并在渴望中互相拥抱”[3]。最终,施皮奈尔无声地跪倒在他的伊索尔德面前,张开双手如敬神般崇拜他的爱人。如果肖邦的音乐象征的是分明和界限,那瓦格纳的则象征消融和结合,这是世界末颓废派与法兰西帝国古典风格间、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间对立统一的辩证矛盾的回响。
同但丁《炼狱》中人物谱系一样,从社会等级划分来看,这些人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从没有一个工人或农民,也没有雇员和公务员,即使是施皮奈尔——如果他唯一的那本描写豪华闺房中沉闷得不近人情的故事的小说不是他的经济来源的话,他定然也像卡斯托普一样,或许是由于继承了不菲的遗产,而轻而易举地支付“古老、朴素、高雅”的疗养院的费用,并“为了风格”呆在这里,同时,施皮奈尔考究的衣着也佐证了这一点。卡斯托普也曾十分细致了计算了疗养费用和他所继承遗产的利息,且从中得到一个让他十分安心的结果。就连毫无教养的施杜尔女士(Frau Sthr)也家产甚丰。
三
而这些逗留在疗养院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中心人物则是以施皮奈尔为例艺术家。托马斯·进行这样的人物组群塑造,原因之一就是在世纪之交颓废派文学潮流的影响下,艺术和疾病渐渐成为了水乳交融的两个主题,当时体弱多病、苍白无力的艺术家形象在关于艺术家的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而托马斯·曼更是把艺术家主题视作纵贯其整个创造生涯的主题,从《死于威尼斯》到《被骗的女人》再到巅峰之作《浮士德博士》,病态就一直同艺术家本性、艺术敏感性、真正天才、灵感等联系在一起,曼自己也曾说:“疾病和健康,这两种艺术家的或压抑或创造性的状态,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难道我这样说没道理吗?在疾病中,或者说是在疾病的庇佑下,健康的因素出现在作品中,同样,疾病的因素也赋予了健康以灵感。我想到一种感情模式,它给我带来苦闷和惊恐,但同时也令我充满骄傲,我认为,这种感情模式就和疾病和健康的关系没有不同:天才是一种在疾病中深刻体会到,并由疾病创造且通过其疾病取得创造灵感的一种生命力。”[2](P471)因此,谈艺术就免不了谈病态,谈病态就逃脱不了疗养院或类似疗养院的舞台背景。正如施皮奈尔的穆斯女神所说,在这里“温火般的寒热,给她一种轻微的振奋感觉,引起沉思、痴想、自我珍惜和一点被损害的情绪”[3](P103),或许正是这种情绪成了世纪末颓废派文学所推崇的灵感催情剂。
因此,疗养院病患的生活方式和曼笔下的众多艺术家都有微妙的类比关系。在疾病的迫使下或者是以患病为借口,疗养院的居住者都同熙熙攘攘的世俗世界断裂了联系纽带,选择或被迫选择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这与曼笔下的艺术家角色也共通之处,他们大都拒绝对社会或其某一群体的归属,游离于人世的边缘,例如施皮奈尔和克莱特杨夫人都回避了令众人趋之若鹜的雪橇旅行。但值得注意的是,疗养院与世隔绝并没有让居住者完全地孤立,形单影只,对月三人,他们大都与几个固定的病友组成了微型社会,并把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局限在这个圈子里。例如疗养院里的卡斯托普(Hans Castorp)与他的精神导师塞塔姆布理尼(Settembrini)和纳夫塔(Naphta),例如艺术家形象克鲁格尔和他的女画家朋友,莱维屈恩及其传记的执笔者蔡特布鲁姆(Zeitbloom)。疗养院是世俗生活之外自成一体的小世界,反照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并在文学再现中可以集中地表现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圈子。
此外,疾病与艺术的关系无论是在小说的细节还是主题上都有体现。例如,《特里斯坦》中的疗养院的名字——Einfried就不禁让人联想到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住址——Wahnfried别墅。①Dort wo mein Wähnen Frienden fand,Wahnfried sie dieses Haus genannt.这句话题写在这座1870建成的别墅上。疗养院象征着疾病,而疗养院的名字则象征着艺术,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瓦格纳的艺术,是他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是歌咏殉情的悲剧。瓦格纳迷醉的音乐充溢这爱欲和死欲的交织,单单小说的题目《特里斯坦》就把病态、艺术、爱欲和死亡的母题暗示了出来。此外Einfried在德语中由与“围困、隔离”(Einfrieden)同样的词根构成,这一联系也揭示了疗养院与世隔绝,疗养者是社会边缘人物的特征。另外,Einfried的第二个音节还同“墓地”(Friedhof)相关,这是死者长眠之地,是生者探望亡魂之地,是最终的安宁之地。以上两点——与世隔绝以及与死亡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是艺术家的性格特征,例如施皮奈尔,他在疗养院便是孤独的,从不与任何人交往,虽然他只需要少许电疗,但他的生命力却十分衰弱,连脸上瘦得没有了肉,腿还不听使唤的老先生都嘲笑他是“败坏的婴儿”。
除了疗养院的名号,故事的女主人公更是病态与艺术交织的聚象化:她炉火纯青的钢琴演奏使其病情恶化到不可挽回的程度,这便使上诉两大主题交相发展的峰值。克莱特杨夫人闺中姓氏是Eckhof,据施皮奈尔的了解,这也是18世纪一位曾担任汉堡国家剧院经理的著名演员的姓氏。她的生命终结在艺术和疾病的交响曲中,而给予她生命的父母本身也是这一矛盾体的映现:她的母亲英年早逝(病态、死亡),她的父亲则极具音乐天赋,是个优异的小提琴演奏者(艺术,天才)。如同《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盖尔达(Gerda)一样,克莱特杨夫人也自小经常同父亲一起合奏。当年,克莱特杨迫切的求婚便让老Eckhof“别有顾虑”,虽然叙述者没有进一步的阐释,但不难推测,这位善感的老艺术爱好者自始便不看好两人的结合:一边是艺术家本质的脆弱,另一半却是极端健硕。
四
尽管疗养院和炼狱有着诸多的类似之处,但疗养院却终究是个倒转的炼狱,进入这个中转站的灵魂,无一升入天堂,疗养院似乎更是设在地狱前庭的炼狱,出口只有一个:商人之妇在这里演奏了生命的绝响,汉斯·卡斯托普的背影淹没在一战的炮火里,施皮奈尔“为了风格的”停留也并没有让他在品格上有所提高。托马斯·曼对于此类结局的倾向性,除了世纪之交的颓废派文学的时代大背景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深受叔本华以批判理性、宣扬悲观主义的特点的哲学体系影响。曼曾把叔本华与尼采和瓦格纳一并比喻为照亮自己思想的三颗明星,在其随笔《叔本华》中,托马斯·曼也坦言:“初读叔本华作品,那醍醐灌顶的兴奋只有少年时初识爱情、初尝性爱的快感能比较”[4](P276)。叔本华作为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始祖,把康德哲学体系中的物自体阐释为“意志”,而意志“本质上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5](P28),意志的本质就是不可抑制的冲动和盲目的欲望,因此也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叔本华认为只有在死亡中才存在对意志的否定,或者当完全沉浸在艺术欣赏、艺术陶醉中,可以得到短暂的平静和解脱。因此,托马斯·曼笔下的疗养院,作为生命意志和意志否定,即生命和疾病(半死亡)之间的灰色混沌地带;同时也常常蔓延着艺术的氛围,遁入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如进入黑洞般无法再返回曾经的世界。
[1]Thomas Sprecher(Hrsg.).Literatur und Krankheit im Fin-de-Siecle (1890-1914)[A].Thomas Mann im europäischen Kontext [C].Frankfurt am Main: bLoch Verlag,2002.
[2]Thomas Mann.Gesammelte Werke in dreizehn Bänden,Band III [M].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1974.
[3]托马斯·曼.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M],钱鸿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Helmut Koopmann.Thomas-Mann-Handbuch [M].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2005.
[5]叔本华.最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scaping to Purgatory—Thomas Mann’s Image of Sanatorium
HUANG He-q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Death and illness is a theme running through Thomas Mann's lifetime creation,with the sanatorium being its special stage background.His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and mythological archetype makes it a chaotic zone between disease and health,death and life,which can be compared to an earthly purgatory,nourishing the decadent art form at the turn of century.
Thomas Mann;sanatorium;purgatory;art;illness
I106
A
1005-7110(2011)03-107-04
2011-02-26
黄河清(1984-),女,山东泰安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语言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