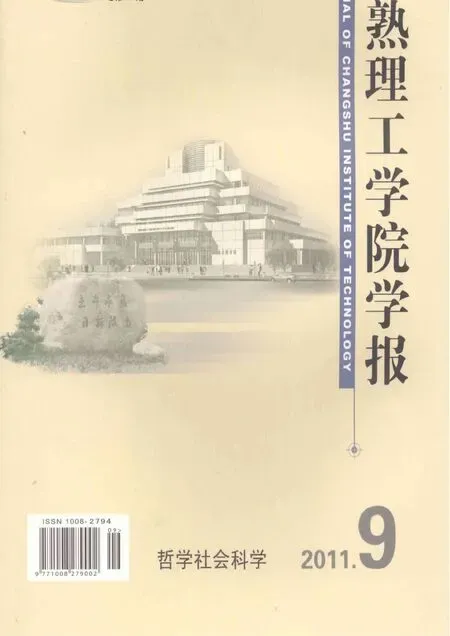论南社诗歌的现代化趋向
许 霆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本文基于以下三个想法。一是中国新诗的发生大致从晚清诗界革命开始到五四文学革命完成,20余年间经历了诗界革命阶段、辛亥诗歌阶段、新诗运动阶段和五四诗体解放阶段,终于完成了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二是新诗发生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里的“现代化”不仅是时间观念,更是价值观念。新诗发生的现代化趋向,大致体现在诗质的现代化、诗语的现代化和诗体的现代化。三是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之间,有个诗歌现代化的过渡时期。不过,这一阶段的文学(包括诗歌)研究常常被人忽视,曾有论者在考察辛亥革命与初期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后指出,思想启蒙和文体革新等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其实早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就已初见端倪。[1]278因此,研究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不能忽视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这一重要过渡时期的诗歌嬗变。它不仅为五四新诗的发生和发展开拓了道路,同时自身就是一个诗歌现代化的发展时期。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南社诗歌,就在整体意义和诸多层面上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这里以南社创作群为主,兼及章太炎和秋瑾等前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概述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诗歌在诗质、诗语、诗体现代化趋向方面的基本特征。
诗歌内质的现代趋向
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这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与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在人脉谱系都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这是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甚至前此的辛亥时期的革命思想,都是应注意的历史事实。而且,这两个运动间在文化革新的思想上是有着直接的相承关系。”[2]128这一理论分析,为研究诗界革命和新诗运动期间诗歌现代化嬗变提供了思想指导。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思考中国文学观念近代化的问题,如刘师培明确区分了文学与学术的不同性质[3]《左盦外集》卷13,鲁迅强调了美术的虚构和想象的性质[4],王国维则强调文学独立的价值,确立其现代文学的功能观[5-6]。这些多元化的观点,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功能观,使文学从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载体,转变为“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把文学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上。换言之,文学成为表达人生、抒发情感、阐释人情、反映现实、呈现世俗的独立的学科门类。20世纪初“文学”独立地位的被确立,表明中国文学观念在西方思潮的推动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趋向,推动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给予20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正当其时的南社诗歌理论是传统和现代的混杂或曰过渡,包括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历史真实。在论述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时,胡韫玉、黄人、蔡寅、沈昌直、高旭、陈去病、庞树柏等都特别强调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如胡韫玉认为,文学除“因言见道,因道立法,因法行政,因政成治”外,“大之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次之布政宣化,利国福民;下至闾巷之歌谣,贤士之诗赋,亦所以写其人情风俗之态,寄其忠君爱国之忱;文字之用,至为广矣。”这里涉及的诗歌内容突破了传统,强调面向广阔的社会和多彩的人生。二是抒写心情。南社诗人对龚自珍十分推崇,柳亚子誉其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论诗三截句》)。抒写童心、崇尚浪漫,是南社多数诗人所追求的一种艺术风尚;呼唤社会变革、追求个性解放,像一条红线贯穿南社诗歌。陈去病于1910年发表的《南社诗文词选叙》历来被认为是南社初期文学纲领,文章以三个“不得已”申说了他们“抒写心情”的具体内容:一是屈原、贾谊式的不满现实政治,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二是宋末遗民谢翱、唐钰式的痛苦流涕,满怀故国之思和民族之情;三是抒发同志反清友谊,特别如向秀怀念被杀的稽康那样的缅怀先烈之情。
“历史真实”和“抒写心情”,超越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也区别于资产阶级维新诗学的宣传工具的观念,把诗歌的写作与多彩人生、与世俗现实、与心灵感情契合,来呈现诗质在现代嬗变中的新面貌,体现了诗歌的现代转型趋向和独立审美评价。南社诗歌的诗质呈现着新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引入新派诗的意境。由黄遵宪、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诞生了以新意境、新语句和古诗风格为基本特点的新派诗。这里的“新意境”,并非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境界,而是指西方的精神和境界。南社诗人也创作了一些不无新意境的新诗。柳亚子自幼敬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他的诗文也因此铸就了新的思想武器和艺术生命,渗透着近代意识。如其《岁暮述怀》(1902年):“思想界中初革命,欲凭稳坐播风潮。共和民政标新谛,专制君威扫旧骄。误国千年仇吕政,传薪一脉拜卢骚。寒宵欲睡不成睡,起看吴儿百炼刀。”写给儿子的七律:“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而公。须知恋爱弥纶旨,不在纲常束缚中。一笑相看关至性,人间名教百无庸。”(《自海上归犁湖,留别儿子无忘》)可谓身教言传,充分体现诗人崇尚自由平等、蔑视封建礼教的民主思想。南社另一重要诗人高旭,其诗在内容上有较多的新思想、新气息。如前期诗《好梦》,通过“梦”展示出一个无政权、无剥削、无压迫,平等、自由、美好的人间乐园,反映了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希望中国建立一种平等、民主的共和政体。作者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所构建的幻想,体现了南社的少壮文艺和浪漫精神(曹聚仁语)。晚年柳亚子回忆说:“‘旧诗革命’的名词是我杜造出来的,也就是继承着四十年前谭复生、梁任公一般人创业未竟的‘诗界革命’系统而来的。”①参见柳亚子《旧诗革命宣言书》,载《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南明史料纂征社1944年编印。无疑,这些诗歌受到了梁启超诗界革命新派诗的影响。不过仔细阅读南社诗人这类具有“新意境”的诗歌,可以发现他们已经跳出了政治宣传的束缚,除了早期偶有所作外,南社诗人并不喜欢玩弄新名词和新术语,而是注重诗歌内质所具有的一种新思想、新意境、新精神,体现了面向世界、面向现实的现代特征。更确切地说,南社诗人的新派诗直接继承了黄遵宪的新派诗风格。黄遵宪和梁启超都提倡“新”,但审美地说,黄氏之“新”主张“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重视内心经验与个性对新思想新精神的转化,梁氏之“新”则是生硬地搬弄新名词,把尚未在现实中生根的新观念、新名词直接当作诗。南社诗人创作中由新思想或新理想构造的新意境,是诗人用诗歌接纳变动时代的新事物、新理致,在接纳中经历了内心经验和个性的转化,因此具有新的诗质,即新诗现代性的特征。
其二,自由地抒写赤子之心。南社诗歌在审美上的重要特征是学龚,重在“尊情”。龚自珍文学理论的核心在于“尊情”,而且斥伪体、重真情,这与他思想上追求个性解放密切相关。龚自珍所尊之心乃是一颗天生无邪的“童心”:“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午梦初觉,怅然诗成》);“既壮周岁施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这一再呼唤的“童心”,就是一颗真心,就是独特个性。由“尊情”到倡言“童心”,体现了在特定的社会变革时期,诗人充分展示个性的现代意识。应该说,与龚自珍所处的乱世时代相比,1912-1919年间南社诗人遭遇的更是政局动荡的混乱时期,所以,他们之学龚,体现着在特定年代抒写心灵、表征童心的现代性追求。身处乱世中的南社诗人多有恸哭:诗人李葭荣(怀霜)作《宋钝初先生谏并叙》千字文,接连出现8个“呜呼哀哉”,极其沉郁的悲愤之情凝聚于中;柳亚子坦言:“我是一个书呆子,既非学人,又非政客,只好弄弄笔头,长歌当哭。”[7]54哭到疲惫时候,便拓展出这一时期诗歌的多种趋向:骂世、混世、避世、售世。诗人周咏骂道:“玄蜂赤蚁,弥漫神州。魑魅魍魉,伺人而食。”诗人顾悼秋骂道:“风景不殊,河山已异,腐鼠沐猴,滔滔皆是。”曾经慷慨高歌的高旭也以极度倦萎的心境写道:“脑筋心血绞全枯,我已年来倦世途。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观剧赠陈二郎·之一》),“不如一舸携西子,老死温柔醉梦乡。”(《海上联吟次陈去病韵》)此时的柳亚子“觉得撇不住这一口鸟气,索性‘沈饮韬精’,和苏曼殊、叶楚伧鬼混在窑子里过日子。”南社活动从来与酒相伴,而在1912年后,饮酒、醉酒发展成闹酒,柳亚子与顾悼秋、周云等发起“酒社”。时人记载柳亚子当时的醉态:“乙卯中秋,闹酒社时,尝与余及大觉乘醉至旷野奔走,折损其足,阅数月而愈。又尝游西湖,酒力既厚,感触国事,涕泪横胸,意欲跃入湖中,其狂态盖可知矣。”[8]244这一时期的《南社丛刻》里,既有陈去病的《山居杂诗》等,也有1914年柳亚子请人作《分湖归隐图》、1916年凌景坚作《分湖晚棹图》遍征同好题咏,借田园逸致之景,托退隐避世之志。对南社诗人这类诗的境界,我们可以持保留意见,却无法怀疑其内在张扬着的诗人个性,这是一种特定方式的入世反抗,体现出了“曳衰世之哀怨拗怒之情”,具有现代诗质的精神。
新派诗歌的意境和面对乱世的酩酊,看似对立的两面有机地结合,充分体现了南社诗歌历史真实和抒写心情的审美追求,从而在文学本质上突破传统观念,推动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文学由此取得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地位。它使南社诗歌的内质达到了那一时代文学面向世界和精神解放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表明一代知识分子正在走向精神独立。南社虽然是个革命团体,其成员大多同政治有染,其中的先行人士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士大夫文人身份,“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9]211向着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新旧过渡而趋向现代的人物。苏曼殊就是南社中这类人物的重要代表,被人称为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身处终结与开端交迭位置的典型。他的诗质包括两部分,首先是参加以孙中山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诗中抒发了对满清封建王朝的仇恨和欲求反叛的激情,这类诗接受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建构起苏曼殊的人生形式,使他满腔民族的与革命的诗情成了人的解放这一总体诗情的组成部分;其次是他的一生行事和创作始终处在入世与出世、否定之否定的冲突关系之中,无时不在与束缚个性、压制人性、摧残人格的种种封建伦理道德、宗教意识作斗争,强烈地渴求着人性的自由、人道的平等、人格的独立。这两个方面都显示着郁达夫所谓的苏曼殊的“近代味”。
诗歌语言的现代趋向
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传统的诗文必须用雅语、用文言、用书面语来写作。因此,推进文学现代化的重要一翼就是白话运动。用通俗的白话来代替典雅的文言,是文学革新运动全面展开的最佳切入点,也是中国诗歌全面完成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期间,正是晚清白话运动最热烈的年代,处于这年代的南社诗人的作品必然受到影响,因此南社诗语的现代趋向也就势所必然了。
诗界革命中说的“新语句”,虽然包括了要求现实词汇(包括外来词语)、通俗口语和散文句式入诗,但这种诗语仅限于面向大众宣传维新的那些诗歌,而且其理论依据尚不是倡言诗语白话、推倒文言,而是言文合一、诗语通俗。进入20世纪以后,白话运动才形成声势。晚清白话运动的基本特点,呈现着新旧杂糅、文白二元的过渡色彩,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作为由传统文人学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南社诗人,基本取向也是新旧杂糅、文白二元,即白话作为时文的语言、文言作为诗文的语言,只是诗文语言在白话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呈现着现代趋向。这就注定了南社诗歌在诗歌现代转型中的过渡性质,由此奠定了它在诗歌现代转型中的特殊地位,成为新诗发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柳亚子曾追忆:
新文化运动发现之初,文言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人,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了。[10]101-102
南社诗人对白话运动的态度分二类,一类是始终抱着反对的态度,另一类是先反对后又赞成。但即使有人反对白话,也并非完全拒绝,只是反对在传统诗文中使用白话,而主张在报刊时文中使用白话。如柳亚子就把文体和诗体分开,说文体可用白话,诗歌则沿用旧体。在柳亚子反对着白话的那一年代,他写过章回体白话历史小说《陆沉记》(1903);1905年,他创办《自治报》,语言是文白兼用、雅俗共赏。当然,在传统文学观念中,诗歌历来使用典雅的文言,所以南社诗人创作多用文言。尽管如此,由于南社创作正处在晚清白话运动的高潮,其诗语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白话报刊的涌现和平装书籍的诞生,标志着文学的传播媒介工业化和商业化,其受众是广大的社会读者,不再局限于少数士大夫,这就自然地推动着作家的创作意识和语言表达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了走向平民、走向世俗、走向世界的基本趋向。南社成员或主办报刊,或任报刊主编,或任编辑记者,新闻报刊业是他们的主要职业。辛亥革命后的各种杂志“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11]3这样,南社成员的诗、词、文、小说、杂著,也就不同于传统的口耳相传,主要是通过报刊得以传播。有人统计,从1903年到1922年间,刊登过南社诗人作品的报刊在100种左右,现有诗文集的作家如柳亚子、高旭、陈去病、于右任、叶楚伧等,都在报刊上或多或少地有散佚的作品。研究表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夜的新闻报刊,“副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当中,有不少是南社的社员。”只要是南社人编辑的报刊副刊,就会发表不少南社人的作品。[12]302晚清白话运动,尤其是运动中白话报刊的推动,直接影响到南社诗人的诗语。所以,南社的诗歌虽然多数仍为文言,但已呈现着现代的趋向。
一是诗语趋向通俗。南社在文学史上首次提倡“布衣之诗”,布衣之诗的重要特点就是无缙绅气,而成草泽文学,诗歌技术粗豪叫嚣。南社成长的时期,正值同光体称“一尊”的全盛时期,柳亚子等“思振唐音,以斥楚伧,而尤重布衣之诗”(《胡寄尘诗序》),就是对诗坛“一尊”的一次挑战。胡朴安评论宁调元:“其诗以缙绅定字学论之,或议以粗豪,或议以无律,而不知其固草泽文学本色也。”揭示了布衣之诗不受缙绅文学格律和风格的束缚,不在精致而在粗豪、不在正统之气而在慷慨激昂、不在格律严谨而在随处泄发。正是这布衣之气,如曹聚仁所说:“南社的诗文,活泼淋漓,有少壮气,在暗示中华民族的更生。”[13]248布衣之诗加上利用报刊传播,诗语风格上就不免粗砺以至走向通俗。如于右任写于辛亥后的《雨花台》:“铁血旗翻扫虏尘,神州如晦一时新,雨花台下添新泪,白骨青磷旧党人。”既表达了神州光复的喜悦,又未忘却献身革命的先烈。明白如话的诗句,显示出独特的风格。写于护国战争时期的五古诗《高陵道中》:“雪后高陵道,平原剪剪风。新坟春草碧,故垒夕阳红。高骨元戎马,号天四野鸿。老兵莫垂泪,不日定关中。”貌似平易的诗句中饱含深情,通俗白话经过艺术锤炼,达到全新的境界。柳亚子的诗用典较多,历来遭人诟病,但不少诗作也趋向通俗,如《吊鉴湖秋女士》四章之一:
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拚狭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诗句语言通俗,没有用典,也无缙绅之气,具有诗的兴象和抒情意味,在郁怒横逸中饱含慷慨悲壮之气。高旭的《大风潮起作歌》、《路亡国亡歌》、《登富士山放歌》、《祝民呼报》等作品,思想激进开放,如《登富士山放歌》的语言,与传统诗语差别较大,在九字句中夹杂七字句、十三言句等,尤其是大量采用叠词,读来朗朗上口,节奏倾向口语,典型地表现了民主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文学的时代气息和艺术特点,高旭也因此获得了南社新派诗人的称号。秋瑾诗多数可谓自抒胸臆、不假雕琢,“恍如天马行空,不受羁勒,非若寻常腐儒之沾沾于格律常调、拾古人唾余者可比。”[14]151
二是诗语趋向媚俗。这首先表现为一些南社诗人为迎合时潮,以西方名词术语直接入诗。比如马君武的诗,常以西方典实入诗,如“娶妻要娶意大利,嫁夫当嫁英吉利”(《贺高剑公新婚》)。外语入诗在其诗中更多,如“君为克考舞,妾唱拜恩歌”,所以柳亚子称其“能合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治者。”他自己也说:“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寄南社同人》)柳亚子诗中也有新名词,如《读〈史界兔尘录〉感赋》:“嫁夫嫁得英吉里,娶妇娶得意大里。人生有情当如此,岂独温柔乡里死。一点烟土披里纯,愿为同胞流血矣。请将儿女同衾情,移作英雄殉国体。”新名词入诗,有着新派诗的味道。
其次是南社诗人写了大量骂世文,其中不少是歌谣体诗。灰暗的社会背景诞生了骂世的谣体。如昂孙的《忘不了》:“军人都说纪律好,只有冶游忘不了。成群结队走街头,茶馆烟间便胡闹。”“议员都说骨气好,只有贿赂忘不了。累累黄白照眼光,十万五万一张票。”“官长都说爱民好,只有金钱忘不了。清官哪得有余赢,利尽民膏供醉饱。”“政客都说爱国好,只有党见忘不了。入者主之出者奴,黑白混淆是非倒。”诗作仿《红楼梦》的《好了歌》,依次为当时的军人、议员、官长、政客等描摹画像。
再次是南社诗人搜集或创作民歌体时,语言更加趋俗。如秋瑾在1906年前后写的弹词《精卫石》①《精卫石》现存前五回和第六回残稿。,主要由说(说白)和唱(唱词)两部分。说白为散文,吸收了不少新鲜、活泼的民间口语,语汇丰富,富有表现力;唱词用北方普通话写成,主要是三字句、七字句和十字句,常常加入口语和俗语,通俗流畅,富有生活气息。当时的一些刊物特辟“杂歌谣”(如《新小说》)、时调歌唱(如《绣像小说》)、歌谣(如《饭报》)等专栏,刊登歌谣体诗。就创作而言,“歌行”体在当时大放异彩,这种形式自由舒展、富于变化,适于容纳阔大奔放的情感,为站在时代前列的诗人们所喜欢。如高旭的“歌行”体诗《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等,通俗的诗歌语言,利用歌行尽情地抒写诗人的革命豪情,鲜明地活跃着一个为推翻清王朝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形象。高旭还继承乐府传统,创作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歌谣体的《水灾叹》,诗语就趋向民间、趋向世俗。
三是诗语转向白话。从总体说,南社的诗歌多用旧体文言,但也常写有通俗的甚至白话的诗歌。如章太炎并不主张诗用白话,即使要用也是有条件的:第一,为了宣传需要,可以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写给一般粗通文字的群众读;第二,宣传可以用通俗文体,而高层次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应用“雅言”,即文言。但他也偶写白话诗歌,如别具一格的《逐满歌》,语言通俗浅显,使用了如“羊子”、“屠门”、“无赖”、“耕田”、“滑头”、“无数”、“永远”、“做官”、“汉奸”、“洋人”、“猢狲”等大量口语词汇,这些词语或是新的双音词,或是流行时语,或是白话文的词,或是民间口语;诗中还有诸如“菜来伸手饭张口”、“人人都道做官好”、“滑头最是康熙皇”等流行的民间口语,这些群众口头词语或俗言,形象生动地揭露了清王朝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诗押韵自然,七言古体读来顺口,采用诉说的调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多次翻印此诗,在群众和新军中广为传诵,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庞齐编《于右任诗歌萃编》中有“白话诗”一辑,更是显示了南社诗人诗语变革的新貌。如写于1908年的《元宝歌》:“一个锭,几个命。/民为轻,官为重。/要好同寅,压死百姓。/气的绅士,打电胡弄。/问是何人作俑,樊方伯发了旧病。/请看这场官司,到底官胜民胜。”全诗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口语,“命”、“姓”、“病”、“胜”自然押韵;“问是”、“请看”、“到底”等句式的运用,使全诗语言趋向散文化和逻辑化;诗句的结构三字、四字、六字、七字,既有三音节作收稍音组,又有双音节作收稍音组,总体倾向说话调子,把传统的吟调改成诵调。诗句精炼含蓄、形象生动,诗尾设问留下思考的余韵,被称为白话新诗的第一首。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认为清词墨守成规并不创造,但从诗语进化的眼光来看,有些词却显示了新的面貌。有论者认为赵熙1912年归蜀后写的《香宋词》三卷“境界真不易到”,如《婆罗门令》:“一番雨滴心儿碎,番番雨便滴心儿碎。雨滴声声,都装在、心儿里。心上雨、干甚些儿事?今宵滴声又起,自端阳、已变重阳味。重阳尚许花将息,将睡也,者天气怎睡?问老天矣,花也知未?雨自声声未已,流一汪儿水,是一汪儿泪!”学者评价:“如果请胡适来评这首词,他大概会将其归为‘白话文学’了。”[15]220在南社诗人中,有许多人写有词,在诗语和格律方面都显示出自由和口语倾向。这些词对于五四白话新诗的诞生有着积极的作用。胡适《尝试集》中初做的几首,就写有词曲的变相,语言和音节趋向通俗。如果把章太炎的《逐满歌》、于右任的《元宝歌》、赵熙的《婆罗门令》这些近代诗词同胡适等人的早期白话诗词联系对比,就会清楚地看到其间的连续性。就诗语诗体来说,胡适等人的初期白话新诗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些通俗化趋向的诗词,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
诗歌体式的现代趋向
南社诗人不满于当时同光体诗人汲汲于为诗之道。周实斥责光宣诗人“宗宋派、讲格律、重声调,日役役于揣摩盗窃之中,乃文章诗歌之奴隶,而少陵所谓‘小技’者也。”[16]南社诗人主张诗歌革新,但其革新内容主要在诗的思想内容,基本追求仍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正如柳亚子所说:“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17]多数南社诗人仍然写旧体诗,在形式上未能有效地革新。但是,由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存在着形神契合的有机统一,所以内容的革新必然导致形式的新变。在民族存亡之际,南社诗作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战斗色彩;同时,为适应新兴媒体报刊的读者审美趋向,一些诗歌的诗语趋向通俗、趋向媚俗、转向白话成为势所必然,由此导致诗体格律、音韵的疏松,一些诗歌突破传统的诗体而具有了新的体式特征。尤其是南社中还有些诗人自觉意识并提出了诗体革新问题,如马君武的诗除了具有新思想、新意境外,在形式上也力求革新,一些诗句式差参不齐、形式比较自由,正是朝着通俗化、自由化、口语化方向努力,因此被称为“海内文章新雅诵”。又如于右任的《诗变》:“诗体岂有常?诗变数无方。何以名其然,时代自堂堂”,强调诗体随着时代变化,其变的方向即“便于大众的欣赏”,具体说就是“诗应化难为易,接近大众”。其主张为部分南社和资产阶级革命人士实践,从而推动了诗体新变,构成中国诗体由旧诗向新诗转变的过渡环节。
这里着重说一下当时创作的歌体诗和翻译的译诗体。歌体诗被学者称为“从旧体诗演变为‘五四’新诗的一种过渡形式。”[18]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诗界革命中就写过歌体诗,包括黄、梁等人的歌词体诗,如《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也包括黄遵宪倡导的杂谣体诗。到诗界革命以后,章太炎、秋瑾、高旭、马君武、金天羽、杨度、于右任等人写下了更多以“歌”(包括“谣”、“曲”、“辞”等)为题的通俗诗作,代表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诗体革新的最高成就。直到初期白话诗人,如胡适、刘半农、刘大白等亦有此类作品问世。可以说,歌体诗的诞生是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适应登高而呼、深入人心的鼓动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时代要求有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来鼓吹革命、唤醒民众、张扬国魂、憧憬理想,要求诗歌通俗自由,突破传统律绝体的形式,便于容纳和表现丰富的内容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就诗体特点来说,歌体诗吸取和融合了传统歌行体民间歌谣、日本新体诗、学堂乐歌等多种因素,开始冲破传统诗歌格律,语言通俗、句式自由、语势自然、韵散杂糅、文白相间,呈现出自由化、通俗化、散文化和口语化的倾向。此外,歌体诗还表现出一种与音乐结合的趋势,形成诗乐结合的独有特征。歌体诗大致分成歌行体、歌词体和歌谣体三类。变通后的歌行体是歌体诗的主体,创作者有秋瑾、高旭、马君武和于右任等。歌词体创作在这段时间里也是持续不断,1904年起沈心工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1906年扩编后的《复报》辟有“音乐新唱歌集”,发表新体歌词。相对而言,歌谣体的歌体诗创作较少,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通俗的民歌体、杂谣体诗歌,诗人借鉴民间通俗的形式,摈除地方特色和方言的影响,写作表达全新内容的诗歌。如高旭的《女子唱歌》、秋瑾《勉女权歌》、《同胞苦》等。这些诗歌特征,清楚地显示着中国近代诗歌与五四初期新诗之间的内在联系。
秋瑾的歌体诗主要有《剑歌》、《宝剑歌》、《泛东海歌》、《红毛刀歌》、《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支那逐魔歌》、《秋风曲》等。这些诗有着沉郁的爱国思想、火热的革命激情和昂扬的战斗精神,诗体革新精神可嘉。如《宝刀歌》一诗,基本格局是七古歌行,在七言中杂有四言、五言,以至十言、十二言长句,读来跌宕回旋,极有气势,有一种起伏错落的节奏和自由化的倾向。诗中间杂“兮”字以助声势,吸收了骚体因素;“愿从兹”、“铸造出”、“上继我”则是散文句式的进入,使诗人对宝刀的赞美和抒情充满着一唱三叹之妙。《宝刀歌》虽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但内在抒情的精神自由和诗体的节奏自然,非常接近五四初期新诗的萌芽。《同胞苦》是一首歌词体诗。如一段:“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苦黄连,压力千钧难自便,鬼泣神号实堪怜。吁嗟乎!地方虐政猛如虎,何日复见太平年?厘卡遍地如林立,巡丁司事亿万千,世如豺狼毒如蛇,一见财物口流涎,我今必必必兴师,扫荡毒雾见青天,手提白刃觅民贼,舍身救民是圣贤。”全诗凡四章,每章均用“同胞苦,同胞之苦苦如黄连苦”起首,结尾也大体相同,重章叠句,逢双押韵,反复咏叹,前三章结尾“我今必必必兴师”与第四章结尾“愿我同胞振精神,勿勿勿勿再醉眠”,句中用三个或四个叠字,节奏鲜明,语气坚定,乐感很强,适宜于传唱。
高旭的歌体诗主要有《新杂谣》、《女子唱歌》、《爱祖国歌五首》、《军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国亡歌》等。其中要者如上所列后几首歌行体,形象瑰丽,汪洋恣肆,句式多变。如《爱祖国歌》:“汝亦世界上无价之产物兮,汝岂不足以骄夸!我愿为祥凤兮,恣披拂扫荡而莫我遮,以激起汝自由之锦潮兮,以吹开汝文明之鲜花!”此诗体式为骚体的变通,通篇六句三个层次,于一唱三叹中抑扬起伏,感情真挚,音调谐和,虽然留有个别文言及文言句式的语言表达,但如一首自由体抒情诗,已明显具有了白话诗韵味。再如歌谣体《新杂谣》,注重向民歌民谣学习,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借助民间文学的通俗形式,表达全新的内容。这些诗歌已经不是传统民歌的再现,也决非文人拟民歌之作,而是作为歌体诗的组成部分,显示了诗歌现代化的重要实绩。
马君武在南社诗人中属于新派中坚,具有较多的创新精神,他的歌体诗同样显示了诗体的现代趋向。如《华族祖国歌》一诗语言通俗,乐感明显,数章合起来成为可以谱曲传唱的歌词体诗。还有《中国公学校歌》等,句式参差不齐,形式比较自由,就诗体来说是向通俗化、自由化、口语化方向努力的。
中国有诗歌入乐的传统,自明以后此道渐衰,近体脱离音乐,又为格律束缚。到了近代歌体诗时期,又出现了与音乐结合的趋势。不同的是由于简谱由日本间接传入中国,此时的创作不再依调而作,而是独立于音乐之前,因而有了自由的天地,打破了传统曲调、格律的束缚。南社诗人的歌体诗写作,恢复了诗与音乐的关系,开辟了现代歌词创作之先河,而且冲破五千言的束缚,较为放纵自由,对于现代诗体的诞生有启示意义。
于右任早期诗歌《从军乐》,历来被人认为内在和形式上都富有创新精神: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斓斑照青史。/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侮国实系侮我民, 胡为尔!/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摐金齐奋起。
全篇虽多用七字句,但句式长短不一,尤其是多为七字以上的长句,大气盘旋,热情喷涌。这种参差不齐的句式,突破了旧格律的束缚,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旋律感,内在律和外在律较好地结合,充分表达了诗人的新思想新感情。《于右任诗歌萃编》将于诗分成五绝、七绝、七律、白话诗、词、曲、韵文等几类,可见其诗体运用之多。如《劝资政议员歌》,诗题称为“歌”,但却是典型的白话诗。诗中虽有个别的文言句式(如“凭他们赠”),多用三字煞尾的吟咏调,但却充分体现着白话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语言规范和诗体解放的格式要求。若把这样的诗放入胡适的《尝试集》中,在格式上是完全可以乱真的。可见于右任等南社诗人的诗体探索,在总趋势上同新诗运动初期的探索完全一致,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南社诗人的翻译体诗同样显示着诗体的现代趋向。中国诗体现代化过程呈现出自身解放与面向世界的双重发展轨迹,这既包括旧诗内部形式自由化和语言白话化的革新趋向,也包括超越传统“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开放精神。期间,外国诗歌的汉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翻译接受欧洲或日本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精神,那种狂放不羁的英雄气概和悲壮的爱国主义豪情,以及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光辉业绩,给予南社等资产阶级革命诗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品质和艺术风格;通过翻译接受欧洲或日本诗歌的诗体革新精神,虽然在翻译中大多还是采用中国传统诗体,但却程度不同地呈现着冲破格律趋向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域外诗歌表达方式和思维方法的差异性,直接推动着诗体新变,表现在话语方式、语体方式、文体方式等方面。马君武的译诗收入《君武诗稿》的有38首。1907年,马君武把英国诗人胡德的歌谣体长诗《缝衣歌》译成整齐的五言古诗,又将法国雨果的《重展旧时恋书》译成七律体式。最能代表其译诗风格的是译自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这首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语言明丽流畅,情意凄婉哀切,如诉如泣,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原作的风格与韵味。诗虽然还是文言,但却较为通俗,语体和诗体的风格与他创作的歌行体有着内在的契合之处。此外,马君武还译有歌德的《米丽容歌》,译诗采用分行排列方式,既在内容上尽量把西方事物中国化,又大体不失原意;体式上用中国古诗和民歌中连章半重体的形式,与原诗每章首句、结尾的反复吟咏基本相合,从而较好地表达了歌德原作的韵味。[19]327这种译诗,使我们看到了马君武歌体诗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追求。
苏曼殊的译诗多数属于浪漫主义诗篇,除拜伦《哀希腊》外,《拜伦诗选》中收苏曼殊和盛唐山民翻译的拜伦诗5题42首。由于苏曼殊懂外文,又抱着“按文切理”的翻译观念,能够较准确地传达原作诗意,善于体味原诗的风格、韵味,历来评价较高。一位现代评论家说:“在曼殊后不必说,在曼殊前尽管也有曾经读欧洲文学的人,我要说的是,唯有曼殊才真正教了我们不但知道并且会晤,第一次会晤,非此地原来有的,异乡的风味。”[20]226-227苏曼殊的格律较疏的译诗,在精神和诗体上给予近代诗体尤其是歌行体诗以重要影响。
[1]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时期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M]//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M]//刘申叔先生遗书.[出版地不详]:宁武南氏排印本,1936.
[4]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王国维.文学小言[M]//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24-29.
[6]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M]//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37-41.
[7]柳亚子.南社纪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顾悼秋.服媚室酒话[M]//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
[10]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M]//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1]郑逸梅.南社丛谈·前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2]孙之梅.南社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3]曹聚仁.南社·新南社[M]//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4]秋宗章.六六私乘补遗[G]//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5]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周实.《诗论》序[M]//无尽庵遗集.上海:上海国光印刷所,1912.
[17]柳亚子.杨杏佛论文学书[N].民国日报,1917-04-27.
[18]龚喜平.近代“歌体诗”初探[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16-23,32.
[19]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0]张定潢.苏曼殊与Byron与Shelley[M]//柳亚子.苏曼殊全集:第4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