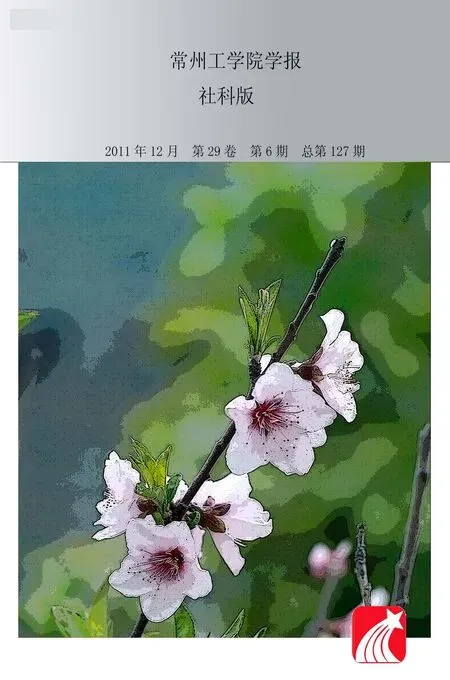山水诗与山水画差异论
姚婷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系,江苏 扬州 225127)
中国的文人对于诗画关系的评论,大体倾向于二者的同一性,尤其是苏轼提出的“诗画一律”,受到了文人们的广泛关注,更生发了“诗画同源”的论断,并成为诗画关系的主调,贯穿元明清而无理论上的突破。事实上,诗画之间存在差异,自然不能完全视同,更不能互相取而代之,我们在看到“诗画一律”这一主流思想在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诗画差异”这条支流。中国古代对于诗画间差异的论述散见于诗画论著中,晋代顾恺之根据嵇康所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句作画时,曾叹道:“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①这是对诗画差异表述最早的例子。此后,唐代方干《项洙处世画水墨钓台》“画石画松无两般,犹嫌瀑布画声难”、晚唐薛媛《写真寄夫》“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的诗句中,都折射出绘画同诗歌之间存在的差异。即便是推崇诗画一律的苏轼,也对诗画差异的问题有过表述。其对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中“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奕棋”两句评道:“此句可画,但恐画不就耳!”(苏轼《调谑编》)其著名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一句,也用了“味”和“观”两个完全不同的动词提醒我们,诗歌需品味,绘画需观赏,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
然而历来对于诗画差异的论述,绝大多数都将焦点集中在由诗画媒介差异导致的表现形式差异上。必须看到,除了诗画二者媒介上的区别外,在表现内容、色彩意象表达、艺术表现上,同样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异,诗与画才能够各寻其路,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一、山水诗之“情”与山水画之“形”
“情”与“形”一直是诗画关系讨论的重点。南朝宋画家宗炳道:“山水以形媚道。”(《画山水序》)北宋欧阳修谓:“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如见诗如见画。”(《盘车图》)北宋邵雍道:“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人秀句,万物无遁情。”可见,诗与画各有自己的长处,区别在于画笔善写“形”,而诗笔宜表“情”,从一定程度上看,鲜明地体现了诗画二者的差异。
探讨诗画“情”、“形”之差异,不可避免地要从二者的媒介差异说起。诗歌以语言文字为建筑材料,重在表现诗人之情感,侧重于主观的一面,由此决定诗歌是“感”的艺术;绘画以笔墨色彩为建筑材料,重在再现自然之形状,侧重于客观的一面,这样的客观性决定了画是“见”的艺术。如果“感”与“见”是从人体主观机能来说,那么“情”与“形”则是诗与画自身所要表达的对象,言情与表形更是二者重要而独特的功能。
对于“形”与“情”,清代叶燮认为“能尽天地万事万物之情状者莫如画”,但凡有形之物,必能表现于画笔之下;“尽天地万事万物之情状者,又莫如诗”,凡是有忧离欢乐、雷鸣风动、歌哭言笑等“触于目、入于耳、会于心、宣之口而为言”之物,惟有通过诗来表现。要言之,画善于表现有形之物,诗善于表现万物情状。然而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形与情的辩证法,“故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赋形则显,是理也。”②“情”、“形”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于艺术创作之中,这一点,在诗与画关系的讨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要探究诗画表现内容的差异,不妨从二者各自的创作过程入手。对于山水诗的创作,古人时有论及:
“旦日初出,河山林嶂涯壁间,宿雾及气霭,皆随日色照著处便开。触物皆发光色者,因雾气湿著处,被日照水光发。至日午,气霭虽尽,阳气正甚,万物蒙蔽,却不堪用。至暮间,气霭未起,阳气稍歇,万物澄净,遥目此乃堪用。至于一物,皆成光色,此时乃堪用思。所说景物必须好似四时者。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取用之意,用之时,必须安神净虑。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言其状,须似其景。语须天海之内,皆入纳于方寸。至清晓,所览远近景物及幽所奇胜,概皆须任意自起。”③
自然景物因四时、气候等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创作山水诗,应选择最佳之景、最佳之时入诗。山水诗中自当有“物”,但绝不能仅有物而已,取用物时应“心通其物”,“言其状”而又“似其景”,“睹其物”更“入其心”,达到“任意自起”的境界。
“作山水诗,何独不然。相山水雄险,则诗亦与为雄险;山水奇丽,则诗亦还以奇丽;山水幽俏,则诗亦与为幽俏;山水清远,则诗亦肖为清远。凡诗家莫不能之,尤是外面工夫,非内心也。……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诠,立跻圣域矣。”④
此言山水诗之创作方法,诗中描绘山水,需对山水之形加以观察,陆机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诗歌创作中的想象能够驰骋万里,万事万物都纳于笔端,然山水诗之重点却在于传达山水之“情”,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大序》),诗歌中的语言文字是为诗人抒发感情服务,语言文字具备无限的张力,同诗人内心情感有机结合,如若做到“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司空图《诗品》),便能到达山水诗所追求的冲淡之境了。
对于绘画来说,表“形”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再现事物形状乃绘画的一大要事。
“客有为齐工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严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留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⑤
这是最早的关于绘画中形与神的论述。这里,“犬马”之所以难以表现,在于其有形,而既定的形象给绘画者形成束缚;鬼魅之所以易绘,在于其无形,无形之物给绘画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但就绘画内容来看,有形之物是绘画中重要的表现对象。山水画的创作中,再现景物之“形”是重要的表现方式:
“眉额颊辅,若晏笑兮。弧岩郁秀,若吐云兮。横变纵化,故动在焉,前矩后方出焉。然后宫观舟车,器以类聚;犬马禽鱼,物以状分。此画之致也。”⑥
山的形状好比人的状貌,顾盼有情。山水画创作中利用线条的横竖变化,创造出生动的形象。山水画以山水为主,但其他附类也必不可少,犬马禽鱼、舟船车舆、各种各样的器物,都是山水画要表现的对象。
形同真境为绘画中较高的境界。北宋郭熙《山水训》道:“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谷而思居,见岩扃泉石面思游。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⑦山水画中“形”若表现得好,就会使人若置真境之中,流连忘返。
然而绘画非以真为最上,“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⑧画家作画时讲究去粗取精,事物形象也要进行处理和提炼方可成为艺术形象,有时更需借助特殊手段处理,比如画不着色、物不绘影等,如此反而更具魅力。当然,作为空间艺术而言,绘画所追求的更在于真之上,“画令人惊,不如令人喜,令人喜,不如令人思。”(清·戴熙)超出画外的感受才是绘画更高的追求。
由以上可知,山水诗“情”的产生同山水画“形”的再现有不同的创作途径,山水诗走的大体是由景到情的路线,山水画则偏重于由景到形的方式。山水自然经由二者不同的创作规律,呈现出不同艺术种类,从而证明了诗画二者同流同源不同质的艺术本质。诗歌所表现的“情”与绘画表现的“形”在艺术创作中各自有规律可循,但终极目的却终究不仅限于物体本身,这也是诗画艺术千百年来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
二、山水诗之“青绿”与山水画之“青绿”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色彩与人类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久而久之,色彩也具有了其特有的象征功能。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有将色彩分为热色、冷色的现象,所谓“炎绯寒碧,暖日凉星”⑨便是人们对色彩通感效应的概括。此外,色彩在哲学家眼中,更别具色彩。先秦时代,孔子将色彩分为正色、杂色、美色、恶色,将色彩同等级、政治联系,有色彩比德说的倾向;老庄主张“素朴玄化”,反对镂彩错金之美,认为“五色乱目”,“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老子更以为“五色令人目盲”。
山水与色彩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山水自然,独具其天然的色彩之美。当色彩与艺术结合,它也就成了表达创作者艺术观念的重要载体。从色彩运用和表达上,我们亦可发现山水诗与山水画之间存在的差异。
诗歌中色彩的应用颇为广泛,山水诗的创作须以天然景物为对象,色彩描绘是诗人惯用的手法,例如: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王湾《次北固山下》)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诗歌呈现给我们的是语言文字,色彩的表达必须通过语言文字传播,“红”、“绿”、“蓝”、“白”等词语并非与天然色彩俱生,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认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表达事物色彩约定俗成的词语。这些词语,虽然书写出来可见,但必须诉诸人脑,传递关于山水景物抽象的理解与感觉,转化为人脑抽象的景物色彩画面。这一过程,充分借助了人脑的功能,实现了听觉到视觉的转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诗歌中的意象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情与物,乃至颜色都可成为诗歌表达的意象。在山水诗中,色彩不仅能够描绘景物的天然之色,有时也能成为作者巧妙设定的意象,表达出超越于一般色彩描摹的情感。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青绿”意象。例如: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远峰明夕川,夏雨生众绿。”(韦应物《始除尚书郎》)
以上两例中,不能将“青青”、“绿”当作一般的色彩词看待,“青青”实为同“柳”并列的单独意象,“众绿”则更为明显。诗人实想借颜色之词传递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之情调。当然,“青绿”意象的意思远不止此,山水诗中用“青绿”作意象的例子众多。例如: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白居易《长恨歌》)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李白《菩萨蛮》)
无论是白居易的碧水青山、李商隐的碧海青天,还是李白的伤心碧,“青”、“绿”之色的运用,已超出青绿色彩的本身,更多地倾向于表达诗人内心或悲或忧的情感色彩。
从这一点上看,“青绿”在山水诗和山水画中体现出较大的差别。
山水画以自然物象为描绘对象,山水画创作是借笔墨、色彩、线条等绘画“语言”塑造形象,并通过视觉形象表达感情。色彩对于山水画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自魏晋始,便有对于绘画传统色彩表现的讨论,这从历代画论中可见。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对山水画的设色也提出了要求;谢赫“六法”之中,“随类赋彩”将色彩作为绘画的施彩法则,对以青绿为主的色彩表现影响深远;顾恺之《画云石山记》中有“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⑩;而明代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评顾恺之:“顾恺之画《谢太傅东山》,层岩叠嶂,飞流急湍……俱用石青绿浓抹,而以苦绿靛青皴染分界,妇人衣饰金装极精丽,使人目骇心惊。”可见色彩山水的萌芽。
青绿乃中国山水画中重要的色彩。中国传统画颜色分为石色与植物色两类,青绿之色乃以石青、石绿等矿石制成,石色厚重,覆盖性强。按技法的不同,青绿山水大体分为“大青绿”、“小青绿”、“金碧”、“浅绛”几种类别。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可谓中国现存最早的青绿金碧山水画。其画中,山峦用青绿重色,山脚采用泥金,山峦树石皆以色渲染,云彩和人物皆用粉渲染点缀,色彩的使用使整幅画面形成金碧辉煌的感觉。
盛世大唐具备豪迈的气象,色彩更是审美的重要色调。此时期的敦煌莫高窟中有众多以石绿为主调的壁画。唐初山水画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青绿山水之代表,沿袭隋代展子虔的青绿重彩山水,总体特征为精工、富丽。李思训《江帆楼阁图》以青绿色为主调,所谓“青绿为质,金碧为文”,其在画中注重石绿、花青、石青的色彩结合光线的变化,“阳面涂金,阴面加蓝”,加以渲染的处理技法,整幅画面中人马云烟、屋宇楼阁,色彩交相辉映,色彩发挥到了极致,因此画史中称其为着色山水之宗。其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设色同样以青绿为主,詹景凤有评:“李昭道《桃源图》,大绢幅,青绿重着色,落笔甚粗,但秀劲。石与山都先以墨勾成,上加青绿,……勾勒树,落笔用笔亦粗,不甚细。”(《詹东图玄览编》卷三)张彦远称其“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可见李昭道与李思训在青绿设色的方法上趋于一致,二者画之区别在一“势”字,所谓“落笔用笔亦粗”,与其父的“春蚕吐丝”法相比,气势殆有所增。
山水画中的“青绿”是山水画创作中重要的建筑材料,青绿色彩赋予山水画景物生动而又具体的形貌特征,诉诸于人的视觉,以二李将军的青绿山水画为例,青绿之色成功地呈现了山水景象,传递出来的是可观、可赏的视觉审美体验。同山水诗中部分独特而又抽象的“青绿”意象相比,山水画之“青绿”色彩运用则显得直接而具体。此项差异,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山水诗与山水画在艺术创作中的不同。
三、山水诗与山水画艺术表现之差异
从诗画二者媒介表达的灵活性看,我们认为,较之于绘画,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更具备灵活多样的表现力。从实践角度看,众多出色的诗歌,是画作很难呈现的。为说明此问题,先以静态表现为例:
王维《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空翠湿人衣”一句,乃作者的想象之语,并兼有夸张之意。诗中欲表现的是山中无所不在、苍翠欲滴的绿色,通过这句诗,便极为巧妙地将此意象传达出来。而绘画则绝难传达此种感受,即使勉强地画出,也难以胜于原诗的艺术表现力。《香积寺》中的名句“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表现了渺无人迹的山中幽冷寂静的寒意,“咽”、“冷”二字极为传神,欲在画中表现出这一感觉,是非常困难的。《汉江临眺》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一联,仍然有作者的想象在其中,天地外的江流与若有若无的山色如何能在画面中较好呈现,同样是摆在山水画家面前的一个难题。
诗歌艺术表现的自由还表现在对于时间、动作、声音变化的灵活表现上,而这一点则是绘画无法企及的。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其中的时间流动以及动作、位移的变化,通过诗的语言可巧妙表达,但是若换成画,由于其表现手法有所局限,若想表达,便是极困难的事。再如:“残霞忽变色,游雁有余声”(刘禹锡《晚泊牛渚》),“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晚霞瞬间的变幻、雁过留下鸣叫声、春天里渐长的春花野草,时间、空间以及声音的变化在诗中均得到了巧妙体现,在画中则很难成功描绘。
此外,诗画在表现意境上各有不同。与诗歌相比,绘画在意境表现上有着更多的局限性。诗歌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山水诗中,诗人情感可通过“情景交融”的方式表现,感情的传达上也因此具备了很大的优势。常建《破山寺后禅院》中“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便是景与物、景与人对话式的写法,至于如何“悦鸟性”、“空人心”,读者自可感受到,但若想通过绘画将此情此景呈现,谈何容易;王安石《泊船瓜洲》一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表达了诗人怀念京陵的情感;孟浩然《宿建德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传神地写出所见之景,融入了作者思乡之情。这些情感多具备“情景交融”的特征,若要用画来展示,仅通过对相关意象进行直观表达,读者想象的余地难免狭窄,因此表现难度也是相当大。
由语言文字组成的诗歌具备独特的表达方式,它可通过文字灵活地塑造形象,采取赋、比、兴等手法表达情感,文学的手法往往比较自由。相比较诗歌而言,绘画在艺术表现上就显得有所局限。其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段和工具为线条、色彩。线条、色彩一经入画,便具有固定性,因此其创作的艺术形象是静止的。若要让绘画表现动作,则需将动态化为静态,或者挑选连续动态画面中的一个经典静态画面,以展现动作的全过程。最好的情况就是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抓住“富于包孕的片刻”,即事情发展的关键时刻而非高潮时刻。可即便是这种情况,也是更多地适用于叙事类的画作,对于本来就出奇平淡的中国山水画来说,想要抓住“富于包孕的片刻”,终究是困难的。诗画间这样的差别也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历史上,为诗配画的“诗意图”往往很难得,但以画为诗的“题画诗”却有着较好的发展。诗与画各自不同的审美表现特点必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综合如上几点,我们发现山水诗与山水画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基于诗画的媒介差异,却又超越于媒介差异。并且,正是由于这样的差异,诗与画才能够各寻其路,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在艺术的星河里熠熠生辉。当然,对于诗画差异的研究,并不能作为区别二者优劣的依据,我们需要实现的,是在诗画一律的洪流中梳理出二者差异的细小支流,如此,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厘清诗画二者之间的关系,把握诗画发展的深层规律。
注释: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21页。
②(清)叶燮:《赤霞楼诗集序》,见王运熙、顾易生:《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③(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38页。
④(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见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44页。
⑤(战国)韩非子:《外储说》,见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4页。
⑥(南朝宋)王微:《叙画》,见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85页。
⑦(宋)郭熙:《山水训》,见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635页。
⑧(战国)韩非子:《论画》,见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635页。
⑨(梁)萧绎(传):《山水松石格》,见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587页。
⑩(东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见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