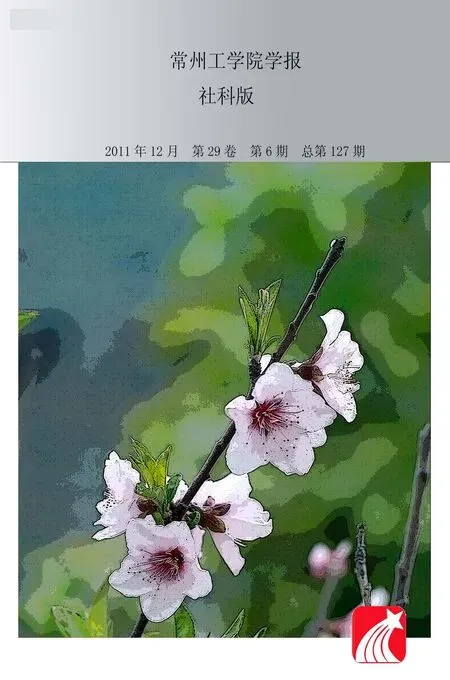论《大地三部曲》中普世化的“他者”
吴丹,肖向东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姚君伟在《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一书中曾说:“赛珍珠最大的愿望是尽其所能地把她所热爱的中国人如实地写进书里,她的终极目标是使人们超越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进入‘天下一家’的境界。”①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以中国为“镜像”的小说代表作《大地三部曲》中努力进行着“他者”形象的普世化尝试,主张从多元文化视角平等看待东西方文化,在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中,既要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又要与其他文化和谐共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②,在此基础上汲取东西文化之所长,在相互渗透与融合中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从而产生新事物,创造共通的理想文化。林语堂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妇女们总是缺乏她们的西方姐妹那种独立精神,被遗弃的妻子总是处在一种无限悲惨的境地。”③鉴于此,赛珍珠不由自主地将女性作为其普世文化尝试的突破口,在作品中努力追求的乃是不同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的全新女性主义思想,注入了蕴含东方文化底蕴的中西合壁的女性意识。《大地三部曲》中的阿兰、梅琳就是中西合璧女性意识的体现。不仅如此,在王氏家族的第三代王源身上赛珍珠也进行着普世文化理想的尝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他是作者对中国出路进行深刻思考后的理想人物④。纵然阿兰、梅琳、王源三者身上都倾注了作者融汇中西的普世文化理想,但结局却大相径庭。
一、普世化的失败尝试:阿兰
赛珍珠对阿兰的塑造非常出色,她使阿兰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中国劳动妇女形象,使得中国农村妇女得以进入西方视野,以其品行、思想意志与西方读者产生共鸣。包括阿兰在内的中国农村妇女之所以能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共鸣,“是由于隐藏在这些女性身体内的强大的力量和蕴藏着的深厚文化根基”⑤。阿兰身上正蕴藏着中西两种文化的因子,作者对阿兰的塑造,实际上是对其普世化理想的一次尝试。
阿兰身上具有典型的东方传统美德:温顺贤良,勤劳坚强。自从成为王龙之妻后,阿兰勤恳持家,执着地爱着她所爱的一切⑥,把家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小说在塑造这一东方女性时,始终将之置放在一个“家庭”空间,写其如何打理家务,如何下田干活,如何为人妻,怀孕生子,侍候公公。对其温顺贤良,其过去的主人黄家老太太在将之许配给王龙时就曾评价说:“你叫她做什么,她都做得很好,……脾气也很好。”⑦事实上阿兰也以东方女性特有的美德印证了他人的评价,家里家外,事无巨细,皆事必躬亲,即使王龙富裕后不让其下地干活,她还是在家里找活儿干,给每个人做新衣、新鞋、新棉褥,以其勤劳获得周围人的欢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东方女性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其柔弱的贤良性格的描画,对于人性另一面的坚韧,赛珍珠也给予了十分生动的揭示,如在王龙发迹之前的艰难岁月里,阿兰身怀有孕,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像所有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下到地里干活,纵然全身浸满汗珠而接近透支,也在所不惜,更让人感到钦佩而具有一种生命震撼的是,在临近生产之时,阿兰挺着大肚,仍像往常一样在地里干活,回家后依然将晚饭做好,然后一个人默默走进房里独自生下孩子。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平常,那样普通,然而,生命在延续,生活在延伸,中国劳动妇女最优秀的品质在此却得到了真切的展现。正是有了阿兰这个贤内助,才使王龙日后的创业心无旁顾,成为可能。可以说,在王龙的事业里,具有典型东方女性美德的阿兰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外,阿兰身上还渗透着西方文化因素:理性与微弱的反抗意识。中国人尤其是女性的思维方式较为感性,正如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所说:“中国人的思维是综合的、具体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去揭开自然界之谜;同样的‘直觉’,或称‘第六感觉’,使许多妇女相信某件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就是如此。”⑧而西方与此不同,它更强调理性,作为西方文化两大源头之一的基督教就“强调人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尊重灵魂,主张人的理智抑制肉体的欲望;轻视人的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重视来世天国的幸福”⑨。再加上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崇尚等等,我们可以看出理性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大精髓。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子地位低下,作为男权社会附属品的她们沦为失语的阶层,缺乏斗争性;而开放外向的海洋商业文化无疑赋予了西方人一种与生俱来的抗争精神,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女权主义的盛行,西方女性地位有了很大提升,其反抗性也更为强烈。《大地三部曲》中,阿兰的形象就闪现着理性和抗争精神的光芒,这无疑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体现。当饥饿的村民冲到王龙家抢劫时,王龙的父亲呜呜哭泣,王龙不知所措,一向沉默寡言的阿兰竟以高过男人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道:“现在还不是从我们家拿桌椅板凳和床的时候。你们把我们的粮食全拿去了。可是你们还没有卖掉你们自己家的桌椅板凳。把我们的留下来吧。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比你们多一粒豆子,也不比你们多一粒玉米——不,现在你们比我们还多,因为你们把我们的全拿去了。如果你们再拿别的,你们会遭天雷劈的。现在我们要一起出去找草根树皮吃了——你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得想着我们自己的三个孩子,而且我马上还要生第四个孩子。”⑩正是这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比有形的肢体抗争更有分量,使得暴动的村民灰溜溜地走了,保住了家里最后的一点财产。此外,当有人要以极低的价钱买王龙的地时,王龙只会愤怒地大喊、啼哭,而阿兰却平淡镇定地说:“我们肯定不会卖地的,……不然我们从南方回来就没有养活我们的东西了。不过我们准备卖掉我们的桌子,两张床和床上的被褥,四把椅子,甚至灶上的铁锅。但是耙子、锄和犁我们是不卖的,也决不会卖地。”阿兰很理性,她比王龙想得远,即使不卖地,要逃难到南方也要有钱作路费才行,况且待他们到了南方,饥饿的村民势必会冲到她家把一切值钱的东西偷走,因而把这些可卖的东西早点卖掉无疑是明智之举。她不仅用理性实现了一举两得,还表达了更具威慑力的抗争,以说理的方式表明卖地后一家自此将没有养活自己的东西,还有什么比无法生存更有说服力的呢?如果说之前的抗争更多的是对强加于人的命运的对抗,那么对仇人杜鹃的反抗则更趋于具体化,真切地反映了阿兰抗争意识的觉醒。当王龙的小妾荷花和丫鬟杜鹃来到王家时,一向沉默的阿兰竟破天荒地与在黄府时的冤家杜鹃发生争吵,第一次质问王龙:“这个丫头片子到我们家来干什么?”面对王龙的无语,她仍不甘示弱,再次追问,纵然抗争失败了,但阿兰没有放弃,她默默地按着自己的主意去做,早上故意不多烧水以致杜鹃只得早起为主子荷花烧水,但家里只有一口锅,阿兰却不紧不慢地煮着早饭,面对杜鹃的叫喊,阿兰无动于衷,她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杜鹃之类小人的不满与抗争。纵然阿兰的反抗在小说全篇中显得很微弱,篇幅较少,但却发人深省,闪现着西方抗争精神的光芒和女性觉醒的曙光。
正是这种保持各自文化特性基础上汲取中西文化长处在阿兰身上的融合,使阿兰这一女性形象具有了一种聚集中西文化优点的全新文化。然而,这种文化的融合是不彻底的,阿兰身上所具有的中西文化并没能真正平等共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大地三部曲》中,纵然阿兰有理性和反抗的西方文化元素,但也只占一小部分,其性格的内核却是在小说中占绝大部分篇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讨论中国妇女的生活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事实上,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他这番话的本意虽然是要为中国男人的纳妾恶俗作辩解,却在不经意之中道出了中国妇女的生存实况。受中国封建礼教禁锢较深的阿兰,她身上的这种男权社会下的顺从、无我尤为突出。在办喜宴那天,她把做好的菜端给王龙,只因为“我不愿在男人们跟前抛头露面”;在南方难民暴动时,阿兰凭着在黄家做丫鬟时的经验乘乱拿到了富家藏的金银珠宝,却悉数给了王龙,就连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对珍珠,还要得到王龙的允诺;当王龙嚷着要从阿兰身上拿走珍珠给漂亮的女人时,阿兰纵然非常舍不得,但还是给了王龙;当王龙要娶荷花,大建两人作乐的庭院时,阿兰也没有大吵大闹,当时只是呜咽着,重复着“我给你生了儿子——我给你生了儿子——”这句话,而这句话也透露出其内心深藏的中国重男轻女的子嗣观念;即使在王龙娶荷花那天,阿兰也是忍着,带着孩子出去了,一大早神情倦怠地回来,还是像往常一样做好饭给大家吃;即使为家庭操劳成疾重病在床时,听到大夫说要治好她的病得五百块银钱,她竟立刻从昏睡中醒来,虚弱地表示不同意,说她的命不值这么多钱,这种自轻完全出于一种本能反应,其受中国封建礼教的戕害之深可想而知。……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还有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兰的形象中中国文化是其内核,西方文化只起着辅助作用。阿兰这一形象最终以积劳成疾,结束了自己操劳苦命的一生。赛珍珠塑造阿兰这一寄予普世化愿望但却失败的“她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凸显受中国封建礼教戕害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同时暗示出普世化理想在两种文化不平等的融合中是无法实现的,从而反衬其寄予理想与希望的普世化“他者”——梅琳和王源才是两种文化相处的最终出路。
二、普世化的理想“她者”:梅琳
梅琳是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中塑造的另一融汇中西的寄予普世愿望的女性形象。与阿兰不同的是,她身上具有着较少的中国封建礼教的禁锢,不是普世化的失败尝试,而是寄予着作者美好希望的理想女性。
梅琳是王虎大太太的养女,在刚出生时,就被丢弃,幸而被太太收留并抚养长大。在收留的众多弃儿中,太太对梅琳情有独钟,希望将其培养成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因为梅琳是唯一一个符合她心意的理想女孩,而这点连她的亲身女儿爱兰都没法实现。在太太的精心栽培下,天生聪慧机敏的梅琳成了医校学生,她刻苦学习,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学业上。她一直铭记太太的救命之恩,因而在学习之余,甘愿为太太做各种杂事,不仅从没有卑躬屈膝之感,反而是满怀感情,大方自然,而且做起事来精明干练,敏捷严谨,深得太太喜爱。
实际上,梅琳不仅是大太太选中的栽培对象,更是赛珍珠所青睐的理想女性。梅琳身上蕴含着中国女性众多典型的传统美德:聪慧勤奋,端庄严肃,诚实信用,温柔贤淑,尊老爱幼,坚韧顽强,对爱情矢志不渝。较之阿兰来说,梅琳一人就将中国女性的这么多传统美德集于一身,无疑更具魅力。她出场时,虽不满十二三岁,但眉宇间已有某种认真严肃的神态,具有灵气和极强的悟性,学习认真,诚实可靠。长大后的她更具魅力,不仅穿着质朴大方,行为庄重,做事得体;而且温柔贤淑,通情达理。与西方崇尚平等独立不同,中国尊老爱幼的传统源远流长,随之而来的则是浓郁的亲情关系。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曾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凝聚着爱的光辉,此种人间真情在梅琳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我们不仅从她对太太和病危的王虎尽心照顾上,看到了其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护;更从她为病逝弃婴的愠怒痛哭,为爱兰不肯母乳喂养自己孩子而破天荒地大吵一架中,真实地感受到她对孩子的一种超乎母爱的情感。如果说透过梅琳对世间老幼的关爱赛珍珠向人们诠释着中国女性人性的伟大与崇高,那么她对梅琳矢志不渝爱情的生动描绘则向人们赞颂着中国女性人性的忠贞与执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诵千古的忠贞爱情数不胜数,杜丽娘、崔莺莺、祝英台、刘兰芝等等都是忠贞不渝的典范,对爱情的矢志不渝也成为了中国女性的重要美德,梅琳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正是这一美德的最好诠释。面对王源的追求,梅琳一开始较为懵懂与排斥,但经历了与王源的相互了解之后,她发现他并不像那些整日花天酒地、蹉跎岁月的半洋化纨绔子弟,因而在心底慢慢滋生着情愫,时刻忠贞于自己的理想爱情,不但对外表比王源迷人的盛不多看一眼,甚至对王源酗酒跳舞大发脾气,也正因为对理想爱情的矢志不渝,她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在王源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守候在他身边。……然而,与对阿兰坚韧生命力的赞颂相似,赛珍珠对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感悟也并不局限于表层美德的歌颂,而是深入挖掘到梅琳人性中最闪光的一面——逆境中的坚韧与顽强。面对恶劣环境,她处变不惊,坚强应对,这点在救治生命垂危的王虎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冒着被暴民杀害的危险,主动前来照顾王虎,不仅以娴熟的医术为其清洗伤口,减轻疼痛,更在粗陋的房子里变废为宝,将稻草编成席子垫在老人身下使之躺得更舒适,将砖头烤热后置于老人脚下为其取暖,更细心地煮小米粥喂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俨然是一个在恶劣环境下灵活应变、坚韧顽强的女性形象,这正如梅琳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想我能在任何地方生活。”赛珍珠对梅琳这一特质的挖掘,不仅是对阿兰顽强生命力的继承,更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精髓发扬光大,使之趋于明朗与成熟。不难看出,正是基于对中国女性传统美德广度与深度上的深刻体悟,赛珍珠将梅琳塑造成了一位触及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理想女性。
当然,除了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于一身之外,梅琳身上还渗透着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独立、自由、反抗等观念在梅琳身上都有所体现。在《大地三部曲》中,她独立设计着未来的事业——拥有自己的医院,为着这个理想,她努力奋斗着,甚至于因担心结婚生子会使她放弃梦想而不愿结婚,正如她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不想结婚,妈妈,我想上完学,成为一个医生。我要不断学习。每个女人都会结婚,我不想只是结婚、料理家务和带孩子。我下决心要成为一个医生。”可见,梅琳不仅在事业、经济上有着较强的独立意识,就连在婚姻上也崇尚独立自由,认为女人不一定要依赖男人而活。面对王源的求婚,梅琳勇敢地说“不”;对于爱兰为保持身材不愿给亲生孩子喂母乳的行为,温和的梅琳竟第一次与爱兰吵架,指责她道:“你不配有这个漂亮可爱的儿子!他生出来时壮实健康、嗷嗷待哺,你的奶胀得满满的,却不愿喂他!可耻,可耻,爱兰!”面对王源像纨绔子弟一样酗酒跳舞,梅琳失去控制,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梅琳的抗争意识,她已经不是封建礼教束缚下那个惟命是从的弱女子,而是注入了西方反抗精神的觉醒了的新女性。
梅琳身上正糅合着中西文化的精髓,这不同于阿兰身上不均衡、不彻底的融合,而是在梅琳体内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地和谐共存。例如,她不仅要学习精通人体经络结构的中医,还要学习在手术和缝合等方面较出色的西医。此外,当王源痴迷地看着她时,她的面颊红了,但毫无躲闪而是大大方方地迎着王源的凝视,“她的脸在发烧,但是她的头勇敢地昂着”;当王源亲吻她后,“她就象一个老式姑娘那样羞怯。他看到她的眼睛扑闪了几下,有一刻她好象在微微颤抖,几乎要转身走开,重新留下他孤零零一人。可是她终于没有走。她勇敢地控制住了自己。她舒展肩背,挺直腰板,昂起头,坚定地迎着源的目光,微笑着,期待着。”从对待异性的行为表现上可以看出,梅琳具有中国传统女子羞怯的一面,但同时具有着西方文化所赋予她的勇敢、自然、坚定。这两种文化恰如其分地结合与交融使得她的形象“既新又旧”,散发着无穷魅力,正如王源所说的:“她有年长妇女的老成稳重和严肃认真,源注意到太太、伯母以及所有以老式方式培养出来的女人都有这种特点。但梅琳身上还有些新东西,她在男人面前既不羞羞答答,也不沉默寡言。在任何地方她都可以坦率从容地讲话,象爱兰一样,自由自在,不拘一格。”这种交融是更为彻底的、寄予人理想与希望的完美结合,她通过汲取两种文化之所长,不仅有效地避免了阿兰身上所背负的中国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压制,同时也避免了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女权主义的盛行,西方文化女性过度放纵的另一极端,展现给读者一个温文尔雅、独立自由、勇于抗争完美融合的新女性形象。这一形象更为饱满,更为完美,是作者寄予人类希望的具有普世文化价值的女性形象。
三、普世化的理想“他者”:王源
在《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除了塑造了寄予理想与希望的普世化女性“她者”梅琳外,还塑造了寄予理想的普世化男性“他者”王源。他是作者对中国的出路进行深刻思考后创造出的理想人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王源就是赛珍珠的理想,他像他的祖父王龙热爱土地,同时也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信仰,找到了自己的志同道合的妻子,王源就是赛珍珠的理想中的人物。”的确,王源身上具备着作者理想化的中西融合的文化特质。
首先,作为王氏家族的第三代人,王源身上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他的文化内涵。他秉承着祖辈所赋予他的中国农民忠厚老实、严肃认真的态度与品性,以及对大地深沉而强烈的爱。在王源年幼时,赛珍珠就在作品中描写了王源的“脾气随和,轻易不生气”;在王源长大之后,作者借孟之口,也称赞了王源“忠诚、老实、始终如一”的品格。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曾说: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为着他们感兴趣的尘世,他们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王源身上正具备着中国人的严肃认真,以及为着理想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幼年时,王源就不同于一般小孩,具有一种超出同龄人的严肃与认真,成年后的王源亦是如此,正如小说中王虎的大太太对王源所说:“你的性格很像你父亲。别人告诉我他像他母亲,她是个严肃沉静的人,总是执着地爱着她所爱的一切。”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促使着王源在六年的国外生活中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不断地充实着自己,最终学有所成,得到了外国教授的赞扬。而他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主要体现在对理想爱情以及对大地、对田园宁静生活的执着追求上。王源的一生中出现过三个女人:因爱生恨的女革命者、白人玛丽、梅琳。前两者都没能真正走进他的内心,这正是因为他心中怀着一份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而梅琳恰好是他完美爱情的化身,她美丽善良,贤惠谦恭,庄重沉稳,果断干练,有理想有抱负,更为重要的是她与他来自同一个国度,她懂他,“无论这个国家怎样丑陋,它毕竟是他们的祖国”,在她面前他可以做回真实的自我。正因为此,他执着地追求着,尽管遭遇挫折,但他的真诚与执着渐渐打动着梅琳的芳心,最终收获了美满的爱情。在探索人生道路的问题上,王源亦是如此,虽屡经挫折,但仍执着地追寻梦想,渴望着大地上宁静祥和的农田生活,因为这不仅能脚踏实地地自给自足,更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体验到大地般充满勃勃生机的生命的弥足珍贵。尽管这种隐秘的爱被憎恨土地、血腥征战的父亲扼杀了,父亲王虎一心一意希望将他培养成一名叱咤风云的军人,但王源身上流淌的却是他祖父王龙农民的血液,他厌恶打打杀杀,一心一意想成为农民,因而他没有沉沦,既没有屈服于父亲;也没有参加革命的队伍,而是与南方军校的革命者分道扬镳,毅然地逃回了家乡大地的怀抱;又没有像爱兰那样自甘堕落,追求享乐,而是在异国他乡发奋学习有关农业方面的科学知识,追寻完善着那个最初的梦想。回到了国内,即使深负巨债,他也不愿担任享有丰厚俸禄的高级军官,在杀戮喧嚣中开创事业,而是在平和宁静的教育事业中传授知识;在那个动荡黑暗的年代,尽管这种期盼也破灭了,但王源没有自暴自弃,最终在梅琳的肯定中,大地的怀抱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做回了真实的自我,尽管前途渺茫,但他们决定共同去创造那个宁静、散发生命活力的新家园。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对田园理想锲而不舍的追求,正体现着中国人坚忍不拔的精神,而对自然的无限深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崇尚,也正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和谐自然观的体现。这种和谐的自然观实质是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它使得王源的形象充满温暖,具有着宁静祥和的理想色彩。
此外,王源身上也具有着西方文化的精髓。他像梅琳一样崇尚自由,具有反抗意识,而且有着较为突出的理性精神。从他对限制自由、单调乏味的军阀生活的排斥,对自由自在田园生活的向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自由的崇尚,他曾说:“我来这儿,还因为我对宁静的田园生活有一种极大的好感。我父亲想把我培养成军阀,但是我恨流血,恨杀戮,恨枪炮发出的气味,恨军队里的一切喧嚣声。当我还是一个小孩时,有一次同父亲一起来到这所房子前,看见一个妇人领着两个怪模怪样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他们,因此,我在军校和同志们生活在一起时,常常想起这个地方,并盼望有朝一日能上这儿来。同样,我也羡慕你们,羡慕你们的家就安在这个村子里。”对他来说,田园生活是不同于整齐划一、单调乏味、征战杀戮的军队生活的,它是自由自在、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他魂牵梦绕的理想家园。此外,他对自由的崇尚还体现在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上。他的自由思想不同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不想遂父母的心愿在家里娶妻生子,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愿自由地寻找真爱,是“中了新时代的毒,内心充满了他自己也不甚清楚的隐秘而顽固的自由思想”。这种隐秘而顽固的自由思想实际上是他对自由理想爱情的向往。正因为对自由的崇尚,当自由之路受阻时,他逐渐表现出了西方文化所赋予他的抗争意识。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说:“在他的内心深处,常常产生一种对父亲的隐秘的反抗感。”“这种反抗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他现在感知到的他与父亲之间常有的那种暗斗的总爆发,他甚至不明白这种争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他不仅反抗着父亲和南方军校的狂热革命者强加给他的军阀生活,也反抗着父母为他张罗的封建包办婚姻。此外,王源身上还散发着理性的光辉,而这正是崇尚理性精神的西方文化的体现。面对年轻人狂热幼稚的革命方式,王源很冷静,富于理性,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大声疾呼,而是不断提问题:“我们如何来做这件事?……如果我们不上课,只是把时间花在示威游行上,那又如何去拯救我们的国家?”英俊魁梧、好学上进的王源散发着男性的魅力,吸引着众多女性,如爱兰周围的女友,革命女孩,白人玛丽,梅琳等等。但王源对跟女人亲近,对爱有着本能的排斥,这或许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关,自小王虎就禁止王源与女人接触,这使得他不敢也不会跟女性接触,但这份压抑也使得处于青春期的他性欲萌动,而王源却用他的理智战胜了欲望,将对不爱之人的欲望扼杀在摇篮中。例如,他意识到自己不爱那个革命女孩,因而每天去他所热爱的地里劳作,为的是避免自己去回忆曾想触摸她的手这回事;面对白人玛丽狂热的吻,尽管他心底有种吻了又吻的欲望,“但有一种他不可理解的厌恶压倒了这种欲望,它是一个肉体对另一个异族的肉体的厌恶”。只有在对待完美情人梅琳时,他才大胆地追求爱,在乡下的一个宁静的夜晚禁不住诱惑吻了梅琳。
在王源身上,中西两种文化特质也像梅琳一样达到了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地和谐共存。例如,在《分家》中,作者就描写了王源在美国求学期间有一次被化学实验课上的溶液迷住的情景:“他也会被自己制作出来的溶液的色彩迷住,并惊异两种平静、稳定的液体混合在一起,竟会一下子产生那么多泡沫,而且变成了有着新的生命、新的颜色和新的气味的另一种物质。”事实上,通过王源对这一新物质形成过程的痴迷,赛珍珠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是她文化融合的普世理想,中西两种文化都具有稳定的独特魅力,它们在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基础上的完美融合无疑可以创造出一种汲取双方美好特质、取长补短的新的文化。除此之外,小说还描写了王源千里迢迢从国外带回精心培育的良种,并将其撒在中国大地上,这其实也象征了王源中西融合的理想。不仅如此,从王源的一言一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身上同时具备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特质,这两种文化在他身上和谐地交融着,使得他的形象被衬托得更加饱满与可爱。例如,当大太太问他有没有向梅琳表白,“源顷刻之间忘了他的大胆,像个老式的恋爱者一样羞怯地说:‘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开口。’”他倡导自己选妻子却又有点羞怯,选择了请大太太做媒婆的老式方法。此外,赛珍珠在小说中更直言了王源处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境况:“他不知怎的处在中间地带,一个孤寂的地方——就像他处在洋房和土屋之间一样。”“梅琳像他自己一样!她也处在两者之间,既不完全新,也不同于旧。”洋房和新事物都象征着西方文化,而土屋和旧事物则象征着中国文化,后一句对梅琳新旧特质的描述也即是对王源自身蕴含的中西两种文化状况的阐述。王源正是这样一个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具有着两种文化特质的人物形象。他像梅琳一样汲取着中西文化之所长,既避免了西方文化因过度放纵而道德沦丧的一面,又冲破了封建礼教对人的过度束缚。与身为男权社会受害者一方的梅琳不同的是,王源是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作者在小说中淡化了这一形象的男权色彩,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倡导自由、平等、反抗与理性精神同时又兼具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忠厚老实、严肃认真、锲而不舍地追求理想爱情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秀品质的理想男性。如果说梅琳这一形象主要承载着作者对女性出路的思考,那么王源则主要代表着作者对男性以及整个男权社会出路的思考,作者通过他将这一出路指向了宁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在这种有如伊甸园般的田园生活中,人们去掉了虚伪的面具,还原为真实的自我,过着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这正如王源所说的:和梅琳在一起,他也会清静自由、返朴归真。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平生活不仅是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更是整个世界的希望。赛珍珠对王源这一特性的塑造不仅纠正了当时西方文化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弊端,也是对整个世界所寄予的美好希望。因而,王源这一形象无疑具有着普世文化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梅琳还是王源,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中西文化的一些优秀品质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如中国文化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精神与西方标榜的自由反抗精神。当他们的理想遭遇挫折时,中国文化所赋予他们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精神促使他们为着理想执着追求,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对自由的渴望,而且在追求过程中有可能会反抗一些阻碍其理想实现的人或事,这无疑与西方文化所标榜的自由反抗精神相类似。由此实例,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这更促使着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
正如姚君伟在《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中所说:“现在,一般认为,赛珍珠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她所热心从事的社会活动,其终极目标是帮助世人超越文化的、种族的界限,而实现她珍视的‘一个世界’的理想,这一理想也可以象征性地表述为‘一种新的生命、新的颜色和新的气味’。”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中正践行着“一个世界”的理想,努力进行着“他者”形象的普世化尝试,在相关人物的描写中创作出了中西融合的两种形象。
注释:
②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⑤陈敬:《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6页。
⑨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