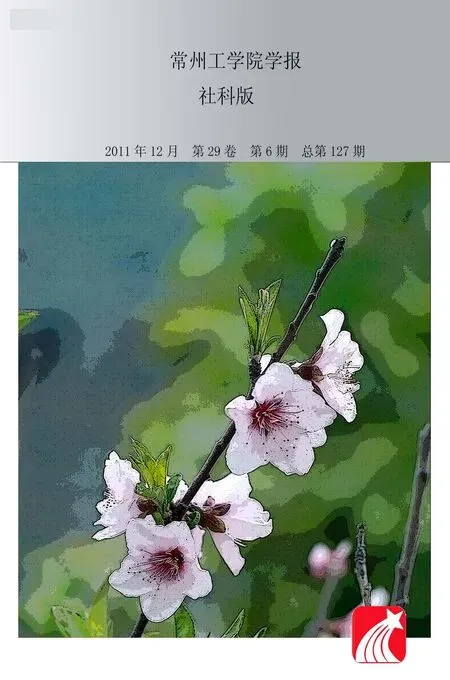论《生死场》艺术之缺憾
房金环
(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1935年12月,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的《生死场》,以容光书局的名义终于问世了。虽然是自费印刷,“非法”出版,但小说却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1]7。小说展示了上海民众知之甚少的东北伪满洲国民众生活场景,再加上鲁迅和胡风两位文学大家的序跋,所以《生死场》一出版,上海文坛就接受了它,作者萧红也因此而一夜成名。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评价,影响至今,已成定论。如今,重读《生死场》,笔者的感受如同王达敏先生论长篇小说《西部车帮》:这是一部让我连连击节称赞又扼腕叹息的小说,一部瑕瑜互见、优庸并存、好差尖锐对立的小说[2]。《生死场》的艺术缺憾,不仅有,而且非常明显。
一、矛盾的“出”“入”
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人间词话》第60则)“能入”,即诗人要深入体验生活,观察人生,对宇宙人生要有真切的体验,能写出真实感受;“能出”,即诗人要把对真实感受的描写提升为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表现。这两方面的结合才可创造“有境界”的诗歌。细读《生死场》,笔者发现《生死场》有“出之太远”和“入之太近”之缺憾。
(一)“出之太远”,激情受挫
萧红曾说,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在《生死场》中,她继承了鲁迅先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写作理念,站在启蒙人道主义立场上,描写了北方地区一群老中国的儿女,他们勤劳而愚昧,苦难而血腥,隐忍而好斗。作者更是从女性视角出发,把女人在男权压制下遭受的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融入了自己不幸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生孩子的痛苦以及被男人侮辱的仇恨,作品也因此而具有真性情,从而达到了“力透纸背”的深度。但只要仔细揣摩,却又发现,为了达到理性的启蒙,作品有些地方竟出现了“图解主题,虚假编造事例”的败笔。
例1:让“鲜花”由荣而枯。
月英是作者为了丰富作品中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硬塞进去的一个鲜花般女子。她既不同于又丑又傻又弱的麻脸婆,又不同于刚烈暴躁“猫头鹰”似的王婆,更不同于纯情幼稚、未婚野合而怀孕的金枝。“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月英美丽大方、柔情稳重,她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化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女人,作者为了谴责男人权威下女人生活的苦难,偏偏让她婚后就瘫了,仅仅一年,她就被丈夫和病魔折磨得“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并且“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在大雪纷飞、寒风呼啸的北中国的十二月份,月英的下身居然还生出了会蠕动的蛆虫!这些描写,既不符合生活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真实,不仅不能激起读者对男权的愤恨和对女性的同情,而且还让人读之恶心。
例2:令“劲草”起死回生。
王婆虽然是像“劲草”一样的人物,但当她得知儿子被迫抢劫而遭枪毙,她还是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而选择了自杀。王婆服毒自杀后,丈夫赵三及周围的村民没有一个想方设法去救人,男人们只是在忙着买棺材,掘墓地,女人们则一边想着自己的不幸一边嚎啕着哭王婆。最后,当人们不再感到伤心、恐惧,心安理得地聚在王婆家喝酒、吃晚饭时,王婆“紫色的脸变成淡紫色”,“忽然从她的嘴角流出一些黑血,并且她的嘴唇有点像是起劲,终于她大吼两声”。这时,丈夫赵三的“大红手贪婪着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地切在王婆腰间,“血从口腔直喷,射了赵三满单衫”。王婆最终是“就算连一点气息也没有了!她被装在等在门口的棺材里”。如果王婆就此死掉,村民的残忍、愚昧、麻木的确令人震惊、痛心。但作者没有这样做,她也许是受鲁迅先生的“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3]文学观影响,作者很欣赏性格倔强、极具有斗争精神的王婆。所以,作者又加上一笔:“将送棺材上坟场!要打棺材钉了!”王婆却轻轻地说“我要喝水!”这里,王婆是活了,但作者的激情却死了,作品控诉男权及封建迷信杀人的震撼力也死了。
文学离不开激情,正像爱伦堡曾指出的:“我认为没有激情,也就没有,而且未曾有过真正的文学。摆脱文字不流畅,结构不严谨以及其他方面的欠缺,比摆脱心灵的冷漠要容易得多。因此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激情,光追求技巧,那他绝不可能获得成功。”[4]在《生死场》中,为了启蒙的需要,作者是做到了“能出”,但她出之太远,“高致”偏高,理性过强,从而导致激情受挫,虚假做作,破坏了作品的真性情。
(二)“入之太近”,浑浊不美
《生死场》不仅“出之太远”,而且也“入之太近”。如果出之太远破坏了作品的真实感受,那么,入之太近却又破坏了作品的审美理想。
在《生死场》里,常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著,血在冒著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著钩子,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把那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
“乱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
“过午二里半的婆子把小孩送到乱坟岗子去!她看到别的几个小孩有的头发蒙住白脸,有的被野狗拖断了四肢,也有几个好好的睡在那里。”
“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
“平儿整夜呕着黄色的水,绿色的水,白眼珠满织着红色的丝纹……”
这些近似于法庭证据似的生活直录,除了让读者触目惊心,难以卒读之外,也让文本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直接录制的录像机。但是,“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5]
因此,艺术既要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艺术是主观的情趣、感觉,而又有些客观的控制和设计在其中,太接近真实,就会压制人们的想象力,人们也就感觉不到艺术美。《生死场》的描写,由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极端接近,逼真书写,进而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感,也因此破坏了作品沉痛的悲壮美。
二、混乱的主题
通读文本,我们发现,全文共98页,作者却用超出三分之二的篇幅,刻画了不同类型女性的悲苦人生。可以说,小说关注的真正主题,应该是在野蛮、粗鲁、愚昧的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奴隶的奴隶”所处的地狱般的生存境遇,以及对这种生存境遇的理性思考。作者站在启蒙者的高度,用同情的笔调,试图从传统男权文化、物质匮乏和女性自身觉醒等方面,来揭示这种生存境遇的悲剧根源。
(一)关注女性悲剧命运
首先,传统男权思想是女性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
静悄悄的林荫道上,成业寂寞的歌声唱开了少女情窦初开的心扉。他远方的口笛仿佛磁铁一般催逼着金枝越陌度阡地奔过去,迷迷荡荡的小河边折倒了长劲草,颤动了花穗。古老偏僻的乡村是最开放也是最保守的地方。闲言碎语向金枝砸来,当金枝确信肚子里有孩子时,“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她患病的样子,“把她变成和纸人似的”。但是成业,他什么都不管,“他丢下鞭子,从围墙宛如飞鸟落过墙头,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的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金枝厮打着说:“不行了!……”成业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结婚后,成业应验了婶婶的预言:“等你娶过来,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
五姑姑的姐姐生孩子难产时,丈夫用烟袋砸,用冷水泼她。而此刻,五姑姑的姐姐“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他的男人”。
寻羊不得反被侮辱的二里半,回到家来,辛苦劳累的爱人麻脸婆让他吃饭时,“他的脸和马脸一样长”,怒骂道:“混蛋,谁吃你的焦饭!”而这时“麻脸婆惊慌着,带着愚蠢的举动,她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
服毒自杀的王婆,当她慢慢地想抬头时,赵三贪婪的大红手抡起大扁担刀一般地死死切在王婆的腰间,导致王婆口吐黑血,最后是连一点气也没有了。
在这个封闭的王国里,传统的男权思想把男人堂而皇之地推到青天上,却把女人踏踏实实地踩进泥土里。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他们评价“出轨”的标准也是“男人扯开她的裤子”,但“没羞的”的却是女人金枝。这里,男权思想这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对准的是《生死场》里的每一个女人。
其次,贫穷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又一个源头。
作品用一个个事实揭示出一个真理:“贫穷是革命与罪孽之母。”[6]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切的感受,多次写道:“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当孩子把爹爹的棉帽偷着戴起跑出去的时候,妈妈追在后面打骂着夺回来。”
《生死场》中,又有哪一场悲剧不是与贫穷联系着呢?王婆儿子被生活所迫,抢劫被毙;金枝丈夫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暴躁烦闷,摔死刚刚满月的小金枝;金枝出走后,为了糊口又被男人侮辱。婆婆毒打小团圆媳妇的理由也是“有娘的,她不敢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小团圆媳妇是不折本的,因为她既禁得住打又不是有钱人家的女儿。甚至民间的忌讳中有这样的说法:“若是女子生在七月十五,这女子就很难出嫁,必须改了生日,欺骗男家。若是男家七月十五的生日,也不大好,不过若是财产丰富的,也就没有多大关系,嫁是可以嫁过去的,虽然就是一个恶鬼,有了钱大概怕也不怎么恶了。……若是有钱的寡妇的独养女,又当别论,……假如说女子就是一个恶鬼的化身,但那也不要紧。”
再次,女性自身的不觉醒是其悲剧的主观因素。
如果男权文化和贫穷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客观因素的话,那么女性自身的麻木就是其悲剧的主观原因。传统的男权思想规定了《生死场》的女人们的人生,而她们也在有意无意地维护着这种传统。麻脸婆对跛脚、窝囊的丈夫,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从没想过要反抗;福发妻子和金枝的爱情都是狂热而纯真的,但男人恰恰利用了她们的纯真与狂热,粗暴地占有了她们的身体。不幸的种子早早萌芽,她们尽管发觉,但没有反抗,而是屈服于她们已经背离的道德规范,用婚姻作为筹码,来遵从传统,掩盖不幸。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与其他的村妇一样了。金枝是不幸的,但金枝周围的一群麻木女人同样是不幸的。金枝沦落街头后,一群处境相同的女人斤斤计较,相互挖苦,甚至争风吃醋。
(二)加进男人抗日主题
《生死场》对男权威力下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探索,用的篇幅长,关注范围广,剖析程度深。如果作者只关注这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将会更深刻,完整。可惜的是,作者也许是受时事影响,也可能是为了追赶时尚,迎合大众的口味,小说偏偏在最后几章里,硬是让抗日分裂了对女性生死存亡的关注。把关注的焦点投射在几个懦弱、粗暴的男人抗日的舞台上。文本结束时,作者让“一点胆量也没有,杀一只羊都不能够”且“对于国亡,他似乎没有什么伤心”的二里半也“快走,跟上前面李青山”抗日去了。这样处理,多多少少都显得不够妥帖。
珀·卢伯克、爱·福斯特、爱·缪尔在其《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中指出:一个主题,单一、完整、不能分解——有了这样的主题作支柱,一部小说才可能开始形成[7]。由于萧红对《生死场》第一个主题有彻骨的体验,才使得其描写展示的人物事件具有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但是,第二个不恰当的主题却分裂了作品主题的完整性,给人混乱、破碎、媚俗的感觉。
三、失当的模仿
艺术上是允许借鉴的,但借鉴与模仿是不同的。借鉴是经过消化吸收内化为自己的艺术个性后,再运用于创作。而模仿就有点像东施效颦,不顾文体风格与主题需要生搬硬套。如果说一部小说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的美感强度和思想深度,而模仿恰恰是破坏小说美感强度和思想深度的一块大顽石。《生死场》的叙述中闪烁着鲁迅的影子。
(一)“画眼睛”的方法
鲁迅先生曾说:“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南腔北调集》)其实,“画眼睛”是比喻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描写人物非得画眼睛不可。它强调的是,要善于细致精确地描绘人物外貌最富特征的部分,而舍弃与表现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无关的其他东西。尽管是比喻的说法,但鲁迅先生仍然是画眼睛的高手,在其小说《祝福》中,他就多次画了祥林嫂的眼睛。例如:祥林嫂新寡,初到鲁镇时,“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再婚家破,再到鲁镇时,“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数年之后,沦落街头时,“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祥林嫂的眼泪“由无泪到有泪,再到无泪”,眼神“由精神到没有先前那样精神,再到只有眼珠间或一轮”,这三幅写意画,活脱脱地画出了祥林嫂在各种势力的折磨下,“由伤心到痛心流涕再到眼泪流尽,由充满希望到悲观失望再到麻木绝望”的心理历程。
在《生死场》中,作者也画了麻脸婆和王婆的眼睛:“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揉擦出脏物可笑的圈子,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1]5“在星光下,她的眼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1]8在文本中,麻脸婆是愚弱卑微的,但这“大得那样可怕”的眼睛,怎么也看不出她的弱势来。给王婆画眼睛时,后半句“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消解了前半句“她的眼纹绿了些,眼睛发青”的神采,实在有画蛇添足之嫌。
总之,乍看起来,麻脸婆和王婆的眼睛都很大,但仔细揣摩,这眼睛虽大却没有神采,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是模糊的。
(二)“雪花”意象
雪花“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它先知、殉道、纯粹、孤傲的象征精神,正是鲁迅先生看重并赞赏的,因此,鲁迅先生的作品时常出现飞舞的雪花。如:《在酒楼上》叙述者辞别吕纬甫走出时的场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在《生死场》里,作者也让雪花在王婆的脚下狂舞起来:“王婆束紧头上的蓝布巾,加快了速度,雪在脚下也相伴而狂速地呼叫。”
《在酒楼上》,当孤傲、敏感的叙述者从沉闷、无聊、压抑的小酒馆走出时,扑在叙述者脸上的寒风和飞雪,正是他在拒绝消沉、确定信念后,从内心感受到的清醒与宁静,是一种心灵的释然,精神的升华。
《生死场》中,王婆目睹了善良美丽的月英在婚后一年内,被丈夫和病魔折磨成了奇丑无比的怪物后,王婆“昏眩了!为着强的光线,为着瘫人的气味,为着生、老、病、死的烦恼,她的思路被一些烦恼的波所遮拦”。王婆是一个对飞雪习以为常,朴实、厚道,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妇。因此,此时的她很难注意到脚下的飞雪。或者可以这样说,即使她注意到了,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雪在脚下也相伴而狂速地呼叫”,这实在是作者没有充分尊重主人公的切身感受,直接跳出来急于替她抒情的结果。
(三)“象征”手法
《狂人日记》中“狂人”妄想:“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生死场·荒山》中有这样的描写:“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
鲁迅先生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他很熟悉象征手法。在《狂人日记》里,他把象征与写实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从而在具体单纯的狂人形象中蕴含了无比丰富的思想意蕴。“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这句话似乎也运用了象征手法,但这个象征手法的运用,却缺少了细节的铺垫,显得不够真实。狂人之所以能看见“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就是因为他是“狂人”。“狂人”看到的当然是“狂像”,而“狂像”也证明着他自然是“狂人”。但是,在《生死场》中,王婆是行动果敢、思维清晰的正常人,因此,读者很难相信她怎么能够看到月英“完全绿的眼珠”和“完全绿的一排前牙齿”。
除了以上这些,文本在人物语言、动作的描写以及题材的选择上,仍有对鲁迅先生模仿的痕迹,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尽管《生死场》在艺术上有诸多的不成熟,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它毕竟让广大读者认识并接受了萧红。在作者后期创作的《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小说中,萧红的艺术技巧日渐圆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2]王达敏.论文学是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31.
[3]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2.
[4](前苏联)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M].孟广均,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1.
[5]朱光潜.谈美·谈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27.
[6]嘉明.30部必读的西学经典[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1.
[7](英)珀·卢伯克,(英)爱·福斯特,(英)爱·缪尔.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