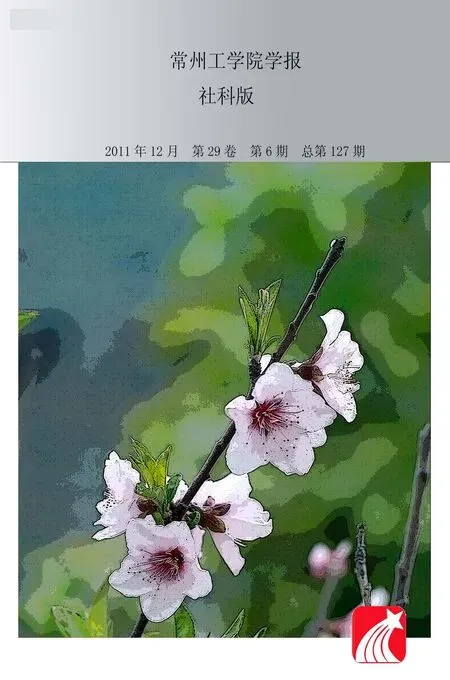论汪曾祺小说“纵”与“收”的艺术
陈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江苏 常州 213002)
梁简文帝萧纲有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放荡,即文章忌拘束,要放恣任性。那文章是不是越放得开就越好呢?也不是。傅庚生先生名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有“纵收与曲折”一章专议及此。他说:“文学创作须富想象力,然一发而难收,失其旨矣。……不纵,则不足以骋骤其情思,不足以渲染其文笔;不收,则或至于荡检失其守,或至于纵辔迷所归。”[1]也就是说为文要如放风筝,既要放得高远,又要能收得住,收放自如。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复出文坛后的作品,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那时有青年作家看了《受戒》睁大了眼睛问:‘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2]而在那些构成汪先生小说独特艺术魅力的诸多要素中,有一点是许多人未及看出或看出来了也学不来的,那就是他“纵”“收”的高超艺术。
一、纵的艺术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3]194这恰是点出了他的小说“纵”的特点和艺术。纵,就是铺得开,“信马由缰”。在其风俗画、生活图、人物志这类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风俗画
《大淖记事》是汪先生的代表作,创作于1981年。小说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和曲折命运。小说共六部分,前面整整三个部分近一半篇幅未曾提到人物,只是写大淖这片水及水边陆地上的风土人情。作者不惜笔墨写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而带点野性的民俗,写了挑夫、银匠、姑娘、媳妇的生活。对于这种写法,一直有人提出质疑,“以为前面(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写得太多,有比例失重之感”。作者巧妙地引用一位青年作家的评价作了回答,那位青年作家说:“题目是写的《大淖记事》,不是《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可以这样写。”[3]235作者对此是深以为然的。汪先生有的篇幅较短的小说,简直就是一幅幅风俗图画,如《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写民国时的一个小学校;《幽冥钟》写一个小县城的寺庙;《茶干》写家乡的一家酱园,茶干就是这家特制的一种豆腐干。三篇小说几乎无故事,人物也无浓墨重彩,主要写风俗人情。这类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悠闲,即使是《大淖记事》这种写生死恋情的作品,也透出一种风俗之美。正如作者所说的:“唯悠闲才能精细。不要着急。”[3]36
(二)生活图
《异秉》是汪先生小说中很有特点的一篇,本是1948年的旧稿,先生于1980年重写。小说中隐藏着极深的对中国旧文化的批判与讽刺,但小说绝大部分篇幅是写生活的,集中笔墨写了摆熏烧摊的王二的“发迹”,写了“一家门面不大的药店”——保全堂。从“管事”、“刀上”写到“同事”、“相公”,写了不同等级人物的生活、情感乃至命运,娓娓道来,极有情趣。作者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3]35《异秉》向我们展示小县城一条街上的小市民的生活图景,作者不吝笔墨,“慢慢地说”,所以“说得有滋有味”。
又如《日规》,写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的生活。化学系主任高崇礼,“是个出名的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人。……可是他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他的花绝不送人,也没有人敢碰他的花。“他的花是要卖钱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是生物系助教,与高教授“朝夕相处,关系很好”。那时的大学生,为了生活到处兼差,“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留校当助教后,蔡很勤奋,每天一大早,“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对于他将来专业上的成就,高教授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出来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就是这么一个青年才俊,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积劳成疾,病了,死了。“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高崇礼与蔡德惠都是对学问、对生活严谨认真的人,虽然差着辈分,但惺惺相惜,是民族危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蔡却英年早逝了。“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小说中,高比蔡更多一点生活的智慧,看来,要成就一个人,缺少生活的智慧也是不行的。小说满含深情地展示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艰难生活图景,人物鲜活,含意深刻。
(三)人物志
小说毕竟是以写人物为主的,汪先生的小说也不例外,更多的是写人物命运。但他写人物不借助于曲折的情节。他的好友、著名作家林斤澜曾说汪曾祺“他反对小说有戏剧性的情节。他认为戏剧性的情节把小说真的也写假了”[4]65。
王四海(《王四海的黄昏》)、鲍崇岳(《鲍团长》),一位是卖艺走江湖的大力士,一位是行伍出身的保卫团长,应该都是有曲折经历的,但作者没有渲染这二位经历的传奇性、性格的江湖气,而是着重写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王四海因为迷上了客栈“五湖居”的女店主貂婵,脱离家族武术班子,留在了这个小县城。小说写了他的风光,他的低谷,写了他从一位明星到黯然收场的过程,铺叙部分用了小说十之九的篇幅。结尾写几年过去了,貂婵给他生的白胖小子满地会跑了,他穿起了长衫,戴了罗宋帽,看起来和一般生意人差不多。他头顶有点秃,而且发胖了——庸常的生活是幸福的,但也消磨英雄气。
《鲍团长》几乎没有写鲍崇岳的军旅生活。他十几岁投军,先是张宗昌部队,后是孙传芳部队,再是国民革命军,升为营长。后到这个小县城当保卫团长,又是十几年。小说没有写他这些经历,反倒是写了这位读过几年私塾,也爱写字的保卫团长温文尔雅的一面,写了他与县城中士绅等的交往。最后,他终于明白,随着世道越乱,他的军旅资格不管用了,那些表面应付他的士绅巨商心底里是看不起他的。最后写了人生的消极与无奈:“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汪先生小说“纵”得有个性。无论是写风情、写生活,还是写人物,都透着独特的韵味。一是散文化,节奏也比较慢,比情节曲折的小说更贴近生活;二是“枝枝蔓蔓”,不够集中,“像一棵树一样”,常有涉笔成趣之妙。
二、收的艺术
有人说,小说是结构的艺术。
而汪先生说:“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3]34他不是说小说不要讲究结构,而是说“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3]33他对小说结构有更独到的感悟、见地。尤其是他小说中“收”的艺术,充满智慧和魅力。
(一)卒章显志又“无迹可求”
卒章显志是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小说常用的点题方法。古代小说结尾甚至常用一首诗来“画龙点睛”。但汪先生追求的是更高明更自然的结尾,即小说家要学会“含藏”,“都说出来了,就没有意思了”[3]44。他说“小说不宜点题”[3]45。
汪先生小说结尾常有一种欧·亨利式的突兀、奇崛,出人意料,又意味深长。
《异秉》写王二的“发迹”和保全堂及市井人物。结尾通过一个叫张汉的人物(此人七十多岁,年轻时在外地做过幕僚,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是个百事通)说“人生有命”,他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禀赋。……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王二在被大家怂恿、敦促之下,只得说出自己的“异秉”:“我呀,有这么一点:大小解分清。”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大家起身送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这里,作者将中国市井社会对宿命的迷信、对成功者的盲从写得含蓄而又入木三分。结构上既戛然而止,又回味悠长。
《鸡毛》写西南联大里一个寡妇文嫂,靠为学生们洗衣服过生活,养几只鸡贴补家用。女儿嫁给一个司机,女婿车翻到山沟里,死了。就是这么一个苦命的人,丢了三只鸡,一直找不到。到学生毕业,她去帮着收拾时,才在经济系学生金昌焕的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而且这金昌焕偷了文嫂的鸡,还是借了文嫂的鼎罐炖的。
小说结尾,作者感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其实小说的主要人物是金昌焕,作者写他生活中种种的怪异:所有东西挂着,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四年级在银行兼职。“毕业以前,他想到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加入国民党,这已经着手办了;一件是追求一个女同学,这可难。”
这么一个功利到极点的人,他会有道德底线么?即使他是一个专业技术不错的人才,他会是一个于国有利、于人有益的人么?小说怎样表现倾向性?汪先生说:“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3]34
(二)轻轻一笔却入木三分
《护秋》是汪先生短篇中的短篇,通篇才不过千余字,写“我”与一个退伍军人朱兴福一起“护秋”(农作物熟了防人来偷,叫护秋)。朱是一个蔫里吧唧的人,不爱说话,动作慢,没精神,总好像没睡醒。他媳妇杨素花和他截然相反,人高马大,长腿,宽肩,浑身充满弹性,像一个打足了气的轮胎内带,紧绷绷的。两个奶子翘得老高,很硬。她在大食堂做活:压莜面饸饹,揉蒸馒头的面,烙高粱面饼子,炒山药疙瘩……她会唱山西梆子,嗓子奇响奇高。她不“待见”她男人,和单位一个会计乱搞。“护秋”时,“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没精神?你要是干净利索些,她就会心疼你一点。”他忽然就显得有了点精神,说他原来挺有精神的。他从部队上下来,有钱——有复员费。穿得也整齐。他上门相亲的那天,穿了一套崭新的蓝涤卡,解放鞋,新理了发。丈人丈母看了,都挺喜欢,说这个女婿“有人才”。结尾是这么写的:他把烟揿灭了,说:“老汪,你看着点,我回去闹渠一槌。”“闹渠一槌”就是操她一回。
他进了家,杨素花不叫他闹,她骂他:“日你妈!日你妈!”“我”在老远就听见了。过了一会,听不到声音了。
“我”在大堤上抽了三根烟,朱兴福背着枪来了。
“闹了?”
“闹了。”
夜很安静。快出伏了,天气很凉快。……
这里没有特别的深意,但人物活了。原来,蔫人也有尊严!为什么生活中许多性格柔弱者往往很愣很倔,也是这种原因吧。
《瑞云》写人物内心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更细腻。
瑞云是杭州名妓,与贺生情投意合,但贺生无力娶她。离鸨母定的“梳拢”期限没几天了,来了一秀才,用手指在瑞云额上按了按,说“可惜,可惜!”瑞云送客回来,发现额上有一黑黑的指印,越洗越真,越来越大。瑞云不能再见客,被贺生赎出来娶了回去,“两口儿日子过得很甜”。
后来,贺生因事到苏州,偶遇秀才。秀才得知瑞云为贺生所娶,遂告:“昔在杭州,也曾一觐芳仪,甚惜其以绝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术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一个有情人。”并随贺生回家,消去了瑞云脸上的黑斑。“晶莹洁白,一如当年”。结尾是这样写的:
这天晚上,瑞云高烧红烛,剔亮银灯。
贺生不象瑞云一样欢喜。明晃晃的灯烛,粉扑扑的嫩脸,他觉得不惯。他若有所失。
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象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
“你怎么了?”
贺生为什么没有瑞云那么高兴,甚至还“若有所失”?是担心自己一介书生守不住这绝世佳人?滋味太复杂,想来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吧!作者在这里“收”得恰是到了妙处:寥寥数语,蕴含的东西实在太多。
(三)平平淡淡写命运曲折
小说最重要的使命是写人物命运。汪先生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所以他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复杂,只追求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但这并没有削弱他的小说对人物命运的深刻把握。
以《徙》为例。不长的篇幅,写了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诗人谈甓渔,虽中举后“累考不进,无意仕途”,但教书有方,“教出来的学生,有不少中了进士,谈先生于是身价百倍,名门大族,争相延致。”谈先生的高足高北溟,十六岁中秀才,第二年停了科举,教书为生。高北溟的女儿高雪,在本县一小教书,心比天高,因抗战爆发,困于小城,郁郁寡欢,抑郁而终。三代人,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德高才厚,心气也高,但都是想“徙”而不能。试问,古来能展其鲲鹏之志“徙于南溟”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人呢?小说以高北溟所教的县立第五小学校歌开头: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很多歌消失了,许多歌的词、曲作者没有人知道。小说的结尾写:五小的学生还在唱: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小说篇幅不长,从从容容写了三代人;结尾意蕴深厚,极富个性和历史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很难表达清楚,只能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汪先生小说“收”的艺术,无论结尾处是落笔在主题,还是人物性格、情感,都能显示其独特韵味。或戛然而止,使人回味,催人猛醒;或出人意料,又让人忍俊不禁。
三、纵收的艺术
汪先生主张小说结构应“随便”,又称自己小说结构的特点是“散”。其实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小说结构艺术。他说:“小说的情节和细节,是要有呼应的。”又说,“埋伏和照映是要惨淡经营的,但也不能过分地刻意求之。埋伏处要轻轻一笔,若不经意。照映处要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要使读者看不出斧凿痕迹,只觉得自自然然,完完整整,如一丛花,如一棵菜。虽由人力,却似天成。”[3]42-43
从这里可看出,汪先生小说结构虽“自自然然”,却是“惨淡经营”的。他“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但以他感觉的敏锐,功力的深厚,达到了他所欣赏的“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3]33的境界。尤其是那些汪先生所擅长的短篇,最能体现他纵与收的高超艺术。汪先生小说中有一些小小说,仅三篇一组的就有《故里杂记》、《故里三陈》、《晚饭花》、《桥边小说三篇》等,其中一些篇幅虽短,却纵得有趣,收得有味,常令人抚掌叫绝。
《故里杂记》中的《李三》,主人公是住在土地祠的庙祝、地保兼更夫李三,作品叙写了他本兼各职的日常事务,娓娓道来,有滋有味。作为地保,既管死人失火,管叫花子,更管缉拿盗贼。小说结尾,偏偏这嗜酒贪小的李三顺手牵羊偷了一根船篙让人当场拿住,罚了二百钱,“老是罚乡下人的钱”的李三“这回被别人罚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晚饭花》中的《珠子灯》,用较多篇幅写当地送灯习俗。才女孙家大小姐嫁给革命党王家二少爷,两口子琴瑟和谐,按当地风俗娘家送了六盏珠子灯。不料二少爷婚后不久就病重而亡,临死对夫人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是说了也无用。……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从此,孙小姐一个人过,后来病了,躺了十年,死了。“她的房门锁了起来。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还有《故里三陈》之《陈小手》、《陈回》、《陈泥鳅》等篇章,在结构上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汪先生小说的特点:铺得开,叙得慢,收得紧而奇。
汪先生小说结构的主张和实践既是他个性、经历、修养等因素所造就,也与他的师承有密切关系。他对乃师沈从文先生小说的结构有深入研究:“他(沈从文先生)常把他的小说改来改去,改的也常常是结构。”“沈先生很注意开头,尤其注意结尾。他的小说的开头是各式各样的。《边城》的开头取了讲故事的方式……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论及戏曲的收尾,说‘尾’有两种,一种是‘度尾’,一种是‘煞尾’。‘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他说得很好。收尾不外这两种。《边城》各章的收尾,两种兼见。”汪先生还饶有趣味地写道:“我有一次在沈先生家谈起他的小说的结尾都很好,他笑眯眯地说:‘我很会结尾。’”[3]94-96
汪先生自己说,除了沈从文,鲁迅、契诃夫等作家曾对他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当然也包括结构。联想到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社戏》,契诃夫的《苦恼》、《瞌睡》、《胖子与瘦子》等小说,我们不能感受到这种影响么?
总之,汪先生小说纵得舒展自如,收得隽永自然,在结构上达到了一种境界:纵收自如。正如他的好友、著名作家林斤澜说:“曾祺不喜欢外在的情节……但他的小说却有一种内在的情节。叫它核也行。”[4]66
[参考文献]
[1]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67.
[2]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文集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2.
[3]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八(其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