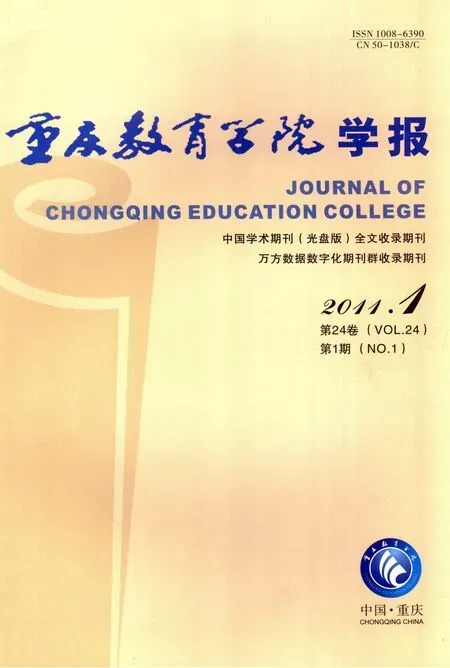断章就理: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的燕卜荪模式
付 骁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断章就理: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的燕卜荪模式
付 骁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燕卜荪模式,是指在文学批评中,以文本中一个字或一两段句子为批评对象,用来证明批评者提出的某一个理论观点的合理性。而中国文艺学研究,在呈现形态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燕卜荪模式”,即断章就理模式。导致其存在的原因深深根植于批评传统、学术机制和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类无法彻底推翻这一模式;但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本质主义”和不实学风的干扰下,断章就理模式就会产生弊端,因此重视论证在行文过程中的价值、摧毁文艺学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重审我国文艺学教材的编写结构则有利于问题的改进。
新批评;中国文艺学;断章就理模式;本质主义;一二三主义
所谓燕卜荪模式,是指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形态:以文本中一个字或一两段句子为批评对象,用来证明批评者提出的某一个理论观点的合理性。
而中国文论传统,特别是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 “文艺学”研究,在呈现形态上,也存在着类似的“燕卜荪模式”,为行文方便,本文命名为:断章就理,即从文本整体中抽出个别词句进行批评,从而得出或证明一个普遍性的学理。
一
“英美新批评”文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英国批评家燕卜荪的著作《复义七型》,是语义学批评的典范,他所谓的“复义”,是指“一个词或语法结构同时有几方面的作用”[1](P3)。循此思路,在批评实践中,燕卜荪忽视了文本的整体性,只是对文本中的个别词句进行分析,下面是他举的例子:
唱诗坛成了废墟,不久前鸟儿欢唱其上。[1](P3)
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第七十三首中的第一节第四行诗句,燕卜荪接着对“唱诗坛”一词引导读者展开联想,说明复义带给诗歌的美感。假定这个词确有复义存在,也必须和上文联系起来理解,因为唱诗坛指的是第三行中的“一簇簇枝梗”,燕卜荪明显将其忽略了;作为一个表意系统,整个文本对唱诗坛的复义是有制约的,燕卜荪也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论述。由此可知,燕卜荪断裂了十四行诗之章,取其一以就他的欲证之理:复义。因此,赵毅衡先生这样评价:“燕卜荪分析的是个别诗行,或小段的诗,很少分析整首诗。这样不可避免地使人怀疑其方法。”[2](P418)《复义七型》里所举的两百多个例子,绝大多数为此模式。方法固然有可疑之处,更可疑的是其结论。同属新批评阵营的美国批评家兰色姆也认为:“如果我们不先读完其他两个隐喻,却在第一个隐喻那里停下来苦思冥想,我们就太愚顽不敏了。”[3](P83)中国文艺学研究中的断章就理模式更为普遍。中国文艺学,从共时的角度,有三个分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从历时的角度,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文艺学教材和专著。例如,宋代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一诗,洪迈这样批评:
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4](P150)
《泊船瓜洲》本有四句,从洪迈开始,千百年来,人们谈及此诗,口不绝于第三句第四字;当人们对这个字心生厌倦后,便开始咀嚼这句的第三字“又”:是“又”好呢,还是“再”好?不可否认,“春风又绿江南岸”确实是名句,但这样批评使人忘却了对文本整体的探索(事实上,“绿”所造之境与诗歌欲达之意义相龃龉),带有病态的文人审美倾向。
在王国维的美学名著《人间词话》里,断章就理模式贯穿了全书,如,他认为文本的理想状态为境界,而境界可以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5](P36)
境界即意境,意境的营造,一般认为必须依靠文本整体。试问,诗词中的一两个精彩的句子,是探索意境的入口,还是意境的本体?更严重的缺陷是,断章就理模式往往轻视论证:朱光潜认为王国维刚好把这两种境界颠倒了,并用“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取而代之[6](P261)。面对这样的批评,如果王国维在世,相信他根本无力还手。王国维关于境界的分类最终被学界认可,然而,他的这种断章就理的行文方法,让他的美学名著美中不足。
广而言之,从朱光潜的《诗论》,到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再到当下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文艺学研究专著,都是这一模式的重复变奏。
二
断章就理模式,类似于陶东风先生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一文中总结的文艺学教材“剪刀+浆糊”的写作方式,然而他仅仅视其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逻辑必然,人为地缩小了追问的时空视域,潜移默化使学界对这一模式带有先验性的偏见与难以扭转的误解,不利于问题的改进。断章就理在特定的条件下的确存在较大的缺陷,但它却广布于中西文论的理论文本之中。归结起来,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批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众多方法之中,就有一种叫 “摘句批评”,“这种批评是通过从一首完整的诗作当中摘出极有限的几个诗句(通常是一联,有时则只有一句)来进行的”,因此“所谓的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摘句批评。”[7](P261)在中国古代文坛,诗文并举,是主导文体形式,所以摘句批评通过历史基因的遗传深深植入后代各体文学批评家的无意识之中。但问题是,摘句批评只是对个别字、词、句、联的个人赏玩,虽然只是孤立的审美对象,本身却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一个欲证之“理”,因此只是局部性的影响。在断章就理的模式中,被有意割裂出来的文本,是“理”的附庸。换言之,此“章”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文本,其欲证之“理”才是主角,不论它是文学的、哲学的、还是政治的理。这一模式的真正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那时,文学还没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是作为一种工具依附于哲学话语、外交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等。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上述话语可以归纳为:用《诗》来达到理。很明显,《诗经》文本只是一个工具性质的功能性环节,因此朱东润先生说“孔子论《诗》,亦主应用,盖春秋之时,朝聘盟会,赋诗言志,《诗》三百五篇,在当时固有其实用之意义”[8](P5)。在《论语·泰伯》篇中,曾子提供了“实践范例”——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乎!小子!”曾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完好保护异常艰难,所以断《诗经·小旻》之篇并引用其中一句向弟子们传达这个道理。西方文学批评亦有“摘句诗评”的现象。兰色姆在《新批评》里论述艾略特时,就称赞他那寻章摘句、旁征博引之精妙。摘句诗评,英文是“touchstone”,意为“试金石”,乃“一种黑色坚硬的石块,用黄金在上面画一条纹,就可以看出黄金的成色”(见百度百科)。阿诺德、艾略特等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用某些著名的、精妙的诗句去和批评对象(也是一些个别的句子)比较,并以此为依据指出它的高下得失和评价它的文学价值。在这里,艾略特以对象文本之外的传统文本为批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意味着批评者脱离了文本。虽然摘句诗评和燕卜荪模式在形式上存在不同,但两者都把文学批评简单等同于对个别诗句的批评,从而产生出简单化的倾向。燕卜荪模式的原初形态在柏拉图那里就成型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指责诗人“说谎”,因为他们“把神和英雄的性格描写得不正确”,随后从荷马、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抽出一些诗句作为例证,说明为何要“审查做故事的人们”,进而提出统治者要制出诗人必须遵守的条条法律[9](P22-25)。柏拉图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后来的人当然不能期望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他把文学文本放在政治视域之下,断其章取其句来为他的政治见解做反面例证,这和他歧视诗人轻蔑文学的文艺观是紧密相关的。
其二,学术机制。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的诞生,决不是纯粹的学术界内部学科资源整合的结果,它和新中国教育权力话语的建构密不可分。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知识的传播主要以高校“文学概论”课堂为平台,以文艺学教材为载体。即便在今日,学生在学习文艺学时也以阅读教材为主,只有文艺学研究生在进行个人的专题研究时才会系统地阅读相应的理论原著。简言之,新中国成立后,它从苏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身份就是“大学的”文艺学,而不仅是“学术的”文艺学。因此,苏联文艺学学科的基本体貌,以及在当代相对自由的学术机制内的嬗变,对断章就理模式的现代定型起了直接的影响。文艺学的性质是什么?长期在苏联的大学文学系作为教材使用的由波斯彼洛夫主编的《文艺学引论》开宗明义:“文艺学是一门科学”[10](P1)!作为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现代中国人 (不管他是学文科还是理科)都明白,科学工作,就是面对研究对象的本身,概括出抽象的理论范畴,并研究它们相互间的作用及其规律;编者还认为,“不运用大量的关于文学作品的某些性质和特点的一般概念,不运用文学发展过程的某些方面的一般概念,就不可能历史地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10](P25)也就是说,文艺学的理论框架,由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抽取出的“一般概念”搭建而成,它不是概览性和情感性的,鲜活的文学作品被硬梆梆的理论概念人为分割开来。从这里开始,文学被纳入科学研究的机械场域中,文学文本和文艺学文本相互摩擦着,产生出强烈的异质性,诚如伊格尔顿之论文学研究 “读者或批评家的角色由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11](P119)传统的那种直觉的、感悟的、整体的、聊天式的文学研究已经失去了话语权。因此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说,文艺学研究,不是在批评文本,而是在生产话语。生产什么话语呢?对中国文艺学研究以及“文学概论”教材编撰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一书开篇就明确指出:“研究文学和语言的专家……其首要任务是如何运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12](P3),即生产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这便应对了伊格尔顿的观点:“所有理论和知识,……都是有私心的”[11](P180)。在西方,理论也呈现出了建构状态。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极端认为:“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3](P3)。中国文艺学基本照搬苏联模式,再加上国内彼时处于教材的饥荒期(许多大学教师自编讲义油印发给学生),教师在编写文艺学教材时,为了尽快提出论点以应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学之急,难免用“跨时空拼凑”(陶东风语,即“剪刀+浆糊”的写作方法)的办法来完成政治意涵明确的任务,这就导致了在文艺学知识生产中断章就理模式的普遍运行。新时期,高校文艺学教师有两个任务(有时成为包袱):教学和科研。教学上,对教师授课效果的评价,通常有“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等硬性标准,因此教师无法避免“概念先行”的尴尬,满堂一点二点三点,各点均用只言片语的诗文去充填,枯燥乏味,讲台下睡倒一片;科研上,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般在一万字以内,要尽快得出结论,中国找一句,外国摘一段,为了把材料系统化,中规中矩地奉行一二三主义。试问,如果其作者不是著名教授,整篇没有例子、没有一二三、只谈论感想的文章,有哪个编辑愿发?断章就理之所以存在,从学术机制看,归根结蒂是因为在科学机械场域和教育功利场域里,文艺学文本被人为地建构成一个独立的话语系统,而本应是研究对象的文学文本反倒在建构活动中转变为功能性的角色。
其三,人类的思维方式。燕卜荪本人数学专业出身,有人认为他用研究数学的方法对待文学,写出了《复义七型》这样的名著,一语中的。他本人并不一定意识到这点,但在书中曾附带地提到人类在进行研究时所共有的思维方式:“在理解有普遍意义的事物时,人们常常会想到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来印证;人们在对生活、科学、数学定理进行思考时,都是如此。”[1](P191)无论是批评传统,还是学术机制,无一不是依据思维方式得以成型。燕卜荪的这段话,印证了逻辑学上基本的逻辑方法,也就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归纳和演绎。归纳,是从一般事物中概括出普遍原理,得出概念,并用概念把研究对象系统化,以便后人的学习,也使整个研究成果成为一个严谨的逻辑系统。演绎,是用一般原理去考察特殊对象。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一书,用的就是归纳法来研究文学作品。弗莱认为,归纳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归纳法已经在自然科学研究内广泛使用,而“文学批评现在也正处于这样一种我们所发现的基本科学的朴素归纳状态。”[14](P20)然后他把文学作品看做类似自然科学里的资料,分门别类放到不同的概念之下,使研究具有系统性。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人类首先占有大量的原始材料,然后得出一个“观点”;当印证这个观点时,只会拿出小部分材料。例如,甲赞美乙“待人真诚、工作负责”,很有可能甲和乙相识已经超过十年,让甲得出这一结论的例子点点滴滴不胜枚举,当丙问甲为什么时,甲只能举一两件关于乙的小事,或是一件大事中关于乙的小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燕卜荪模式”和“断章就理”都与人类思维方式相契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
问题是,既然最终可以归结到归纳和演绎这对人类的正常的思维方式,那么为何“燕卜荪模式”和“断章就理”仍然漏洞百出、问题多多?指出了问题的来由,就可以提出改进的方法。为什么是“改进”而不是“解决”呢?因为这种模式有其合理的一面,要建构一种新的模式形态在操作上存在难题。其实就是“本质主义”和不实学风在捣鬼。“本质主义”先验地把一个论点或结论嵌入研究对象,反过来再用其一隅去证明论点或结论的真理性,加上有当下不实学风摇旗呐喊,归纳并未做实,因为这一步必须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相互比对、仔细论证,才能进入演绎阶段。而事实上,断章就理模式很多时候是马虎地归纳后直接把演绎作为研究起点。例如,一本文学史教材讲到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时,论点是“(引者按:李清照)善于将语言变化与声情、词情相结合”,论据是“寻寻(平声)觅觅(入声),惨惨(平声)戚戚(入声)、点点(上声)滴滴(入声),平声、上声与入声交互运用,形成抑扬有致顿挫有节的声调,读之有长吁短叹之感。”[15](P267)且不说论据和论点之间内在逻辑性存在与否,仅用一首词中的一个名句作为例子,其论点当然值得怀疑;如果学生在脑海中牢牢记住了此原理,再去读李词其他文本时依此演绎,便会发现他例并非均如此。该例是断章就理模式的极端个案,归纳和演绎界限不清,论据和论点陷入相互阐释的怪圈。据此,提出改进的方法:
首先,重视论证在行文过程中的价值。具体地讲,就是要反思学界长期奉行的“一二三主义”。一篇学术文章,新颖的观点固然是文章的亮点,而且是其学术价值的根本体现,但观点是否具有科学性必须由材料支撑,所以中间这论证一环在实践操作中就显得特别重要。断章就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弊端是作者先把文章分为一二三点,然后逐点削足适履、堆砌材料,再简单评述一下材料就算完成文章,忽视论证以致整个过程中找不到观点与材料的逻辑性。“一二三主义”的本意在于使文章具有层次性和可读性,但在现代的学术规范下,文章前面的“内容摘要”已经承担了这一职责;有时作者可以按照文章的内在逻辑连续行文,不必苦心焦思硬要分为“一二三”,如果文章真的有创意且论证严谨,读者依然会在通读文章之后轻松地归纳出论点。当然,只要论证这一环没有省略,严谨可靠,使论点和论据紧密结合,大可让“一二三主义”存在下去。因此,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一二三主义”,不妨这样认为:只要论证严谨,找不出漏洞,在行文的过程中可以“一二三”,也可以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如此,断章就理模式的片面性得到很好的抑制,也就不必重新建构另一种中国文艺学的话语模式了。
其次,摧毁文艺学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断章就理模式深深根植于批评传统、学术机制和人类的思维方式之中,有其存在的合理一面,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论必然,但本质主义却可以给其提供走向片面化和荒谬性的温床。陶东风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典型的写作方式是先想出一个所谓 ‘理论’问题,然后到各种工具书中去找各种各样的‘证据’。貌似学贯中西,雄辩滔滔,实则一知半解,满脑子名人名言。”[16]依这种思路写作,难免断章就理。在这里,不仅涉及到本质主义的问题,还涉及论文的写作态度、结论可不可靠的问题。王力先生早就对此早就说过:“如果没有归纳就作分析,那么结论常常是错误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17](P5)李泽厚也曾谈过学术论文写作的问题:“写论文最好不是先定题目,然后找材料去想去写,这样往往为了写而去凑。应该是通过自己多年的学习阅读,有了某些自己的看法和材料,再去确定题目。”[18](P15)在实践操作上,即使研究者进行了踏实的归纳,最后文本呈现如果仍然是断章就理模式,在读者看来同样有拼凑之嫌,所以摘句+统计——不失为一个突破瓶颈的好方法。
再者,重新审视我国文艺学教材的编写结构。诚如上文所述,教育权力主导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改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回到大学课堂,以学生为主体进行课程改革。“文学概论”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而如今,我们应该思考一个看似有些幼稚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跨时空跨文明的意识形态,假使我们有权去抽取它的“基本规律”并用概论的形式让学生掌握这些知识,但是反过来,这些在教材里被加大的黑体字面对一篇篇具体的、形态殊异的文本时,能不能指导读者阅读?对此,钱锺书认为:“具有文学良心的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Blake)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To generalize is to be an idiot)。”[19](P532)谈艺言概,在中国古已有之,晚清刘熙载著有《艺概》,他的方法是面对异常繁杂的文艺作品“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又认为“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20](P1),由此观之这又是一个“差不多先生”!文学本身丰富多姿且具有反概括性,但在实践中决不是不能概括。“文学概论”课程能帮助初学者对文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我们必须先前就要告诉他们:这些“原理”和“规律”,在整个文学谱系中呈散点分布状,它不能代替“读者的单独体验”。读者的单独体验,是韦勒克使用的概念,他认为从诗学的角度讲,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中,“语言”是诗本身,而“言语”则是读者的单独体验[21](P160)。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学教材研究的是诗本身,与它具有同等价值的就是文学学生在课后对自己感兴趣的文本进行的单独体验,两者并行不悖,彼此照应。放眼西方大学,除了苏联及其追随者,各国均没有文艺理论教研室,德国学者成立“文学科学”的努力也不果而终,既是这样,他们是如何学习文学的基础知识的呢?在这里,美国新批评家布鲁克斯、沃伦、退特等人的努力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为大学英语系的新生们撰写了许多供课堂教学使用的细读文,其方法是:依文体分类,每类选取经典文本,同时也照顾现代作品,把文本完整地抄录于前,后面再写细读文,这样就避开了断章就理模式,有利于学生历史地具体地阅读和思考文学,有利于学生单独体验文本;代表作有:布鲁克斯、沃伦《文学入门》、《理解小说》、《理解诗歌》;布鲁克斯、海尔默《理解戏剧》;卡罗琳、退特《小说之屋》;布鲁克斯本人的学术代表作《精致的瓮》也属于断章就理模式,但他在书后附录了涉及诗歌的全文,这样读者更能全面地评价“悖论”、“反讽”、“隐喻”、“意象”等论点。因此,编写我国文艺学教材的时候,能否考虑打破“文学概论”一体独尊的地位,和各类文学的导读或“文学鉴赏”等共享江山?武汉大学中文系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编写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10种。在“总序”里,主编认为“过去全国高校中文专业教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一些共性问题:从课程构成看,通论性、概述性、通史性课程多,原典性课程少”[22](P1)。有多少中文系系主任认为这确是一个问题,并使用这套丛书、开设相应课程?这些由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研室的教师撰写的偏向感性的导读文章,能否被惯于理论思辨的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接受?笔者就不知道了。
[1] (英)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M].周邦宪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
[2]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 (美)约翰·克娄·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张哲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洪迈.容斋随笔.转引自: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M].滕咸惠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6.
[6]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7] 曹文彪.论诗歌摘句批评[J].文学评论,1998,(1).
[8]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 (苏)波斯彼洛夫.文艺学引论[M].邱榆若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11] 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12] (苏)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M].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
[13]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4] (美)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5] 赵义山、李修生.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J].文学评论,2001,(5).
[17]王力、朱光潜等.怎样写学术论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8]文艺美学丛书编委会.美学向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9] 钱钟书.钱钟书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0] 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2]龙泉明.中国新诗名作导读[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于 湘]
Duanzhangjiuli:the mode of Empson in the Chines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ry
FU Xiao
(College of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400715, Chongqing, China)
The mode of Empson 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refers to the mode of choosing one word or sentence as the critical object to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a certain theoretic idea put forward by a critic.In the Chines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 however,there is also a mode----the mode of duanzhangjiuli, similar to the mode of “Empson”.The cause of its existenc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ritical tradition, academic mechanism and human thinking mode.With certain rationality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got rid of.But interfered by the “essentialism”and the phony style of study,this mode is likely to produce some abuses.Therefore,it is favorable to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proving,destroy the thinking mode of “essentialism”in th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 and reexamine the writing structure of textbooks of the Chines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
new criticism;Chinese study of art and literature;duanzhangjiuli mode;essentialism;one-two-three ism
I06
A
1008-6390(2011)01-0104-04
2010-10-15
付骁(1986-),男,重庆万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