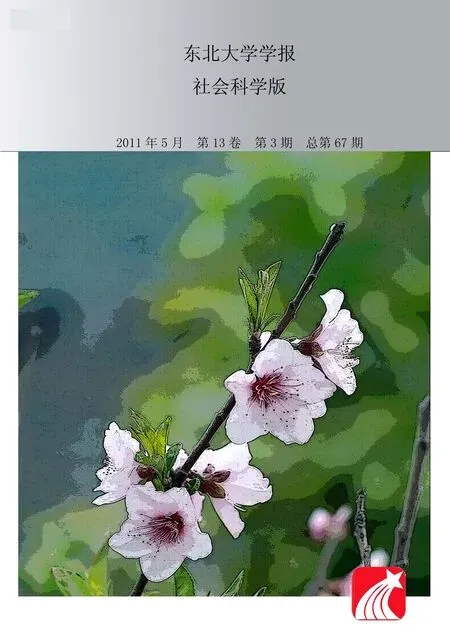技术哲学视野下的苏联工业化问题研究
万长松,张 引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 066004)
对技术本性(природа)和本质(сущность)始终如一的关注使苏联技术哲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即使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技术哲学研究也未因意识形态上的高压而停止,而是以各种相关的形式(特别是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基础)继续发展着。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技术哲学游离于社会实践,相反,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苏联的工业化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工程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苏联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苏联的工业化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技术手段论”、“科学技术革命论”等一直作为苏联技术哲学的核心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苏联工业化政策制定和工业化道路选择。
一、工业化的准备阶段与苏联技术哲学的萌芽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生存环境。国内的主要困难就是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工厂停产、铁路停运、粮食奇缺,失业和饥荒笼罩着苏俄大地;国际上,来自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分子相勾结,使本已不堪重负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濒于崩溃。为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不被扼杀在摇篮里,“在恢复大工业方面必须尽速取得尽可能扎实的成绩”,否则,“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1]。
直到20世纪初,俄国还是一个废除“农奴制”不久的落后的农业国。内战结束以后,恢复国民经济也是从农业开始的。但是,“最先进的工业形式和半中世纪的农业形式同时存在,无疑是一种矛盾”[2]。因此,“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3]。按照列宁重工业是独立国家物质基础的思想,苏俄重工业的发展显然是不适应要求的。十月革命前俄国装备的现代化生产工具仅为美国的1/10,德国的1/5,英国的1/4,“说到铁——现代工业的主要产品之一,也可以说是文明的基础之一,俄国是特别落后和不开化的”[4]。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不仅是恢复重工业、发展轻工业、改造农业和手工业,而且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列宁曾经把实现工业化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贫苦的马上,跨到大机器的、大工业的、电气化的马上。而重工业,就是这个基础的实质。他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5]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既需要物质基础,也需要人才和思想基础。“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6]482十月革命特别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国家需要大量的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布尔什维克进行经济建设。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民间自发开展了一场“专家治国”运动,其宗旨是依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企业和社会。最早倡导“专家治国论”的两位学者是П.恩格迈尔和П.帕尔钦斯基。专家治国论(Технократия)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表示建立技术专家的政治,其特点是不把某一阶级的“私利”,而是把技术专家集团为全社会利益而利用的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管理社会。作为管理社会的一种模式,专家治国论有它的合理之处,它为提高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为苏联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高潮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但随着政府对工业化的强力干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酷斗争,专家治国论遭到了激烈的批判。1929年,帕尔钦斯基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苏联政府的“工业党”的领导人而被秘密处决。在接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中,有几千名工程师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到关押和流放[注]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详细地描述了这一事件。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名噪一时的“专家治国”运动就这样夭折了。
今天看来,尽管这场短暂的“专家治国”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这场运动却促使一批职业工程师开始反思技术本身以及工程师的社会地位问题,产生了苏联技术哲学研究的最初萌芽[7]。之后,由于一批“红色工程师”(比如卡普斯京、安德尔曼、斯特列尔科夫等)对专家治国论的批判,特别是官方的重视和介入,以恩格迈尔、帕尔钦斯基等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技术哲学”日渐式微,而以布哈林、库津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技术哲学”开始兴起。可见,没有苏联工业化实践的迫切要求和国家对工业化的强力干预,就不会有工程技术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不断攀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建基于新世界观和历史观之上的哲学思考。
二、工业化的实施阶段与苏联技术哲学的产生
沙皇俄国没有能在封建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工业国,然而这一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却最接近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俄国也只有完成这一革命才能摆脱落后于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局面。列宁指出,机器大工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源泉和基础”,而且“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6]500。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口号,并且强调“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8]。列宁关于电气化和工业化的论述,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经过五年的经济恢复工作,1925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宣布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他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9]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核心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即优先发展煤炭、石油、冶金和机器制造业。与以轻工业为起点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0]。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针是从当时苏联的国情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出发的;但从深层次上看,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和当时主要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布哈林等)对于技术的本质和机器大工业的意义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充分把握住这一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工业化”这个概念(当时称之为工业革命或大工业的发展)。列宁创造性地研究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系统理论。他用有关大工业发展所引起的技术进步的资料,深刻揭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较之消费资料的生产有较快增长的规律的实质。这一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说来,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11]。在多方面研究了俄国近代工业化历史的基础上,列宁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12]。表面上,这是一个经济学的结论,但实质上,列宁已经把技术(生产资料)作为工业时代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是第一个把技术进步(机器劳动)与工业化(电气化)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权基础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苏联技术哲学的奠基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正在部署和实施工业化的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年),在苏联也产生了第一批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阐述技术观的哲学家,他们的杰出代表就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集中阐述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布哈林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认为生产力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标志,并且指出:“社会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精确的物质标志,是该社会的社会劳动工具的体系,即技术装备。在这种技术装备中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13]。和布哈林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米龙诺夫、谢姆科夫斯基等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同时也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批评,认为忽视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并将生产力的内容归结为技术,是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斯大林的哲学老师斯滕针对把生产力和劳动工具、技术等同的观点批评道:“劳动工具以及广义的生产资料只有在和劳动力辩证统一之中才能成为生产力。”[14]这场哲学辩论深化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为苏联技术哲学打下了最初的桩基。
这一时期是苏联技术哲学产生的最初阶段,其理论成果对于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学术争鸣变成了政治斗争,很多人遭到迫害,其中就包括苏联工业发展的规划者——布哈林。须要指出的是,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在苏联实现工业化,而是怎样实现工业化。布哈林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15]。斯大林还是不顾反对而竭力追求高速度;布哈林等人也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决定性意义,但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主张经济保持平衡发展。斯大林却指责布哈林等“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1929年11月,布哈林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斯大林以“反右倾”的名义用政治手段结束了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辩论,也结束了苏联技术哲学学术观点自由争鸣的时代。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在实行过程中是存在严重错误和缺陷的,但是,不能因为有了这些错误和缺陷就全面否定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方针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作用。至于全盘否定列宁经过大量调查和严肃思考后得出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等理论,那就更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逻辑推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诞生的,因此,理论上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就不存在工业化问题了。所以,如何结合各国具体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研究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三、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与苏联技术哲学的成熟
截止到1940年,苏联工业和农业产值的比例达到85.7∶14.3,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达到61.2∶38.8。在30年代末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强国,工业化成绩斐然。但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关系不协调,生产方式粗放,经济效益较差,国家财政负担过重,人民生活水平不高,市场供应紧张,经济体制僵化。如果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畸形发展的结果,在“二战”前还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战后长时期内没有扭转这种重重、轻农、轻轻的局面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能源危机,苏联曾从出口燃料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仍然把大量资本投向重工业、军事工业,形成了苏联军事工业和与之有关的重工业的产值几乎占了工业总产值的2/3。相反,人民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实惠,信息产业和与之有关的高新技术长期被忽视,没有抓住西方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实现信息化。由此可见,在苏联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有两个显著的问题:一是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没有使轻工业和农业与之协调发展。二是在先进科技的运用上明显落后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任务之后仍然长期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这固然与苏联领导人急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望和“冷战”思维有关,但是,植根于苏联工业化理论深处的“技术手段论”是不能忽略的思想根源。在苏联技术哲学中,技术(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一条从马克思、列宁到布哈林、库津等苏联技术哲学家始终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技术手段论”的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马克思也提到了技术的理性因素,但这一点经常被忽视。因此,苏联的技术本体论往往就等同于“技术手段论”。比如,苏赫尔金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技术”条目指出:“技术就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为社会的非生产需要服务而创造的人类活动手段的总和”,“生产技术是技术手段的主要部分”,而“生产技术中的最积极部分是机器”[14]。简单地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技术,进而等同于机器,只强调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自然属性,忽视技术的认识论价值和社会属性,在实践上势必就要采取重重、轻农、轻轻等一系列非平衡发展战略。
尽管在能源、化工和航天、航空等工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至今仍使俄罗斯人引以自豪),但总的说来,苏联并未抓住20世纪下半叶以来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错过了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时机,没有及时实现重化工业向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没有实现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以及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之间的平衡发展,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企业生产效益的提高,更没有主动完成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在“二战”后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却走向了“停滞”和“僵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并不意味着苏联工业化的失败,更不意味着苏联技术哲学一无是处。相反,与苏联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反应迟钝”相比,苏联技术哲学界对新技术革命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在苏联技术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莫过于“科学技术革命”(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认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技术哲学的中心概念。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学者加强了沟通与联系,几年后,苏联科学院和捷克科学院合作出版了《人·科学·技术:关于科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73年)一书,这是苏东学者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理论的经典著作。该书作者认为,技术对科学来说是一种新的认知方法,科学则为技术提供新的技术手段,“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性变革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过程,科学成为技术和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为其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科技革命就是当前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统一,它“在人与自然之间放置的不是工具或机器,而是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生产过程”[16]。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在科学和技术中心及相应地在生产中出现的综合过程,这些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显著发展。为了理解科学技术革命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苏联技术哲学家C.海因曼博士认为,必须研究大机器生产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逻辑。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相比,苏联大机器生产在五六十年代发生了以下重大变化:一是“不断提高主要类型的动力和工艺设备的单位功率和生产率”,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积聚的发展;二是“同自动化机器的建立和推广相联系”,自动化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最主要的环节之一;三是无论是在企业水平上还是在部门水平上的“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物质因素和人的因素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结合空前复杂化;四是“劳动产品的积极作用及其对生产本身的影响”,即这些产品在满足已经产生的需求的同时,又引起了新的需求。发生上述变化的原因在于:“科学以知识的形式表现为精神(思想)生产力,但同时物化在生产的物质因素中,物化在生产工艺和生产组织中,从而成为直接生产力而起作用。”[17]今天看来,上述对科学技术革命及其作用的概括依然是正确的,这些哲学思考超出了当时苏联工业发展的历史局限,对科学—技术—生产—社会—人之间的关系有很精辟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STS理论的最初探索。与“技术手段论”在技术本体论研究上的落后相比,“科技革命论”在技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与西方是同步和趋同的,表现出苏联技术哲学对其工业化道路的相对独立性与超越性。
苏联工业化是苏联历史问题中一个争论不休、常谈常新的问题。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是因为这种争论不是从一个热点上和一个角度上迸发出来的。对苏联工业化持肯定态度的人所论述的大多是苏联的工业化本身,即那种持续了十多年甚至延长到“二战”后的工业的迅猛发展及其毋庸置疑的成就。而对苏联工业化持否定态度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快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经济计划化和肃反扩大化等带来的副作用,是工业化与苏联社会发展的负面关系,是其对苏联文化、思想、哲学等上层建筑的消极影响。从后一种情况来看,苏联工业化确实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
第一,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又好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是苏联在当时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对于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包括中国)而言,在工业化初期往往也很难避免。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为了实现工业化而脱离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增长,不惜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那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第二,如何实现速度与效益、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了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党和政府不断追求建设的高速度,但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高速度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许多高指标不仅无法完成,而且助长了浮夸、冒进和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长期忽视人民利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所谓高指标,影响和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最终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苏联工业化的惨痛教训一再警示我们要坚持走一条可持续的、平衡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如何处理好政治路线斗争与学术观点争鸣的关系,如何使技术哲学更好地“为国服务”[18]。怎样处理好政治与学术、领导人与哲学家的关系是苏联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由于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最终胜利,使苏联技术哲学从诞生伊始就被打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表现在苏联技术哲学著作中,就是到处充斥着历次党代会文件的官话套话,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柯西金等人的阿谀奉承,偶见西方技术哲学也是作为批判对象而提及的,鲜有创新。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把苏联技术哲学作为其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其次,二者存在着间接的、内在的联系,认为苏联工业化道路与其技术哲学思想没有任何关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最后,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一损俱损、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
历史上,在处理经济、政治与文化、学术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和苏联一样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投入到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去,埋头于书斋做“纯粹”学问的态度当然不足取,但过度跟风和逢迎的做法更具危害性。被阉割了批判功能的哲学不仅失去了现实性,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替某些错误的政策、实践、理论作辩护的帮凶。正确认识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之间的关系,为中国技术哲学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1] 列宁.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M]∥列宁选集:第4卷.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23.
[2]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M]∥列宁选集:第1卷.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33.
[3] 列宁.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M]∥列宁选集:第4卷.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24.
[4] 列宁. 农民经济中的铁[M]∥列宁全集:第2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397.
[5] 列宁.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M]∥列宁选集:第4卷.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97.
[6]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M]∥列宁选集:第3卷.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7] 万长松. 苏俄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J]. 哲学动态, 2002(11):42.
[8] 列宁.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M]∥列宁选集:第4卷.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64.
[9] 斯大林.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M]∥斯大林全集:第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294.
[10] 斯大林. 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M]∥斯大林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62.
[11] 列宁. 论所谓市场问题[M]∥列宁全集:第1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83.
[12] 列宁.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M]∥列宁全集:第3卷.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466.
[13] 布哈林.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127.
[14] 万长松. 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述评[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4):3.
[15] 布哈林. 目前形势和我们报刊的任务[M]∥布哈林文选:中册.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309.
[16] 米切姆. 技术哲学[M]∥吴国盛. 技术哲学经典读本.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20.
[17] Хайинман С 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егодня и завтра [M]. Москва: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77:136.
[18] 朱训. 在为国服务中发展自然辩证法[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