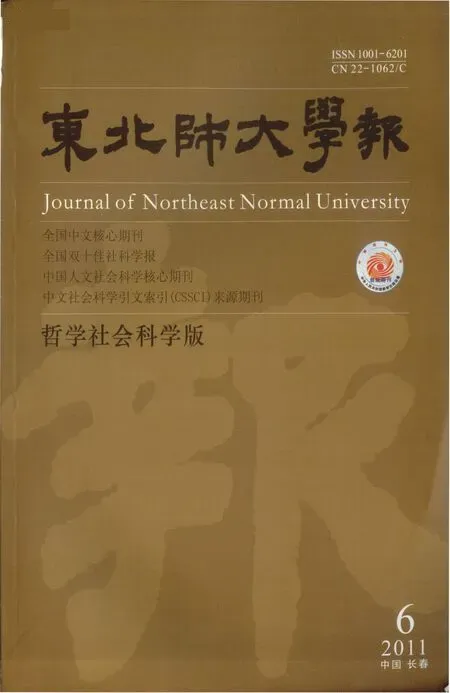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自我意识
邢 蓉
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自我意识
邢 蓉
在女性探索人的自由本质的过程中,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和特殊的存在位置,使女性产生了特殊的自我意识,而缺失意识、恐惧意识、关怀意识和对生命的敬畏意识等四种意识流溢于西方女性的文学创作中,形成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价值的阐释。
缺失意识;恐惧意识;关怀意识;对生命的敬畏意识;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从自身的感受体验出发,对自己的存在、本质进行思考后,所形成的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一系列认识。尽管每一个女性个体由于生活经历、思考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女性自我意识,但这一意识是在女性探索人的自由本质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和特殊的存在位置,她的自我意识是有别于男性的,她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重生理感受、重情感性、具有坚韧性等独特的方式。而这些意识的发展历程通过女性文学作品这个载体,而被呈现在我们面前。女性文本的创造者是女性,体现的是女性的意识,探求的是女性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道路。其核心就是,女作家站在“我就是女人”的立场上,以女性的眼光审视现实,同样,女性读者也是要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进行阅读和接受。由女性作者和女性读者共同创造的女性文学作品承载着女性对其存在和本质的思考和省察。
一、缺失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女性意识是以阳物缺失的确认为特征的。女性的心理结构,在于对自己性别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的心理结构。弗洛伊德在《妇女心理学中》说过:“我们研究女人的性的发展,系由两个已有的概念出发的。第一、和男人相同,她的体格如果不经过一番奋斗,就不能适应它的机能;第二、决定性的变化在青春期之前就开始发动和完成了。”[1]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界定,其核心在女权主义批评看来,在于一种“阳物妒羡”,这种对女性的分析是以男性的生物学特征为基础的,但他并没有抛弃社会性因素对女性人格形成的影响。弗氏在讨论完女性性别认同的任务之后,试图要进一步回答如何使某种特定的标准价值内在化的问题。特里·依格尔顿指出:“弗洛伊德著作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帮助我们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个人的成长。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确实是一个关于个人这个主体如何形成的唯物主义理论。”[2]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父母的作用,抚育儿童的习惯方式,与此相联系的一切意象和信仰,都是文化问题,而在这个社会或这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社会或另一历史阶段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别……在这些制度中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信念是,女孩和妇女不如男孩和男子,这个偏见似乎把所有已知社会连成了一体。所以说,弗洛伊德对女性性别的分析,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决定论。
弗洛伊德通过对男女的性别分析得出结论,女性为缺失和不完整的存在,并认为这一特征在女性的心理发展和人格结构及身份的获得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女性因为“阳物”的缺失(生理上),而导致主体性(人格)的不完整,这种思想不断积淀在人类的思想中,从而内化为一种思维定式,进而使男女两性用不同的标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因而成为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女性缺失的是什么呢?缺失意识使女性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被动心理、依赖心理、客体心理,这种心理又使女性产生了强烈的被保护感和依赖感,渴望成为家中的天使。男性的价值规范成为一种衡量时,女性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将其应用于自身,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有系统的自我贬值。弗洛伊德的理论经常被批评为用男性中心论来定义女性,而忽视了女性的真实存在。其实,这种忽视并不能否认女性的存在,只是女性以一种被忽视的方式存在。
二、恐惧意识
无论男女都有对自己无法掌握的事物的恐惧感。然而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还存在着不平等的控制。通常所说的男人“占有了她”,这种占有已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是进一步的精神上的控制。正是通过这种控制,男人的特权地位——来自他生物学的进攻角色与他作为领导者或主人的社会职能才统一起来。而女性却由于被征服,只能表现出被动的特征。所以说,女性恐惧意识一方面表现为对社会道德所规范的女性贞洁的丧失而导致的道德谴责而恐惧不安;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则表现为觉醒的女性对自我的丧失而感到的恐惧。这里的自我的丧失不单单只是某些权利(如选举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等)的被剥夺,而是把自己放在主体的人的位置上去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思考的思辨力被扼杀了,女性害怕“我”被戕害、被消灭。此时的女性恐惧意识已是建立在女性人的觉醒的基础上的了。
小说《简·爱》中爱的迷雾让简也曾陷入自我的迷失。但她对迷失的超越是由于她恐惧失去她精神上的独立、顽强的自我。如果她失去了自我,她就可以成为桑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但她会幸福吗?伯莎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和哭声成为简恐惧的直接表现。静谧的夜中恐怖的声音加剧简的内心对桑菲尔德庄园平静如一潭死水的生活和只能“局限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口袋”的生活的恐惧。“家中的天使”对她意味着与她曾经的奋斗格格不入和自我的毁灭。这是简无法忍受的。可以说,简的自信、独立、平等的女性意识不是一促而蹴产生的,也不是一成不变、坚定不移的。在经过了一次次的恐惧洗礼后,简才成熟起来。
三、关怀意识
女性从怀孕到生育孩子,这一系列过程都与其身体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女性从孕育生命之初就对孩子产生了强烈的关注。随着孩子的出生,这种关注日渐增强并撒播到日常生活每一个角落。同时,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情感的渗入使简单的关注变成了一种关怀。帕森斯曾指出:“所有的人类群体都需要履行两种类型的活动:其一是执行任务或者‘工具性’活动;其二是旨在通过情感性或感情的表达来维持团结的活动。在小群体研究中,后者被称作‘社会感情’活动,但帕森斯却称之为‘表达性的’。家庭作为小群体的范例,在这些方面因社会性别不同而产生分化,妇女履行表达性的任务,而男子履行工具性的任务。”[3]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南茜·乔多萝在《母性的再造》中提出女性在性别认同过程中注意与母亲的情感联系,而导致女性更注重关系,更具关怀意识。男孩社会化的经历强调成就和自立,而女孩的社会化经历则强调养育和责任。成人的人格同时反映了无意识的过程与有意识的过程:男人往往倾向于个人主义、客观性和社会距离;而妇女则取向于主观性和亲密关系。在幼儿生命的最初几年,照看她们的多是女性,两性幼童的性别认同和人格定型结果是不同的。“母亲常感到女儿像她,是她的延续体,女儿也常感到她像母亲,于是认同过程有产生混淆的可能性。”[4]
四、对生命的敬畏意识
要理解女性意识中所包含的对生命的敬畏意识,我们首先要对生命做出解释。格奥尔格·西梅尔指出:“生命概念在客观和主观精神的对立中获得了它的中心意义。”[5]108人在有限的生命中,面对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但人们永远无法驱走它、消灭它。唯一可以战胜它的方法就是从精神上寻找出路,这一过程体现在人的有意识的认识和行动中。人的精神活动的超现实性和不甘受束缚性又使得人的精神活动有了不断向上的趋势。人类对有限生物生命的关注和对无限精神生命的探索都表现出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意识。
女性因其特殊的身体结构而导致她要比男性经历更多的身体上的痛苦,并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失去生命的威胁。命运对她比对其他雄性更苛刻,因而她对个体的维护也更坚决。女性极其敏感地对待身体的疼痛与异样,因为她害怕身体受到损伤,生命受到威胁。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她经历了太多的死亡挑战,所以在面对困境时女性表现出了更大的坚韧性、更强的耐力和更多的生存欲望。这就衍生出女性对生命的珍视与敬畏。在心理层面“意识同生命的连接最清楚地表现在苦难中,苦难的现实永远是现时。属于生命的痛苦构成了对世界现实的一个标准,世界在苦难中获得最高的强度。谁因为这个世界受苦,世界现实就通过他受苦这一点得到了证实。死亡让活着的人看到,随着每一个人的死亡,世界就失去了某些东西,即要求生命的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是不能通过理论上的提法而得到取代的。”[5]33承受苦难的多少可以让人对生命的价值做出不同的解释,在抗争的过程中,她们对生命的意义也产生了更深刻的理解,并进而将这种理解积淀在她们的思想中,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女性对生命的敬畏意识突出表现为面对苦难时所迸发出的坚韧性和无畏性。
女性对自我意识的寻找,并不是企图建立另一个女权中心或女权话语体系。而是以性别为起点,对女性的存在进行思考,对女性的本质进行探索。但是,女性毕竟只是人类性别中的一支,对其本质的探索并不能寻找出整个人类的本质,它必然有其类属的局限性,男性意识亦然。所以男女两性如现象学所说是两个不完整的主体,这两者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与对话,才能完成对人的本质的、人的存在价值的阐释。正如埃及女作家梅·齐亚黛在一篇演讲中曾提出的构想:未来的文明不是男性或女性单一的文明,而是整个人类的文明。只靠单一性别构建的畸形文明并非实现理想未来文明的模式。
[1][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2.
[2][英]特里·伊格尔顿.20世纪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79.
[3][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73-274.
[4]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C].北京:三联书店,1997:109.
[5][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I106
A
1001-6201(2011)06-0221-03
2011-08-12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