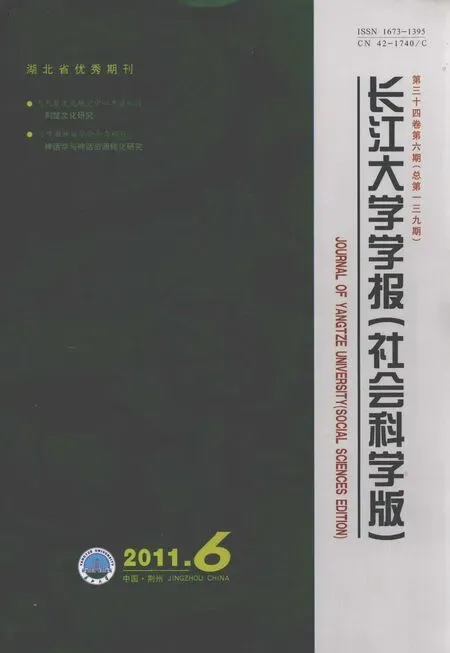孟浩然及其诗歌之“清”略议
——荆楚诗人论列之一
孟修祥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孟浩然及其诗歌之“清”略议
——荆楚诗人论列之一
孟修祥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孟浩然追求明净、雅洁、澄清、透亮人生之境与诗歌之境,故人们用“清”形容之。“清”的形象、“清”的人品与“清”的诗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孟浩然对“清”的诗性追求颇具宗教精神,也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就其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而言,其与李白、杜甫有着较大的差距,但作为一种人格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存在,孟浩然人“清”、品“清”、诗“清”,永远超越于时代之外。
孟浩然;清;诗如其人;诗性精神
一
自古至今众多论孟浩然其人其诗者,大抵以“清”称之。“清”本以形容水之澄澈状貌,如许慎《说文解字》云:“清,朗也,澄水之貌。”由此又产生了与“清”相搭配以形容各种自然现象的众多词汇,后来人们将其引申到对社会现象与人的形象、品格、文艺审美特征的品评,赋予了这一概念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而“清”在孟浩然其人其诗中体现得特别突出,故而称之。
最早从容貌的角度评孟浩然形象之“清”的是王士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孟浩然,字浩然,襄阳人也。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王士源与孟浩然是同乡,自然因乡情难抑而盛赞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更在于王士源本人也是高思清远,喜好自然山水之人。据韦滔《孟浩然集·重序》云:“宜城王士源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著《亢仓子》数篇传之于代。”从而引孟浩然为同调。据说当年张洎亲眼见过王维为孟浩然所画之像,并亲笔题识:“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葛立方《韵语阳秋》)闻一多先生以此认为,“颀而长,峭而瘦”,符合孟浩然的诗人形象,就连他的白袍靴帽也是孟浩然作为诗人的必然扮相,而“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无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不与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1](P51)
最早从人品的角度评孟浩然性情品格之“清”的是李白。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与孟浩然的友谊传为唐代诗坛的一段佳话。孟浩然长李白12岁而二人结为忘年之交,不仅诗酒唱和,更视彼此为灵性飘逸的同伴、知音。李白此诗在盛赞孟浩然风流儒雅的同时,更表达出他与孟浩然性情品格上的一致性。其“清芬”大体言其淡薄名利,品格高尚,超尘出俗。后来者如白居易《游襄阳怀孟浩然》说“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符载《从樊汉南为鹿门孟处士求修墓笺》言孟浩然“纳灵含粹,仗儒杰立”,胡震亨《唐音癸签》言“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尽凡俗”,也都是从“清芬”角度来赞赏孟浩然之“清风”、“含粹”、“清远”之高尚人品的。孟浩然也正以其耿介不俗的个性和清亮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的人们所倾慕。
最早从审美的角度评孟浩然诗之“清”的是杜甫。杜甫《解闷十二首》之六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后来者如胡应麟《诗薮·内编》言“襄阳时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然自是孟一家,学之必无精彩”,陆时雍《诗境总论》言孟浩然诗“语气清亮,诵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翁方纲《石洲诗话》云:“读孟公诗,且毋论怀抱,毋论格调,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举唐初以来诸人笔虚笔实,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也仍然从孟浩然诗的审美特征而言其“清”。无论是评孟诗的清空清幽清淡的语言,还是评其清亮清旷的色调与风致,孟浩然诗确实具有一种独特的清美,或清幽,或清空,或清亮,或清旷,或清淡等等,我们都可以从其诗作中找到例证。[2]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孟浩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再如《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有“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之句,是典型的清幽之诗。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杜甫诗时说:“《奉先寺》诗,‘阴壑生虚籁,月森散清影’,清幽何减孟公‘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之句?”还有如“竹露闲夜滳、松风清昼听”(《齿坐呈山南诸隐》)、“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京怀辛大》)、“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武陵泛舟》)、“迟尔长江暮,澄清一洗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等诗句都是极好的例证。当然,也有人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类诗句说明他“冲澹中有壮逸之气”(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谱》语)。曾季貍的《艇斋诗话》说:“老杜的《岳阳楼》诗,浩然亦有。浩然虽不及老杜,‘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亦自雄壮。”清代潘德舆也举例说:“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也有人因为《新唐书·文艺传》有关于孟浩然“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的记载,而孟浩然又有如《醉后赠马四》所谓“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秦城游侠客,相得半酣时”,以及《送朱大入秦》所谓“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之类的诗句,便认为孟浩然有“豪侠性格”[3](P300)。如此评说似乎遵循了鲁迅先生评陶渊明的准则,而考虑到了孟浩然的“全人”,但以孟氏的诗人本质而论,无论从形象、人品、诗歌的创作特点上看,还是体现在一个“清”字上。浩然身处盛唐,而盛唐整个社会中弥漫着浓烈的英雄主义氛围,说几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之类的雄壮之语,甚或是涉及兵刀弓马、立功边关之类的雄强之语也是极其自然之事,至于“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可以有多种途径,并非一定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之举。就盛唐诗人而言,赠人之诗说几句赞赏游侠之士的话,以表达对朋友的一片豪情,本在情理之中,由此而视孟浩然有豪侠性格,恐与“颀而长,峭而瘦”的诗人形象相去甚远。
孟浩然追求明净、雅洁、澄清、透亮人生之境与诗歌之境,故人们用“清”形容之。“清”的形象、“清”的人品与“清”的诗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自王士源、李白、杜甫等开其端,后来对孟浩然表示崇拜和敬仰之情者甚多。他们以一“清”字对孟浩然及其作品的整体评价颇为中肯。
二
孟浩然诗如其人,人如其诗。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1](P51)孟浩然以一种极其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故其诗“清”而高妙。
诗品体现人品,人品之最高处莫过于持有一颗赤子之心以待人应物。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浩然坦诚待人,始终持有一颗赤子真心,深得人眷爱,因而拥有众多的朋友。在孟浩然的朋友圈中,既有众多的社会名流、诗坛才子,如张说、张九龄、韩朝宗、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裴朏、卢僎、裴揔、郑倩之、独孤策、张子容、王迥、崔国辅、阎防、张愿等,皆与浩然为忘形之交,也有一些不知名姓的僧道、隐士、村夫等交情至深的朋友。且不论他与朋友赠别酬答的众多诗作中见出他对朋友的款款深情,只举《过故人庄》一首,即可见他与处于社会下层的村居朋友的深情交往:“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清人黄生《唐诗摘抄》说:“全诗俱以信口道出,笔尖几不着点墨,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绩俱化矣。”如果没有与朋友交往中那种真诚与坦荡,就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意的清纯至极而品位至高的诗作。
孟浩然想做官,也本可以去做官。想做官的证据是他青年时代,一度隐居鹿门山,未尝不是为了走终南捷径。证之于那篇著名的《临洞湖赠张丞相》,认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渴望这位张丞相能推荐他,但没有结果①傅璇琮主编《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714页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五年八月,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第298页看法亦同,但恐与孟浩然此一时期的心态不吻合,当以王辉斌《孟浩然研究》之说为是。王氏认为:开元五年,29岁的孟浩然游湖湘时,参加了当时任岳州刺史张说主持的岳阳楼“诗酒笔会”,当场写下了《临洞湖赠张丞相》(张说此前曾任宰相),张说也确实对此诗赞赏有加,以致于孟浩然“始有声于江汉间”(陶翰《送孟大人入蜀序》)。参见该书第1、1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孟浩然本可以去做官的极好机会至少有三次。一次是在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因其“清绝”,令举座惊叹而纷纷搁笔,在“以诗赋取士”的唐代,这位名动京师的诗人及第入仕应该不成问题,结果因浩然诗人气太重而没有找到门径。第二次是在王维处见到唐玄宗,却因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种因拘谨而过分的自谦,加上唐玄宗的误读,而导致机会的再度失去。第三次是因为饮酒失约。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说,“韩朝宗谓浩然间代诗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饮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这与李白何其相似!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自己在《忆旧游谯郡元参军》一诗中说:“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诗人处于一种沉醉状态,整个情绪系统得到一种自然释放而不愿受任何抑制与约束,此种状态在诗人为多,“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将韩朝宗这样的社会名流相约之事都可以置之不顾,将天子呼唤的御旨都可以不予理睬,更何况其他的社会约束。诗人让自我的个性自由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这就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之处。《新唐书》本传说“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作诗作文的时候,是为了求“真”,而不因为求“仕”而受到束缚,不为“利”所牵扯,那怕是经常处于贫困的生活之中,仍然保持一种放诞不拘,泰然自若的心态,这也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之处。
深知孟浩然个性的挚友王维曾劝其“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他确实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不愿意违心而为。有人不解孟浩然的这种心意,认为他晚年想“摆脱经济困窘,便入了张九龄幕府”[3](P297),这实在是误解了诗人。他有《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岁暮登城望,偏令乡思悬……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畋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李白以“楚狂”自许,浩然自称“狂歌”之人,二人的表白,说明他们与荆楚文化中的狂士文化深有关系。楚狂者,清高之士也,肆意直言,张扬个性,也就是孟子所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尽心下》),这也是他们两人在个性品格上产生共鸣之处。
孟浩然的行为与诗说明,他追寻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实与娱悦,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是否能做官,与财富、名望、地位无关。孟浩然说:“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诗缘真情而作,以真情感人,这也应该是孟浩然诗“清”的最根本的原因。
孟浩然对“清”诗的追求颇具宗教精神,因为宗教的精髓在于修炼到“明心见性”、“中道无为”的境地。这种境地妙观庄严、静穆、平和、安详。佛教认为“烦恼即菩提”,禅宗也有“心斋”、“静悟”、“坐忘”之说,人生在不断经历体悟烦恼、超越烦恼的修炼中亲证菩提,通过“心斋”、“静悟”、“坐忘”而渐通玄妙之理,达到无我之境。孟浩然说:“误入花源里,初怜竹径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寻。舞鹤过闲砌,飞猿啸密林。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诗人深知,人能否将一切烦恼与不幸转化为一种诗意的体悟,提升到用诗意的审美的心态去应对一切人生的遭遇和经历,这正是诗性精神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他好游寺观,寻幽访胜,又常与僧道交往,也是他向往诗性“清”境的一种体现。虽然孟浩然有时也有心底不平与矛盾的时候,但从他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这是他的诗明心见性、清空自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到孟浩然之“清”,也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登楚望山最高顶》)表明了他对襄阳深深的眷爱。张祜《题孟浩然宅》亦云:“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认为襄阳是属于孟浩然的,可见襄阳优美的地理环境对孟浩然是多么重要。《南齐书·州郡志》说:“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据《舆地广记》记载:“襄阳府……其民尚文,田土肥良,北据汉沔,西接梁盖,外带江汉,北接宛许,南包临沮,独雄江上,岘山亘其角,挟大江以为池。”不仅有“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4](P367)的隆中,更有濒临汉江,云遮雾绕,如仙女忽隐忽现,令人心驰神往的鹿门山,还有风景如画的岘山与“西行度连山,北出临汉水。汉水蹙成潭,旋转山之趾。……月炯转山曲,山上见洲尾。绿水带平沙,盘盘如抱珥”(苏轼《万山》)的万山等等,均说明襄阳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他的《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诗说:“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秋登万山寄张五》诗亦云:“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愉悦。相望试登高,心随飞雁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月如舟。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由此不难理解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对孟浩然之“清”的心性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汉魏以降,襄阳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隐逸文化。襄阳不仅风景优美,水陆交通便利,而且距离洛阳、长安又不算远,由此引来许多隐士高人,将襄阳作为隐逸的最好去处。据《舆地广记》记载,东汉末的庞德公曾隐于鹿门山,《襄阳耆旧记》说他隐于岘山。至于诸葛亮曾隐于隆中,那是名闻天下之事。孟浩然青年时代,曾一度隐居鹿门山,除了想走终南捷径的用意外,未尝不与受庞德公、诸葛亮这些先辈的影响有关。闻一多先生说:“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的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德公的继承人,此身俨然是《高士传》中人物了。总之,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1](P52)他的《齿坐呈山南诸隐》、《万山潭作》、《寻滕逸人故居》、《夏日浮舟过滕逸人别业》、《题鹿门山》、《夜归鹿门山歌》等诗歌便是隐逸文化影响下的“清”响之作。他反复表白“予意在山水”、“归赏故园间”的意思,虽与他仕途追求的人生挫折有关,亦与受襄阳的隐逸文化影响有关。
三
但孟浩然毕竟与李白、杜甫有着较大的差距。陈师道《后村诗话》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严羽《沧浪诗话》亦有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孟浩然生活的经历非常简单,也正因此对社会生活深入了解不够,与李白、杜甫相比较而言,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孟浩然基本生活在盛唐繁荣上升时期,与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李、杜时代有着绝然的不同是其客观原因,但未尝不与他的生活经历简单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开元元年王维已进士及第,孟浩然还在襄阳隐居,之后数年,才开始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漫游活动;开元十二年入京求仕未果又转道蜀地、吴越漫游;开元十六年冬赴京应举落第,后回到襄阳,其间除了与张九龄被贬荆州时作了一年多的幕僚外,大部分时间隐居襄阳。孟浩然的人生经历大体就是或隐居,或漫游,或求官。由于大部分时间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他的诗中几乎没有关于当时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边塞战争之类的思想内容。从王士源将其所存260多首诗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七类即可知其基本内容,不外乎漫游中的欢欣、隐居时的乐趣、交往赠答时的感怀、寻幽访胜的兴致,再就是求官途中遭遇挫折后的不平,只要看他应举落第后的诗作,如“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侍御维》),“岂直昏垫苦,亦为权世沉”(《秦中苦雨思归》),“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等等,然后就是自我安慰式地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带异抽簪。”(《京还赠张淮》)思想内容的逼窄,实乃源于生活视野的不够开阔所致。
就艺术形式而言也比较单调,其创作形式主要是五言诗,而五言诗中其突出成就在五律、五绝。《蠖斋诗话》指出:“襄阳五言律、绝句,清空自在,淡然有余;衍作五言排律,转觉易尽,大逊右丞。盖长篇中需警策语耐看,不得专以气体取胜也。”当然也有认为他的五古写得好的,如《四溟诗话》说:“浩然五言古诗近体,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长篇,语平气缓,若曲涧流泉而无风卷江河之势。”也有当代学者认为“孟浩然的五言排律,在孟集中与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三足鼎立,各具成就而又各有特点”[5](P144)。如果细列古人评议,大多认为孟浩然五言律为其所擅长。
顾璘《批点唐音·各体叙目》云:“五言律诗贵乎沉雄温丽,雅正清远……唐初唯杜审言,创造工致。盛唐老杜神妙外,唯王维、孟浩然、岑参三家造极。”许学夷《诗源辨体》云:“浩然五言律兴象玲珑,风神超迈,即元瑞所谓‘大本先立’,乃盛唐最上乘。”宋育仁《三唐诗品》云:“襄阳……五律含华洗骨,超然远神,如初月芙蕖,亭亭秀映。《唐书》称其方驾李、杜,固知名下无虚。”王溥等《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云:“孟公五律,笔洁气逸,为品最高,较之诸生,尤为神足……自是一代家数。”因此,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而论,都证明苏东坡之语不虚。后来明代的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从正面肯定地说:“徐献忠曰: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净,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淡疏豁,翛翛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其实质意思与东坡所云无异。当然因人的审美差异与偏好的存在,有人偏好孟浩然之清淡冲和之美,也很自然。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偏向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一边,以司空图《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说法为择诗标准,偏向于冲和淡远之诗,而不取“掣鲸鱼碧海”的李白、杜甫诗,这与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察其幽情单绪”有类似之处,而何焯批评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乃钟谭之唾余”,实在是一语中的。
指出孟浩然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不足,并非是否定其诗性意义与审美价值之所在,正好相反,孟浩然诗歌之“清”是人们走向时间与空间深处的一把钥匙。他“文不为仕,伫兴而作”,“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游不为利,期以放性”,“虽屡空不给而自若”的诗人品格,捍卫着人的生存中最可宝贵的诗性精神。人类不能缺少“清”的人品与诗品,不能缺少对心灵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实与娱悦的追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诗情、诗意、诗心、诗性,因此,“诗人何为”并非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定,而是一种强烈的内在诉求。不同的时代都有为世俗者趋之若鹜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能成为诗人恒久品质与“清”美诗性彰显的障碍物。作为一种人格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存在,孟浩然人“清”、品“清”、诗“清”,永远超越于时代之外。
[1]闻一多.孟浩然[A].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6册)[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张祖安.论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意蕴[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3(1).
[3]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罗贯中.三国演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5]王辉斌.孟浩然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207.2
A
1673-1395(2011)06-0001-05
2011-04-22
孟修祥(1956-),男,湖北天门人,教授,主要从事楚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