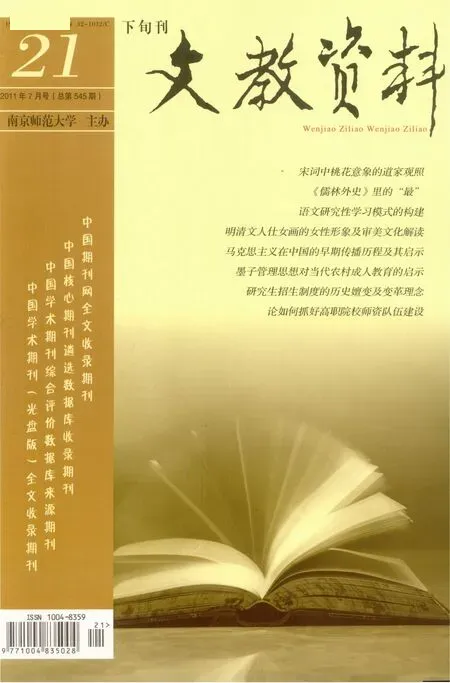“诗有别材”理论明清以来之流变
周 艳
(南京大学 图书馆 古籍部,江苏 南京 210093)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诗有别材”说对中国后来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影响极大。其言曰:“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①此言的出现与南宋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但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历史变迁,明清以来对之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也不停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不同的理论阐释和诗学主张。本文梳理明清以来几位代表性的学者对这一理论的不同阐释,以见其发展变化之脉络,尤其揭示清儒陈寿祺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阐发,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别材非关书”说
强调“别材”者,代表人物为明代胡应麟,他在《诗薮》中多处提及严氏之论并加以阐发,如:
严羽卿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十六字,在诗家即唐虞精一语不过。惟杜老难以此拘。其诗错陈万卷亡论,至说理如“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之类,每被儒生家引作话柄,然亦杜能之,后人蹈此立见败缺,益知严语当服膺。②
汉名士若王逸、孔融、高彪、赵壹辈,诗存者皆不工而不知名,若辛延年、宋子侯,乐府妙绝千古,信诗有别材也。③
皇甫子循以六朝语入中唐调而清空无迹,杨用修以六朝语作初唐调而雕缋满前,故知诗有别才,学贵善用。④
胡应麟对严氏理论“断章取义”,强调的重点在“别材”。在他看来,“别材”是诗歌创作成功的首要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可以自成一家面目。相比之下,对学养的作用则不甚重视,认为学养对诗歌创作能否成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有学而能诗者,如杜甫、皇甫子循;有不学而能诗者,如辛延年、宋子侯“乐府妙绝千古”;也有学而不能诗者,如汉名士王逸、孔融、高彪、赵壹辈及杨用修“以六朝语作初唐调而雕缋满前”。总之,胡应麟认为学养要经诗人的别材驱遣,方可在创作上起到正面作用,而成功的诗歌创作不一定非要依赖于学养。这种论调在一定层面上有其道理所在,但其弊端显而易见,易将人引入“不学”之途,很快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二、不学无以为诗说
正统的士大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显然会对诗有别材非关书之说加以讨伐以强调“学”的地位与重要性。明儒黄道周即言:
仆始创为诗篇法,大则十余,小则数首,以错综事物,酌于情理。今古之间,其流连风月,泛滥觞彩者,概不得与。惟吾乡蒋八公独信其说,此道关才、关识,才识又生于学,而严沧浪以为诗有别材,非关学也,此真瞽说以欺诳天下后生归于白战打油钉铰而已。八公云必欲登峰造巅、刊皮抉髓,则人不数章,章不数句,安得尽如《烝民》、《大东》而后得其正变乎?仆亦深以为然。⑤
黄道周承认诗歌创作关才、关识,但他认为才与识不是凭空而生,而要从学中来,严羽的说法有将世人引入不学之途的危险,故力反之。入清以来,随着重学问风气的渐次兴起,对严羽此说的批判占了上风。从四库馆臣对《沧浪诗话》的提要中可窥风气之一斑:
……由其持诗有别材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故止能摹王孟之余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严沧浪所论超群轶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顾其所自为作,徒得唐人体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处,予尝谓识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沧浪之谓乎云云,是犹徒知其病未知其所以病矣。
《提要》认为严羽诗作之所以少超拔警策之处,皆因其持诗有别材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学养不够所致。这在清代知识阶层中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见,对“学”的强调成为这个时代诗论的最强音。朱彝尊的意见颇具代表性,其在《楝亭诗序》中言:
尔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 “诗有别材匪关学”一语启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通政司使楝亭曹公吟稿,体必生涩,语必斩新,盖欲抉破籓篱,直开古人窔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公于学博综练习掌故胸中具有武库,浏览全唐诗派,多师以为师,宜其日进不已。譬诸骅骝骥騄,郭椒丁栎,腾山超涧,驰骋既熟,下而纵送剧骖之区,其乐有不可喻者已。⑥
又其《静志居诗话》言:
严仪卿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学也,其言似是而实非。不学墙面,安能作诗?自公安竟陵派行,空疎者得以借口。果尔,则少陵何苦读书破万卷乎?兴公藏书甚富,近已散佚,予尝见其遗籍,大半点墨施铅,或题其端或跋其尾,好学若是,故其诗典雅清稳,屏去粗浮浅俚之习,与惟和足称二难。以此知兴观群怨必学者而后工,今有称诗者,问以七略四部,茫然如堕云雾,顾好坐坛坫说诗,其亦不自量矣。⑦
又有诗曰:
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材非关学,严叟不晓事。顾令空疏人,著录多弟子。开口效杨陆,唐音总不齿。吾观赵宋来,诸家匪一体。东都导其源,南渡逸其轨。纷纷流派别,往往近粗鄙。群公皆贤豪,岂尽昧厥旨。良由陈言众,蹈袭乃深耻。云何今也愚,惟践形迹似。譬诸艻蔗甘,舍浆噉渣滓。斯言勿用笑,庶无乖义始。⑧
朱彝尊以经学家的立场对“别材非关学”一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尔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诗有别材匪关学’一语启之。”他认为经史之学是诗歌创作的源头,没有学问不好而能创作出一流诗歌的。朱彝尊强调学问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但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后人多有补正者,钱大昕在《瓯北集序》中对严羽和朱彝尊的观点皆有评判,其言曰:
昔严沧浪之论诗谓:“诗有别材,非关乎学;诗有别趣,匪关乎理。”而秀水朱氏讥之云:“诗篇虽小技,其原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二家之论几乎枘凿不相入。予谓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沧浪比诗于禅,沾沾于流派,较其异同,诗家门户之别,实启于此。究其所谓别材别趣者,只是依墙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转蹈于空疏不学之习。一篇一联,时复斐然,及取其全集读之,则索然尽矣。秀水谓诗必原本经史,固合于子美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之旨,然使无真材逸趣以驱使之,则藻采虽繁,臭味不属,又何以解祭鱼、点鬼、疥骆驼、掉书袋之诮乎?夫唯有绝人之才,有过人之趣,有兼人之学,乃能奄有古人之长而不袭古人之貌,然后可以卓然自成为一大家。⑨
钱氏在此所持的是两家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认为严羽和朱彝尊对于作诗之道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皆不能卓然成一大家。钱氏的论调对矫正过于重视学问,将诗与学问视为一路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就其对于严羽理论的态度而言——“究其所谓别材别趣者,只是依墙傍壁,初非真性情所寓,而转蹈于空疏不学之习”——与前人相比,并无认识和解释上的超越。
三、别材、读书、穷理统于一而为诗
相比之下,陈寿祺(公元1771—1834年)对严羽这一理论的解释,便具有很强的创发性和积极意义。陈寿祺是清代中后期举国闻名的学术大家,以《三家诗遗说考》在经学史上为人所熟知。实际上陈氏的学术领域及成就远非《三家诗遗说考》所能涵括,他在《尚书》学、《诗》学、礼学及五经总义之学等传统经学领域,以及古文、骈文、诗歌方面均有造诣并有大量著述传世,在当时是朴学与辞章兼擅的学者。⑩陈寿祺在自己的理论纬度内,对著名的诗学命题“诗有别材”说作出了颇具特色的解释,将人们对这个传统诗论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提供了另一个理解向度,这是其对传统诗论的贡献,他在《萨檀河白华楼诗钞序》中这样解释“诗有别材”一说:
严沧浪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卓哉是言乎!牦牛不可以执鼠;干将不可以补履;郑刀宋斤,迁乎地而弗良;樝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此别材之说也。五沃之土无败岁,九成之台无枉木,饮于江海,杯勺皆波涛,采于山薮,寻尺皆松枞,此多读书之说也。解牛者目无全牛,画马者胸有全马,造弓者择干于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阴,三睹阳,傅角缠筋,三年乃成。学琴者之蓬莱山,闻海水溟洞,山林杳冥,一动操而为天下妙。此多穷理之说也。才不俊则意凡,学不丰则词俭,理不博则识褊。古大家之为诗,虽风格各殊,顾于是三者必有所独至,然后其腾实大,而收名远。而世徒执“别材”一语为沧浪诟病,抑过矣![11]
可以看出,陈寿祺所强调诗歌创作的“别材”、“多读书”、“多穷理”三个因素,其实前人已分别强调过了。但是,在他之前,无论是严羽理论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没有很好地把这三者统一于对严羽诗论的阐释中。因对这一理论的理解阐发不够,种种流弊也因此而生,如前所言,或导致渺闻浅识之徒,以诗有别材非由学问,而开后学油腔滑调、信口成章之恶习;或因反对者过于强调学而使泥古拘墟之士专主渔猎,食古不化,家有类书便成作者。认识较全面者,又无法开创出一种影响力足以与严羽诗说相匹敌的理论来扭转风气。陈寿祺的做法不啻旧瓶装新酒,通过对这一理论的重新阐释,将诗歌创作的三个重要因素统一于这一理论之中,得出“才不俊则意凡,学不丰则词俭,理不博则识褊。古大家之为诗,虽风格各殊,顾于是三者必有所独至,然后其腾实大,而收名远”的结论,使这一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对诗歌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陈寿祺在他的历史语境中对这一诗学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余论
一种理论经过发展,它初出现时的部分甚至是全部含义往往会被遮蔽而在历史语境中产生种种不同的新义,这一过程在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中皆有其积极意义,后人在理解和评价前人的理论观点时,应报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样庶几可避偏颇。同时,脱离当时的具体语境,后人对一种理论的发展,其创造性是有高下之分的,高明的理论阐发,往往可以指导后来的创作往更高境界发展,这也是通过对这一诗学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得出的启示。
注释:
①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诗辨.人民文献出版社,1961.②《诗薮》内编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③《诗薮》外编一.
④《诗薮》续编二.
⑤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十八.“蒋德璟”评论之《漳浦集》.商务印书馆,1936.
⑥《曝书亭集》卷第三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⑧《曝书亭集》卷第二十一“古今诗”.四部丛刊初编本.
⑨《潜研堂集》文集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⑩陈寿祺著述集中见于 《左海全集》(清嘉庆道光间刊陈绍墉补刊本)及《左海续集》(清道光同治间刊本).
[11]《左海文集》卷六.清嘉庆道光间刊陈绍墉补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