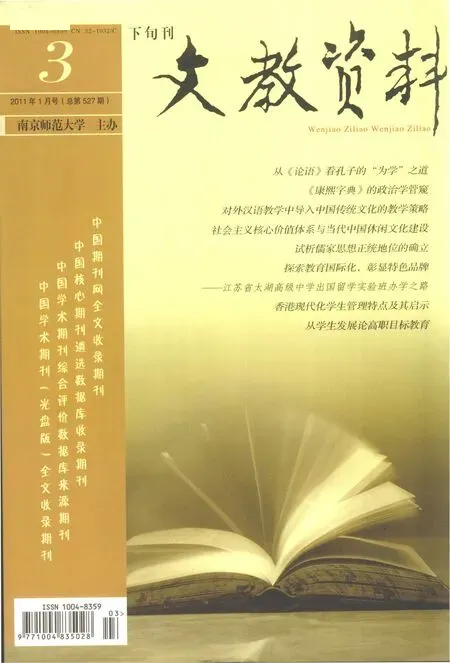论永恒的生存困境下的精神处境——《日瓦戈医生》悲剧性的尼采式解读
李云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江苏 南京 210097)
一个热情燃烧着、爱着、恨着、愿望着、渴求着的人在向我们诉说着所有人的原始痛苦,抑或是试图将我们从煎熬中解脱出来,这便是《日瓦戈医生》①的愿望,日瓦戈的心境。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小说自发表之日起便引起了巨大争议,或褒或贬。毋庸赘言,小说《日瓦戈医生》具有丰富的主题与精神内涵,其中所蕴含的悲剧精神深刻反映了人类痛苦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②生存困境是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日瓦戈的故事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主人公们在永恒的生存困境下直视人类的浩劫,自然的残酷,无疑对现代人具有巨大的启示。尼采对艺术魅力的探究有一个假定的前提:人生是痛苦的,而对艺术的追求是寻找人生快乐的一种方式。在尼采看来,悲剧这种艺术是日神与酒神二元相结合的产物。《日瓦戈医生》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像两股生命洪流在主人公精神探索的历程中交替鸣响。“这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悲》,第2页)
一、个体化苦难
《日瓦戈医生》使人充分感受到了生活在那样一个战争阴影笼罩下的人的痛苦:无情的炮火,离散的亲人。尤里和拉拉在那个时代里首先面临的生存境遇是战争。他们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外力驱使而非自愿地卷入战争,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战争对他们是一种困境。他们的个体化苦难从此开始。战争让他们妻离子散,饱尝相思之苦。困境中的人生,注定了的悲剧。一个厌倦了战争的血腥,一个明确了寻亲的无望,尤里和拉拉各自逃离战场回到家乡。但是战争仅仅是主人公生存困境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尤里第一次离开前线返家时怀抱着重新找回自我的美好愿望,“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日》,第219页)在前线的几年当中,尤里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对过去生活的想象之中,陷入如尼采所说的“酒神状态的迷狂”,个人所经历的一切淹没其中,“一条忘川隔开了日常的现实和酒神的现实”。(《悲》,第28页)所以在体会了和妻子冬妮娅一开始的那种重逢的瞬时的喜悦之后,尤里面对的是失去已有规则的日常生活,是个人价值与追求实现的无望。平庸让尤里窒息。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精神气质不俗的青年,他的理想是有时间来写作:“我多想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日》,第398页)然而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准则似乎不复存在,都成了暴力的牺牲品。事实世界的不和谐甚至是残酷长久地在尤里的内心里与价值世界中那遥不可及的理想斗争着,撕扯着。这就是尤里所面临的又一生存困境。“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相,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酒神精神要解决的问题”。(《悲》,第5页)拉拉是一位集美丽、高洁、智慧于一身的女神般的形象,是尼采笔下的“发光者”,是光明之神。拉拉面对的生存困境除了战争外还有更多也或许更为残酷,困境感、孤独感也更强烈。失去了节操,失去了丈夫,独自养活女儿……然而“她仍然保持着美丽光辉的尊严”,她摆脱科马罗夫斯基的纠缠;丈夫失踪后,当护士去前线。在拉拉的身上有着相似于又不同于尤里的气质,她勇敢地追求幸福,执着人生。叔本华写道:“喧腾的大海横无际涯,翻卷着咆哮的巨浪,舟子坐在船上,托身与一叶扁舟;同样的孤独的人平静地置身于苦难世界中……”
如果,尤里和拉拉的人生轨迹是两条平行线,二人独自面对个人化的生存困境,那么他们对抗人生悲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一致性在于给予人生以快乐,而不同之处在于给予的方式,前者间接而后者直接。尤里执着地沉湎于对自我的追求中,沉醉于对艺术的狂热钟情里。尤里所选择的对抗人生痛苦,寻找人生快乐的方式便是一种酒神状态。“酒神精神,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回归世界本体的冲动,‘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悲》,第349页)是一种消极的方式。他明白自己人生的快乐在哪里,却只是无望地钟情于自己的精神与艺术探索,钟情于“酒神的现实”,缺乏追求快乐、改变困境的具体行动。尼采的一句话可为佐证:“一旦日常的现实重新进入意识,就会令人生厌,一种弃志禁欲的心情便油然而生。酒神的人与哈姆雷特相象:两者都一度洞悉事物的本质,他们彻悟了,他们厌弃行动;由于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永恒本质……不是顾虑重重,不!是真知灼见,是对可怕真理的洞察,战胜了每一个驱使行动的动机……”(《悲》,第28页)日瓦戈诗作中的《哈姆雷特》为我们解读了他的心境:“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虚情假意使我自怜自叹∥度此一生绝非漫步田园。”(《日》,第704页)哈姆雷特是第一个以个人精神反抗社会的典型,而尤里在战乱、压抑的社会中寻求自我,沉浸于精神探索又何尝不是与哈姆雷特王子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呢?在拉拉的身上闪闪发光的是面对生存困境的不屈的精神意志和实际的行动,而这恰恰与尼采的日神精神有内在的联系。“日神精神,是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作为驱向幻觉的迫力’”,(《悲》,第349页)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她试图枪杀那个玷辱她的科马罗夫斯基;即使逃离前线,她也要把手头的事务交代清楚;为了给予卡坚卡一种稳定的成长环境,她甚至可以理智地接受可憎的律师给予她们母女的安排。拉拉努力维护女性的尊严和母性的无私,种种美德集于一身。这一完美的女性形象犹如光辉的日神,指引了一条积极地面对人生苦难的大道。
二、永恒的困境
尤里和拉拉的人生轨迹注定了不是平行线,两个同样苦难的灵魂在合情合理的安排下逐渐接近,走到了一起,即使面临道德的谴责,良心的不安。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高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地方在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结合。二人本来以个性化的方式面对个性化的生存困境,现在不得不共同面对的时候,日神与酒神有了神秘的结合。
在前线医院,日瓦戈一见到拉拉就感悟到她的全部美丽与痛苦。终于在尤里携家眷避难到瓦雷金诺,偶然而又必然地与拉拉相遇在图书馆里的时候,两颗燃烧着炙热爱情的灵魂结合了。他满足于对着她彻夜长谈,她欣赏他卓越的才华。已为人夫的尤里和已为人妻的拉拉首先面对的便是真爱与道德的冲突。尤里几次以欺骗的方式向妻子隐瞒真相,内心深处受着道德的谴责。而后更为强烈的受谴责感,使尤里产生了与拉拉分手的打算。然而,站在与冬妮娅生活的平庸琐碎的对岸的是与拉拉有着真情真爱的快乐的生活的幻影和憧憬。尤里面对分手的抉择迟疑了,他虽然生活在了一种双重人格之下,但是这样的生活他并不打算打破:一种哈姆雷特智者般的延宕。他迟疑了。面对道德的破坏,他有能力维护道德使之恢复秩序,可是考虑到秩序下的道德只会使他重返原来的生活,他迟疑了。本是以一种酒神状态处世的他仍旧采取了一种酒神的方式,但是这是一种在遭遇了道德和真爱的矛盾之后的选择。这种酒神方式便有了日神的色彩。这时人生的困境不再是战争、琐碎、平庸,而是上升到了道德与纵情、日神与酒神的对话上来,是一种人生永恒的困境,而面对着永恒的困境,人的选择便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永恒的意义。天平向情感的一端倾斜了,即使对于妻儿的责任使选择中的人心生不安。在和拉拉相处的日子里,尤里能够凝视那双美丽的眸子倾诉衷肠,无论是表白爱情,还是畅谈艺术。他在情感的一端找到了人生的快乐,即使承受着道德一端的痛苦。酒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的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悲》,第7页)尤里在痛苦中找到暂时的快乐,但可贵之处就在于尤里的选择只是倾斜,而不是完全抛弃了责任的道德的一端。否则那种纵情就只是禽兽的行为,没有了人的意义。尤里寄希望于外界力量的介入,“他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够解决矛盾的预见”。(《日》,第423页)随后不久他就被游击队抓走了,暂时性地缓解了矛盾。尤里处理人生困境的方式从本质上来讲是酒神式的,但这已经处于一种日神的状态之下,有了日神的色彩。尼采在分析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时说他具有一种兼备了“酒神和日神的本性”的“二重人格”。(《悲》,第40页)尤里的双重人格与之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日瓦戈医生》也和《普罗米修斯》一样具备了永恒的艺术之美。
《日瓦戈医生》的魅力,并不在于展现给人们一种战争年代的特有的生存困境,而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生存困境。可以明确地说,人的生存困境是自我的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是道德和个人情感,也可以理解为道德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如何面对这种困境,帕氏也以尤里一生的两次逃跑为例作出了诠释。尤里第一次逃跑是为了回到妻子冬妮娅身边。有对战争的厌倦,有对妻儿的责任,也有对妻子冬妮娅的思念,这可以归纳为理智的、道德的、情感的三方面的原因。起决定作用的是情感,是对冬妮娅的由于长久的分别而产生的无尽思念。也正因这长久的分别,思念加剧,对冬妮娅的感情加入了大量幻想的成分。原始的那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记忆在尤里的头脑里渐渐淡化,幻想出来的完美的像一个爱情的女神的形象越来越强烈的在头脑里定型、强化。召唤尤里回家的不是替他带孩子的妻子,而是头脑里幻想出来的冬妮娅,后者这种被幻想出来的日神形象激发了尤里的行动力。第二次逃离游击队是在和拉拉产生了感情之后。尤里决定逃离的原因中起支配作用的还是感情。又是一次长久的分别,思念的加剧,但是思念的对象却变成了相互之间有着真爱的拉拉。拉拉作为一个爱情的女神的形象强烈召唤尤里采取行动,这个时候,召唤尤里的是拉拉这种完美的日神形象的强烈化,而不是先前的那种强烈的日神形象的完美化。两次逃跑,是日神精神激发了主人公尤里的行动力。
相反的,拉拉的行动力,是一种积极的日神方式,在和尤里相爱以后,被掺入了酒神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尤里和拉拉成为永别的最后一次分别的凄美画面。当时,拉拉必须在为了女儿离开还是留下来陪尤里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她这样一个具有独立判断力果敢行动力的人却在这个选择面前迟疑了,她的决定是痛苦的又是坚决的。如果尤里不走,她和卡坚卡也坚决不会离开。拉拉的日神方式掺入了酒神色彩,使得行动力减弱到了几近丧失的地步。酒神精神提供的是行动力的反作用力了,其特点就是消解行动力。
对家庭的道德责任和彼此感情发生了冲突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日神和酒神第二层含义上的冲突。日神就是适度,要求人的行为在一定的原则之内,不能超越。尼采说:“日神要求它的信奉者适度。”(《悲》,第15页)酒神就是没有限度,它冲破原则的限制。尼采说:酒神是“自负和过度则被视为非日神领域的势不两立的恶魔”。(《悲》,第15页)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使得他在生活中找不到支柱,这也正是日瓦戈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原因。他拥有“一种灵魂致命的风度,一种永不屈服的真正意义上的优雅和铮铮铁汉式的柔情,一种从不示人、克制着的勇气”。③
总之,《日瓦戈医生》为读者展示了在那个时代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尤其代表了人的永恒的生存困境——个人与世界、道德和情感(意志)的冲突,具有着日神和酒神冲突的特点。主人公面对生存困境所采取的精神探索的方式——积极和消极的矛盾与转化,也同样具有着日神和酒神结合的特点。尤里和拉拉面对永恒的生存困境所采取的具有时代特点的解决方式,对人们探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提供了有益的尝试。日神、酒神二元结合的艺术,昭示着《日瓦戈医生》具有如古希腊悲剧般永恒的魅力。也许正是在人生的一幕幕悲剧之下,这种精神探索的方式才历久而弥新。
注释:
①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日瓦戈医生.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本文所有引自小说的文字均出自该版本,下文只注明作品名及页码,不再另注.
②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86:28.
③庞培.俄国四重奏.世界文学,2000,(3):289.
[1]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出版,1986.
[2]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周国平.略论尼采哲学.哲学研究,1986,(6).
[4]冯玉芝.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符·维·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