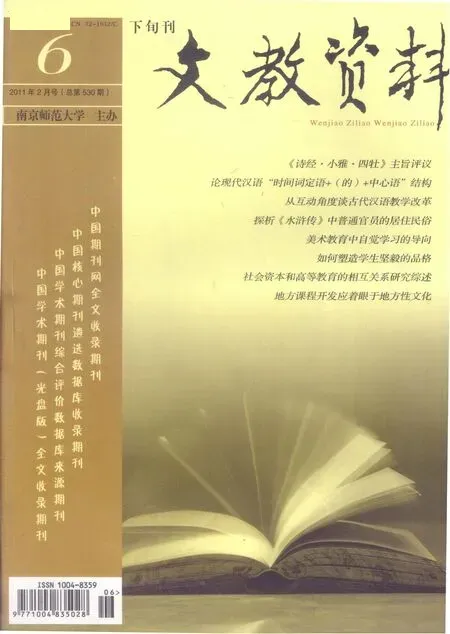《诗经·小雅·四牡》主旨评议
刘志军
(吉首大学 文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对于《诗经·小雅·四牡》这一首诗的主旨,古今注家观点约分为两派:第一种认为是慰劳使臣的诗,以诗序、毛传、孔颖达、朱熹等为代表;第二种认为是“念及父母、怀归伤悲”[1](《诗三家义集疏》引齐说)、“出使的官吏思归”[2]或“为统治者在外服役的人的辛勤与思家情绪”[3]的诗歌,近代学者程俊英、高亨、金启华等持此观点。
《诗序》云:“《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郑玄《笺》阐发序亦云:“使臣以王事往来于其职,于其来也,陈其功苦以歌乐之。”孔颖达疏云:“事毕来归,而王劳来之也。……此经五章,皆劳辞也。”《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一脉相承,对本篇诗旨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是慰劳使臣的诗篇。于末章“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句下,郑玄笺云:“故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此语与开篇语龃龉,开篇认为是文王所作,篇末陡然改为使臣自作,认为是使臣借此诗告诉王养父母之志。孔疏忽焉不察,照郑笺引申发挥云:“‘是用作歌,将母来谂’亦序使臣之意,明为使臣作此诗之歌,其来谂不得为告也。”孔疏沿袭了郑玄笺的失误。孙矿为解决此矛盾,推测云:“此自使臣在途自咏之诗。采诗者以其义尽公私,故取为劳使臣之歌。”(《诗经批评》)
产生上述两类说法源于解说者对此诗中关键词句的不同理解,认为此诗诗旨是“念及父母、怀归伤悲”的学者,他们可能由于对篇中“王事靡盬”“是用作歌,将母来谂”等关键语词的不同解读,而得出了和传统主流观点不同的见解。
按照“慰劳使臣说”的观点,首章“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句,毛传云:“盬,不坚固也。”结合《四牡》篇原文来看,此上句意为王事无不坚固,下一句缘何说“我心仍然伤悲”?似乎于情理不合,合理的逻辑应当是:如果王事已经无不坚固,那么我应当高兴,而不必伤悲。孔颖达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其疏云:“以王家之事无不坚固,我当从役以坚固之,故义不得废,我心念父母而伤悲。”孔氏于此增字解经,多方迁就以申己说,然不顾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王家之事既已无不坚固,何需汝再从役以坚固之呢?
“王事靡盬”若照郑笺、孔疏意理解为“王家之事无不坚固,我当从役以坚固之”,这表现的是一个尽心尽力为公事而努力行动之人。作如此理解方可和诗前小序协调。然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后世好学深思者的疑虑。今世学者发现郑玄、孔颖达注疏中存在的这个问题时,只好另寻出路,将“王事靡盬”解作“王事靡有止息”。如王引之《经义述闻》:“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马瑞辰《诗经通释》有大致相同的见解。他们对“王事靡盬”虽有新解,然并不反对诗序所说,依然认为此诗是慰劳使臣之诗。
后来学者在王引之将“王事靡盬”解为“王事靡有止息”的引导下,仅就诗论诗,进而提出此诗是“念及父母、怀归伤悲”、“出使的官吏思归”或“为统治者在外服役的人辛勤与思家情绪”的诗歌。此篇五章中有四章不断重章复沓“王事靡盬”一语,“王事靡有止息”当然更像一个对现实抱怨、不满意现状的使臣的叹息,而不类君王慰劳归来使者的话语。于是有学者提出了和传统不同的第二类见解——“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新说“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不必迂曲,能使全篇句意通畅、逻辑连贯。
“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是在传统主流说(即“慰劳使臣”)对本诗诗旨的解说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新说。从历代对本诗研究的情况来看,慰劳使臣说直到唐代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无人怀疑,间有感到前人之说有不周密的地方,亦多方辩解以圆其说。传统的“慰劳使臣”说无法顺畅解释篇中“王事靡盬,我心伤悲”“是用作歌,将母来谂”等处。
传统的、占据主流地位的“慰劳使臣”说为近代的学者所冷落,究其原因,大略有下面几点:第一,从《四牡》全诗字面所写的内容来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将母来谂”等句,体会其语气,更像是抱怨,而不是慰劳的话语,理解为“小官吏苦于行役,叹息他不能回乡,奉养父母”或“为统治者在外服役的人的辛勤与思家情绪”更符合全篇字面所传达的意思。因而“念及父母、怀归伤悲”似乎比“慰劳使臣”更容易让人接受;第二,自宋代朱熹解读《诗经》主张破除《诗序》的权威,认为:“看诗不当只管去《序》中讨,只当于诗辞中吟咏着,教活络贯通方得。”(据朱鉴,《诗传遗说》)宋代的郑樵、王质等也认为不能太依赖诗《序》解诗,此三人以他们在学术史上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使《诗序》的权威性大为削弱,后世不再唯“诗序”是从的学者越来越多。
确认本诗主旨为何,我认为需要厘清本诗是否为使臣自作这一问题。
持“念及父母、怀归伤悲”说的学者认为此诗全篇皆为使臣所作;持“慰劳使臣”说的学者(郑玄、孔颖达)认为篇章中一部分是使臣所作,一部分是记录君之言语,是君臣对话体。这可从注疏中窥见,本诗末章的“将母来谂”孔颖达注疏从郑玄笺解“谂”为“告”,郑玄笺云:“以养母之志,来告于君。”孔颖达则疏云:“谓君不知,欲陈此言来告君,使知也。”据郑玄笺,郑玄认为此诗是使臣所作,孔颖达与郑氏意同,亦认为是使臣自作,至少认为此诗部分语句出自使臣之口。基于此,孔氏认为全诗为君臣对话体(并在注疏中认同郑玄,谓为文王为西伯时事),现将《四牡》全诗依孔颖达注疏意按对话体标注于下:
文王:四牡騑騑,周道倭迟。
臣:岂不怀归?
王事靡盬,
我心伤悲。
文王:四牡騑騑,啴啴骆马。
臣:岂不怀归?
王事靡盬,
不遑启处。
文王:翩翩者鵻,载飞载下,
集于苞栩。
臣:王事靡盬,
不遑将父。
文王:翩翩者鵻,载飞载止,
集于苞杞。
臣:王事靡盬,
不遑将母。
文王:驾彼四骆,载骤骎骎。
臣: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将母来谂。
我认为,全篇不当是使臣所作,全篇都为国君之辞或代国君所作之辞。对于孔氏见解,黄焯在其著作《诗说》中依据诗经篇内体例“诗中凡次章以下,其章首之语,有叠前之辞,而其下有不相连贯者”,“必明此例,方知此章不与首章行文相类也”,评孔疏曰:“此二句(指“是用作歌,将母来谂”)为全篇之总束。传训谂为念,谓上作此诗之歌以述使臣念养父母之心,虽文连岂不怀归句,不得以首章为例,而谓使臣作此诗之歌也。”[4]我赞同黄焯之说,认为全篇都为国君之辞或他人代国君所作,用来慰劳使臣之辞。
综观全诗,以全篇都为国君之辞或代国君所作之辞来理解,本可以畅通无碍,“慰劳使臣”的主旨也非常显豁。君王对归来的使臣表达因为自己“靡盬”的王事,使使臣“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看到这样的结果作为国君心里很伤悲(一章“我心伤悲”)。使臣听闻君王此类言语,知自己之功已经为君王所明察肯定(《诗序》“有功而见知则说矣”),则其以往之辛酸得以宣泄,定会深深感佩于心,起到极佳的“慰劳使臣”的目的。
全诗五章,每章的前三句都是使用赋的手法。这个不论作以上两说的任一说法理解都没有争议,故不赘述。争论的焦点在每章的后两句。首先是对 “王事靡盬”中的“王”是指谁,郑笺言此诗作于“文王为西伯之时”,即姬昌此时尚未为文王,故诗中之“王”不是指姬昌(后来为文王),而是指殷纣王。汉人重师法,郑必有所本。西伯侯姬昌当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当时实际的执政者。他口出此语或由他人代出此言于身份正合,与事实相合。此处的“王事”不论是指殷纣王所派发的无尽头——靡盬的事务,还是指国家的正当的事务,对于辛苦从外归来的使臣都是一种安慰,靡盬的王事此正体现了使臣的能耐。不是有能耐又怎能对付靡盬的事情?前四章的“王事靡盬”都是对使臣功劳的承认、认同、赞赏,赞美他们为完成靡盬的公事,而“不遑启处”、“不遑将父”、“不遑将母”,牺牲了自己的安闲和奉养父母等个人利益。王符《潜夫论·爱日》篇解此诗云:“在古得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钱钟书先生《管锥编》亦有此意,认为:“后世小说、院本所写‘忠孝不能两全’,意发于此。”[5]
从诗字面意思来考察,认为诗是:“小官吏苦于行役,叹息他不能回乡,奉送父母。”[6]似乎文从字顺。将此诗作此类解读者忘掉了一个最大的前提——此诗在诗三百篇中属小雅。《诗集传》云:“正小雅,燕飨之乐也。”即指明了小雅是用在喜庆的宴会上的乐章。如果此篇抒发的是“小官吏苦于行役,叹息不能回乡”之类怨愤消极的情感,与宴会喜庆和乐的氛围将完全不相符,自然不会被编排归纳入小雅之中。从《四牡》篇所处的位置来看,本篇是小雅的第二首诗。《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车》、《杕杜》、《鱼丽》十篇,据诗前小序所言,大都为营造欢乐喜庆的气氛而设。这些诗篇因具有大致相同的性质被类聚群分排列到一起。从孔子当年删定编排诗经三百篇时初衷的角度推测,《四牡》为慰劳使臣的诗可能性更大。
[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556.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89.
[3]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8.
[4]黄焯.《诗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138.
[5]钱钟书.管锥编(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4.
[6]金启华.诗经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