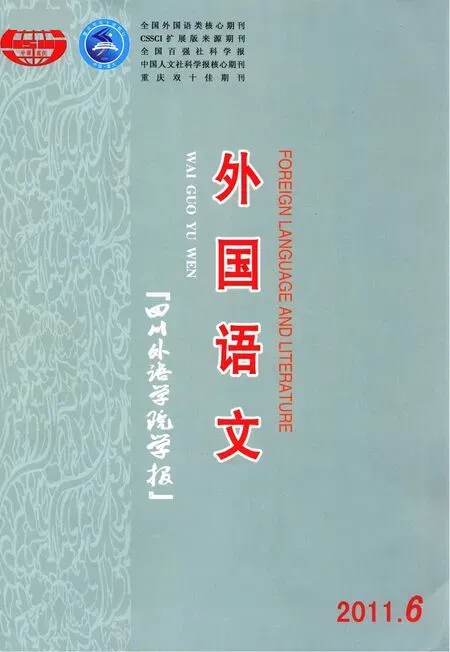“何必非真”的审美原则与黄梅戏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
李伟民
(四川外语学院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0031)
一、引言
由马兰、吴琼、黄新德、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莎剧《无事生非》(以下简称《无》)无论是在黄梅戏表演方面,还是在彰显莎剧表现的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精神方面都赢得了莎学专家和观众的赞誉,为中国戏曲如何与经典莎剧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土生土长的黄梅戏如何改编莎剧,拓展其表现领域提供了理论思考的空间。[1]“这说明一个特定事件可以在不同配置中阐释为不同功能。配置的改变引起阐释的变换。”[2]该剧将原剧五幕十七场,改为七场,既不脱离黄梅戏音舞、表演的本体,又在原作的框架内建构故事、安排情节,通过黄梅戏唱腔和舞蹈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心理,对黄梅戏《无》以其音舞的叙事特点,为中国戏曲改编莎剧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对《无》的改编不仅仅局限于对叙事文本本身的关注,而且将叙事学讨论范围扩展到“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3]这样以舞台为媒介的戏剧也就被挪入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由于对语境更为关注,《无》的黄梅戏改编充分利用了“叙事作品所得以表现的媒介”[4],为世界莎剧剧坛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莎剧改编样式。
二、“何必非真”的叙述
黄梅戏以歌舞演故事,改编的成功与否全在于所运用的唱腔能否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黄梅戏的曲词具有抒情性强、以情感人的特点。将起伏的情感用极具情感的唱腔表现出来,实现话剧莎剧由“写实”、表现“真实生活”向“写意”、“写情”的虚拟审美转化。可以说是找到了莎氏喜剧蕴含的欢快、开放式的喜剧内涵与黄梅戏的抒情艺术特性之间叙述的契合点。黄梅戏《无》的唱腔和舞蹈已经改变或颠覆了我们业已建立起来的对莎剧《无》所呈现的喜剧叙述的理解,这是审美观念的根本转变。而喜剧精神的保存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又使矛盾双方戏剧观的对立性得以转化。黄梅戏《无》中的唱段以创新的腔体表现、刻画人物性格和情感变化,使黄梅戏与莎剧跨越时空的阻隔,遇合在黄梅戏舞台上,并使黄梅戏的唱腔、舞蹈成为《无》的主要审美叙述方式,创造出一部具有黄梅戏审美特点的莎剧。黄梅戏《无》“从整体上改变黄梅戏抒情、缓慢的节奏,注入轻松、明快的喜剧节奏,演员的表演也尽可能丢掉一些戏曲程式化的东西,唱念节奏相对加快,整场戏幽默、清新、和谐,既忠于莎士比亚原著,又不失黄梅戏艺术特征,使黄梅戏与莎士比亚戏剧结合成一个新的艺术整体”[5]167。借助于莎剧的经典型和对人性普适性叙述,突破了黄梅戏原有的表现领域和“表现范围”[6],在世界莎剧舞台上创造出的黄梅戏莎剧已经超越了时空和民族的界限,跨越了文化、艺术形式之间的鸿沟,为世界莎剧舞台提供了黄梅戏莎剧的演出形式,必将为莎剧表演和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考和阐释角度。
黄梅戏《无》“何必非真”的叙述拒绝了西洋化的包装,采取了黄梅戏化的形式、既通过大段的唱腔叙述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又通过念、做、打、舞使人物的心理、情感得以鲜明呈现,在化用莎剧语言的基础上,充分中国化,如第四场杜百瑞让巡丁脱下帽子统统露出光头皮,对当差的巡丁唱道:
当差只留光头皮,双脚踩着西瓜皮,能剥老鼠皮,别摸老虎皮。佛面贴金皮,人顾两张皮。又要肥肚皮,又莫破脸皮。[5]624 -625
这种体现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言语以其叙事功能的讽刺效果、叙事任务的二重性、叙事色彩的异质性构成了具有喜剧色彩的叙事者角色,叙事的接受者既是巡丁,更是观众。他的叙事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幽默中含有喜剧的讽刺,配合夸张的“跑驴”的舞步,削弱了“主体与客体、做与叙之间的区分”[7]589使“叙事成为一种必要”[7]590的模式,观众不仅认同舞台上的唱、舞叙事,而且通过黄梅戏的风格中对莎氏喜剧风格、叙述的隐喻性加深了认识,取得的是会心一笑的美学效果。正如曹禺所说,黄梅戏《无》“使莎士比亚到你们手头忽然变得更亮了”①曹禺:《莎士比亚更“亮”了——曹禺、黄佐临等同志看戏后的谈话》,安徽省黄梅剧团/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印:《黄梅戏〈无事生非〉演出专刊》,1986年6月,第7页。这种把莎氏喜剧审美转化为黄梅戏喜剧审美,通过对唱、独唱、合唱、独舞、群舞的“形式和功能来对其加以描绘”[8]表演形式,使其在外在形式上既远离生活、变异生活,又在形式表现上贴近了中国观众,从而使观众在幽默、诙谐、调侃、讽刺的唱叙、表演中获得了节奏、韵律、整饬、和谐的黄梅戏莎剧的审美体验。
黄梅戏《无》在吸收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创造出新奇、诗化的表现场面,使其通过黄梅戏丰富的艺术手段,达到貌虽离而神合的审美效果。如在第一场中,娄地鳌与李海萝目光相遇,李碧翠从两人眼前各牵过一条“丝线”,一拉一弹,两人身体随之晃动,“丝线”断了,两人从忘情中回到了现实世界,顿觉羞涩脸红。运用这种“牵线打线”[5]370的舞台叙事表现手法,将娄地鳌与李海萝的爱情表现得形象而深挚,含蓄而富有象征意味。又如在原剧中,克劳狄奥当堂羞辱茜罗的一场戏,黄梅戏《无》把教堂婚礼改为洞房花烛夜,用“三揭盖头”的传统表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舞会一场,编导汲取了中国古代角牴戏和傩戏古朴稚拙的风格,以假面舞营造了气氛,反映了人物心理。[9]52再如第七场中,娄地鳌来到李海萝“坟”前,挥剑劈墓,八位头戴面具,身着素服的女子飘然而来,娄地鳌要从中选择一位替代李海萝,而选中的“瞎眼婆”正是假传死讯的海萝,这些舞蹈设计新奇不俗,在“三重叙事”中,既有叙述者,又有表演者,也有评论者,既置身事中,又置身事外,演员以丰富的舞蹈语汇叙述,使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舞蹈中得到了理解,既充满了诗情画意,又以具象化的舞蹈表达出人物的情感。[5]370正如齐如山所说:“中国剧处处是用美术化的法子来表演,最忌向真。”[10]72可以说,以唱腔、舞蹈为舞台叙事形式的黄梅戏《无》之审美已经解构了莎剧《无》之“真”,它不在“真”上做文章,而是在“美”上表现“生活之真”,这是“三重叙述”中表演者的叙述,也是评论者的叙述,更是“行当”的叙述,黄梅戏《无》有别于莎剧《无》的关键就在这里,中西方戏剧的审美分野也在这里。黄梅戏《无》既利用了化装、服饰、动作、语言“矫情镇物,装腔作势”[11]7-8之感这样的审美表现,也把莎剧《无》中的语言、日常的动作、戏剧性的冲突强化、美化、艺术化,以黄梅戏超出生活之法的审美表现生活。[11]9黄梅戏《无》这种“何必非真”的叙事在张扬喜剧精神的基础上,“非常的真,不过不是写实的真,却是艺术的真,使观众看了,觉得比本来的真还要真”[10]106。黄梅戏《无》以其表演形式创造出了莎剧《无》所需要的内容,在“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基本规律的制约……符合生活逻辑”[11]16的同时,“高度发扬戏剧的假定性,与此同时又沿用模拟生活形态的真实性,达到虚拟与实感相结合”[11]16。黄梅戏《无》是全面借鉴黄梅戏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改编,融中西两种戏剧艺术表现、审美观念于一台,以叙事和抒情的叙述,既深刻表现出莎剧《无》的喜剧精神,又充分调动、发挥了黄梅戏的表演技巧,在文化、戏剧观的碰撞中显示出两者的无限生命力。
三、符号体系之间的审美转换
黄梅戏《无》的改编遵循的是以“黄梅戏为体,莎剧为用”的方针,如同王蒙所说“洋戏土演”[12]92是也。而这样的定位可以将莎剧念白、行动与黄梅戏的“唱”、“舞”结合起来。重要的不在于对莎剧《无》内容的叙述,关键是黄梅戏《无》在原作的语言“符号体系”[13]和黄梅戏已经形成的符号体系中以其音舞如何表现的问题。黄梅戏《无》通过唱腔、舞蹈和念白的舞台叙述与莎剧《无》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观众的欣赏感受也不一样。黄梅戏《无》在表现矛盾冲突时,不仅通过对白叙述,还化“对白”为“对唱”,通过“对唱”的方式叙述矛盾冲突,在针锋相对的对唱交锋、交流中渲染矛盾的尖锐与化解,在“平词对 板”[5]302的演唱中,持续不断推动戏剧冲突发展。[14]如在原作第一幕第一场中,克劳第奥向裴尼狄克问起希罗,裴尼狄克说“她是太矮了点儿,不能给她太高的恭维;太黑了点儿,不能给他太美的恭维……”①莎士比亚:《无事烦恼》,《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辑·第三种),朱生豪译,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第8、10页。在黄梅戏《无》中,以诙谐、讥讽的“取莎翁之意境化为戏曲之词”[15]192“特定词语对人物加以直接标记”[2]168的方法对人物进行描绘,其描绘以黄梅戏特有的“有意识地误会纠缠”表现白立荻、李碧翠评价娄地鳌的对唱:
他比我身材高一分,哎呀呀,还是一根三寸钉。他被我脸蛋白一分,不过是黑炭头洒上粉一层。他比我武艺强一分,只能拍死小苍蝇。他比我容貌美一分,哎呀呀,还是猪八戒又还魂。[5]613
李碧翠和白立荻分别互为叙述者和叙述的接受者,叙述中的“她”虽为第三人称,但无论是白立荻,还是观众都明白实指的是在场的李碧翠。黄梅戏《无》做这样的改动使其喜剧性通过唱叙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加强,黄梅戏在独唱、重唱、合唱、对唱、背唱等传统手法的运用中,“以欢快的仙腔和彩腔为旋律的基调,糅合经过创新的花腔小戏的曲调,在描写音乐上又选用了具有少数民族风味的音乐,并配以色彩性打击乐”②殷伟:《新花初绽清香四溢——记黄梅戏〈无事生非〉的演出》,《安徽日报》1986年4月9日。又见安徽省黄梅剧团/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印:《黄梅戏〈无事生非〉演出专刊》,1986年6月,第12页。,人物的性格、情感、心理、行动依据所迸发出来的审美效果“集秀溶美,使莎剧(包括一切外国的优秀戏剧)的美和中国戏曲的美,在新的意识与更高层次上凝铸成美的结晶”[15]190,使“戏中人”的心理活动被黄梅戏的唱腔激活,诙谐、俏皮的唱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艺术地诠释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如裴尼狄克袒露自己的心迹:“一个女人生下了我,我应该感谢她;她把我养育长大,我也要向她表示至诚的感谢……我愿意一生一世做个光棍”③莎士比亚:《无事烦恼》,《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辑·第三种),朱生豪译,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第8、10页。化为:
只感女人恩。我是落花不结子,我是浮萍不留根……丑女我不念,美女不放心,生为大丈夫,怕戴绿头巾。不如终生做光棍,自由自在似天神。[5]613
在叙述中,黄梅戏《无》的喜剧气氛与主人公的直率、聪明、执著的性格特征得到体现,改编者与作曲、唱腔设计反复研究、实验,根据黄梅戏的特点,继承、发展了黄梅戏小戏“运用夸张手法,冷嘲热讽”[5]29的特点,在挖苦、讽刺的笑声中,揭示了人物直率、大胆,既高傲又软弱的性格特征。情节的进展以说说唱唱、边舞边唱的叙述形式,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气氛。用唱腔、舞蹈表现人物性格、心理,叙述人物行动成为改编是“否成功的关键,在黄梅戏《无》中第七场“真面真心结丝罗”[5]640的唱段中,把李海萝对爱情的真挚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一种含义深长、余音未尽的感觉。这时表露心迹的唱叙已经使“叙述者不仅成为主动性的第一叙述者,也可成为回应性的第二叙述者,即自我对自我的叙述进行叙述的回应”[16]171-172。此时的叙述者不仅是对观众的交代,也成为自己内心的回应者,李海萝经过一系列误会之后,终于找到了爱的归宿,并对人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四、假定性中的后经典叙事
在后经典叙事中,达到叙事与故事的同一的手段,涵盖了“元叙事”[17]146。黄梅戏《无》以唱腔、舞蹈为表现形式是对生活假定性叙述,达到了舞台叙事与故事之间的同一,这种假定性将审美的表演和艺术的假定性加以放大,是以其元叙事(metanarrative)的表演方式,将语言的表述转变为音舞的表述,实际上是从审美层面颠覆了戏剧之“真”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使“戏”为“戏”也,而不是“戏”为“生活”。元叙事所要表现的是其他叙事的叙事。“把莎剧化为戏曲演出,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一种再创造。”[15]182黄梅戏《无》在形式上创造出的是一个审美的世界。它并不以叙述现实世界的可能性为目的,而是以通过叙述现实世界中人的矛盾达到审美目的。黄梅戏《无》的改编与元叙事放弃叙述世界的真理价值,而以终极的审美为旨归这一理论不谋而合,“它肯定叙述的人造性和假设性,从而把控制叙述的诸种深层规律——叙述程式、前文本、互文性价值体系与释读体系——拉到表层来,暴露之,利用之,把傀儡戏的全套牵线班子都推到前台,对叙述机制来个彻底的露际。”[18]269经过这样的审美转换,演员放下了“真”的包袱,可以将莎剧《无》的喜剧性发挥到极致,黄梅戏《无》的元叙事也就成为人造性和假设性的成功实践。黄梅戏《无》唱腔的“音乐因素属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歌唱。由于有歌唱,念白就不能保持生活语言的自然状态,它必须是吟咏,强调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11]112。这样就与话剧形态的《无》拉开了距离,使“真”必须通过唱腔、舞蹈之“美”方能得到表现,在这里“无论是舞蹈,还是唱念,都不过是剧情的一部分,因此它的音乐性、舞蹈性、节奏性是统一于戏剧性的”[11]112。黄梅戏《无》中的人物的舞台动作是通过舞蹈化身段、音乐化的念白演唱形成了一种经过提炼、强烈、鲜明、可看、可听的表现形式。[11]113-114经过叙述者、评论者、表演者的三重舞台叙述,“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己。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 后 才能说。”[18]I-II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莎剧《无》审美呈现方式完全不同黄梅戏《无》,“尽管莎士比亚剧作的台词不是像中国戏曲的唱词那样用的是比较严格的韵文体,但也同样具有诗的韵律美”[15]187,人物的性格就通过黄梅戏的唱腔、舞蹈得到了鲜明呈现,如第七场李碧翠、白立荻、李海萝的唱、做:
喜欢他与我合秉性,无情冷面锁情心。口若心来心如口,舌头刺人不伤心。喜欢他情海舟自稳,风亲浪吻不动心。唇枪舌剑传情语,我的坟墓是他的心。[5]636-637
……你没见侯爷和将领,都张着血口来喷人。这世道,丈夫气概已丧尽,豪侠精神也无存,壮志消磨在打躬作揖里,良心融化在逢迎阿谀中……[5]637
悄悄一声请,果然变温柔。她说美意少,哽住乌鸦喉……要我细品味,将她情意留。我若不把她怜爱,立荻真是一条牛。[5]627
呆呆呆,痴痴痴,苦苦苦,悲悲悲。唾沫赛过东海水,舌根重似千斤锤。一片真情换得千重罪,死了清净活着卑。[5]632
李碧翠、白立荻、李海萝以唱和舞传达给观众的是,感情是戏剧,激情也是戏剧,演员“用诗、用歌、用优美的舞蹈、用强烈的形体动作,诉说直接使她激动、愤怒的事物,剖析‘自己’的思考,倾吐‘自己’的感受、披露‘自己’的隐私……这个行动,最能表现性格,它的意义也超过了激情本身”[19]。马兰的唱法较本色,声音富有磁性,演唱朴实大方,以情带声,把戏剧内容与演唱技巧统一起来,创造出角色所需要的音乐形象,[5]325;黄新德的唱法表情细腻,嗓音圆润明亮,底气充足,又注重小腔,抑刚扬柔;这里在“背白”、“互视”等一系列身段表演中,李碧翠的叙述使“二人动了真情,竟致飘然起舞,相依相 偎”[5]637。而吴琼的在模仿严凤英唱法的基础上,把握了其精髓,重视声音的造型作用,音色与唱法多样,音色纯正,[5]325如李海萝的“相伴永相随”的唱段:
人醉地醉天也醉,紫雾托着彩霞飞。故土更香林更美,赤颊红花两相辉。枝头鸟语声声脆,似问我,问我嫁后几时归?[5]627
她的叙事更多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和观众,表达的是内心对真挚爱情的憧憬、向往,而观众通过其唱腔既把握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又领略了黄梅戏唱腔特有的美感,叙事与唱腔互相生发,从而引起观众共鸣。通过这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唱腔,加上身段与造型所形成的舞台叙事,带来的是对话语细节(优美唱腔)和象征特色明显的强化聚焦审美,[20]一个个直率、俏皮、真挚、爱憎分明的青春男女形象在音舞叙事的审美效应中得到放大,在唱腔、舞蹈、语言三者之间的有机叠加中,以突出演出的虚构性、表演性为目的,在唱腔、舞美的喜剧性叙述的过程中,造成了“悲中喜,喜中愁”[21]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所谓“戏”“戱”也的目的,观众获得的是黄梅戏莎氏喜剧的审美愉悦,改变的是戏剧等同于生活的观念。观众从黄梅戏《无》的声腔之美和舞蹈的身段之姿中体会到莎剧的魅力,这正是两种戏剧、不同审美形式嫁接的结果。
黄梅戏《无》所要带给观众的早已不再以描写现实生活、反映现实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唱腔、舞美呈现所需要达到的审美愉悦为旨归,元叙事表明“叙述者直接面对听众的不仅有叙述者的话语,还有其在叙述过程中的表情、动作和语气等等。可以说,口头叙事中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行为是共时存在、相辅相成的。”[22]从后经典叙事这一角度观察,莎氏喜剧的叙述方式和呈现的舞台效果悄然发生了改变,观众主要不是通过语言感受喜剧的轻松明快,而是把莎剧语言戏曲化、黄梅化,通过唱腔、舞美的呈现达到审美目的。表明“莎士比亚在中国戏曲里活着,他获得了新的生命,英国戏剧也获得了新的生命”①菲力浦·布洛克班克:《莎士比亚在中国戏曲里活着——国际莎协主席布洛克班克看戏后的谈话》,安徽省黄梅剧团/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印:《黄梅戏〈无事生非〉演出专刊》,1986年6月,第8页。,他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中,怎样演绎,如何演绎得成功和美,才是或应该是改编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审美理论的指导下,唱腔的抒情色彩与戏曲身段的舞蹈化奠定了统一的节奏基础[6]27。黄梅戏《无》在适合中国观众“审美”方面所形成的后经典叙事性与元叙事,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而且对原作的内容和人文主义精神也化为道德、伦理的评判,但这仍然是莎士比亚,也是黄梅戏的《无》。
黄梅戏《无》化莎剧原作中的独白和部分对白为唱段,既承担了叙述者的任务,叙述了故事内容,推动了情节发展,表现了人物情感,又把“隐含叙述者”思想通过主人公之口叙述出来。音乐所营造的语境本身也是叙述。“黄梅戏是以演唱为主的戏剧,而戏剧音乐则应当是富有戏剧性的,戏剧需要利用音乐手段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配合戏剧矛盾的展开、渲染戏剧环境、制造戏剧气氛、协调戏剧节奏”[5]304。按照巴赫金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直接放到主人公的嘴里,从作者的理论或伦理(政治、社会)价值的角度把这些思想说出来。”但是在西方戏剧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戏剧里“台词会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立足于一般水准,并不禁止既想到姿势动作又想到言词,甚至在这一点上,言词会获得更重要的效能……西方戏剧中言词仅仅用来表现心理冲突,特别是用来表现人及其日常生活的真实性”[23]。而在黄梅戏《无》中,以“主腔”为主,富有变化的大段唱词,除了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功能以外,以观众所形成的欣赏定式为审美参照,已经在后经典叙事中,通过舞台创造出符合“隐含作者”思想价值判断的人物性格。正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给曹禺的贺信”中所说:“尽管莎士比亚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剧作家,但他一直是为普普通通的男人和女人而写作的……正是这种将复杂思想和感情变得简单易懂,将崇高的思想用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能力,使他成为伟大的剧作家,不管他用什么语言来写作。”[24]封2在莎剧《无》中,台词的任务,主要是“把这些思想传达出来”,具有揭示人物思想、行动原由、心理特征的作用,而在黄梅戏《无》中,由此构成的“剧中人和剧中人性格成长的历史——情节的整一性,及由此而带来的效果的幻觉性”[16]172,就必须以黄梅戏的审美为主要标准,“角色既与常见的花旦行当有很大的区别,又不同于一般的小生或武生,也绝不是四平八稳的老生,”[24]13而是人物性格的反映,通过李碧翠、白立荻、李海萝的“唱”和马兰、黄新德、吴琼对以“柔”为主的黄梅戏舞台的“做”的舞台叙述,黄梅戏《无》已经对莎剧《无》进行了假定性的彻底改造,而也正是这一改造使我们看到了黄梅戏《无》可以在后经典叙事的阐释中得到更好的说明,也使我们能够通过后经典叙事与元叙事更深入地把握其改编特色。
五、结语
在后经典叙事中黄梅戏《无》已经彻底摒弃了西方戏剧的全知视角,而是以唱腔、舞美的艺术虚构性、假定性为前提,毫不掩饰表演的虚拟性,虽然是“代言体”的“现身说法”,但是仍要通过音舞叙事塑造人物形象,“叙述者的背后不仅有一个人存在”[25],而且具有“三重叙事”的特点。黄梅戏《无》改编演出的成功为世界莎剧舞台上增添了一朵绚丽的黄梅戏之花,丰富了莎剧的演出形式,为当下莎剧舞台提供了饱含中国文化、戏曲形式的不可多得的改编莎剧,也在后经典叙事中完成了一次中西方戏剧审美实践与戏剧观念之间的打通工作。
[1]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401-402.
[2]卡法勒诺斯.似知未知:叙事里的信息延宕和压制的认识论效果[C]//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6.
[3]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二版)[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4]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
[5]王长安.中国黄梅戏[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马兰、吴琼主演:《无事生非》(黄梅戏),VCD(上下集),导演:蒋维国,文学顾问:张君川,安徽省黄梅戏剧院,1986年,文中除了参考剧本之外,也参考了实际演出时的唱词和宾白。)对于莎士比亚的原作可参看,莎士比亚:《无事烦恼》,《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辑·第三种),朱生豪译,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三十八年。)
[6]蓝凡.中西戏剧比较论稿[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29.
[7]佩吉·费伦.表演艺术史上的碎片:波洛克和纳穆斯通过玻璃,模糊不清[C]//James Phelan Peter J.Rabinowitz主编,申丹等,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89-590.
[8]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
[9]葛剑群.黄梅戏史上的一次突破——记黄梅戏移植莎剧《无事生非》[J].黄梅戏艺术,2005(2):52.
[10]齐如山.梅兰芳游美记[Z].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章诒和.中国戏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12]谭霈生.戏剧本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13]晴空,成瑞.黄梅新花香更浓《无事生非》晋京演出散记[J].黄梅戏艺术,1987(3):86 -93.
[14]吕效平.戏曲本质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
[15]金芝.当代剧坛沉思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16]邹元江.中西戏剧审美陌生化思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祖国颂.后经典叙事:泛互文性及其文化表征——以《反复》的叙事策略为例[C]//祖国颂.叙事学的中国之路——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8]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9]金芝.惶恐的探索——改编莎剧《无事生非》为黄梅戏的断想[J].戏曲艺术,1987(1):4-9.
[20]J.H.Murray.Hamlet an the Holodeck:The Future of Narrative in Cyberspac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49-50.
[21]郭汉城,章诒和.师友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22]申丹.叙述[C]//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738.
[23]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C]//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365.
[24]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给曹禺的贺信[Z].合肥:安徽省黄梅剧团/安徽省艺术研究所编印.黄梅戏《无事生非》演出专刊,1986年6月.
[25]格雷塔·奥尔森.重新思考不可靠性:易犯错误的和不可信的叙述者[C]//唐伟胜主编.叙事(中国版·第一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