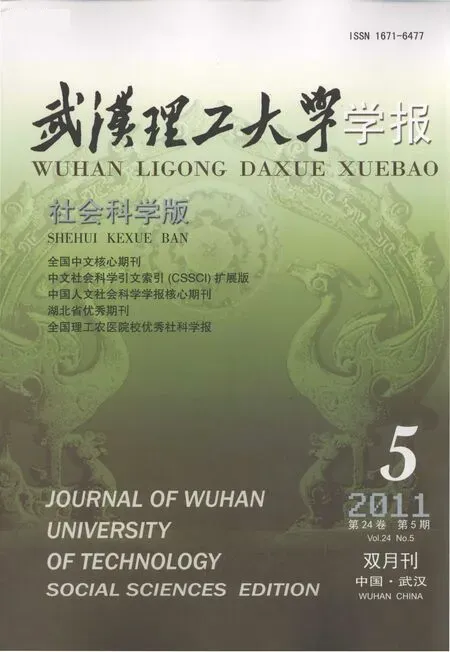论G.E.摩尔的自然主义的谬误*
孔文清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学院,上海201418)
论G.E.摩尔的自然主义的谬误*
孔文清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思想政治学院,上海201418)
摩尔的“自然主义的谬误”所指涉的是祛魅化后的自然与心灵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因此,不能用自然的性质来说明和定义属于另一个领域的善。如果将规范性混淆于或还原于事实性,那就是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但摩尔在提出“自然主义的谬误”时,错误地将不属于“自然主义的谬误”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也归入了“自然主义的谬误”范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这是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意义所在,但事实与规范又不能没有联系。为了克服这一割裂,麦金泰尔和麦克道尔分别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
自然;自然主义的谬误;事实;规范;第二自然
G.E.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对以前的伦理学进行考察时,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谬误”这一概念来说明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所犯的错误。由此,“自然主义的谬误”成为了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人们在构建、审查一种道德哲学时往往会着力避免陷入这一错误或者是用它来指明某一理论存在的问题。例如,对环境伦理学来说,自然主义的谬误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在构建环境伦理学时陷入了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虽然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避免这一点,那么,他们的理论就变得非常可疑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恐怕是现代道德哲学无法回避的一个概念。但是,与这一概念的重要性相比,国内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与研究却很少。为什么摩尔会提出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自然主义的谬误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解决自然主义的谬误?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浅的回答。
一、自然与自然主义的谬误
按照摩尔的理解,“自然主义的谬误往往暗指:当我们想到‘这是善的’时,我们所想到的无非是所讨论的事物跟某一别的事物有着一确定的关系。可是,参照来给善下定义的一定事物可能就是我称之为自然客体——其实存公认是一经验对象的某种事物——的东西,也可能是一个仅仅被推想实存于一个超感觉的实在的世界之中的客体”[1]54。被摩尔当作自然主义谬误的有两种:一种是用自然客体来定义善,一种是用形而上学的实存来定义善。这两种用来定义善的事物正如摩尔自己所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需要分开来说明。前一种情况也就是“用一个自然客体的或者自然客体集团的某一性质来代替‘善’”[1]55。那么自然是指的什么呢?“我正在用,而且已经用‘自然’表示作为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东西。可以说,它包括一切或者曾经存在,或者现在存在,或者将会存在一定时间的东西。”[1]56由此可见,摩尔的自然主义的谬误也就是将“善”这一概念等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领域的事物。那么,将“善”这一概念等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领域的事物何以是一种谬误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以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为分界,在此之前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与之后人们对自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前,自然是未经祛魅的自然,自然被认为是包含于理由的逻辑空间里面的。自然本身是有意义的。“在中世纪的常识性观点看来,我们现在自然科学的主题被认为是充满了意义的”[2]70。而在自然科学兴起之后,自然被祛魅了。自然被认为是与人的自发性自由分列于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在自然的领域,属于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空间,遵循的是因果律。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理由的逻辑空间。两者之间性质不同。“现代科学以至少是预示着将它祛魅的方式来理解其主题,就像韦伯用以说明这一点时所使用的形象,这一形象现在已经成为了常识。韦伯的这一形象标记出两类不同的可理解的事物:一类是自然科学探究的,一类是在与塞拉斯的惯用语——‘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其它事物间的关系中发现的事物”[2]70。现代自然科学兴起后所形成的新的观念,反映在哲学中,就是心灵与世界的二元论。笛卡儿区分了思想的事物与广延的事物,心灵具有与广延的事物——亦即摩尔所说的自然客体不同的性质,二者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人的身体也被划入了广延的事物这一范围。由此,心物之间、身心之间是不统一的。而在康德那里,对峙的双方是概念和直觉。在自然科学兴起之后,祛魅化的自然成为人们的常识,人们说到自然,意指的就是这一与心灵对峙的祛魅的自然。这一划界,用塞拉斯的术语来说,亦即两个逻辑空间的划分: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自然客体、因果律、经验、对自然的描述,使自然科学座落于自然的逻辑空间之中。而知识、概念、证明座落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自然的逻辑空间是描述的,理由的逻辑空间是规范的。因此,关于“是”的问题与关于“应当”的问题是分属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的,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等同。塞拉斯认为“将认识的事实毫无保留地分界为非认识的事实”这一错误与伦理学自然主义的谬误相同。塞拉斯在这里所指出的错误不是将特殊的(精神的、意向的)领域还原为另一个(物理的)领域,认识论上真正的混淆是在“描述的领域和规范、实践和价值的领域”[3]180。由休谟所提出的“是-应当”问题所指的也就是“是”与“应当”性质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鸿沟,因此,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他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者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讨论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4]休谟觉得不可思议的,正是人们常常在伦理学中从属于自然的逻辑空间中的“是”中推出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应当”,而它们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逻辑空间,这一推导跨越了一个逻辑鸿沟,因此是不成立的。
明白了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人们所认识的自然是祛魅的自然,与知识、概念等规范性的事物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我们也就能理解摩尔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含义了。显然,摩尔无疑也是站在现代自然科学对自然做祛魅化处理后的立场上来理解自然和心灵的。自然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祛魅的自然,而善则是与自然性质不同的,是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的。“‘善’本身并不是一自然性质”[1]57。对于二者之间的区别,摩尔有着清楚的认识:“‘自然界’与超感觉实在之间的差别是众所周知和十分重要的。”[1]146摩尔用来说明善不能用自然客体定义的例子是不能用黄的东西定义黄。黄的东西是存在于自然中的客体,而黄这一概念却是属于人的思想领域。用自然客体或者自然客体集团的性质来定义善,也就是混淆了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将规范等同于事实性。这也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将不是自然领域的善归结为自然的性质,因此,在他们看来,“伦理学是一门经验科学或者实证科学,因为它的各项结论全部都能够运用经验观察和归纳法来予以建立”[1]54。摩尔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也就是所谓的“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bald naturalism)所犯的错误。当然,自然主义的谬误不仅仅是“是-应当”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要大于伦理学中的“是-应当”问题。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的谬误的实质就是“是-应当”问题。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的。
二、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的谬误
将“应当”与“是”混淆,规范性等同于事实性,确实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东西。因为自然主义的谬误,如同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目的在于将概念能力纳入作为规律领域的自然”[2]73。也就是说,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否认自然与自发性之间存在鸿沟,他们将概念能力等自发性能力还原为自然。这样一来,人的自主性就被取消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摩尔反对自然主义的谬误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他所捍卫的是人的自主性、自发性和自由。而这正是人不同于只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自然物的关键所在。
如果摩尔仅仅将自然主义的谬误用来批判他所谓的自然主义伦理学,那么,他的这一批判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上文所引,被摩尔归结为自然主义谬误中的不仅有用自然客体的性质来定义善,而且还有形而上学的超感觉的客体。摩尔虽然看到了自然客体与超自然客体的区别,但是,依然将用超感觉客体来定义善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他说:“应当注意,我参照来给‘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下定义的那种谬误是同一类的,我无非是也把它叫做自然主义谬误。”[1]54而我们已经看到,所谓自然主义的谬误是指将思想的事物、概念、自发性以及自由等座落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事物混淆于祛魅化后的自然对象,将规范性还原于事实性。摩尔将用自然的性质定义善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按照自然主义的谬误这一含义,那么,用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客体来定义善,就不能被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了。因为这些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客体无疑是与祛魅化后的自然的客体是不一样的,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客体的位置不是在自然的逻辑空间中,而是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对此,摩尔也不否认:“当我说到‘形而上学的’命题时,我意指关于某种超感觉的东西(某种并非知觉对象,从而不能依据我们推测所谓‘自然界’之过去未来的同一推理法则,从一个作为知觉对象的东西推想而知的东西)之存在的命题。当我说到‘形而上学的’术语时,我意指关于这样一些特质的术语,它们属于这种超感觉的实在,而不属于任何‘自然的’的事物。”[1]145这样一来,用自然的性质来定义善这一情况中存在着混淆规范性与事实性以及抹煞二者之间存在鸿沟的错误,在用形而上学的客体定义善这种情况中并不存在,因为,形而上学的客体与善是座落于同一个逻辑空间,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摩尔将这种情况也称为自然主义的谬误本身就是一个谬误。按照摩尔的这一看法,康德、斯宾诺沙等也犯了他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而实际情况却是,康德在伦理学上的一大特点正是区分了两个逻辑空间。因此,布劳德说:“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已经谴责康德是自然主义,但是,我看不出这种谴责有什么道理。”[5]
那么,摩尔为什么会将不属于自然主义的谬误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也归结到自然主义的谬误之中呢?
摩尔的论证是这样的。任何形而上学的理论都认为有些事物虽然与自然的事物具有不一样的性质,但是,这些超感觉的实在必定是实存的。而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意味着它们用有关某种(它们认为)确实实存、但并不实存于自然界的东西的术语,即用有关超感觉实在的术语来描述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的特色就是好作这样的断言:某种确实实存、但并非自然事物的东西,即某种具有超感觉实在之某个特征的东西必定是完全善的”[1]146。这样一来,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看起来与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有了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先确认某物存在,然后用这一存在的事物来定义善。而这个就是摩尔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我们能够从任何断言‘实在具有这种性质’的命题,推导或证实任何断言‘这个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的命题,就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1]147。摩尔的这一论证,其渊源来自于休谟。休谟同样将从上帝存在中推出“应当”看作是一种错误。但是,摩尔这一断言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两种以实存的性质定义善的方式,仅仅在形式上是相象的。实质上,它们具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自然物的存在与上帝存在看起来都是描述某一对象存在,但是,自然物与上帝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讲到。从事实性与规范性的角度来讲,说某一自然物存在是描述一事实,这一事实与价值、自由等座落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事物无涉。而说上帝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如果我们能将它们存在称为一个事实的话,这一事实也是与自然物存在的事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事实本身是规范性的,因为它们本来就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
因此,摩尔所谓的任何从“实在具有这种性质”中推导出或证实“这个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就是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是站不住脚的。也许摩尔所说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的错误正如有人所说的其实是善不可定义的问题。对此,宾克莱也委婉地说:“穆尔(即摩尔)选择‘自然主义的谬误’一词似乎是有点不合适的。”[6]
三、超越自然主义的谬误的两种进路
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使用“自然主义的谬误”这一术语批评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抓住了自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人们逐渐将自然祛魅化,从而将自然和心灵理解为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由此出现了规范性与事实性以及“是”与“应当”之间的鸿沟的新动向,强调在道德哲学中不能混淆规范性与事实性。摩尔的这一思想,反对将人混同于没有自发性和意向性的自然物,捍卫了人的自主性与自由。而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不仅在伦理学领域存在着自然主义的谬误,而且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的谬误。例如,洛克将认识等同于外在世界作用于人的心灵的过程,这样一来,他也就混淆了“我们心灵运作的机械描述和知识主张的‘基础’”[3]140。需要予以证明的知识在洛克那里被当成了外物作用于心灵的自然过程,把合法性还原为了来源。
在自然和心灵之间划界虽然有必要,也有意义。但是,如果自然和人的心灵与价值领域之间是分离的,那么必然也会带来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们将人的身体看作是自然的,而心灵等与规范性、价值相关的领域与之分离时,就益发显得严重了。我们将看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自身被分裂成两个互不相干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部分。在现代祛魅化的自然观下,“假定感觉是自然的能力,我一直在讨论的这样的自然主义将独特的自发性与主体对感觉的享有分开。同样,假定移动手指的力量是自然的,那么独特的自发性与手指的移动也是分离的”[2]89。也就是说,在近代自然观的视野下,身体的移动、活动与人的自发性是隔绝的、分离的。为了与人的自然的身体活动相区别,人们在内部构想出一个空间来安置意向、意志。人也就被割裂成了两个不同性质并遵循不同原则的领域。
这一分裂的人的图景在伦理学上带来的问题是明显的。就像摩尔所坚持的那样,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人及人的身体没有关系。我们思考和谈论善与正义就如同讨论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思考时我们在一个空间中,思考完后我们回到自然的世界,按照我们身体的召唤行事。这一割裂还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善良意志能否促使我们行动?这一问题在康德那里显得尤其突出。虽然,康德认为自由意志就是人们行动的理由,而且还构造出一个没有丝毫“自然”的情感味道的情感——尊重——来帮助推动人行动,但是,康德,到最后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要想实现惟有理性才去规定受感性刺激的理性存在者应当做的事情,当然还需要理性的一种能力,来引起对履行义务的一种愉快或者满意的情感,因而需要理性的一种因果性来依照理性的原则规定感性。但是,要看出一个本身不包含任何感性成分的纯然思想如何产生一种愉快或者不快的感觉,亦即先天地使之可以理解,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因果性,对于它,和对于所有的因果性一样,我们根本不能先天地规定任何东西,而是为此必须仅仅请教经验。但是,既然经验只能提供两个经验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这里纯粹理性应当仅凭理念(理念根本不为经验提供任何对象)而是一个当然存在于经验之中的结果的原因,所以,作为法则的准则的普遍性,从而道德如何以及为什么使我们感兴趣,其说明对于我们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7]468-469。纯粹理念世界里的意志自律一旦落入尘世,将如何自处呢?对于不包含任何情感因素的理性如何能促使人——整体的人——按照理性制定的法则行事这一问题,康德始终无法完满地加以解决,最终他不得不承认:“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无须其他无论取自别的什么地方的动机,单凭自己就是实践的?也就是说,单是其一切准则作为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原则(这当然会是一种纯粹实践理性的形式),如何能够无须意志的一切让人们可以事先有某种兴趣的质料(对象),单凭自身就提供一种动机,并且造成一种会被称为纯粹道德上的兴趣?或者换句话说,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一切人类理性都没有能力对此作出说明,试图对此作出说明的一切辛苦和劳作都是白费力气。”[7]470人被割裂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以后,道德不仅被看作是与人的欲望、情感等自然性质无关的,往往还会被当作是欲望与情感的对立面。道德也就是排斥、压制人的欲望与情感。基督教将人的欲望等同于恶,康德一再说明道德必须出自义务,而不能出自人的偏好。中国历史上的宋明理学则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8]这种倾向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绝非罕见。虽然基督教和中国传统伦理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与我们所讨论的自然主义的谬误不同,但是,它们的这一倾向也暗示了人的欲望、情感与道德是对立的。
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觉无概念则盲。没有了经验的内容,思想就空洞无物,只剩下形式。因此,在认识论中人们借助“所与”(given)这一概念来赋予思想以内容,并给予知识一个基础。在伦理学中,人们也试图超越规范与事实的截然两分,试图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将两者沟通起来。
麦金泰尔的方法是提出功能性概念。麦金泰尔将道德训诫与人性事实之间的联系的割裂看作是论证道德合理性的启蒙筹划的失败。“尽管我们所提到的所有这些思想家都试图在肯定性的论证中将道德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在其否定性论证中又都走向了这样一种主张的愈来愈无限制的翻版,即,没有任何有效论证能够从全然事实性的前提推出任何道德的或评价性的结论。这一原则一旦被接受,就成了他们全部筹划的墓志铭。”[9]71麦金泰尔认为不能从事实性前提推出任何道德结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从“他是个大副”中可以有效推出“他应该做大副应该做的事情。”麦金泰尔在这里主要诉诸的是功能性概念这一特殊的概念。功能性的概念是那种包含了目的在内的概念。“‘表’和‘农夫’概念具有特殊的性质。这样的概念属于功能型概念,这就是说,我们是基于表或农夫被期望实现的特有目的或功能来界定‘表’和‘农夫’的。可见,我们既不能完全独立于好表的概念来界定表的概念,也不能完全独立于好农夫的概念来界定农夫的概念。所以,衡量某物是不是表的标准与衡量某块表是不是好表的标准不可能相互独立”[9]73-74。麦金泰尔实际上是在说,在这些功能性概念里,事实与规范不是分离而是纠结在一起的。表是计时的工具,表的概念里包含着走时准确的表是好表的含义。同样的,人性的概念中事实与规范也是纠结在一起的。“偶然所是的人”与“实现其本质而可能所是的人”之间既不能等同,又不是分离的。“实现其本质而可能所是的人”蕴涵在“偶然所是的人”之中,“实现其本质而可能所是的人”是“偶然所是的人”的目的。人性中所蕴涵的理想即构成了道德的维度。“实现其本质而可能所是的人”是一种理想的人,它显然不能等同于作为一个事实的人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韦伯的理想类型。从“偶然所是的人”到“实现其本质而可能所是的人”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人有意识、有选择的结果。在好的行动中,人们逐渐实现其本质,成为可能所是的人。
麦克道尔在赞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德性论传统上,与麦金泰尔站在同一立场。但是,他却不赞成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他认为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以现代人理解自然的方式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2]79-80。麦克道尔一方面反对彻头彻尾的自然主义,一方面也反对膨胀的柏拉图主义。他试图在区分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前提下,勾连被塞拉斯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逻辑空间。麦克道尔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反对近代的自然观。“现代科学革命带来的是规律领域的清晰观念,我们可以拒绝将它等同于关于自然的清晰看法。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空间,既坚持自发性与规律领域相比是独特的,又不会陷入膨胀的柏拉图主义的超自然主义”[2]78。麦克道尔认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听命于自然规律,而是由我们的自发性塑造的。“自发性的运用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是作为动物的我们实现我们自身的方式。也就是说,自发性的运用属于作为动物的我们实现自身的方式。这样我们就不必将我们自己看作是分裂的:一只脚站在动物王国,另一个分离的神秘部分卷入理由联系的超自然的世界”[2]78。这样一来,自发性就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麦克道尔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是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他说:“我坚持认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道德的理性要求是自主的,我们不必被迫从外在的伦理思考方式获得其合法性。但是这一自主性并非与膨胀的柏拉图主义那样将道德要求与人的特殊性分开。它们本质上是在人性之中的。我们不能将它们(道德要求)理解为祛魅的自然这一意义上的人的自然(人性),因为祛魅的自然不包括理由的空间。但是,通过伦理教养——它将合适的方式渗透进生活之中——人类可以进入理由的空间。作为结果的思想与行动的习惯就是第二自然。”[2]84麦克道尔的这一方式是利用第二自然这一概念对自然进行部分的附魅。通过教养,人的自然被引入自由的空间。概而言之,麦克道尔认为通过人的自发性的运用,通过教养,人的自然被塑造成了第二自然。第二自然这一空间,既属于自然的逻辑空间又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事实与规范,“是”与“应当”纠结在一起。
麦克道尔与麦金泰尔的不同,似乎在于有没有辟出第二自然这一空间之差异。麦金泰尔的人性由于没有第二自然,因此,他在麦克道尔看来依然是从人性(即人的自然)中推出了道德要求。但是麦克道尔似乎也没有说清楚,由教养所塑造的第二自然如何与形形色色将道德要求看作是社会要求的伦理思想划清界限。而道德教养也似乎先得有一个什么是正确的教养方式的问题,这又牵涉到如何界定善以及正当的问题。麦金泰尔的方式中似乎也包含有通过道德的作用使“偶然所是的人”成为“实现其本质可能所是的人”的含义,也许麦克道尔的第二自然与麦金泰尔的德性有着相同的含义。
[1]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 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d[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M].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4]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09-510.
[5]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M].田永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8.
[6]宾克莱.二十世纪伦理学[M].孙 彤,孙南桦,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22.
[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M]//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朱 熹.朱子语类:卷十三[DB/OL].[2011-02-10]http://www. guoxue. com/gxzi/zhuziyulei/zzyl013.htm.
[9]麦金泰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On G.E.Moore's Naturalistic Fallacy
KONG Wen-qing
(School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hanghai 201418,China)
G.E.Moore's naturalistic fallacy means disenchanted nature and mind were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Therefore,good can't be defined in line with its nature.It's mistaken to reduce something normative to empirical facts,which was the so-called naturalistic fallacy.When Moore used the concept of naturalistic fallacy,he made a mistake too.He got metaphysical ethnics mixed up with natural ethnics.To overcome the division between nature and mind,Alasdair Mac Intyre and John McDowell put forward a solution severally.
nature;naturalistic fallacy;fact;normative;second nature
B516.59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20
2011-04-15
孔文清(1970-),男,湖北省浠水县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思想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资助(12YS133)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