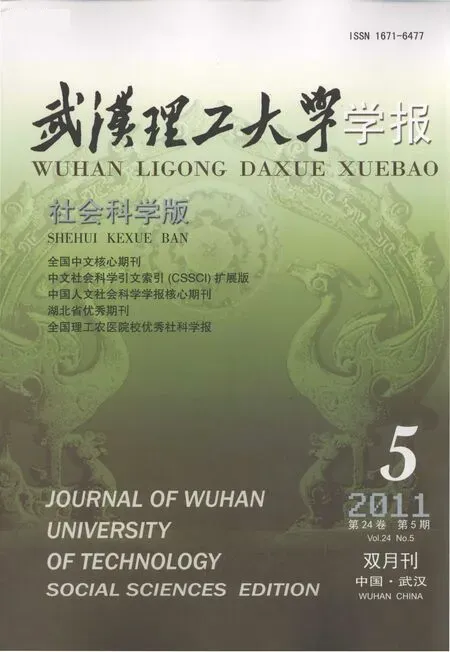“客观性”与科学本体论
杜 杰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430063)
“客观性”与科学本体论
杜 杰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430063)
“客观性”是科学知识的终极诉求,科学事实、科学测量以及科学真理的确立都要寻求一种客观性作为基础和支撑。而所谓客观性只是思维的建构,是一个本体论逻辑预设。科学本体论阐释了科学知识内在具有着建构性和规范性,科学构造了一种认知模式,也构造了一种信仰模式。
科学;客观性;本体论;预设
科学不需要本体论吗?或者说,科学没有本体论吗?在本文看来,科学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推动着现实的科学思维和科学观念的深化和发展。也可以说,科学知识的确立必然有一个本体论的逻辑预设,“客观性”就是科学的本体论预设。
一、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诉求
本体论的要点,是区分开感性的东西和思想,并用思想的东西——范畴——来解释世界。因此,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超验的逻辑思辨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说:“‘本体’可有二义:(甲)凡属于最低层次而无须再以别的事物来为之说明的,(乙)那些既然成为一个‘这个’也就可以分离而独立的。”[1]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十个范畴:本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个范畴不是平列的,其中“本体”为一类,其他九个范畴为一类,和“本体”相对立,亚里士多德有时又把它们统称为“属性”[2]。本体是其他范畴(属性)存在的根据和基础,而其他范畴都要依赖于本体才能存在。由于本体存在于现象世界之外,其原理就不是从经验中概括得出的,只能靠概念本身的逻辑推论。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明确提到:由理念表示的知识是神所具有的知识,是最精确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与关于我们所在的世界里的事物的知识是不同的[3]。可以说,自古希腊哲学始,对于世界的认识,就有“本体”与“现象”的二分。本体论哲学认为,现象并不具有客观本质,只有本体才是客观实体;但本体是超验存在,是无法被感性经验和实证的。“客观性”即是实体(本体)的本性、本质,或者说就是实体本身,因此,只能靠概念本身的逻辑推论。巴门尼德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思辨命题确认了思想的对象的实在性和客观性,确认了超经验的本体属性(客观性)的存在[3]。康德则将“自在之物”(本体)划归不可知的范畴,同时强调“理性为自然立法”,作为思想范畴的本体(客观性)同样获得了确认。简而言之,在经典的哲学理论中,客观性诉求都表现为一种思辨的本体论;或者说,本体论的意义就是确立起了“客观实在性”或“客观真理”这一概念或观念。黑格尔曾概括性地写道:“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作源泉,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或者把所有这些规律和现象,依照着表面上似乎相反的路线,引回到那唯一的源泉,但为的是根据它来把握它们,这就是说,认识它们是从它派生出来的。”[4]对现象的真理性认识必然要回归到实体(本体)本身,在逻辑上,就是回到本体论。
落实到科学层面,对客观性的诉求就是科学思维背后的本体论逻辑预设。这首先表现在关于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诉求上。
科学的经典形态是实验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科学事实”的理论解释模型。科学事实是指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实。它是形成新概念、新理论的基础,不论概念和理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形成的,一定的事实基础总不可少。从内涵上讲,科学事实是指人们通过感官获得的以感觉、知觉、直觉、表象形式描述出来的经验知识;从外延上说,它则主要分为观察事实与实验事实。在科学认识论的意义上说,事实作为某种特殊的经验陈述或判断,其中描述着被认识的事件和现象,所以通常称为经验事实、实验事实,科学理论中将其标明为“事实2”,即科学事实。而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即客观存在的现象、事件、事物本身则标明为“事实1”,即客观事实。事实的本质属性就在于其具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实在性;科学认识应当以客观存在的现象或事件为基础,反映和揭示它们自身的内在联系及规律。因而,科学理论中,在科学事实的概念之外,还引入了客观事实的概念。从其中的关系上看,科学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两者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反映过程的复杂性,两者往往并不能直接一致,不能简单地把经验事实与客观事实等同起来。
在科学活动中,科学事实的确定要求观察和实验结果可以用某种标准的方法进行重演,这是科学研究中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实验或观察中发现的情况或事件能够被多个观察者重复检验,就被认为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客观性。如果一个事实根本无法复核并重现,那就无法成为科学事实。从操作的实质意义和基本原则上说,强调科学事实的可重复性,就是在追求客观性;换言之,科学的可检验性的真谛就是寻求落实客观性。也可以说,离开客观性,科学事实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所以,任何一种科学事实都必然要寻求某种“客观性”,而客观事实本身则是非经验性的,它只是思维的建构和预设。
在科学哲学视域中,一方面,科学是一种经验论,科学认识的对象已非纯粹的客体,而是涵括了由认识主体参与其中的人的实践;另一方面,现代哲学同样无法排除一个超越于我们操作,包括测量以及语言表述等过程的“本体”世界的逻辑存在。这样,科学事实实际上是“客观性”与“解释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客观性表征着客观的因素、客体的因素,显示着实体世界的超越性;解释性意味着科学事实的意义与指称对于操作以及概念框架的依赖性。从这一视界看,“观察渗透理论”这一科学历史主义的基本命题无疑要比培根以来的归纳主义者所倡导的独立于理论之外的纯粹的观察更具深度和合理性。这首先是因为观察不仅是接收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加工信息的过程;其次还因为观察陈述是用科学语言表述出来的,而科学语言总与特定的科学理论联系着。汉森提出这一命题,用于表达“对X的观察是由关于X的先行知识构成的”的思想;波普尔、库恩等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也都否认有纯粹的中性观察存在,明确支持了“观察渗透理论”的基本科学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同意当代建构主义者所坚持的“科学是弱决定的”纲领。在他们看来,经验世界或自然界的作用在实验室和事实证据方面实在太微弱了,科学家有足够的自由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科学知识。这一纲领在科学知识方面就表现为对科学事实“客观性”的否定,随意夸大了科学事实的可“解释性”,从根本上模糊了科学的标准。因之,坚持科学的科学性,首先就是坚持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具体体现为科学事实的可重复性,这可以说是科学的第一原则。科学事实的客观性诉求也在表明,科学事实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而且就是在事实世界的封闭与开放的运动中展开其有序的层次的。这一点在科学的发展历史中得到了恰当的印证。
二、科学测量的客观性诉求
在主流的科学理论中,科学就是对经验或经验现象的描写和记录,知识只有靠切实的观察和测量才能探求和发现。显然,从科学活动本身及其结果看,量的观察是很重要的。科学实验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实验者(主体)、实验对象(客体)和测量系统。量的观察就是观测或测量,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定量描述。需要强调的是,科学测量总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进行和完成的,其间有一个信息“编码”过程,测量的实质是实验主体运用特定的测量手段对客体事物即认识对象的某些性质做定量的比较性的描述研究。也可以说,测量结果中所得到的数字,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量的反映(认识),并不是客体的直观映象。这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实验者从测量系统中获得的信息是否表征着客体的真实状况?它所测定的是客观存在的量吗?科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并引申出多种理论,其核心内容即是阐释测量的客观性问题。
经典的测量理论认为,测量是某种类型的量与其单位量间的数值关系的发现和确定。就在经验的范围内,测量、数字、量与量间的关系被赋予实在的意义。这样就把测量看作是对客观存在的量及其关系的测定,并由此给数字、量、测量陈述以客观的意义解释。操作论则与经典论相反,强调测量的约定性、主观性。在操作论者看来,特定的操作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就是测量,测量本身只与完成了的操作有关而与独立于个人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无关,也和量的客观存在无关。与前二者不同,测量的表征论认为,测量只不过是数字与非数字的存在(物体或量)之间的关联,是将数字指派给被测存在(物体或量)。如测量物体时,我们就在物体的长度与正实数之间确立了对应关系。它要求测量按照某种规则为对象的特定性质给出数字,并且力求在经验关系结构和数字关系结构之间呈现“同构”。
无论哪一种理论都表明,科学事实以测量语言为意义框架,典型的实验就是产生一个或一套测量。解释性是科学测量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形式,从实验中获得的是一些由数据、曲线、照片等等表达的意义,在实验报告或者论文中这些有意义的“量”和“形状”往往又表现为抽象的命题。测量语言作为实验的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它一方面使人们的观察测量及其结果处于一种有序化的结构中,并就测量结果(如“长度”、“重量”、“温度”、“力”、“时间”等物理量)无歧义地进行交流,另一方面测量语言限定着实验的相关性。任何具体实验都是对可观测物的某些而且也只是某些特征的一种抽象,不同的测量则选择不同类的“值”作为它的特征参数。如果不了解这些数据所依据的概念及概念框架,人们就根本无法给它赋予任何意义。这里的要害问题在于,科学实验者在寻求一种共同的测量语言来描述观察对象并进行相互交流,他们都要寻求语言的确定性:一方面是(主体)测量语言与(客体)观察对象对应的确定性;另一方面是主体之间使用语言交流的确定性。显然,没有这种确定性,科学测量本身即无从成立也无从解释。那么,这种确定性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确定性就是客观性的体现,它诉求的就是客观性——这也就是科学测量的客观性诉求的命题含义。要之,科学测量是一种解释,而客观性乃是解释性得以实现的逻辑基础和共识原则。所以说,客观性诉求乃是科学测量的内在秉性。自然,作为本体论范畴,客观性只是被诉求的思想对象或观念对象,正因为是被诉求的思想对象或观念对象,客观性也才成为科学知识背后的本体论逻辑预设。
三、科学真理的客观性诉求
考察科学真理观近两个世纪的变化,可以看出一条明显的轨迹,即从确证到确认再到约定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转化,观念符合事实转换成理论被实验或经验检验,及至理论被科学共同体所规范(约定)。这种转换的深层逻辑已经有了多层面的讨论和说明,本文认为这种转换正是与科学真理的客观性诉求相印证的。换言之,确证—确认—约定主义—相对主义的科学真理观的转换实质是对于客观性观念的认识转化,即从独断论的客观性观念到相对论的客观性观念的转化。
在传统实在论者那里,真理被解释为与实在的符合,真理与客观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实在论者看来,科学具有获得真理和客观性的有效方法,并且是能够提供真理和体现客观性的唯一科学,它应该成为文化其余部分或其他学科效法的榜样,其他学科都必须比照科学才有可能获得被现代文化所认可的认识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实在论者实际持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确证真理观。确认的真理观则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深刻性内涵有了新的理解,所谓绝对的深刻和绝对的确实,在实际科学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于是,逼真性和确认性就成为了表达真理性内涵的理论概念。对理论的确认,不过是理性根据实验结果对理论的暂时接受,而理性终究会越过这个阶段,把曾经确认的理论否定。从科学理论发展的实际看,把逼真评价和确认评价联系起来,反映了一种更符合科学认识实际的深层次的真理观念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独断论的真理观。
在现代科学哲学视域中,真理性只不过是一种“人工”的文化境域或话语系统。库恩的“范式”理论指出,理论评价实质上是科学共同体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和范式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标准就是一切科学理论拥用的五个基本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评价一切科学理论真伪好坏的标准化和支持度,亦即真理性程度。彭加勒的“约定主义”也表述了相同的关于科学的真理性的观念:科学定律被认为是真的并不取决于诉诸经验这一事实,只不过反映出科学家不言而喻地决定把这条定律作为规定科学概念意义的约定来使用。约定主义实质上乃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规范原则。
后现代哲学的相对主义真理观则进一步把真理性与客观性相脱离,仅仅把科学知识和真理看作那种适合于我们去相信的东西,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后哲学文化就是承认我们无法超越我们的共同体而得到一个客观性的中立立场,承认我们都只是“种族中心论者”。罗蒂称:“成为种族中心论者,就是把人类区分为两大类,我们只须对其中一类人证明自己的信念正当即可。这一类(即我们自己的本族)包括那些持有足够多的共同信念以便进行有益的对话的人。在此意义上每个人在进行实际辩论时都是种族中心论者,不管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产生了多少有关客观性的实在主义修辞学。”[5]人类即使能够超越出个人的主观性,但也不可能超越出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局部文化准则”以至整个人类的主观性而处在一个完全中立的客观的基础之上。劳丹认为,追求真理虽然是科学的主要任务,但这一任务并不构成科学的本质,在科学活动中也不存在保证科学获得真理的永远有效的方法。他指出:“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试图证明科学是一种追求真理的事业,但这些努力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失败,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像科学这样一种体系,连同它手中掌握的方法,能够保证达到‘真理’,无论是一时达到真理还是永久达到真理。”[6]费耶阿本德则在人类文化学的框架中考察了客观性,指出客观性是一种历史传统;对人类理性而言,不可能找到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知识的终极基础。因此,我们只能在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中看待世界,超出框架谈论客观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关于真理性问题,费耶阿本德甚至宣称:“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境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7]
科学真理观念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了科学知识背后有一个本体论预设,从而牵引着科学真理观的转化。没有科学本体论就没有科学观念进化的逻辑基础和共识原则。现代科学哲学将真理与客观性相脱离并没有否定科学本体论,而恰恰是从科学本体论视角来申论的新真理观,其阐释了科学知识内在的建构性和规范性,从而推进了对于科学自身的新认识。如此看来,科学构造了一种认知模式,也构造了一种信仰模式。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5.
[2]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5.
[3]Plato.Parmenides[M].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Samuel Scolnicov.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 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4-25.
[5]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418.
[6]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119.
[7]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兰 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6.
Objectivity and Scientific Ontology
DU Ji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Objectivity”is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cientific fact,scientific measurement and the scientific truth to seek a kind of objectivity as foundation and support.The so called“objective”is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ing,as well as a logic presupposition of ontology.The science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xplains its building and normative.Science has constructed not only a cognitive model,but also a belief model
science;objectivity;ontology;presupposition
N0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1.05.018
2011-04-10
杜 杰(1962-),男,河南省信阳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及科技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