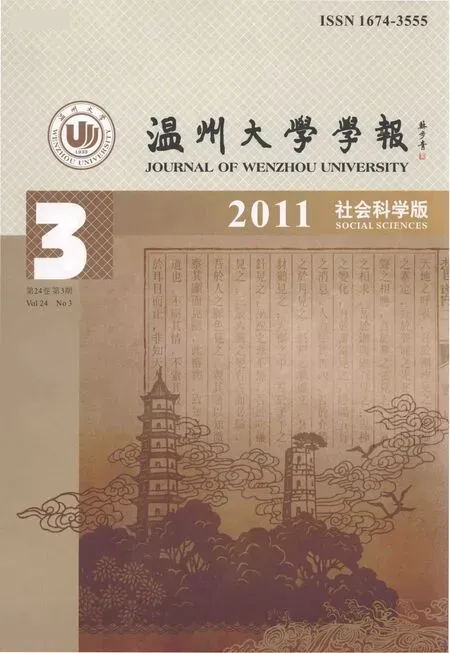动物福利与建设慈善社会—— 从刘绍宽论西人禁止国际禽羽贸易谈起
孙邦金
(温州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部,浙江温州 325035)
动物福利与建设慈善社会
—— 从刘绍宽论西人禁止国际禽羽贸易谈起
孙邦金
(温州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部,浙江温州 325035)
晚清时期,西方人士曾经在中国设立动物保护组织,并敦促中国政府禁绝珍稀禽鸟羽毛的出口贸易。近代温州著名学者刘绍宽,在其日记中记述这一事件时却将西方人此举片面理解为以动物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多年以后,刘绍宽才肯定了西方人在动物保护方面的贡献。结合同一时期宋恕的“兼爱异类”的动物保护思想,则可以管窥近代温州乃至整个中国在动物福利方面的进步与缺失。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破除人道主义思想中偏狭的人类中心主义成见,建设慈善温州、生态温州乃至建设和谐中国,皆不无借鉴意义。
动物福利;慈善社会;刘绍宽;宋恕;禽羽贸易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要想建设一个慈善社会,人们还应该给予动物界以适当的关怀,充分照顾其福利境遇。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存需要,还直接关系到人类由“仁民”而“爱物”的道德责任。可以说,反对非法猎杀、贩卖和消费以及肆意残害、虐待和遗弃动物之行为,切实改善动物福利水平应该是建设慈善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亦当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不过,在强调人的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人本主义大背景之下,动物福利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未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从晚清温州学人刘绍宽(1867 –1942)、宋恕(1862–1910)等人的动物福利思想谈起,进而管窥近代温州乃至整个中国在动物福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尚需弥补的缺失之处,为破除人道主义思想中偏狭的人类中心主义成见,建设一个慈善温州、生态温州乃至一个福利完善、环境友好的和谐中国提供建议。
一、刘绍宽对于西人设会保护禽鸟的态度
刘绍宽,浙江平阳人,字次饶,号厚庄,近代浙南著名教育家、文史学者。除了多种传世著作之外,他还留有1888年2月–1942年3月的日记手稿2 043大页(分订为40册,今藏温州图书馆;平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藏有由该单位誊印的《厚庄日记选编》10卷本),成为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温州的重要史料。在他的日记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十五日有一段有趣的记载[1]:
阴。西人设会,保护禽鸟。盖以华人猎取五色珍禽,取其羽毛,运售欧洲为贵妇冠上之饰,海关册籍每季出口多至数十万或数百万金。因纠集会中同志,禀请驻京钦使,照会总署尽力玉成,行将示禁鸟羽出洋矣。按西人通商,于进口出口之货物,必通盘筹算,唯此鸟羽一宗,实为彼国漏卮,故特为严禁,可见西人商务经营严密如此。若云,则饰辞耳。不然,彼舱坚炮利,日新月盛,生存竞争之说日腾于口,于人类异种且不恤,复何爱于禽鸟哉?
刘氏在这段日记中说了三个问题。一是记载了当时的一个历史事件,西人成立了专门保护野生禽鸟的动物福利组织,以“恐伤造物之和,且恐禽类灭绝”——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两大理由,纠集会中同志力促中国政府及海关禁止国际间禽羽贸易。二是解释了动物福利组织为何要敦促政府禁止禽羽贸易的真实原因。刘绍宽认为:“惟此鸟羽一项,实为彼国漏卮,故特为严禁。”这就是说上述两大理由仅是“饰辞”,实质是西方国家为了减少禽羽贸易所造成的贸易逆差而故意设置的一个贸易壁垒而已。三是还解释了为何西方国家并没有爱护禽鸟的真实意愿。刘氏认为,西方进化论奉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人类生存竞争学说,对于不同种族和国家的人们尚且不能予以平等尊重与爱护,遑论爱护禽鸟?正所谓“于人类异种且不恤,复何爱于禽鸟哉?”刘氏所表现出来的对西方近似本能的抵触与不信任情绪,在当时中国人之中具有普遍性、代表性。晚清中国不断遭受外国列强欺凌,作为弱者一方的中国人从骨子里拒斥外国人,其过分敏感的心理和举止失当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西方人的言行,如果一概简单地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匪夷所思”等心理积习衡量而不加以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逢西必反、自怜自艾的困境。刘绍宽对于西方人要求禁止国际禽羽贸易这一举动的思想实质存在很大的误解,就是一个显例。
二、晚清中国禽羽贸易状况与西方动物福利思想的初传
刘绍宽对西方人禁止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之国际贸易的良善意愿的理解有着明显的偏差。
首先,清末时期,由于西方人(尤其是女性)爱好以珍稀禽鸟的羽毛用作发饰或衣饰,导致了许多珍稀禽鸟濒临灭绝,这确实是一个事实。清末著名学者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论及日本人爱好折扇时提到:“近日又喜聚羽为扇,鹊翅、鹭羽、雀翠、雕翎,长或二尺,是以彩绳系以明珠,光彩射人。西国妇女喜购之,又遍传于泰西矣。”[2]这表明,以鹊、鹭和雕等珍禽羽翼为材质的羽扇曾经在近代日本风行一时,并且在“遍传于泰西”之后,西方妇女亦以拥有一把羽扇和用禽羽装饰为荣耀。当时禽羽及羽扇等物品显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种常规货物,而晚清中国正是此一贸易的出口大国,当时的海关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据 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附属关税税则》记载,当时中国口岸课税的进出口贸易物品中曾专列有“缨皮牙角羽毛类”,并明确标明:孔雀毛每值百两抽税5海关两,全翠毛每百副课税2钱5分,毛税率大约5%。在同一时期,羽扇也是一个较为大宗的出口产品,以每百柄7钱5分征收关税[3]。其实,不独西方人爱好禽羽作装饰,中国人亦如此,而且很可能是这一消费时尚的始作俑者。早在宋代,用一种蓝翠鸟羽毛作为头饰和衣饰就已经风靡一时,有宋一代因此限制或禁止捕杀野生动物的法令不绝于书[4]。这种风气后来不仅没有禁绝,而且还极有可能随着国际贸易的兴盛远传到日本和欧洲。中国同时作为禽羽消费大国,其出口量可能远非国内消费量可比。
其次,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组织保护禽鸟协会,敦促禁止禽羽贸易的真实动机,并非如刘绍宽所说的那样,以动物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事实上恰恰相反。西方人提请禁绝禽羽贸易的两大理由——“恐伤造物之和,且恐禽类灭绝”,亦并非饰辞虚谈。在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之后,予生命以平等尊重和关爱的人道主义开始广为世人所接受,并且出现了从关注人的生命向关注动物的生命扩展的趋势。早在 1824年,英国人在伦敦就创立了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动物福利组织“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至今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与此同时,欧美各国相继制定了保护动物权益的动物福利法案,开始关注动物的福利状况,并对野生动物贸易进行管制。动物保护运动发展至今,业已成为全球化的浪潮。
晚清时期,在中国的西方人谈论动物保护最有力的当数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花之安(Ernest Faber,1839–1899)。在其影响甚广的《自西徂东》一书中,他曾专门比较了中西“仁及禽兽”的动物福利思想,批评了当时中国人普遍把野生动物“借作求财之具”的行为。在谈及为何要善待禽兽时,文章从道德情感上推论:“禽兽虽与我异形,而亦有知觉,亦识痛痒,皆宜爱惜,不可过于伤残,此孟子所以有仁民爱物之遗训也。”[5]36当然,花氏在书中并没有主张一律禁止捕杀利用动物,而是采取了“用之有节,取之有时,乃无伤于残酷”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务实立场,既反对“人物不分”的“失之过愚”的行为,也反对肆意虐待禽兽的“失之过虐”的行为。相对而言,他认为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设立“禁戕害牲畜之会”(即“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仁及禽兽,无微不及”[5]38-39的行为,是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借鉴的。应该说,当时西方人设立协会要求禁止禽羽贸易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而是带有一种“己欲达而达人”式的向中国传播西方先进动物福利思想的良善意愿。
大约四十年后(1940年),刘绍宽本人也意识到西人保护动物的真诚动机,因此对上述写于1899年的日记写了以下按语:“好生恶杀,人有同心,西人托辞请禁,亦可见天良之未泯。”[1]虽然刘氏对于洋人还是没有多少好感,仍然固执地认为西人禁止禽羽贸易乃是“托辞请禁”,但是“天良之未泯”的理解显然已趋积极正面。刘氏在近代中国外患频仍、民生穷蹙和民命倒悬的时候,犹能够予西洋人的动物保护思想赞一词,实属难能可贵。
三、宋恕“兼爱异类”的动物福利思想
儒家历来讲究博施济众,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长期浸淫于儒家传统中的温州近代学者也不例外。温州早在南宋时期就有东南小邹鲁之称,民众乐善好施翕然成风。晚清以来,秉承永嘉学派经世传统的温州知识群体,热心慈善、关怀民瘼,将“勇于办事、敢于任怨”①参见: 宋恕. 宋恕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下文凡出自该书的的文献都以①xx标出(xx代表页码).572的力行精神和“与我伦者,我爱必之;爱之不已,因而护之”[6]的仁爱精神发挥到极致,使得温州的慈善风气在当时显得卓尔不群。在他们中间,近代学者宋恕“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①51-52的人道主义思想堪称温州人悲天悯人、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最强音。他在《六字课斋卑议》开篇就说:“礼义生于富足,冻馁忘其廉耻,可为寒心者也!”①2直指使人类免于饥寒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而民生凋敝正是晚清中国最大的人道灾难。相比之下,“欧洲诸国,深明斯理,故极力求富,而藏之于民。”①2他通过求富来解决民生问题的人道主义思想呼之欲出。可是在当时国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尚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让人们去关注动物福利无疑是一种奢谈。不过,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清代著名诗人和史家赵翼有诗云:“于物何太忍,于人何过爱?此理不可问,思之动深慨。”[7]就表达了杀生在道德和功利等层面上存在着诸多难以让人释怀之处。对于深具民生关怀意识的宋恕来说,也没有囿于“专爱同类”的狭义人道主义,而是进一步阐发了一套“兼爱异类”的爱生节杀、保护动物的博爱理想,十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宋恕在其《佛教起信篇稿》中说:“广义者,兼爱异类也;狭义者,专爱同类也。”①263-264仁爱作为儒家的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关怀,可以从对象上将其分为狭义的“专爱同类”与广义的“兼爱异类”两个不同层次。其中,“兼爱异类”即“无界之戒杀也”,要求我们不分人类与其他有情之生命的界限,应一视同仁地予以平等关照;而“专爱同类”即“有界之戒杀也”,人类为了维系生命可以利用包括动物在内的异类生命,但是人类应自爱爱人,绝对不能够同类相残。前一层次类似于现代的动物或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后一层次接近于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准。依据这样两个不同的标准,宋恕认为猎杀动物之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正如他所说:“然则业猎非定不仁:无界之猎,广义属不仁,狭义尚属仁;有界之猎,则广亦属仁矣。”①263-264无限制地猎杀动物在广义上虽不符合“兼爱异类”的博爱精神,但尚具有“兼爱同类”的道德正当性。有限制地猎杀动物,既实现了爱人之目的,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动物的生命权利,因而在道德上更具包容性。对宋恕来说,“断一切杀者”——禁止一切生命之杀戮是广义人道主义的终极目标,然而“无界之戒诚非人道之世所能行也”①263。即在现实条件下,完全禁止猎杀动物的目标尚难以实现,人类只能做到“节杀”而无法做到“禁杀”。固然人类还无法做到“兼爱异类”,但这不等于肆意猎杀“异类”。正所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即使做不到“禁杀”,也要力所能及地尊重动物之生命,禁绝不必要的动物杀戮。宋氏为此给出了三个具体的节杀方法——“断太惨之杀也,减多杀为少杀也,杀生且放生也。”①262-263换言之,就是禁止残酷虐待动物,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动物捕杀行为,再加之食素放生。以今观之,这已经基本上囊括了现代动物保护运动中的反虐待的动物福利论和素食主义思想,诚属不易。
既然现阶段尚且无法完全避免猎杀动物之生命,那么人类正当地捕杀、利用动物的标准又在哪里呢?宋恕的回答是:“人道之世戒杀则必立界。何谓立界?害人类者杀,不害人类者不杀。害近善之非人类者杀,不害近善之非人类者不杀是也。”①263这里提到了两个杀与不杀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动物是否有害于人类利益:人类出于自我保存的需要,可以采取必要手段避免动物的伤害,而“不害人类者”则可以不杀。第二个标准是在于动物害不害“近善之非人类”,即对于与人类相近的动物有害与否。第一个标准基于首先要尊重人类生命及其福利的考虑,人类在生存竞争中捕杀动物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即使在今天最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那里,也无法否认为了生存必需而捕杀野生动物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第二个标准由于宋恕不自觉地站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表现出强烈的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道德代理人意味。其实,动物界中“近善之非人类”与“非近善之非人类”的分别,完全是人为强加在动物身上的,人为地干预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现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们大都认为已无此种区分之必要。
宋恕虽然对于当时的动物福利状况抱有悲观态度,但终究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人道必进于天道”,人与动物等有情生命必定能够和谐相处、共生共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即“同类他观”或“狭他观”),从“自观”转向“他观”,站在非人族类和被猎食者(动物)的立场上来看待生命价值(即“异类他观”或“广他观”)。只有这样,“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博爱精神与大同理想才能够实现。如其《佛教起信篇稿》结尾有云:“夫人,吾狭同类也;群动,吾广同类也。张横渠氏曰:‘物,吾与也。’然则吾属何忍不发勇猛愿力以助无量广同类早一日离苦海乎?何忍不发勇猛愿力以助无量广同类早一日离苦海乎?”①269我们可以看到,宋恕的人道主义思想最终是希望从关爱“吾狭同类”——人类自身的爱人层次,进而提升至关爱“吾广同类”——一切有情生命的博爱境界,已经从人类中心主义转换成弱人类中心主义和某种程度的生态中心主义。
四、动物福利与建设慈善社会
今天绝大多数人已经承认:无论国别、种族、性别、年龄、语言、区域和宗教信仰有何不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天然拥有某些基本的权利。可是即使我们达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除了人类之外,仍然把世界上大多数有感知能力的物种排除在外,拒绝给予在我们自身界限之外的非人动物哪怕是有限的道德关怀[8]。这种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鉴于自身的物质利益需求,人们还是简单地以为在人类利益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去保护动物福利是一件荒谬绝伦的想法和无比荒唐的行为。殊不知人类欲壑难填,即便是摆脱了绝对贫困,但似乎从来就未曾满足于哪怕是基本生活条件的实现。人类出于食用、药用、器用、表演、宠玩和装饰等种种目的,一直在滥捕滥杀野生动物。现代野生动物贸易从捕杀、运输、屠宰、加工、交易到终端消费等环节业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环环相扣、牢不可破。据《美国国家地理》报道,仅自2000–2007年间,共有13 356 588只活体动物和30 309 815个动物身体部位自东南亚合法输出[9]。这种合法输出的数量,尚不能与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数量相比。据统计,全世界每年野生动植物贸易额至少达到100亿–200亿美元,其中仅动物走私交易额就高达100亿美元以上,成为仅次于毒品、高于军火的第二大走私行为[10],由此可见野生动物贸易的规模之大。
当下,中国境内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贸易和消费司空见惯、十分猖獗,对驯养动物的需求数量亦不断升高。若对此掠夺性地行为不加以限制,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则虽举天地之大、万类之众,杂然并出,不足以供一强者之并噬,而宇宙将无一物”[11]。其结果无论是对于动物还是我们自己都将是灾难性的。仅就温州和浙江地区来说,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消费数量与日俱增,逐渐成为中国野生动物贸易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终端市场。
另一方面,在对动物施以道德关怀这一终极层面上,肆意残害、虐待和遗弃动物的事件屡屡发生,动物福利事业任重而道远。但凡是看到过“注水牛肉”等残酷恐怖的生产过程的人,看到种种残忍虐待动物行为的人,都应该意识到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法律问题和一个心理健康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
上述种种现状及发展趋势,对于人类提升自身道德境况,保持生态多样性和物种安全性,改善动物福利状况等皆构成了极大的阻碍与威胁,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警惕。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不仅不缺乏从道德高度上关爱动物的思想资源,而且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与动物保护思想源远流长,丰赡多样,堪称世界上最早要求对动植物施以道德关怀,并予以立法保护的国度。宋代学者张载说过一句名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2],堪为中国传统动植物保护思想的最洗炼的表述。如果人类仁爱之心和慈善义举不能够爱人及物,不能够如宋恕所说的那样从“专爱同类”扩展至“兼爱异类”,对于生活于悲惨境遇之有情生命无动于衷,任凭动物种类不断地减少与灭绝,那么,我们人类的道德何以安顿?我们人类的未来何以维系?我们的慈善义举又何其有限?因此,我们在建设慈善社会的同时,不能够忘记我们还背负着动物福利方面的社会责任。
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必须加大生态保育的教育宣传力度,自小开始养成良好的道德认知与消费习惯,从思想上树立动物权利意识与绿色生活理念。其次,加大动物福利的立法规制的行政管理的力度,将保护动物权利规定为公民的法律义务,以禁绝残酷虐待动物,切断非法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贸易的利益链条。再次,促进相关民间志愿者组织的发展,依靠和发动民众的力量,群策群力地推进中国动物福利事业的进步。只要脚踏实地去做,中国当前的动物福利现状必将会大为改观,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慈善社会与和谐中国也一定是可以期待的。在此谨录一百多年前的花之安一段话,以兹共勉[5]39:
推仁慈之心,以广施其惠,将见万物皆得其所,此盖有厚望于当世也。……仁量之大,推而至于及禽兽,始无欠缺者欤!
[1] 苍南县政协文史委. 苍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刘绍宽专辑[R]. 温州: 温州市政协文史委, 2001: 132.
[2] 黄遵宪. 日本国志[C] // 陈铮. 黄遵宪全集: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563.
[3] [日]滨下武志.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M]. 高淑娟, 孙彬,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495-520.
[4] 魏华仙. 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 (2): 53-62.
[5] [德]花之安 自西徂东[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6] 陈黻宸. 伦始[C] // 胡珠生.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575.
[7] 赵翼. 放言九首[C] // 华夫. 赵翼诗编年全集.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602.
[8] [美]彼得·辛格. 动物解放[M]. 孟祥森, 译.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4: 2.
[9] [美]布莱恩·克里斯帝. 亚洲野生动物交易[J]. 国家地理: 中文版: 2010, (1): 2-31.
[10] 高智晟, 马建章. 野生动物贸易与野生动物保护[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4, (1): 85-86.
[11] 陈黻宸. 德育: 上册[C] // 胡珠生. 东瓯三先生集补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334.
[12] 张载. 西铭篇[C] // 张载. 张载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62.
Animal Welfare and Constructing Humanistic Society—— Starting from Liu Shaokuan’s Comment on Westerners’ Prohibition against International Trade of Rare and Precious Birds’ Feather
SUN Bangjin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me Westerners established many animal protection groups to protect animal rights in China, and urged that time’s Chinese government to ban the export trade of rare and precious birds’ feather. Liu Shaokuan, a modern famous scholar in Wenzhou, recorded this historical case in his diary.In the beginning, he misunderstood the protection as certain trade protectionism. Some years later, Liu admitted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Westerners in protecting animal welfare. Combined with another scholar in Whenzhou Song Shu’s thought of “Non-anthropocentrism” in the same period, the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cy of animal welfare protection in modern Wenzhou and even the whole China could be reflected.Reviewing on this historical event could help to break through the one-sided anthropocentrism prejudice of humanitarian thought. And it could also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building of a charitable, ecological society in Wenzhou and of a harmonious China.
Animal Welfare; Humanistic Society; Liu Shaokuan; Song Shu; Trade of Rare and Precious Birds’ Feather
(编辑:朱青海)
B824.5
A
1674-3555(2011)03-000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3.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10-04
孙邦金(1978- ),男,安徽定远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明清思想史、地方文化史
book=12,ebook=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