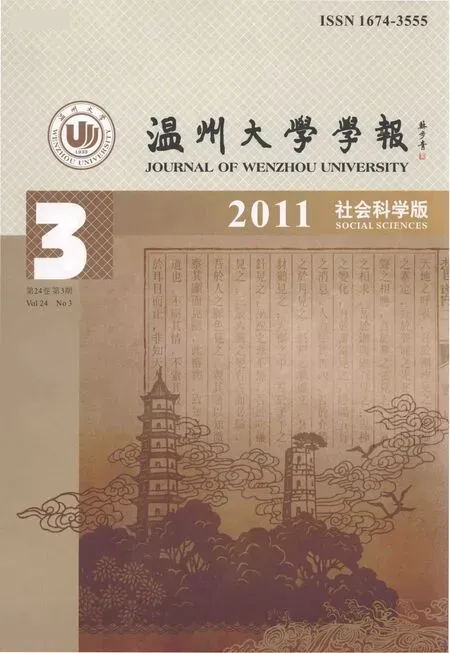试论《战争论》对郁达夫政论时评的影响
郑薏苡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试论《战争论》对郁达夫政论时评的影响
郑薏苡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政论时评是郁达夫后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郁达夫的政论时评中可以看出他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影响。表现在他对抗战的政治与军事、军事策略、民众武装、精神力量和战争与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看法上。
郁达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政论时评
《战争论》①参见: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M].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下文所论该书内容, 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注出.为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所著,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战争论》被誉为军事领域的“圣经”,而克劳塞维茨也享有“西方的兵圣”的美誉。该书自 1832年问世以来,先后被译成英、法、日、俄、汉等多种文字。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1901年该书在日本翻译出版,名为《大战学理》。随后《战争论》由日本传入我国,出现了多种中译本,影响甚大。《战争论》的这种影响也在郁达夫的政论时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政论时评是郁达夫后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1938年12月,郁达夫去了新加坡,目的是“把南洋侨众的文化,和祖国的文化来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②郁达夫. 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C] // 郁风. 郁达夫海外文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532.下文所论郁达夫的政论时评(只注篇名者), 均出于该文集.因此,他主持了《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以及英国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等副刊,写了大量政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报道抗战形势,分析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的消长,传递必胜的信念;第二,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揭露其在文化上推行殖民统治的野心;第三,积极为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进言,批判中国政治的不良,同时,提倡自力更生,呼吁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郁达夫的政论时评对战争的看法切中要害,他的真知灼见,与其受到《战争论》的影响是紧密相关的。
一、政治与军事
1939年,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不断加快,抗战形势日趋严重。郁达夫指出:“使我国之国脉垂危,招致强邻压境之第一原因,原在我国历来官吏之贪污。而其次,则正值当局之度量狭窄,排挤国家有用之人才,亦为我国运中落之另一主因。”(《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抗战在现阶段没有取得绝对胜利的原因,“不在武器的不足,不在士兵的不勇,也不在国际助力的乏,根本问题,总还是在政治的不良。”(《政治与军事》)“我们这一次在过去抗战中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战略不行,统帅无力,士兵少勇等;也不是物质上的失败,如炮火不继,运输不灵,给养不足等;归根结底,却要归罪于政治的不澄清,民众的不训练与不组织,国是国策的不确立这三点。”(《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郁达夫明确指出抗战失利的原因为:政治不良、民众不群、国是不确。这里政治是关键。当时的中国“吏治之坏,几可以说无有甚于今日者,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贪官污吏,到处充斥,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惊人。”①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9册[M]. 北京: [出版者不详], 1979: 315.郁达夫还指出外侮与内政的必然关联:“德名将克劳粹味知的名著《战争论》里,亦曾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一个国家的政治,假如真正是彻底澄清的话,当然,内乱也不会起,外侮也不敢入,战争是决不至于发生的。即使受到了侵略,防御自然有余,准备哪里会得不足?”(《政治与军事》)他还指出“人类在这世上经营努力的结果和理想的实现,必然地须由于政治,而不是由于军事的。人的一生,社会的各处,若只是战争的话,那不能执武器,不能辨黑白的婴孩,就不会长成大人了。从这一点极普通的常识来想,就可以明白人类是决不会为了杀戮与战争而出生,社会也决不只因战争而存在,或可以成立的。”(《日本的议会政治》)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有关政治和战争的论断大致包括三点内涵:第一,政治引起战争,政治是整体,战争是部分,政治性质决定战争性质;第二,政治支配战争,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第三,政治不能违背战争的特性,政治目的并不能任意决定一切,它还需适当的手段。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中,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莫过于这一论断,它充分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属性。郁达夫十分认同这个观点,而这个观点也成为郁达夫对战争各方面认识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当论及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时,郁达夫强调政治重于军事。他认为,“军事并不是人世社会的一切,这也是说军事不过是为达到一个理想,实现一个目的的暂时手段的一种。”(《日本的议会政治》)“所谓政治重于军事的主意,就在这里。在第二期抗战的期间,只教政治能够澄清,则壮丁的补充,游击区的整理,就马上可以就绪。”(《第二期抗战的结果》)而政治重于军事的看法,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无疑是一脉相承的。1938年7月,日军逼临武汉,时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郁达夫暂时避难常德汉寿,14日,他应邀发表演讲《政治与军事》,并期许:“大约不久的将来,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个绝大的变革,把过去的贪污不惩,赏罚不明,虚名是务的种种弊政除去,而实施抗战建国的政治。”(《政治与军事》)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知识分子的郁达夫虽然无法亲自“从戎”,但因为在国民政府中的亲身经历,理论与现实的合拍无疑加深了他对政治腐败与战场崩溃的认识。
二、军事策略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军事行动中的进攻和防御,在他看来,进攻和防御不仅相互作用,相互包含,而且可以相互转化。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斗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唯一手段。战斗由进攻和防御两部分组成,“进攻的目的是驱逐敌人,防御的目的只是据守。但是据守并不是单纯的防守,因而不是忍受,而是在据守中还要进行积极的还击。”同时,“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同防御交错着的。”“打垮敌人是战争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手段,不论在进攻中还是防御中都是如此。”所以,他强调战略上最重要的原则是集中兵力,即“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和“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在强调集中兵力的同时,克劳塞维茨也提醒要根据情况适当地保留一定兵力以备后用。
克劳塞维茨对进攻与防御的看法,及有关“空间”和“时间”的观点,对郁达夫“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面对日本侵略者扬言三个月亡华,企图整体征服中国的进攻形势,郁达夫表示,“为奴为主,只在一念,对付强暴,是不能够用和平的手段的。”他认为要在军事上取得主动,须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的战略。他指出:“在面积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所占的,谁也晓得,只有几个据点,和几条时断时续的游丝似的线。”(《抗战两年来的军事》)“我们的战略,在持久,在消耗敌人的兵种与资源。我们的反攻,不必要一定占领几个城池,只求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而搅乱它的后方,断绝它的交通。所以,围攻一地,并不必要速战速决,这是一点。我们的反攻,是对敌人进行的抵抗,我们的目的,是在设法使敌人消失进攻的能力之后,才一举而收到胜利。”“至于我们的策略呢,是长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积小胜为大胜,以不变应万变,实为我获取最后胜利之两大指针。”(《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关于这一点,若坚持郁达夫只是受到克劳塞维茨影响,或许有点牵强。特别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观点,也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概括,郁达夫对此不会忽视。在这一点上,与其说郁达夫直接受《战争论》的启发,不如说是他在前人基础上的思考或体认的结果。
三、民众武装
基于民众武装会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认识,欧洲当时不少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极力反对民众武装的。而克劳塞维茨则强调民众武装是巨大的战略防御力量,并对民众战争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注意到,自从民众介入战争之后,军队的面貌和作战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单个居民对于战争的影响像一滴水对于大河一样无足轻重,但是全体居民对于战争的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当民众看到自己被置于深渊的边缘时,他们会像溺水的人本能地只抓稻草那样,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自己,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一个国家即使比敌人弱小得多,也不应该不作这种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不能不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但他又指出,民众武装并不是万能的和无法抵抗的,而是要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他指出人民战争发生效果的五个基本条件:战争在本国腹地进行;战争的胜负不仅仅由一次失败决定;战区包括很大的一部分国土;民族的性格有利于实行民众战争;国土上有山脉、森林、沼泽,或耕作地等,地形极其复杂,通行困难。而这些条件无疑和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基本上是相符的。
基于以上条件和认识,郁达夫呼吁发挥民众的重大作用。他指出:“抗战之初,我们因为忙于军事的应付,对于组训民众的一层,没有加以十分的注意。并且又因为小组织的互争民众,致发生摩擦的现象,亦随地都有。但现在到了第二期的阶段,大家就觉悟了;大家都晓得民众实在是比土地、政权更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因素。从前的古公亶父,不堪夷敌的侵凌,率老百姓而来至歧下,奠定了数百年周室统一之基,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在持久抗战的第二期里,这一个组织民众,使军民得联合一气的工作,不得不彻底去做了。”(《第二期抗战的成果》)
郁达夫认为只有动员民众,依靠民众,合理利用民众的力量,抗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胜利是寄托在各沦陷区的永不能使敌寇有开发利用的游击之上,我们的全力,是附着在我广大众多,绝对不妥协的民众之上的。”(《“九一八”九周年》)他指出,“既已澄清政治,巩固团结之后,则抗建之初步基础,可说已经打完,其次便是紧握时机,如何利用我伟大的民众力量的一点了。向敌反攻,是要齐一步骤,同时并进,方能收效的。既获胜利于甲地,对乙地亦不可以放松,而敌前敌后,辽阔漫长的战线之上,只有动员民众,方能制敌之死命。”(《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
四、精神力量
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活动是充满危险的领域,而危险的领域又是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最好舞台。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消灭敌人不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他指出,“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考虑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都根本得不到说明”,“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主要的精神力量包括: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军队的民族精神。此外,还有政府的智慧、作战地区的民心等。
在民族危亡时刻,郁达夫也深刻地认识到精神力量的重要性。面对日本侵略,首先他呼吁,要重振“闻胜勿骄,遇挫勿馁”的精神,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只是一帮政客、军阀的一意孤行,“日本除了军阀以外的人民,是如何地在厌战,如何地在希望战事的早日能结束。这种厌战的心理,怕战事拖长,先天不足的岛倭必至陷入泥潭而遭灭顶的心理,不但是敌国的一般人民有之,就是敌国政客与军阀中间,也未始没有。”(《倭敌已在想绝计了》)相反,我国的民众则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信念日趋坚定。郁达夫在发动国人奋起抗战的同时,既善于揭露敌人营垒内的种种矛盾,又暗含告诫中国政府及盟国不该向日妥协之意,全国人民从政府到民众唯有众志成城,团结抗战,日本才能在内外压力下投降。其大局观念和整体性的思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郁达夫在指出日本民众上下交怨之时,也高度赞扬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1938年9月,他写道:“至于中华民族的忍耐性,坚毅性,与反拨的弹力性呢,完全是由于我们丰富的资源,与悠久的文化所赐予的大宝;到如今抗战已及一年二阅月,而各乡村以及各内地的民众生活,仍旧是丝毫没有影响,除了有飞机不时来残杀妇孺的威胁之外,他们仍在安居乐业,不改他们的常态。所以,外国人也老在说,中国所潜在的国力、民族力富庶,就是抵抗的力量,非但外国人看不到,便是最狡猾细心奸诈的日军阀,也大吃了轻视灭估的亏;并且从这一次抗战的结果看来,恐怕连中国人自己,当抗战开始的时候,也许还不自己觉得的;这潜在的国力、民族力,真是世界上的奇迹。”(《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郁达夫当时正在湖南汉寿躲避日军,然而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告诉他日本是外强中干,而中国民众心中暗藏着持久生命力和爆发力。在郁达夫眼中,中国这只睡狮俨然“已经在张眼睛,振精神,准备怒吼”。在称赞英勇的军队和无畏的士兵时,他写道:“至于我国之军队,则忠勇绝伦,视死如归,久已为世界各国所称颂;我国抗战之所以得维系迄今,愈战愈强者,厥唯此辈无名英雄之是赖。即今后之最后胜利,再造国家,亦唯赖此少年气壮之新中国勇士,能不惜生死为国捐躯耳。”(《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我国的士兵,个个都以驱逐敌寇出境为天职,敌忾心的一致高涨,与夫保国家保民族的信念的例外坚强,是比抗战当初,更增加了十倍。”(《抗战两年来的军事》)其乐观主义精神毋庸言表。
克劳塞维茨指出,进攻者具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优势才能发起进攻。基于此,郁达夫表示,抗战以来日本侵略者最成问题的是人的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枯竭,而“我们的最大的凭借,总之,是在兵种的源源不绝,土地资源的广大无垠,以及抗战到底,精诚团结的这绝对不会摇动的一个大决心。”“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民生活,在这八年中,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以八年以前的诸种状态,来和今天——虽则在敌军的践踏蹂躏之下——全中国的一切情形一比,谁也会觉到这长足的进步,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纪念“九一八”》)所以,郁达夫呼吁广大民众认清敌我形势,坚持团结抗战,自力更生,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他更坚信中国抗战必胜,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五、战争与经济文化
郁达夫在分析敌我形势方面之所以能击中要害,与他受到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克劳塞维茨作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在对战争的整体认识与把握上自然比郁达夫更加深刻与周全,但郁达夫也看到了被克劳塞维茨忽视的因素。
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克劳塞维茨对“政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思想极大地冲击了法国的军事贵族阶层。所以,出身贵族的克劳塞维茨更多地是从民族国家兴起角度来看待“全民皆兵”的重大意义。这里的民族国家更多地是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正是因为贵族身份,克劳塞维茨能一生出入“宫闱之中,军幕之后”。他深知位于政治中心,主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那些人的活动的影响。他深知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可能只是国王与军事贵族间的游戏[1]。这是他军事战争观的重要来源。在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认识到其局限在于:他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指出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克劳塞维茨也因此反对从政治上把民众战争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模糊了民众在不同性质的战争中的意义,把民众武装只看作是用于正规军战争的辅助手段。再者,他没有充分重视战争的经济基础,以及文化对战争的重要影响等。而郁达夫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明确的认识。
首先,郁达夫指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严厉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卑劣的侵略行径。他写道:“敌阀自从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来,三年之中,对我非武装平民,尤其是对我老幼妇孺之奸淫杀戮,已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恶毒之记录。”“敌人的滥炸我不设防城市,及非军事要区,以及彻底破坏我文化机关,与第三国之教会,医院,使领馆等暴行,更为自有国际公法以来之绝无现象。”“诸君将不信人类竟会有如此的行为;而古代史书所记载之野蛮种族,比之现代倭寇,或竟可以称作极度文明。”(《欢迎美国记者团》)可见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深切痛恨。因此,他表示:“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必胜的信念》)
其次,郁达夫强调经济及文化对战争的重要性,“敌人于施武力侵略之先,必以文化侵备与经济侵略为前导”(《缅甸与中国之交谊》)。他指出,决定近代战争胜负的很大成分在于经济。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敌国国内经济崩溃,产业界破产,兵源断绝,因恶性通货膨胀,乱发赤字公债,无理增税之故,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且食粮不足,频年荒旱。”(《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战后日本的一些数据来分析。日本在战争中的财富损失率达36%,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战前水平的8.7%,农业生产指数下降58%,船舶总吨位从战前的630万吨锐减至战败时的153万吨。人口损失268万,失业者达413万人[2]。日本战后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3]。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其付出的经济代价也足以决定其失败的命运。他还指出文化是敌人进攻最隐蔽的一个方面。“敌人除用了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以外,谁也知道,还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甚而至于和平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种种手段。但是兴亚院的工作做得最起劲,一批军部御用的学者文人也顶卖气力得文化进攻或文化侵略,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敌人的文化侵略》)他对比双方文化状况:“敌国的文化,本来就是模仿文化,或可以称作猴子文化,在侵略战争发动之前,各文化人早已就丧失了自由与生气了。”而“我国的文化,则在这两年之中,真有了二十年的进步。第一,文艺界、知识界的合作,普遍地在一般民众心里脑里,唤起了国家民族的意识。第二,知识与文艺,在这抗战期中,从特权阶级的手里,移交给了广大的群众。第三,是个个人想创造文化,个人想对国家、民族尽力,尽他们最善的力。”(《抗战两周年敌我的文化演变》)1938年3月27日,包括郁达夫在内的文艺界97人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发行《抗战文艺》杂志,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俨然成为文艺界抗战的旗帜和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让郁达夫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生动地比喻:“侵略者,譬如是野火,被侵略的文化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流水,水流决不会绝塞,被火烧得沸了,反会得跃出流程,来消灭火种。这一譬喻,可以用之于文化,也可以用之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战争,史绩俱在,这是决不会错的定理。”(《侵略者的剿灭文化》)。
抗战爆发后,中国文人中对抗战、对国家的命运都有自己的态度,或持正面态度,对抗战充满信心,如林语堂认为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日本必定失败[4];或临危转向,对抗战消极悲观,如周作人认为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5],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他自己也最终“下水”出任伪职。郁达夫在民族危亡之时自始至终体现出来的民族大义和精神气节,“匈奴未灭,家于何有,我们这些负有抗战建国重任的男儿,终于是不能在这穷乡僻壤里坐而待亡的。”(《国与家》)虽然克劳塞维茨及其《战争论》有其局限性,但总体来说,郁达夫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可谓鞭辟入里,在这种分析与判断中明显地留下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印记。
[1] 吴潮. 克劳塞维茨学术思想及《战争论》的文化与社会底蕴[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 (6):57-59.
[2] 吴宇廑, 齐世荣. 世界史: 现代史编: 上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119-120.
[3] 孙执中. 荣衰论: 战后日本经济史: 1945–2004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6.
[4] 林语堂. 日本必败论[C] // 林语堂. 且行且歌.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0: 280-300.
[5] 周作人. 弃文就武[C] // 周作人. 怀旧.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251-254.
Study on Influence ofThe Theory on Waron Yu Dafu’s Comment on Current Affairs and Politics
ZHENG Yiyi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Comment on current affairs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Yu Dafu’s later period of literature creation. From his comments, it could be clearly observed that Clausewitz’sThe Theory on Warhad posed great influence on his creation. The influence was contained in his views on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military strategies, folk armies, spiritual power, relations among war,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other fields i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Yu Dafu; Carl Von Clausewitz;The Theory on War; Comment on Current Affairs and Politics
(编辑:刘慧青)
I206.6
A
1674-3555(2011)03-0087-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3.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0-03-21
郑薏苡(1957-),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