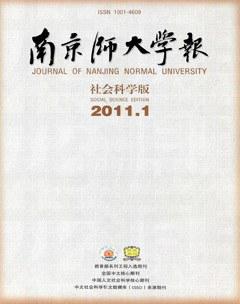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摘要: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对气象灾害及其带来的自然及文化影响的描写,这一题材的写作主要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话语立场和阐释视角,一是将气象灾害置于“人类中心”的视野中作为人的对立面进行阐释,一方面歌颂人类改造自然的激情,另一方面控诉底层生活的苦难。另一种是在“天人合一”的视野中将气象灾害所体现的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活状态结合在一起,对自然的灵性和人文内涵进行“复魅”。
关键词:自然灾害;人类中心;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1)01-0149-06收稿日期:2010-11-10
作者简介:潘盛,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210044
文学反映的不是常态化的平常生活,更多通过矛盾冲突将非常态的、极端的、人的本质的东西加以集中表现。而气象灾害的爆发恰好是一个偶然性的典型事件,更能折射人的心性、情感、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文化的深层意蕴,这也正是文学最大的魅力所在。因此,气象灾害便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之一,而写作者面对气象灾害中出现的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冲突所显示的创作心态和价值取向,也恰恰是这一题材文学作品中值得解读和反思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反映的气象灾害内容作为对象,重点考察小说作品在书写气象灾害及其所带来的自然及文化转变中,所体现的话语立场和阐释视角。
一、有我之境——“人道主义”
话语中的气象灾害书写
1气象灾害与激情颂歌
知青文学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类别,与文革前大量反映“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宏大叙事模式农村题材的小说相比,这类小说更多地反映了“知青”这一群体,在从城市青年到农村“被改造者”的命运转移中,所面对的残酷以及环境和精神肉体的双重痛苦。因此,其基调一改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文学的乐观色彩,展现出被蹉跎了的一代年轻人痛苦的控诉和沉重的思考。
当知识们的“城市青年”身份遭遇到了他们下放的偏远农村,便产生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知青遭遇到了他们生活的种种挫折,农村意识的愚昧、生活权利的被剥夺、人性自由的压抑……在这些挫折中,偏远农村所特有的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成为了给知青带来痛苦的力量之一,甚至是作为城市青年时不会在意的一场风雨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遭遇。这是他们在来到农村前所无法预知的。“大伙把心中的北大荒描绘成了翠绿的原野,乡间的小路,一派田园风光,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多姿,那么情趣盎然。我们一路风尘来到北大荒,迎接我们的是寒风,是飞雪,先一步的梦幻早已飘逝。我们茫然了,女同学躲在宿舍里哭了起来。”生存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心理落差,使自然灾害的出现对知青的情感冲击更为激烈。对于抱着“战天斗地”、“大有作为”信念的知青来说,灾害所带来的恶劣条件自然都成为他们斗争的对象。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便设置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冲突场面,将大自然的暴风雪灾害作为人类社会的象征体,描写了一场善恶斗争的风暴。小说叙述的是一个“知识青年返城闹事”的事件,在农场干部故意拖延时间,造成知青不能在规定时间最后返城的消息泄露后,黑河农场的知青群体中掀起了一场暴乱。而与此同时,一场巨大的暴风雪也即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夜晚来袭。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知青与农场管理者都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如果说这种混乱局面的书写还仅仅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作者对北大荒的一个突出气象现象——暴风雪灾害的集中描写,便将故事的背景扩大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合二为一的悲剧情景中。北大荒特有的暴风雪在来临之前便带来了万物的肃杀和死寂,而在沉寂中知青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引发了武力搏斗,而此时团部的干部间矛盾冲突亦开始尖锐。故事情节一步步发展至高潮,暴风雪的威胁也一步步逼近,而裴晓云充满温情的回忆,却正好与寒冷的暴风雪交错形成叙述结构上的对比。而当暴风雪真正来临,“在惨淡的月光下,潮头般的雪的高墙,从荒原上疾速地推移过来,碾压过来。狂风像一双无形的巨手,将厚厚的雪粗暴地从荒原上掀了起来……”,此时,知识青年也因为压抑和狂暴,进行了砸军务股、抢银行和在团部放火的暴动,两个派别的生死搏斗正式开始。作为正义一方的刘迈克、曹永强和裴晓云等,一面要抵抗狂怒的反对派的冲击以保护集体财产,另一面还要抵御可怕的暴风雪。梁晓声独具匠心地将一场大自然的风暴与体现人类善恶冲突的风暴融合在一起进行叙事,目的在于将北大荒特有的暴风雪与小说中狂暴的反面人物互相烘托,通过叙写这种让人恐惧的双重灾难,来映衬出裴晓云等知青奋斗的光芒。正如主人公曹铁强对即将离去的郑亚茹的一番话:“希望你,今后在回想起,在同任何人谈起我们兵团战士在北大荒的十年历史时,不要抱怨,不要诅咒,不要自嘲和嘲笑,更不要低毁……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要比失去的多,比失去的有分量。”梁晓声的主体即在于“青春无悔”的歌颂,气象灾难的设置,凸显了悲壮的叙事情调。尽管刘迈克死在同伴的匕首下,裴晓云微笑着冻僵在哨所,但在作者看来,通过对自然和社会两种灾难的对抗,他们找到了贡献青春、证明自我的最壮美的形式。
人的价值的证明需要对立面的设置,对于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域的知青,除了农村的落后愚昧,自然的残酷恶劣成为了最能体现人的“主观改造”和参照系。此外,知青文学的作家大多为当时的知识青年,对自我形象的美化亦包含着对恶劣自然气候条件的夸大。而新时期从国民经济崩溃的恶梦中醒来的人们,也有力地激发出了改变落后面貌、进军自然的热情。因此,在“主观改造”的单一主题背景下,知青作家笔下出现了大量的人与自然搏斗的场景,其中大部分都是叙述人与气象灾害作斗争。张承志的《黑骏马》、《春天》中多次提到暴风雪、“白毛风”,“暴风雪像一个狰狞的怪物,半夜时分闯进了草原,……只要跨出蒙古包,马上会被风雪裹住,就像掉进了一个嗷嗷怪叫的深渊。粗硬的雪粒狠狠打在脸上,又冷又疼。迈开凡步,就再也找不到近在咫尺的屋门。天地间飞闪着急速卷过的灰白色雪雾。”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中,知青渡河经常会面对“呼啸而过的台风暴雨:暴涨的河水几乎与河岸一样平,狂流发出可怖的吼声飞泻而去”。在这种气象灾害频频出现的恶劣环境中,知青的奋斗无疑是对抗生命流逝的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阅读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凡是涉及气象灾害的部分,其中无论是对暴风雪的抵御,还是对白毛风或者台风暴雨的抗衡,大多是以失败告终,少数的成功,也都让小说中的人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面对这种自然规律对人的惩罚,小说却少有反思,而都是以对人的英雄主义的歌颂告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气象灾害是和当时的反动分子、错误思想等一起,被列入“反面形象”的素
材库的对象,成为可以凸显人物高大形象的“对立面”。
作为文学复苏时期的主要潮流之一,知青文学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它真实地描写了知识青年在激情和苦难间度过的艰难岁月,并提供了对这种被欺骗和被侮辱的命运的思考。这些小说通过描写知青对气象灾害的抵抗和征服,歌颂了知青一代的理想和信念。
但另一方面,它过于重视人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对立矛盾的表现,而忽视了气象灾害本身所表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片面歌颂人对自然生态的这种强力干预和醉心改造。在195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观念所体现的“战斗美学”影响下,知青文学的“悲壮美”定位要求塑造知青的英雄形象,将他们面对自然灾害所遭受的苦难崇高化和审美化。小说对暴风雪、沙尘、洪水、干旱等极端气象中人的抗争的描写,无论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显示出知青改造环境、永不屈服的激情。这种对人类青春激情的过于沉迷,对自己往昔岁月的价值认定,使气象灾害和其他灾难一样,是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人生挫折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其中的冲突和对抗,凸显人物的精神世界。
2气象灾害与苦难叙述
气象灾害是自然灾害中最为频繁而又严重的灾害。老鬼的《血色黄昏》中,曾经对知青下放地之一的锡林郭勒草原冬天恐怖的白毛风有过具体描写,这地方奇冷,“年年都有冻死的人”,冬天要是迷了路就只能等死;“白毛风要是来了,伸出胳膊都看不见”,它铺天盖地,越来越大,把整个世界刮成了一团呼啸的银白色旋转体。烟雾腾腾,……每人眉毛、胡子上都染着白霜。像一条几百里长的巨龙,上下翻滚着,把个天地搅得烟雾腾腾,白尘滚滚。高速旋转的雪花,淹没了草原上的一切。六月天刮白毛风也能冻死人,就连经冻的牧民,他们的鼻子、耳朵也一样会冻掉;最冷的天,人尿一出来就立刻冻成冰柱,得用棍子敲。“气温之低,连鼻孔里的毛都冻硬,吐口唾沫,掉地上就成冰块”;“在严寒中,谁偷懒,谁挨冻。那不撬下石头不休息的斗气,那一口气打700锤的拼命,那一刻不停地背石头的韧力,无不是与严寒抗衡”。在人为造成的专制环境之外,严酷的自然条件进一步加深了知青生活的艰难和惨烈。尤其是处于回忆中的知青小说书写,映衬着青春岁月中人的独立、尊严和权利,当时灾难性的气象特征便成为越发清晰的记忆和象征,控诉着一代青年所遭受的摧残。
如果说知青的乡村生活还是他们在重返城市后记忆的书写,那么对于有着广大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气象灾害带来的后果往往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忍受。正如都梁在《血色浪漫》中揭示出旱灾肆虐的北方农村“春天把谷种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着下雨,要是二十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旱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是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八九个月的。”因此,对气象灾害所带来的人的苦难的书写,是从“五四”后的乡土小说兴起后一脉相传的写作立场。如果说1950年代至80年代的乡土小说更多地聚焦于农村的落后和进步观念的冲突,那么9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再一次回归了“人的文学”,以这种文学观念对“底层”群体物质和精神生活困境投以注视的目光。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陈应松《吼秋》中的泥石流、《望粮山》中的冰灾,余华《活着》中的各类灾害等。苦难叙述体现了新时期以后小说悲剧意识的觉醒。相较1949年以后文学中面对气象灾害盲目的英雄乐观主义,这类小说认识到了人类力量的局限,体现了初步的反思意识。但是作家的视角往往过多地注视气象灾害给人带来的苦难,热衷于展示苦难或者仅仅停留在对苦难的控诉和悲悯上,而少有超越性的思考。
其中阎连科小说《年月日》是较为特殊的一篇。先爷作为一个常年劳作在北方农村的老农,他遭遇的是多年不遇的旱灾,“千古旱天那一年,岁月被烤成灰烬,用手一捻,日子便火炭一样粘在手上烧心。一串串的太阳,不见尽止地悬在头顶。先爷从早到晚,一天问都能闻到自己头发黄灿灿的焦煳气息。有时把手伸向天空,转眼问还能闻到指甲烧焦后的黑色臭味。”恶劣的气象条件使得村里的居民纷纷逃难,然而只有先爷留了下来。理由是他的田地里冒出了一棵玉蜀黍苗——未来的种粮。为了收获这荒凉世界里最后一棵希望,先爷和干旱展开了惊人心魄的抗争。一年之后,为了秋种逃难回来的人,在早已枯黄在地里的那棵玉蜀黍杆上发现了七粒指甲般大小如玉般透亮的玉蜀黍,而玉蜀黍的根,却是扎在了倒在地上的先爷的血肉里。这种对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苦难、抗争、失败、希望交缠的叙述,显现了作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的悲剧精神和生命意识,然而将目光仅仅聚焦于先爷对苦难千方百计的忍受和抗争上,就无法看到气象灾害给人类生活带来苦难的深层原因——人本身的异化以及带来对自然环境无休止的掠夺和摧残和整体世界的异化,亦是造成这些灾难性气象的一大原因。对于被摧残的人类发出的控诉,自然无法回答。只有通过越来越暴烈的气象灾害,提醒着自然本身的被破坏。
人道主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对举于中世纪时贬抑现世的神道主义而出现的,“是以人类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一种学说、一种态度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指一种哲学,它反对超自然主义,把人看做是自然对象,肯定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以及人运用理性和科学方法获得自我实现的能力。”在1980年代初长时间的思想禁锢刚刚开始出现松动的政治语境下,这一思潮的流行因其对强权、专制、独裁保持的批判姿态、对情欲和物欲的合理辩护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人道主义往往把人当作唯一的价值主体,而将人以外的自然世界当作价值客体。这就导致了小说在描述气象灾害时,过分地突出人在灾难面前的苦难和反抗,使得灾害本身成为一种“背景”,退出了被关注的视野。
二、无我之境——“天人合一”
视野中的气象灾害书写
1气象灾害与牧歌情调
上文已对新时期以来小说中对气象灾害描写的部分类型作了初步分析,这些小说的叙事模式,是新时期以来与土地、自然相关的小说题材中被重复书写的。其中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处处对人之抗争的强调,使得再酷烈的气象灾害,在人类奋斗和苦难的主题中,亦显得黯然失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曾经论述过的“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具有浓厚主题色彩的创作手法,可以用来形容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写作模式。而与“有我之境”相对的,便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这在新时期以后小说的气象描写中,亦可找到相应的对象,便是迟子建、汪曾祺等人充满田园牧歌隋调的乡土小说。
汪曾祺《小说三篇》中的《求雨》曾经描绘昆明春天的气象:“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
下,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积蓄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人们戴着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对于记忆中温润的春雨,汪曾棋的笔调波澜不惊却依稀透着水意;而对于突如其来的旱灾,“稻田里却是千千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晒得结了一层薄壳,裂成一道一道细缝。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汪曾祺却没有用大量的笔触渲染灾害的严重,也没有强调异常的气象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而是尾随着十几个孩子组成的求雨队伍,去展现“求雨”仪式所表现的人对一切生命的爱惜和诚挚。
同样执着于书写人与风云变幻的自然气象互相倾听、和谐交融的,还有东北女作家迟子建。或许是因为她出生的记忆里就带着漠河奇特的气象:“从中国的版图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于最北端,大约在北纬53度左右的地理位置上。那是一个村子,它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每年有多半的时间白雪飘飘。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里漫长的寒冷。冬天似乎总也过不完。”因此在迟子建的笔下,无论物候和气象发生何种异常,村民们都可以学会与其和平共处。《初春大迁徙》是书写一次旱灾逼迫乡民们集体迁徙,但同“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下的小说书写所不同的是,迟子建没有将气象灾害作为乡民的对立面,而是将其带来的后果作为大自然不可变更的规律的体现,从而突出灾民的迁居途中对自然气象的倾听和融合。在这次迁徙中,不是对立和仇恨,没有诅咒,乡民们遵循着自然的旨意,“去年雪下得轻飘飘的,点眼药水一样”,这一征兆预示着来年的灾害,于是他们群体迁徙去“避难”。全村人都知道这一次自然灾害对于他们只是暂时的,他们避过难以后还要回来,因此这一次迁徙对于他们来说,是对自然的一种亲近和探寻。这篇小说里自然和人类并不处于对峙状态,在面对自然带来的气象灾难,原始的乡土思维赋予乡民原始的灵性,那些最淳朴人类中的“觉醒者”听懂了自然的话语。而在《采浆果的人》中,作家更通过不同人群对待气象变化的态度,深化了这一主题:秋天到了,村里来的收购贩子使村民们看到了采浆果带来的收入,于是大家一起去山里抢着采浆果赚外快,因为这个冷落了他们的田地。然而季节交替的气象物候却并未因为这种物质上的富足而被阻挡,在村民们陶醉于釆浆果带来的额外收入的喜悦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打破了金井村人的美梦,“金井人一年的收获,就这么掩埋在大雪之下了。大地彻底地封冻了”。而此时,只有遵循着四季的自然气象运行,在大家抢着采浆果时按部就班地忙着抢收粮食的智障兄妹大鲁和二鲁,反而获得了一年的丰收。在传统的农业思维中,春天播种,秋天下了霜就应该收获,一切按自然气象运行的指示。然而当蓝色卡车带来了外面世界的金钱诱惑时,自然气象所带给乡民们的启示失去了效力。霜降之后,采浆果的村民引以为傲的精明和无止境的欲望被一场大雪无情地毁灭,对自然规律的尊重的智障兄妹,却获得了比绞尽脑汁盘剥自然的人们更好的收成。现代化常常以物质收入的增长为指标,为此放弃了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掠夺。然而自然与人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自然的气象现象作为对人类的一种提醒,打破了人类利欲熏心的迷梦。
除了提醒和警示,迟子建笔下的气象变幻,还充满着温暖的情感色彩:《雾月牛栏》中村民居住的村子一到六月就会起雾,村民们都深信一个传说“三百年前有位仙人云游四方经过此地,但见田里庄稼长势喜人,牛羊成群,家家户户仓廪殷实,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只是很多人家的男人却在骂老婆,骂的又都是一个词‘丑婆娘,仙人大惑不解,问了几家挨骂而啼哭的女人,她们说一到六月,阳光灿烂而农事稍闲的时候,男人们就嫌她们丑陋而牢骚不止”,于是神仙就“斩首了泼辣的阳光,袅袅雾气中的女人恍如仙女,男人却少了脾气,有一种羽化登仙的感觉,消逝的柔情又湿漉漉地复活”。《微风人林》中,方雪贞在高度理性化的医院工作和毫无激情的家庭生活之中失去了生气,在上夜班时被鄂伦春人孟和哲满脸的血污吓得闭了经。作者给这种生命力的萎缩设计了一种解药,就是在自然的气象变幻中和丛林中走来的充满自然生命力的鄂伦春人孟和哲欢好。这时候,自然的气象现象与孟和哲这个“自然之子”的行动交织在一起,正是由于这种多变的气象,使得方雪贞领略了孟和哲身上所散发的不同的自然生气,是她的对自然的感觉也由微风、细雨、星月和暴雨重新唤起。因此,小说孟和哲所说的“风也是药,雨也是药”,不仅仅是鄂伦春人在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下对自然的崇拜,也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从气象的多变中所感悟到的自然生机。
这种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局面的写作模式,与迟子建认识世界的途径有关:“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却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早衰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人与自然的互相交通,把人的位置从世界的中心解脱出来,“人就是‘世界的成分,人与世界万物交融在一起,彼此不可须臾分离,也可以说人融化在世界万物之中”。在这种将自然界与人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中,自然的气象转化,无论是和谐的风雪雨雾,还是暴烈的气象灾害,都和人类社会无法区分,这也暗自应和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被打破,从现代性要求下自然的“祛魅”转向“复魅”:“它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事实上,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的界线,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单一宇宙的一部分。‘世界的复魅意在更进一步解放人的思想。”这类小说将自然界的气候现象和人类本身的处境放置在一个平等的视野中。对灾害的破坏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没有加以夸大和渲染,希望营造一种田园牧歌般的审美情感,来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这类小说中除了灾害,更多描写的是气象现象所带来的美好感受,便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创作立场。
2气象灾害与生态伦理
面对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所带来的“自然之蚀”乃至“自然之死”,当代小说在19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出现了生态伦理的视角,开始关注“天道”所蕴含的自然本身。在小说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呈现“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的同时,小说中的气象灾难逐步从人类世界的“背景”中走出,成为小说表现的主体。
无论是张炜《刺猬歌》中的“早魃”,张抗抗《沙暴》中的沙尘暴,阿来《空山》中的干旱,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的漠风和沙化,还是郭雪波等人专门创作的系列生态小说,都打破了人作为唯一文学主体的局限,直接展现生态整体内部关系。这些小说中有对自然“灵性”的敬畏,有对传统“气象”观念的接续,也有对生态乌托邦的建构,这些都体现了作家面对气象灾害时的超越性思考。拯救和忧患意识是这类小说面对气象灾害所体现的基本视角。但如何避免一味的控诉和批判,走向具有个体意义的思考,如何将这一题材的写作融科学、哲学深度以及文学的审美意义于一体,依旧需要探索。
气象灾害频繁发生与人类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有紧密的关联,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本身的变化过程。但我们所看到的对气象灾害的文学书写,却仅仅局限于乡土题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气象灾害对现代都市以及城市文明的影响,却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赵本夫的《无土时代》中的“木城”,就显示着城市中自然气象的缺失,“星星和月亮早已退出城里人的生活,他们有电和电灯足够了”,“在木城人眼里,星星和月亮都是乡下很古老的东西,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早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而这种缺失正是人类现代文明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由此便引起了城市中的气象灾难。在夏天,现代性的马路楼房反射日光,汽车排成长龙散发热气,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大蒸笼;冬天的洁白大雪,也就被城市废气污染得黑乎乎的。虽然《无土时代》中作者安排天柱的绿化队在木城街道、花园、草坪里种上了麦子庄稼,并由此解决了“木城”的气象灾难,使其显现出入与自然的融合。但这类题材在当今为数众多的城市小说中的缺失,使得在消费文化和科学主义占主导的语境下,如何来写作这一题材,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