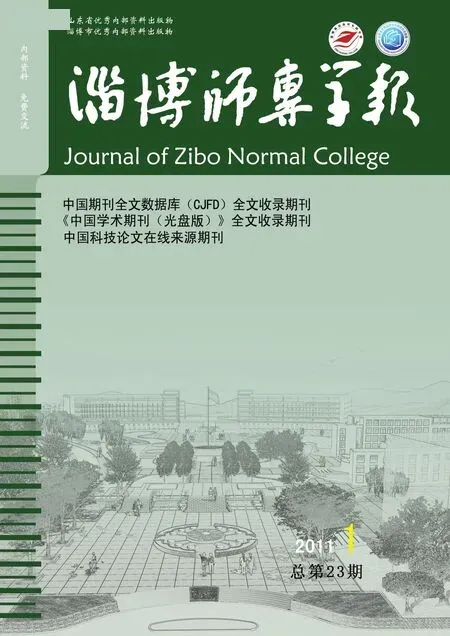自适与自远
——论魏晋文人的饮酒精神
徐文翔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酒在古人的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酒之为物,已经远远超出了饮食的范围,而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明宣宗在《酒谕》中所说:“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成欢”。与此同时,酒也对古人——尤其是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而独特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酒与文人结合得最紧密的时期莫过于魏晋,魏晋文人钟情于酒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酣醉的身影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在西方哲学中,有以“狂欢性”和“悲剧性”为内核的“酒神精神”之概念;相比而言,魏晋文人在借助酒追求美与心灵自由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文精神的承载、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笔者试图以“魏晋文人的饮酒精神”为主题,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将其内涵概括为“自适”和“自远”。
一、自适
所谓“自适”,指的是一个过程,是借助酒醉的状态,实现对人生负重的消解和本真心灵的追求。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不仅表现在历朝历代无休止的天灾人祸、征战杀伐以及广大百姓的颠沛流离和被奴役压迫上,而且表现在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自由的禁锢、尊严的践踏、思想的扼杀、道德的扭曲上。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里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指出,中国实际上只存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这种缺乏独立的个性价值观和人权意识得不到尊重的文化背景下,文人所遭受的精神上的苦难是难以言表的;而且作为社会的良知和道德体系的维护者与践行者,他们还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精神痛苦。再加之生死哀乐的无常、动辄得咎的境况……,更给文人敏感的内心增加了苦闷。因此,中国古代文人身上,常常存在着悲苦的体验和忧患的意识。正是这样一种境遇与生存状态,催发了文学史上不平则鸣和发愤著书的传统。
不平则鸣和发愤著书,毕竟还有表达的渠道,有“鸣”和“著”的权利;但是到了魏晋时期,有时连这些表达的渠道也容易招来杀身之祸,那么文人只好向酒——这精神上最后的避风港去寻求慰藉了。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评论汉末魏晋六朝道:“(这一时期)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诚然不错。但是我们也应当全面地看到,这也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极致”的时代。遗憾的是,往往是丑恶、残忍、恶魔把住了话语权,这朵灿烂的“自由、解放、智慧、热情”之花,却盛开在一个肮脏的池塘里。文人拥有睿智的大脑和伶俐的口才,却手无寸铁,在权力面前,他们的思接千古、游心太玄,无异于站在刀尖上跳舞。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许多文人都与酒空前亲密起来。文人与酒的缘分由来已久,但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魏晋饮酒这么厉害。例如司马昭想同阮籍结亲,阮籍坚决不同意,但又不能回绝,于是他想到了饮酒。整整两个月,阮籍都饮酒大醉,使者每次前来,阮籍都酣醉如泥,时间久了,这门亲事也就不了了之。阮籍的饮酒,除了避祸之外,也将内心那种深深的痛苦寄于酒中。酒之于魏晋的文人,已经远远不止是一种饮料而已,而是精神上最后的寄托与避风港。
如果说自由的禁锢和尊严的践踏给文人带来深切的痛苦的话,那么思想的扼杀和道德的扭曲无异让文人在精神上更加难于承受。如同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所论述:孔子是中国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孔子所建立的道德体系的核心:在于诚,在于真性情——即所谓的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仁”。而一切的礼法,只是它寄托的外表,如果舍本逐末,只讲求表面上的礼法,而舍去了“仁”的真精神,甚至假借礼法之名义去谋私利,那便是“乡原”、“小人之儒”。孔子本人对这类人是深恶痛绝的——“乡原,德之贼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然而不幸的是,自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掌握着社会政权,借礼法之名,行苟且之事,将孔子所建立的道德体系破坏殆尽。曹操借“乱伦败俗”之名杀孔融,司马昭借“不孝”之名杀嵇康,皆是如此。然而,身怀赤子之心——“仁”的真正的道德的维护者和践行者,此时精神上却是痛苦万分的。关于这种情形,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得很透辟:
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这种信仰被毁坏的痛苦,对于文人们来说远在自由的禁锢和尊严的践踏之上。于是,文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酒。历来人们议论及此,多认为魏晋文人的醉,只是一种逃避现实、远祸全身的办法,所谓“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但实际上,他们的饮酒,更是一种借酣醉来体验自由、在酣醉中寻找本真心灵的过程。既然“醒”时看到的社会是如此浑浊,礼法是如此的严酷,心灵是如此的压抑,倒不如在“醉”中让情感得以放纵,精神得以解脱了。只有在醉中,才不必顾及被统治者所利用的虚伪的礼法,本真的心灵才得到解放,向着自然敞开。于是,我们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看到了: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
这些文人狂放不羁的言行,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宣泄和无声的抗争。然而,这不得以地逃向醉乡,却让文人们从酒中发现了自己的本真。他们内心中隐藏的赤子之心——真性情、真情感,本来已不为世俗所容,却从这酣醉的世界中找到了天地。浓烈的酒精麻醉了人的神经,却也解除了一切规范的束缚。酣醉扯下了世俗生活的虚伪面罩。于是,负重的心灵在醉中敞开了闸门,真情的泉水便自然地汩汩流出。
魏晋文人以狂狷来反抗桎梏性灵的礼法与世俗,以自己的真性情、真情感来发掘人生的意义。这是一种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并启示后人,酒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藉此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然而更重要的是,酣醉的过程包含了对生命的关注以及心灵的自觉。文人在醉境中追求内心的放松、人格的完整,以期获得回归自然的状态,进而追求与生命本体的融合——酒与心灵的本真联系在了一起。这自适的饮酒精神,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不断传承,从而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史与思想史。
二、自远
《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这里的“自远”可以结合《庄子·达生》中提出的“醉者神全”的概念来阐释: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
庄子所说的“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慑”的“神全”,实际上是一种“无我”境界,也就是《逍遥游》和《至乐》中所说的“至人无己”和“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其追求的是一种物我两忘和与天地同化的自然人生。进一步看《庄子》中的“无我”境界与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境界》中所阐释的“天地境界”又是相通的。冯先生指出,人所有可能的境界有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中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挥,始能尽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如果说,上文中论述的魏晋文人饮酒精神中的“自适”,是文人超脱了功利境界而到达道德境界的话。那么,“自远”,则是文人已不满足于道德境界,而自觉地向天地境界进发的过程。不论是“醉者神全”,还是“天地境界”,都要求人追求“无我”,哪怕这一过程是如此的艰难。
魏晋人能够从醉乡中找到人格的完整和心灵的本真,他们认识到了“本我”的价值之所在。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魏晋人对自然的观照,是从“本我”出发而观之的,以“本我”之心赋予山水以情致,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然而,魏晋人毕竟也在向着“无我”之境展望着、探寻着,哪怕只是神游而已;饮酒酣醉,则为他们提供了条件。借助于酒,在醉中即可进入身与物化、物我两冥的境界,与万物融为一体。刘伶在《酒德颂》中形象地描绘出在醉的状态下达到的与天地同化的境界: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羸之于螟蛉。
事实上,完全如庄子所说的“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迕物而不慑”的“无我”境界,是任何人也无法达到的,庄子本人也不例外。但是,庄子毕竟向后人指出了一条靠近“无我”境界的途径,那就是“得全于酒而若是”。魏晋人已经凭着酣醉在意念中向这种境界进发了。哪怕仅是想一想,这在精神上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超脱。
第一个在践行上初登“无我”之境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同他的前人们一样,也遭受着文人难以逃避的苦闷,但是他却并没有以嵇阮那样不羁的言行和狂放的饮酒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在境界上,陶渊明显然是高出同时代其他人一筹的。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中说:“陶既熟谙老庄、孔子,又不限于重复儒家道家的思想;他既未违背魏晋时期的思想境界的主流,又不随波逐流;他有来自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这种“独特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便使得陶渊明身体力行地向着“无我”之境靠拢。
以其《饮酒》诗第五首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心远地自偏”岂不是“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的基本的写照吗?“悠然见南山”岂不是内心中纯粹的淡然吗?“欲辨已忘言”岂不是嵇阮等前人毕生也难以企及的“无我”之境吗?因此,陶渊明的饮酒,并不是苦难和抑郁所逼迫他去饮,而是将苦难和抑郁咀嚼了,消解了。在一种淡然的心境中,不带有任何目的地去饮酒。酒之于陶渊明既不是什么避祸的手段,也不是提供酣醉以神游天地的工具,而是在无我境界中遨游的精神伴侣。如果说饮酒精神中的“自适”是为了醉而醉,那么如陶渊明这般的“自远”,则早已无所谓醉与不醉了。诗人在东篱下偶然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相会。那一刻,诗人所处的是一个纯然平和、物我两忘的“无我”心境,至于有没有喝醉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自上古时代就有隐士,但直到陶渊明,才真正开启了隐士的风流。这种风流在陶渊明身后的千百年中,为无数隐与不隐的文人提供着借鉴和慰藉,同时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寄情于酒,以酒为精神伴侣,自觉地向着天地境界靠近。陶渊明饮酒的自远,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但我们愿意看到这种模仿,它为中国历史的杀伐气息与名利气息中,增加了一股清醇的酒香。
[1] 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全译[M].柳士镇,刘开骅(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2] 冯友兰.新原人[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王守国,卫绍生.酒文化与艺术精神[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6] 戴燕.玄意幽远——魏晋思想、文化与人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