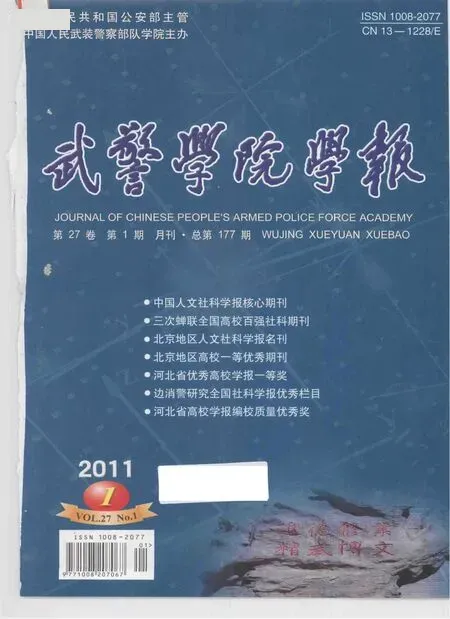“大旨谈情”与补天之恨——《红楼梦》思想价值再探
●佟瑞坤
(武警学院基础部,河北廊坊 065000)
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二百多年来争论不休,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文本的阐释,如爱情主题、封建社会衰亡主题等,另一种则侧重文本之外的创造过程和创作背景,如影射政治说、自传说等。但目前,这两方面的探讨似都陷于涩滞的境地。过分偏重于阐释文本容易疏而无当,而过分脱离文本则容易缘木求鱼,穿凿附会。笔者以为,要在《红楼梦》主题研究上取得突破,必须把关注作者(不仅是身世、经历和作品本事的考证,还应更多地关注其思想)和阐释文本有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作品对人生、社会的基本认识及其价值取向,从而进一步揭示作品的思想价值。
就题材而言,《红楼梦》无疑是在“大旨谈情”。因为在开头明确表明要为“闺阁昭传”,但这只是说明了作品的题材,题材不等于主旨。试想,如果作品只为谈情,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与谈“情”无关的情节,和有所寓意的表述?由于作者明确声明本书并“无朝代年纪可考”,也就宣告了这是纯文学创作,而非真正的自传体或家族史。即便有自身经历和家族本事在里面,我们也必须首先把它看成作品文学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必要把它与作品中具体的情节人物一一坐实对号;但同时,对于这些引起人们“索引”、“探佚”的部分文本的特殊意义,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或故意忽略,它既然作为作品文学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是形成作品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因子,所以我们应在深刻解读其寓意的基础上把它和作品“大旨谈情”的题材结合起来分析,这样也许能更深刻地认识作品的主旨所在。
一、“甄士隐”与作品主旨
把通灵宝玉的来历和“甄士隐”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可以作为进一步解读作品思想的一把钥匙。
首先,作品把“通灵宝玉”的来历安排在“女娲补天”的神话之中,本身就有为“闺阁昭传”之外的另一层深意。否则,若只为“大旨谈情”,有“绛珠仙子”与“神瑛使者”为宝黛爱情作引子也就足够了,无须再给男主人公复合一个补天之石——通灵宝玉的身份。此石虽无缘补天,但它毕竟为补天而来,所谓“无材”者,非无才也,以本可补天之灵性,去经历人间之事,其见识与感受,自当秉天地之性而高于世人。故“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的自责乃非本意,而对于其“爱博而心劳”[1]、惜香怜玉的行为实则无悔,甚至视为一生之事业,所以才为“闺阁昭传”。既然以“补天”之灵性而为“闺阁昭传”,“闺阁”中人肯定会与“补天”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小说第一回就已经交待出来了。且看这两段文字:“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狭窄,人皆称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自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不料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起,使烧着窗纸。南方人家用竹篱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一夜,方渐渐的平息下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烧成一片瓦砾场了。”[2]甄士隐即“真事隐”,隐曹家之事而为小说素材,而这场大火的起源地——葫芦庙,则隐指清延。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甲戌本有脂砚斋侧批云:“……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盖作者立意写闺阁尚不暇 ,何能又及此等哉?!”[2]而卷首“凡例”云:“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可见,廊庙即指朝廷。葫芦庙者,“胡虏庙”也,胡人之朝廷也。清廷里出了事,“牵五挂四”,波及了“真事隐”的家,使其同时遭遇灭顶之灾。脂砚斋在这段描写之上特别有眉批云:“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2]“南直”即南直隶,即江宁织造所在,其意已明。书中甄士隐名费,妻封氏,加在一起乃是“真废封”之意,即曹家被黜之事。而甄士隐的女儿英莲亦因家人霍启(祸起)而失踪。之后第四回在一场官司中,英莲由于冯渊(逢冤)被“乱判葫芦案”,而流落到薛家为奴,从此开始悲苦命运。判断此案的贾雨村本非僧人,而以“葫芦僧”名之,安排其籍贯为“胡州人士”,改湖州为 “胡”州,并非讹字,实有用意。作者是在说,“胡虏庙”(朝廷)里的“胡”僧乱判了这个关于甄家的案子,“真事隐”女儿之命运,也终因这场官司而改变。我们还要注意,甄士隐这个人物出场的背景是“地陷东南”,在梦见太虚幻境时又“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天崩地陷”。《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西南,故水潦尘埃归焉。”[3]引用这个神话意在说明“隐去”的“真事”即曹家“召祸”之背景与宫廷帝位之争有关,整个甄士隐的故事就是大体在说这个真相,既然真相与神话混而合一,那么它主要意义也就在于文学文本之上。作者花了整一回的文字来写甄士隐的故事,实际上是在暗示全书的情节与主旨:甄士隐的家事即暗示了书中贾府的整个故事,所谓“不怕繁中繁,只要繁中虚;不怕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则省中实也”。[2]故 “十二钗”副册中的香菱,出场才如此隆重,她浓缩了贾府内所有女儿命运:“真应怜”。正因她的出场背景是“地陷东南”,也就揭示了为“闺阁昭传”与补天的联系。《淮南子·览明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3]在《红楼梦》中,《淮南子》中两个神话合而为一,其用意即为:闺阁中人(真应怜)的悲剧之根源,在于天之不补。于是,补天之恨遂成贯穿全书的一个情感线索和创作主旨。补天之恨化为悼红之情,悼红之情更寄补天之恨。
这样,我们就明确了卷一的偈对于全书主题的揭示意义:“只因无材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脂批:“书之本旨”、“惭愧之言呜咽如闻”;在第一回写癞头和尚说甄英莲“有命无运”时,又批 “谁谓独寄兴于一‘情'字耶?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未尽,况今之草芥乎!”可见,作者把通灵宝玉的补天之恨与悼红之情,等同于历史上经天纬地之杰出人物国事未平、壮志难酬的遗憾。以脂砚斋和曹雪芹的关系及对《石头记》写作背景、写作过程的了解,我们完全可把以上批语看成是曹雪芹的代言。“他的批不是小说正文以外的赘物,而是被作者本人看做为小说的一附加部分”[4],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乃是一部包含了作者大想法、大志向的小说,那就是:天还是要补的!
二、以情补天的济世理想及文化价值
既然作者把“无缘补苍天”看成人生之绝大悲哀,那么天应该如何补呢?
首先,要找出“天”坏在哪里。在甄士隐的故事中,大火的起因是“葫芦庙”里“炸供”。实际上是说朝廷里“轧攻”即政治斗争,但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把这个原因看成是悲剧的全部根源。从《红楼梦》的情节来看,作者所针砭的各种劣行污迹,皆因人心不古,纷争不已,其中既有为官者的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也有家族内部的嫡庶争锋、奴仆夺利,还有家族成员的行止不端。细恶既多,终成颠覆。凡此种种,使作品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仕途经济”传统价值体系的彻底绝望。这与同时代另一伟大作品《儒林外史》是完全一致的。而要补天,使世间变得重新美好,则须弭私心、去纷争、尚和睦,使人心向善。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儒林外史》给出的方案是恢复古代的礼乐制度,以此来厚风俗、淳人心。《红楼梦》中虽没有明确提出具体方案,但其中蕴涵的是与《儒林外史》一脉相通、但比《儒林外史》走得更远、更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理念,那就是以真情补天济世。
关于作品的济世愿望,我们首先来看第四回的回前诗:“捐躯报国恩,未报躯犹在。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按这一回写的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很显然,这两句诗既不是颂扬贾雨村,也不像是在讽刺他,而是由英莲这个人物的不幸遭遇而引发的自身感慨。他要拯救眼前的“多情物”,以此来“报国恩”,证明作品所要表明的人生价值取向最终还是入世济世。第二十二回中,林黛玉、史湘云、贾宝玉三人搅在一起发生误会,宝玉无法解决此事,于是就想到“目前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于此脂批说:“看他只这一笔,写得宝玉又如何用心世道。”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既然曹雪芹已对当时社会如此绝望,且书中暗讽朝廷中的争帝行为,何以这里又要入世、又要“报国恩”呢?我们应该看到,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眼中的“国”、“君”不止是哪一个具体的朝代、帝王;所谓“报国恩”泛指的是他们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在王朝时代,知识分子们只能这样表述他们的最高政治理想,所以忧国忧民的杜甫最终也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5]。在这个问题上,曹雪芹的话语方式也不可能超出其历史时代,然书中的“报君恩”已完全不是这个词的本意,而是一个代名词,即拯时救世,实现个人理想。这个理想,与“仕途经济”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无关,只是作者心中的一个“情“字。故将补天之石安排为“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以“总应十二钗”、“照应十二副钗”,其用意即是说,要想补天,非用女儿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行止见识”不可,以真情补天,才能拯救人间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第一次把女性推上了小说主角的地位。第十三回末尾的两句诗,再次明确了这一思想:“万千金紫①金紫,金印紫绶。黄金印章和系印的紫色绶带。古代相国、丞相、太尉、大司空、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及六宫后妃所掌。后代指高官显爵。谁治国,裙衩一二可齐家”。也就是说,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已沦为“禄蠹”、“浊物”的男人们已不能为,须以女儿之真情而为之。作者所能见到的,只有“女儿”可以做真情的载体。但曹雪芹这里强调的应该是人间所有的真“情”,即贾宝玉的“情不情”,把人的个体价值“情”与人的社会价值“补天”完全统一在一起,这就是《红楼梦》之“大旨”所在。
从表面上看,提倡以情补天是作者对当时主流社会价值体系极度失望的结果,也是作者治世思想的朦胧表述,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个跨越历史时代的了不起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构想。因为,只要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形态,人的真情至性就会与社会的现实要求存在冲突,只不过随着社会进步,这个冲突的剧烈程度会逐渐减弱,表现形式也会有所演变而已。然而人类社会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指向个体的最完美的生存状态,它要求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基于人的个体价值即真情至性充分发挥的基础之上,反过来社会又能充分地保护和发挥个体的真情至性。这应该是整个人类最高的社会理想。而《红楼梦》引导人们的正是对这种审美境界中的社会状态的向往,所以它不仅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东方出版社,1996:184.
[2][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M].邓遂夫,校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83,90.
[3][西汉]刘安,等.淮南子全译[M].许匡一,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04,350.
[4]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690.
[5]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