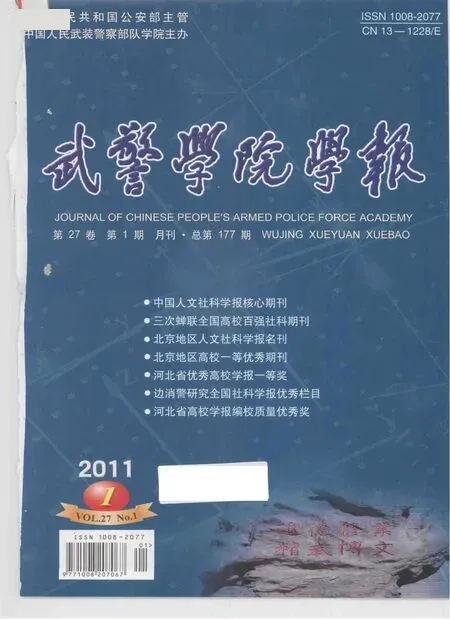鲁迅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王吉鹏,范艳娥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辽宁大连 116029)
(本栏责任编辑、校对 李献惠)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发动了一系列新的侵略,使其在华北的势力大为增强,日本军阀想进一步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于是策动了所谓的“华北五省(冀、晋、察、鲁、绥)自治运动”,这一运动并未完全成功,达到使华北完全自治的目的,但最终成立了由国民党政府中卖国军阀政客组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华北变相的受控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委员会的成立,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这就是“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这一运动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十分恶劣,人民生活受到极大束缚和压制,言论也极其不自由。这对用文字揭露社会黑暗和抨击时政的鲁迅造成极大阻碍,有关时局的文字根本无从发表,所以鲁迅只能以最具隐秘性的文字来抒心中之愤。通过鲁迅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研究,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黑暗,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在严峻的“文化围剿”情况下仍能坚持自身立场的战斗精神。
一、“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鲁迅所处的政治环境及文化氛围
当时,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基本方针是占领华北,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在日本侵略者看来,华北五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保障他们已攫取的东北四省的利益,并继续侵略中国,就必须使华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因此,他们制定了分离华北,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侵略计划。但这次他们采取的方法与侵占东北时不同,一改“武装侵略”为“政治谋略”的方式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以达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把侵占华北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以《塘沽协定》为武器,扫清华北自治的障碍,把国民党的势力赶出华北;第二步是选择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成立华北自治政权。1935年 6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中日先后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从而使日本关东军分离华北的第一步骤基本得以实现。接着进行侵略的第二步即选择傀儡对象,实行由日本军人操纵的华北自治,然而这一步骤走的颇为困难,由于一些军阀头目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愿与其为伍,因此拒绝他们的利诱,再加上国民党政府为反对华北自治而运用一些策略,所以在选择傀儡对象上受到一些阻碍。直到 11月 21日以后才将目标最后锁定在原本就效忠日本的汉奸殷汝耕身上,这死心塌地的奴才于 11月 24日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国民党政府再一次表示屈服,于 25日决定成立由国民党政府人员组成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来统治华北,以应付当前危局,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实现分离华北,使华北自治的最初目的,但迫于英美等国家的压力和中国国内的抗日怒潮,只能接受以“冀察政务委员会”来统治华北的形式,但这一委员会的成员多是卖国军阀政客,实际上仍然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只是日本对华北的控制变得更加隐秘,由地上转到地下,这样既缓解了来自英美等国的压力,也平息了中国国内的抗日情绪。
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过程中,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的妥协、退让,但对中国内部的统治却极其残酷,在文化上进行大肆“围剿”,简直让人不能开口。1935年 5月 4日,上海《新生》周刊第 25卷 15期内刊有易水的《闲话皇帝》,涉及日本天皇,日本驻沪领事极为不满,向我上海市政府提出交涉。当时,国民党中宣会给各省市党部的电令如下:“各省市党部监:本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国体以万世一系著称于世,其国民对于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人所能想像者。……嗣后对此类记载或评论,务须严行防止。再关于取缔排日活动,中央迭经告诫,……”[1]《新生》因此遭停刊厄运,国内的排日活动也一再遭到镇压。从电文中我们除了看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谄媚外,也感到言论受限的可怕,此时的文化环境已经极其恶劣,不允许人轻易开口,从鲁迅的文章中,我们深切的体味到了这种气息。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指出文坛令人窒息的气氛和环境,他指出“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萧红的《生死场》)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的。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闲话)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2]鲁迅以沉郁的心情谈了萧红《生死场》原稿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扣押的过程,揭露反动派的文化统治和投降媚外政策。鲁迅在 1935年 7月17日致李霁野的信中,也同样指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他说:“教育界正如文学界,漆黑一团,无赖当路,但上海怕比平津更甚。”因此他对李霁野说“到英国去看看,也是好的,”但对文化界的前景仍持消极态度,认为“回来的时候,中国情形也不比现在好。”[3]而在 12月 3日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情况时也说:“我仍很忙,因为不得不写。但苦于没有东西可写,想写的则又不能发表。”[4]在 24日致谢六逸的信中也慨叹文化环境的恶劣,“看近来稍稍直说的报章,天窗满纸,华北虽然脱体,华南却仍旧箝口可知,与其吞吞吐吐以冀发表而仍不达意,还不如一字不说之痛快也。”[5]从中我们已经真切的感受到当时文坛言论的控制之严,使鲁迅难以再开口。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文化围剿最终导致了文坛的“可怜”,正如鲁迅在发表于《文学》月刊上的《文坛三户》中指出的,文坛上只剩下了顾影自怜“破落户”、做作颓唐的“暴发户”和兼有二者特质的“破落暴发户”,但这些都只是文坛沼渣,“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6]这就说明现在在文坛上能说话的也都是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文人学士,起的是欺骗民众的作用,真正讲真话的人是不能开口的,开口就跟《新生》的命运一样,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那些文人学士又都嚷着要“保护正当舆论”,而像鲁迅这类人自然说的都是“不正当的舆论”,说了自然就要受到惩罚。
二、“华北五省自治”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及鲁迅对此的看法
1935年以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不抵抗政策”,而在 193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逐渐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所改变,放弃绝对“不抵抗政策”,而代之以“安内攘外”、“剿共抗日”的双重国策。很多人也许又开始对这个政府抱有希望,希望它能起而抗日,维护中国的权利,夺回中国的领土。但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一直认为共产党是最大的敌人,在 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武装力量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中心,他当时就认为“现实的匪区是全国中心区域,长江一带,是中国精华所萃,现实的匪区,就是中国的中枢”。[7]因此,他决心将中共力量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而在1934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使蒋介石剿共安内的任务基本完成,因此对中共可暂时放松警惕,这样蒋介石才有精力把目光转向日本帝国主义,他是在“内”无忧的情况下才开始对“外”的。但就算这样,蒋介石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也跟对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他对日的态度始终是以和平为主。他提出了“以不侵犯主权为限”的所谓“最低限度论”,指出“如发生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否则,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8]从中我们只能体会到蒋介石的些微抗日之心,但前提要先“忍”,忍到无法可忍时才“下最后之决心”。再看他在 1935年 11月19日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外交的报告,他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9]仍然是让我们“忍”,忍到“绝望时期”,而“绝望时期”又是毫无标准的。但我们知道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让华北变相的由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是还未到“最后关头”的,所以不能“言牺牲”。但鲁迅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鬼把戏”,他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顾北事正亦未知,我疑必骨奴而夫主,留所谓面子,其状与战区同。”[10]“骨奴而夫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奴才嘴脸和卖国本质。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做的这些表面文章,对于当时紧张的时局于事无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宣称要“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11],但对本国人民却实行专制统治,以致造成穷人连享受日光、空气和水的权利都被剥夺,在上海的穷人“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到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到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而报上却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12]将人民的苦难说成是由天灾造成的,以此来掩饰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人民在说话时更是担惊受怕,最终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国土的沦丧”。正如鲁迅所说:“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13]国民党如此卖力的“安内”,对于“攘外”却束手无策,最多发表些“最低限度论”来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字上的“恐吓”。鲁迅的文章控诉了国民党的这一行为,他在文章中也表达了一种希望,他希望这“大国民的风度”在“极有益于敦睦邦交时”,也用在自己人身上,“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有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14]
三、“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后鲁迅对中国黑暗现状的担忧
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5年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逐渐加深,看见国土的日益沦丧,每一位爱国人士都会痛心疾首。鲁迅更是如此,他对中国渺茫的前景表示担忧,对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专制的黑暗统治表示痛恨。1935年 12月,鲁迅写了《亥年残秋偶作》一诗,从中我们能看出鲁迅对民族危机和人民苦难的百感交集,也表达了他对前途终将光明的信念和激情。诗中首先写“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写出国民党政府统治了“天下”,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拱手让出了大片国土,充满了“秋天的丧声杀气”。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写出如花似锦的文章,来粉饰现实,欺骗别人呢?前两句就足见鲁迅的悲痛之情和自己苦于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无奈。而“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两句则指出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过程中,一些不肯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官员纷纷被国民党政府按照日本军阀的旨意撤职而离开华北,在金风萧瑟中“走千官”,而“我”只能在苍茫的人世间百般忧愁。最后人民将“菰蒲尽”,连一席藏身之地都将不存在,体现了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的境况。这些都表达了鲁迅对中国黑暗现实的沉重感情和担忧。但最后两句“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15]则指出黎明即将来临,鲁迅在黑暗中看到了中国和人类的希望,这也是鲁迅对中国将来的美好愿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愿望最终实现了,只可惜他没能看到这一天。他的好友许寿裳在评价鲁迅的这首诗时说:“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16]准确而全面的概括了鲁迅诗中表达的内容和蕴含的感情。
[1]华北资料选编·国民党中宣会给省市党部的电令(1935年 7月 7日)[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155.
[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2.
[3]鲁迅.书信·致李霁野[M]//鲁迅全集(第 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5.
[4]鲁迅.书信·致山本初枝[M]//鲁迅全集(第 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8.
[5]鲁迅.书信·致谢六逸[M]//鲁迅全集(第 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13.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M]//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4.
[7]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二档藏·参谋本部档案[B].案卷号(78),(135).
[8][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 3卷)[M].湖南:湖南出版社,1988:377.
[9]华北资料选编·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外交报告(1935年 11月 19日)[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315.
[10]鲁迅.书信·致台静农[M]//鲁迅全集(第 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3.
[11]华北资料选编·邦交敦睦令(1935年 6月 10日)[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154.
[1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靠天吃饭[M]//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9.
[13]鲁迅.花边文学·序言[M]//鲁迅全集(第 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9.
[1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七)[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58.
[15]鲁迅.集外集拾遗·亥年残秋偶作[M]//鲁迅全集(第 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5.
[16]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旧体诗集》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