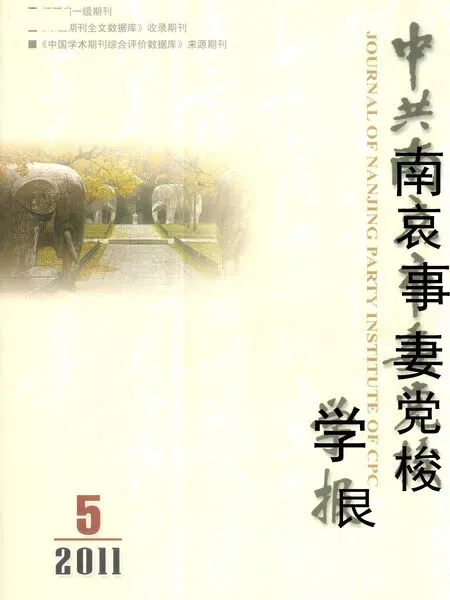人权的幻想——浅析阿伦特“人权的终结”观*
夏子芬
(南京大学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1189)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人权。”
“如果所有的人都是魔鬼,任何关于人权的讨论都将同样没有意义。”[1]
——托马斯·弗莱纳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她在其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了“人权的终结”这一观点,人权何以终结了?引发她思考的现实背景是什么?她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谈论这个问题?而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审视人权问题有怎样的意义?接下来将围绕这些问题加以展开。
一、民族国家的衰落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法国革命之后出现的,根据阿伦特的观点,民族国家是在绝对君主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将具有历史、文化的统一体的民族与领域性的主权国家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政治体制。其实民族性与国家这两种因素在18世纪仍是分离的,直到法国革命后,民族国家才将这两种因素融合起来,“国民”与“民族”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这也是民族国家稳定的基础。然而基于民族国家本身的特性,对民族身份的要求与国家法律本身的普遍性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起就内存于民族国家的结构”[2]中,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资产阶级要求政府权力的输出以保障资本输出,于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永久性功能之一将是权力扩张”。[3]资产阶级也由之前的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开始转向政治,让扩张成为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最终政治目标。然而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并不适应资产阶级的无限扩张运动,这使得民族国家的内部平衡开始被打破。一战后,民族国家体制在欧洲广泛普及,但“少数民族”问题和“无国籍者”问题最大程度地冲击了民族国家的秩序,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即产生了大量被剥夺人权的人。
“少数民族”问题更多地出现在东南欧新兴建立的国家,阿伦特指出,是“《和平条约》(Peace Treaties)创造了少数民族”,[4]条约将一个国家里某些民族定为“有国籍民族”,将统治权委托给他们,又将一些民族作为一个团体称作“少数民族”。很显然“少数民族”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只能依靠《少数民族条约》(Minority Treaties)来加以保护,而《少数民族条约》是让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来保护这些生活在正常的法律保护之外的人,而不是各国政府。然而不管怎样,都不能阻止新建立的国家同化他们,①这也是民族国家衰落的一个体现,只承认具有同一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成员作为其公民,或者说,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不能对坚持另一民族身份的人负责。②国家从法律的执行者转变成民族的工具,民族战胜了国家,民族利益已经高于法律。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民族国家似乎还打着人权的幌子用少数民族条约来保护本国处于法律之外的人,而无国籍者的到来则让人权彻底成为幻觉了。自从一战以来,无国籍者就不断增加,到二战之后上升到一个顶峰。解决无国籍者公认的有两种方式:遣返或归化,但原来的国家不接受无国籍者,无处可遣返,至于归化,此时各国都将政治避难权——“在国际关系中唯一可视作人权象征的权利”[5]——搁置一旁了。面对大批归化浪潮到来时,没有哪个政府能够顺利应付,甚至连之前的归化都取消了。而问题无法解决,也给民族国家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尤其在法律制度结构上,甚至出现通过犯法来获得权利的情形。③
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阿伦特看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启蒙以来的“天赋人权”的理念是深入人心的,人有作为人而享有的与之不可分离的权利——人权,然而从“少数民族”尤其是无国籍者身上,人权的影子似乎荡然无存,此时人权面临了窘困。正是基于对经验现实的深刻分析——而非单纯的理论思辨的维度,阿伦特提出了“人权的终结”。
二、“人权的终结”
法国《人权宣言》的问世,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提出了“天赋人权”,第一次鲜明地指出了每个人生而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理念被人们广为接受,同时也成为西方近代政治的一个基础。《人权宣言》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是它宣告由政治体来承担由于世俗化的进程而丧失的、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保证。”[6]而这种权利又被宣告是从人的“天性”(“nature”of man)中产生的,所以阿伦特指出,人权首次被提出时,已经和历史无关,与社会阶层也无关了,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取代了历史权利(historical rights),“天性”取代了历史。当大量的“无国籍者”失去原来政府的保护,诉诸最低限度的人权时,为何却发现什么权利都没有呢?
阿伦特认为,这是因为人权与民族主权联系在一起了。首先,从一开始宣称与人不可分离的权利中的“人”就好像是“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7]这并不是现实的经验中的人,因为现实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一种社会秩序中。因此,抽象的人在政治领域就成为了包含复数性的“人民”了,也就是说“人的形象应该是民众,而不是个人”,[8]只有适用于民族一员的人权,而“少数民族”和无国籍者并不属于民族国家中“民族”的成员,人权对他们而言,就显得暧昧不清了。其次,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人权问题与民族解放问题纠缠在一起,人们相信,“只有自己的民族主权的解放才能使人权得到保障。”[9]事实上,这一点早在法国革命将人权宣言与民族主权结合起来时就已经产生了,同一个民族在宣布服从法律时,而法律又是来自于人权和民族主权,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从那时起,人权只有作为民族权利时才受到保护和强化,国家作为一种机构,它的最高任务是保护和保障人作为人的权利、作为公民的权利,以及作为民族成员的权利。”[10]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国家成为民族的工具,保护的仅是民族成员的权利了。此外,人权毕竟是因为假设为独立于政府之外而被定义为“不可分离”的,所以一旦没有自己的政府而不得不求助于最基本的人权时,也就没有政府能保护它,没有一种机构愿意保障它。因为之中存在一个复杂的矛盾:如果有国际团体僭称对一些少数民族有统治权威的话,一方面,会多少引起各国政府的公开反对,认为这是对其国家主权的侵犯;另一方面,有关的各民族也不一定就会认同这种保护,怀疑这并不是支持其“民族的”权利,而是另有所图。不仅是少数民族,无国籍者也是如此,都“相信失去民族权利等于失去人权”,[11]他们迫切寻求回归本民族群体,要求拥有属于本民族的权利。阿伦特指出,更糟糕的还在于,为保护人权而建立的一切团体,或者为达成新的人权法案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尝试不仅被一些国际政治家嗤之以鼻,甚至遭到受害者本身的鄙视和漠不关心。“天赋人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没有任何意义。近代政治哲学根本区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地方就在于,“近代政治哲学将‘权利’视为它的出发点,而古典政治哲学则尊崇‘法’”。[12]身为近代政治哲学开山祖师的霍布斯,第一个明确把自然权利,即个人的正当诉求,④作为了道德和政治的基础,以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法的地位。个体的权利作为逻辑的起点,成为论证国家合法性的一个基础,国家的目标就在于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因此,一旦作为逻辑前提的自然权利这个地基崩溃,那么其支撑起来的整个近代国家大厦岂不成了“空中花园”?这也是近代政治理论的一个吊诡,这一点在后面还会提到。
在批判天赋人权后,阿伦特进一步提出无国籍者失去公民资格后,到底丧失的是什么权利而陷入被剥夺人权的境况?她认为,首先,丧失人权者丧失的第一种权利是家园,家园即意味着出生和立足于世界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社会环境,它承载着他们的历史和过去。尽管丧失家园的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然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是,“不可能找到一个新的家园”。[13]因为几乎所有地方都有非常严格的移民限制,且各自贴上了民族国家的标签,这是民族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普及所引发的困境。其次,无权利者还丧失了“政府的保护”。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失去在自己国家里的合法身份,“而是失去在所有的国家里的合法身份”。[14]互惠条约和国际协议都还可以保障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任何地方的合法身份,而不属于任何国家公民的无国籍者不管在哪里都没有合法性。无国籍者正是在丧失了这两项重要的权利后陷入了彻底无权的状态,这就促使阿伦特重新思考人权的概念。
她指出,原来的人权概念本身也存在一些混乱,美国定义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法国定义为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反抗压迫权,后面在进一步修改后的《人权宣言》中又提出共同幸福的权利。不管是哪一种定义,对于那些被逐出20世纪法律保护之外的人,他们的境况都显示即使丧失了上述公民权利也不引起绝对无权利的后果。因为这些权利“都是设想来解决社群内部问题的公式”,[15]而无国籍者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社群,自然对他们也就没有意义。在此,阿伦特提出,像生存权和自由权这些权利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是最基本的人权,事实上公民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公民权,是指从属于某个政治社群的权利,它是一种能“获得各种权利的权利”。而无国籍者正是丧失了对某个政治体的归属才导致陷入了完全无权利的状态,即被剥夺了人权。阿伦特关于人权的观点与英国的埃德蒙·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的观点很相似,他也认为人权是“抽象”的,⑤“一种中间的、不可能界定的东西”,[16]最好的方式是将它限定在某个政府的公民权利上,因为探讨人的权利的一个前提“是公民社会中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17]人的权利本身就来自“国家内部”。所以阿伦特就提出,人只有归属于某个政治体——在之中他人是根据你的行动和言论来判断——才能获得享有各种权利的权利。事实上阿伦特对公民权的强调与她对于人的境况的分析是联系在一起的。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就提出,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包括劳动、工作和行动,合在一起就是“活动生活”(vita activa),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了“生命本身”、“世界性”和“复数性”这三种人之境况。而最重要的是复数性,因为它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18]至于从事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在她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著名划分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处于私人领域中的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可以用海德格尔的“常人”(das Man)来阐释,但阿伦特并不像她的老师那样消沉避世,而是认为人们可以在公共领域通过行动脱颖而出,也只有在这一领域,人们的存在感才得到展现——我是“可以认出的”。同时因为公共领域不仅是我们与同时代人共同拥有的,而且也是我们与前人和未来的人都共同拥有的世界,正是这种公共性,它就弥补了人生命的有限性,于是行动成为人们追求永恒性的一种方式。
阿伦特在阐述自己的人权观念后,分析了希腊奴隶制剥夺人权的状况,奴隶不被当作人,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所有物”,[19]被永远地隔绝在政治领域之外。但就连奴隶也还是属于某个人类社群的,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了必需品,而无国籍者不属于任何一个社群,所以在他们失去一个国家时,也就被逐出了人类。无国籍者事实上也不相信所谓的源自人的天性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权利也可以赋予野蛮人,这一点柏克早就说过,如果人们讨论原始权利,那么也就意味着“处于它们原始取向的简单状态之中”。[20]尽管他们不是野蛮人,但的确也被扔回到奇特的自然状态了,成为文明世界的“蛮族”。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自然权利的问题,近代的政治哲学家基本都坚持这个观点,认为近代国家起源于人们为更好地确保自己的权利而订立契约将其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共同体,这也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然而这个契约并不如宣称的那样合理,它事实上是一个“魔鬼契约”。这表现在:首先,个人在订立社会契约时保留了一部分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但是这种保留是主权者来进行裁定的,“只要允许国家权力确定自己的限度,天赋人权的观念立即便会形同虚设。”[21]其次,这个契约只有单方面约束性,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毁约,将个人开除其列,而个人不可能与之决裂,因为决裂的后果和被开除的后果都是一样——丧失一切权利。这种情况已在现实中(如无国籍者)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回想卢梭对社会公约的规定——“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22]无疑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这或许就是近代政治最大的“阴谋”:以个人自然权利作为逻辑前提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作为论证国家合法性的一个不得不的选择,而当合法性建立后,这个前提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自然权利面临的尴尬也正是基于此,所以阿伦特才指出无国籍者并不相信它,因为它并不能给自身带来任何保护。一旦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赤裸裸的存在”中,那必然会威胁“文明社会”的政治生活,阿伦特甚至形容为,“很像自然界的猛兽曾经威胁人造的城市和乡村一样,或许更可怕一些”,[23]因为这种威胁是来自文明内部。这是一个多么惊悚的状况,但是不要忘了,这是文明社会自己逼迫千百万人成为“野蛮人”的,能产生如此多野蛮人的文明社会还是“文明”的吗?
三、在“人权终结”之后
事实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阿伦特提出人权的终结这一观点是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无国籍者的人权问题之上的。她从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来解析人权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人们一般的人权相比,这个群体的人权无疑有其独特性,却也常常被人们忽视。因为它是人权问题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尤其是当人们探讨普遍人权问题时往往是回避了它。然而正是这个群体的人权问题直接触及到天赋人权的内核,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也映射了欧洲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弊端。无国籍者人权保护的“空场”不仅使得人权理念陷入尴尬之中,同时也形成对人权的现实保护的一大尖锐挑战。所以阿伦特对人权的探讨有其独到的地位,而且她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极大地暴露出了民族国家面临的困境。
“人权的终结”深刻地揭示了人权理念自诞生以来,尽管作为一种观念事实被人们接受了,但是与其现实的保护状况之间有着很大的断裂。这种断裂也正是阿伦特心中的矛盾:一方面,她相信普遍人权的理念,每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人的权利,不然也不会为无国籍者的无权利状况深深地担忧而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她又看到人权的保护在现实中犹如空中楼阁,许多人都生活在无权利的境况之中。用后来哈贝马斯的话来解释这一情形就是,“在人权的普遍意义与实现人权的具体条件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紧张关系:人权应当适用于所有人,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可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呢?”[24]所以阿伦特将人权归于公民权上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一矛盾同时也折射了启蒙以来所追求的人权价值理念与人权保护的实现层面之间的鸿沟是如此的巨大,事实上,早在人权理念诞生的那一刻,它自身存在的漏洞就已经彰显了。
圭多·德·拉吉罗就曾指出了这个问题,《人权宣言》讲“天赋人权先于国家,仿佛国家存在之先这些权利就已经存在了;它把自由与平等放进人类的原初状态中,而事实上这些却是社会生活中逐渐认识到的价值。”[25]而天赋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矛盾上文中也曾提到过,人权有着如此多的漏洞,但为何依然成了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一大假设?这其实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人权宣言》本身就是“高度折衷过程的杂烩”,[26]是一个各方妥协的产物,而这种折衷在后来的革命发展中又显得如此的必要。不管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但自《人权宣言》把天赋人权奉为神圣后,就已经为历史作出了一个不朽的贡献:它体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的存在也是促使国家不断完善的力量源泉,因为被造物会在与创造者之间的妥协、冲突中不断地成长。人权本身存在的断裂折射的就是一个理想国家与现实国家之间的对立,所以即使“从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利益来看,为个人的权利进行辩护,也是极其重要的。”[27]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即使人权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人们也不可能因此放弃它。因为人类不是天使,“人不能被授以无监督的权力”,[28]所以人权是必要的。
尽管“人权的终结”揭示了人权理念与现实的鸿沟扩大了,但后来的人们也在不断试图弥合它。二战后,国际人权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人权观念几乎被所有国家接受,其内涵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从早期关于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个人权利进一步扩展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上,并出现了一些关于人权的国际协议,人权的国际保护似乎蒸蒸日上。然而一些大国却把人权作为在国际事务中挥舞大棒的工具,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在全球根据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利益来判断他国是否侵犯人权并恣意采取相应的措施——制裁或是发动战争,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人权的确实现了国际化,但是就“保护”而言却让人有点触目惊心。人权的现实遭遇与其理念本身的蓬勃发展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现在人权问题面临的状况不再是不被人提起,而是被人们过分“关注”,以至成了强国的一种政治工具,这离国际人权运动想要真正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初衷走得越来越远了。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人权从最初被人们提出,然后作为一个观念事实被人们接受,并逐步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以让更多人能够真正地享有这份权利,一路走来是如此的不易。然而路为什么却变得越来越难了呢?
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人权理念本身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这就给人权的实现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更为棘手的在于,人权本身面临的“异化”:它本来的目标是保护人的权利,然而在某些意义上却成为了侵犯人的权利的手段,它使一些军事干预非政治化,“使之变成基于纯道德原因而进行的对人道主义灾难的干涉”,[29]在普遍人权的掩盖下,这些军事干涉被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了。这种行为给整个国际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于是人权沦为政治上的一个吊诡:宣称人权的普遍性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⑥让人们觉得人权的那些内涵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事实上政府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加以阻止被允许的形式成为现实的可能,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的那些表层宣言都得到那些潜规则的支持,也为它们所限制。”[30]这让人权显得尤为尴尬,“维护人权”的口号在国际上似乎都显得很有反讽意味,人权的这些遭遇致使人权的实现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回头路了,人权从它提出到现在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思维方式,⑦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衡量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准,人们会参照它来努力追求自己应得的权利,一旦没有得到,就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变革。所以对人们而言,不能退缩,只能让人权的保护紧跟其上。如何让人权这个美丽的幻想成为现实,这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
注释:
①甚至缔造《少数民族条约》的英国代表奥斯登·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宣称,“《少数民族条约》的目标是成为使少数民族逐步准备融入他们所属的国家社群的保护措施和公平措施。”(C.A. Macartney,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London,1934,p.277.)
②就这一点而言,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巴西代表德·梅洛·佛朗哥(De Mello Franco)说得很明白:“我看很明显,构想这种保护制度的人并不梦想在某些国家里创造一个居民群体,而他们认为自己对于国家的总体组织机构来说永远是外国人。”(C.A. Macartney,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London,1934,p.277.)
③具体介绍可参阅[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版第377-378页。
④列奥·斯特劳斯对此做了一个解释,这里的诉求指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诉求,因为“它是一种只保护人身生命和躯体安全的诉求”([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87.),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是正义的,且“它的公正性是无条件的,因为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对它负责。”([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而这种诉求本身就源于暴力造成的死亡恐惧,他同时也指出,霍布斯从人的自然欲望出发,推出的第一个法律事实和道德事实就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后来才出现的“自然法”。
⑤柏克就曾指出,天赋人权确实完全独立于政府而存在,且是“以更大得多的明晰性和以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的抽象完美性而存在的;但是它们的抽象完美性却是它们实际上的缺点”。([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8-79页)。
⑥这里借用齐泽克关于幻想的一种假面具——空洞的姿态,来阐明这个问题。齐泽克认为,空洞的姿态就是指提供一次选择的机会,但选择的对象却是不可能的,是注定不会发生的。这种附着于社会秩序上的自由表象又是为社会系统所需要的,因为这种表象的崩溃会导致社会本身的崩溃,社会系统被迫要允许选择的可能,但是又要利用潜规则来阻止它的实现,潜规则本身一方面违反了公开的社会规则,但另一方面又会对公共法所允许的加以禁止,以此就限制了选择的范围(详细可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7页)。这样一种方式事实上为许多政府所采用,美国在人权问题的政策上无疑是对此作了一个完美的诠释。
⑦这事实上也是近代社会的一个进步,在之前的社会,人们因为饥寒交迫揭竿而起,但他们不知道以正义之名提出要求,因为在等级社会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尺度,找不到嫉妒的来源,但是近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人们都有一种生而平等的权利意识,对于享有特权的人就会存在一定的怨恨,感到社会的不公正。拉吉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社会公正与不公正的深刻感受纯粹是现代的产物。”([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67页)。
[1][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M].谢鹏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
[2][3][4][5][7][8][9][10][11][13][14][15] [23][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66、200、359、371、383、383、383、313-314、384、385、386、388、396.
[6][日]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M].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9.
[12][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M].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88.
[16][17][20][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81、78、81.
[18][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21][25][26][27][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60、65、66、66.
[2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
[2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8.
[28][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 [M].谢鹏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
[2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易碎的绝对[M].蒋桂琴、胡大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53.
[3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