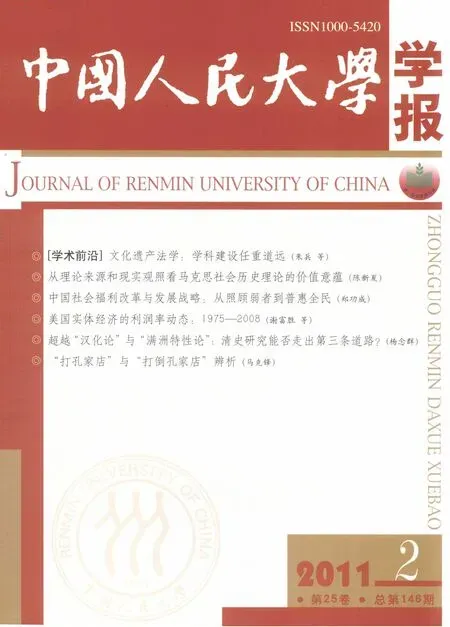玄学情性自然论与当代主体审美精神的建构
王小岩
玄学情性自然论与当代主体审美精神的建构
王小岩
魏晋玄学家会通儒道,以“自然”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原则与价值标准,建构了其情性统一的人格美本体论,即情性自然论。情性自然论对后现代语境中主体审美建构有着重要的建设意义:“情”的建构性功能表现为境界的提升和情感普遍性准则的呈现,“性”的建构性功能则更加关涉到诗性和智慧的层面,情性自然论由此成为当代美学主体审美精神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
魏晋玄学;情性自然;主体审美
玄学情性自然论是针对人生的价值意义问题来讲的,目的是对人格理想做一种本体论的解释。玄学情性自然论试图在现实的人生,特别是在情感之中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进入一种超越有限的、自由的人生境界,这样一种境界正是审美的境界。如果说先秦道家哲学和美学的联结主要在于顺应自然而取得自由,使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那么情性自然论与主体审美精神的联结则主要在于个体在人格理想上、在内在的自我精神上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目前,虽然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专门的探讨仍然欠缺,因此,本文试图从个体人格建构的角度来分析玄学情性自然论,并揭示其对当代美学主体精神建构的意义。
一
在中国哲学史上,“情性”真正作为一对反映“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本质特性,或人与生俱来的作为“人生之究竟根据”的哲学范畴而被提出,应首推先秦儒家孔门后学及老庄道家。《中庸》说:“天命之谓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儒家把“情性”视为“天”赋予人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即使是“明于天人之分”、强调外在教化的荀子也不否认“情性”为人受之于天的本性。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正名》)同时,儒家又对“情性”做了动静、内外以及“未发”与“已发”的区别。《礼记·乐记》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感物而动”的“欲” (情)有可能“不中节”,所以儒家希求通过静心寡欲、引导调节等手段达到与天地自然的同一。《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先秦道家的“情性”观不同于儒家,他们以“情性”指称人的真性或自然真实状态。张岱年说:“道家所认为‘性’者,是自然的朴素的,乃是所谓‘德’之显见。宇宙本根是道,人物所得于道以生者是德。既生而德之表见于形体者为性。人之本性,道家亦名之曰‘性命之情’。情者真实之义,性命之情即是性命之真。其中不含仁义、亦不含情欲。”[1](P194)先秦道家对“情性”做如上界定,所以对道家而言,作为“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情性”本身已经是一种真善美的和谐体,不存在区分并节制、引导损益的问题,而只有整体地护持、保养的问题。
到了汉代,董仲舒糅合道、法、阴阳、五行等思想,在先秦儒家由动静、内外、善恶论情性和道家以道德而言情性的基础上,以性阳情阴论情性。董仲舒认为,性为仁,生于阳,而情为欲、为贪,生于阴。性善情恶成了汉代最流行的学说。汉魏之际,有意志的天道观受到了桓潭、王充等人的批判而渐失其势,老庄的自然天道观日渐流行,天道观念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圣德法天、“圣人无情而为人伦之至”仍然是汉魏之际流行的学说。何晏、钟会等人所持的“圣人无喜怒哀乐”说,正是当时思想界实际情况的反映。
何劭在《王弼传》中记载了何晏与王弼关于情性的讨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附何劭)很显然,玄学家何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圣人存在着现实的情欲,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中国文化本是一种世俗文化,若没有现实的基础支撑,再玄妙的学说也不可能走向人间,从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王弼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再者,人伦范围的情性怎能不食人间烟火呢?即使是孔子也提出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并不否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
王弼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引入人性范畴,以“物性自然”的观点立论,强调人性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对此要因而不为、顺而不施。王弼在解释老子的“道法自然”时则说:“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违也。”[2](P65)将“自然”观念引入人性论范畴和美学范畴,并将其提升为价值尺度,是魏晋士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观念一经兴起,便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调整自己人生理想和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以及追求一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主要哲学基础和价值依据。
王弼认为,“圣人有情”,而有情无情之别则表现在应物与不应物上。说圣人无情,是因为圣人纯乎天理,圣明足以寻极幽微,故不以物累;说圣人有情,则是有见于情乃人的“自然之性”,为人格本体之原有部分,它与圣人的“神明”共同构成“性”之全而“不可革”。何晏因为看到了“凡人任情喜怒,违理”,所以主张“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王弼则从“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的“民之自然”中受到启发,大胆地主张以情应物,做到体用不二、性情为一。因此,他不同意何晏等人因圣人无累“便谓不复应物”,从而去其“自然之性”而认为“圣人无情”的观点。在王弼看来,“情”既然是人的“自然之性”,它感物而动就必然会产生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外在表现。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情与其众多外在表现形式的关系,就是本和末、体和用、静和动、一和多的辩证关系。王弼将“圣人”即完美人格的审美问题纳入“情”“性”的哲学思辨之中。
王弼所说的“自然之性”,即人的自然本性,人有自然本性,故“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据《晋书·王衍传》记载:“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王弼在《论语释疑》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正实而后言之不怍。”这段话实际上阐明了一个哲学道理,即荀融与何晏张扬的“寻极幽微”,也就是玄学的本体论,如果不能以人为本,建立在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认同与尊重基础之上,则只会成为一种失却人格灵魂与人生意义的“玄远之学”,是不会被士人与社会所接受的。这是王弼思想最值得珍视的亮点之一。它说明哲学的终极追寻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形而上的精神是以人的自然存在为前提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定形态下的人道情怀与人文精神。赞同王弼思想的西晋玄学家王衍公然指出,何晏所说的那种“圣人忘情”是士大夫可望而不可即的彼岸世界,人们宁肯要那种“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格,也不愿意去做不及人情的“圣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实际上是魏晋风度的人格宣言。
王弼将玄学本体论作为人格精神的形而上的依据,从自然作为人格精神的基本属性去立论。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对于情性加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儒家的情性观。王弼认为人性本静,性发而为情,他主张对情加以控制引导,在《论语释疑》中,王弼说:“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利而正者必性 (其)情也。”“性其情”的实质是要求情的发展合乎自然的规定,体现自然的要求。王弼通过会通儒道,为他的人性论与人格精神的建构做了坚实的铺垫。
循着这一方向,嵇康、阮籍等进一步突出了人性自然,在《达庄论》中,阮籍如是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之,游魂之变欲也。神也,天地之所以驭者也。”[3](P140)人生天地之中,“身、性、情、神”都是属于“自然”、源于“自然”,并且体现了“自然”的特性,亦即自然本身。他们认为现实的名教制度违背压抑了人性,必须予以评判。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论述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4](P261)王弼的圣人有情说尚未将人之情感与儒家之礼对立起来,王弼所言圣人“体冲和以通无”,意思是圣人能体道则天,故应物而不为物累。嵇康则明言儒家礼法所规定的行为准则违背了自然之道,若要行不违道,就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不受儒家礼法的束缚。他们公然“非汤武而薄周礼”,激烈反对学习儒家“六经”,“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要求超脱名教的束缚,全性养真,推崇自然人性。如嵇康认为:“马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耽此礼为矣。”[5](P261)所谓人的“真性”,就是“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须之理,吾所不易也。……夫论理情性,折引异同,固寻所受之终始,推气分之所由。”[6](P261)情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是人所具有的必然之理,亦即“自然”。这就将个体情感的表现与人格本体联系起来,换言之,所谓个体人格之本体,既非中和平淡,亦非仁义谦让,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一种观念的确立,为两晋六朝士人之重情、重个性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在此之前,先秦儒家虽然也肯定人情之不可免,但认为情感表现应限制在一定的规范之内,情必须服从于理,人的自然本性必须受种种外在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因此,在先秦两汉时期,理性主义和群体意识实际上成为理想人格的内核。只是到了魏晋以后,随着儒学的衰微和玄学人格本体论的建立,个体情感、自我意识才空前地突显出来,影响到士人的行为方式,就如魏晋风度的种种表现,尤其是重情、任诞等。
向秀曾就“养生”问题与嵇康展开过论战。嵇康《养生论》的宗旨是宣扬洁身自好,远离世俗;而向秀则在《难养生论》中鼓吹“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得”,将当下的情欲作为人生的最高存在,是不可加以抑制的。向秀的观点反映了西晋后期由于命运的转折、理想的失落,士人精神走向世俗的必然性。由此,郭象对王弼以无为本哲学的修正势所必然。郭象看到了王弼贵无论在生成论上的不足之处,他明确提出,宇宙万物都“独化而足”,事物本身就是其产生与存在的根据,不应再于此“有”之外去寻找什么存在的依据。“有”作为一种现象与存在,固然不能从自身获得自证,但它更不可能从“无”中产生。“有”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自身的变化中产生的,这种变化是无从知晓、倏忽自变的,是为“独化”。而“独化”的依据即是事物自身之理。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必然的,它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和消失。郭象将这种自生自灭叫做“玄冥”。“玄冥之境”的事物都由“迹”和“所以迹”两方面构成:“迹”指事物外部之形,“所以迹”指事物之“真性”;“迹”受时空局限,“所以迹”则没有时空限制,所以要“捐迹返一”,如此便会“理至”而“物性自一”。在郭象看来,“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人亦如此,“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人在与外物的接触过程中对于外物的选择 (“趣舍”)就是“情”。“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这是针对常人的。圣人因为无为、至淡,故圣人在与外物的接触中不会有情的表现,即“无情之情”。“有无情之情,故无为也。”郭象在注释《庄子·逍遥游》时阐释了其圣人的人格理想,就是尘世中的“逍遥游”,它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乌托邦,而是各得其所、无分大小的自足自乐。郭象在《庄子·逍遥游》的题解中申明:“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郭象直截了当地指出,性分大小虽殊,但只要放任情性便可达到逍遥的境地。郭象在注《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时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金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7](P240)“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8](P240)神人与世俗化的圣人是一致的,郭象强调圣人也好,神人也好,都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顺从自然,只要自足其性,便能够达到精神的至境。他在注“圣人无名”时提出:“圣人者,物得性之名耳,为足以名其所以得也。”郭象据此认为,圣人即神人,神人即圣人,其特征是自足其性,而不是凌超万物,睥睨一切。
二
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自然,不是机械论、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在中国哲学中,“自然”一方面是最高的存在本体,象征着生生不已的万象的和谐;另一方面,“自然”还是主体的精神存在和创造活动的准则、依据。《庄子·齐物论》推崇自然的“天籁之音”,将其作为审美的最高标准。至魏晋,玄学将自然与生命联系起来,从王弼、何晏经过阮籍、嵇康到向秀、郭象,以“自然”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本体的最高原则与价值标准,建构了情性统一的人格美本体论。
从此,中国思想史开创了对个体人格研究的新领域。情性自然论一反儒家要求人们“以情从理”、把“情”束缚淹没在烦琐礼法和神学迷雾中的传统,而是把“情”安放在自然人性的位置上,反对否定“情”的价值和割裂人“性之全”,不是使“情”从“性”或以“性”控“情”,而是追求“情性自然”,这正是魏晋玄学在人格论上区别于传统的最主要的标志。魏晋玄学从人格本体论的高度对“情”的价值的论证和肯定,为现实社会中的世俗情感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嵇康的行义不屈、阮籍的“歧路恸哭”、陆机的“华亭鹤唳”之叹以及“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自豪标榜、《世说新语》对“才情”的品题欣赏等等,都足以表现“情”的解放。人们不再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是以“任情背理”、“以情坏法”来张扬自己的人格价值。“即事缘情”、“缘情制礼”于是成了人们处理伦理政制等一切社会问题的新立场和新方法。魏晋南朝的“缘情制礼”,不但与先秦两汉儒家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要求上截然相反,而且在“情”和“礼”的内在含义上,前后也有质的不同。在先儒们看来 (特别是汉儒),“情”往往与“人性恶”的观念相表里,是指一己的私情,因而他们更强调“忘”及其对“情”的统摄:“礼”是外在于人的本性而用来束缚、禁锢“情”的,二者的对立性要远远大于统一性。而在魏晋人看来,“情”乃人的自然本性,一切外在于人的典礼之制,皆应顺乎人情,缘情叙情,二者的统一性要远远大于对立性。
情性自然论将与有限事物相应接的“情”提高到无限的境界,追求一种与无限合一的情感体验、抒发和表现,而这正是一种审美的情感的体验、抒发和表现。从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都自觉地将“情”提高到了极高的位置,从情感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陆机的《文斌》、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都无不将“情”放在中心位置。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将情性自然与文学审美融会贯通,开创了一种“纯文学的时代”。陆机在从“人的觉醒”到“文的自觉”的历程中,第一次从情感、修辞的角度理解文学,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生活信条化为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使真实的“情”通过优美的文辞得到无遮无碍、无拘无束的张扬。“诗缘情”昭示的这种情性美的回归,情采互映的审美呼唤,可谓前无古人,这与清谈、饮酒一样,共同构成魏晋人唯美的人生追求,也激起后人的千古景仰和追求。齐梁时代的文论家刘勰对陆机有“可谓先迷而后能从善”的赞语,暗示了刘勰本人对“以情论文”的前代传统也是心香供奉、有意薪传的。刘勰专设《情采》一篇,以“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从“情”和“采”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上来剖析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正是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的主要特点。钟嵘的“吟咏情性”进一步发展了“缘情”说,它彻底背弃了美刺比兴的诗学传统,标志着诗美观念的最后确立,标志着中古这个文学自觉时代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在“吟咏情性”的思想指导下,诗人们倾全力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在诗歌史和美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钟嵘的《诗品序》不但说诗歌是外物“摇荡性情”的结果,而且尤其注重“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9](P781)等等生活中深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事件激发下的“长歌骋其情”。“吟咏情性”即是通过诗歌的形式将情性对象化,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
可见,情性自然论所追求的“情”,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再是传统儒学所说的那种使“情”从“理”(礼法)的“情”,而是一种和个体的人格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情”。其实,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正是对情性自然的美学完成。嵇康对属于客体的“声” (诗)与属于主体的“哀乐”(情)做了区别论证,指出“心之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基于对客观之“声”与主观之“情”的严格区别而建立起来的“声无哀乐论”,以个体的超哀乐的无限自由的人格本体为艺术的本体,最为明确系统地论证了魏晋玄学的审美理想。
三
情性自然的人格本体论,其深层次的价值在于对人之生存的价值关怀。它关注人的自由和人格建构,这对沉湎于技术理性中的现代人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
现代人正遭遇着普遍的文化困境,这种普遍的文化困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道德、习俗、家庭等不再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外在强制力对特殊阶级和阶层的统治和压迫,而是通过技术理性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二是文化的统治所形成的物化和异化生存样态已不仅仅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越来越表现为现代人的普遍境遇。
这种普遍的文化困境不是人之生存的枝节性问题,而是直接涉及人类历史“轴心期”确立的历史意识或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危机问题。雅斯贝尔斯说,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文化和人类精神的“轴心期”,那时形成的自我意识、理性启蒙等“轴心期”的历史精神因素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原动力。尤其是中世纪之后,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契约论等精神整合与文化创造,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基本内涵的理性主义历史意识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这种历史意识或文化精神相信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相信理性及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理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和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增强都毫无疑问是对人作为宇宙中心地位的确证,理性构成人的本性。人性永远进步,历史永远向上,不幸和弊端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或时代错误,随着理性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终究可以进入一种完善完满的境地。
然而,这种包含着坚硬的绝对意识内核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在其自身内部就包含着冲突和张力,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和人之自由之间、有限的工具和无限的目的之间存在着张力和冲突。这种张力和冲突在20世纪规模集中地显现出来。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异化和失控发展,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均受到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面对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社会机器,个人的渺小感、无能为力感油然而生。理性不再至善至上,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转变成可以灭绝人寰的“技术恶魔”,人从自然的主人沦为技术的奴隶,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之自由的异化力量。
后现代语境中的我们沉溺于生产和流通、购买与消费、娱乐和享受等循环的链条之中,却遗忘了对自己自然情性的维护。我们面临着对自然“天籁”的失聪,我们的耳朵不再敏感于鸟鸣溪歌,倾听不到树叶摇落和雪花轻舞,没有对秋草哀怨和孤鸿悲鸣的同情。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色彩和形态的科技光源已经掠夺了眼睛对于繁星满月的热情和神秘,失去了古人“惊鸿一瞥”的诗意颤动。我们的视听沉浸在对以现代都市为中心的技术世界和消费市场中,我们的生命敏感和律动全然被理性目的和感性欲望所抑制和压迫。我们被淹没在合理化、标准化的文化工业中,成为一个个“伪个体”。我们被所谓的“大众”娱乐所垄断和操纵,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多尔诺所说:“歌曲的标准化透过群众的收听活动而将其听众安排在预先的队列中。”[10](P78)在强大的文化工业面前,我们实际上只能接受,“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供的东西心满意足”。[11](P133)“标准化”下的个体是一种“伪个体”,这种“伪个体”一方面向群众提供自由选择文化娱乐的假象,另一方面却为“标准化”本身的扩大市场提供最实际的服务。我们“千人一面”,没有个性。没有对个性的张扬和尊重又何谈人格的造就,又何谈生命的圆满欢畅?
面对此种精神困境,当代美学呼吁拯救被异化的主体,建构一个相对诗意和智慧的主体。
“情”对于主体审美的建构性功能主要表现为境界的提升和情感普遍性准则的呈现。从自然山水的情感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是魏晋士人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是其独特精神风貌——“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普遍地染上了山水之癖。他们不仅发现了自然山水“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形色声音之美,也由自然山水之境激发了他们“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人生之叹。诚如宗白华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12](P183)自然不再是道家“无限”观念的象征,也不是儒家“比德”意义上的情感寄托物,而是个体人格与自然永恒无限的和谐共处。陆机《文赋》的“物感”说首先揭示了这一变化,刘勰《文心雕龙》则对此和谐关系做了系统总结。如《神思》篇提出“神与物游”,《物色》篇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一方面是艺术家的心、气、情,另一方面是外物的貌、色、容,二者达到双向对流、平等对话的和谐状态。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模仿理论 (只强调外物对人的作用)和移情学说 (只强调人心向外物的投射)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境界,而是一种“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语)的和谐境界。在这种和谐境界中,审美活动维系着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准则,诸如同情心、恻隐之心、孝心、怜悯心等辅助美感的实现和完善。我们对大自然生命尊重和热爱的同时,也诗意和智慧地对待自我,这是人类对于自然和自我的爱心和同情心。在这种爱心和同情心中,主体从而保有了空灵飘逸的美感。
“性”对主体审美的建构性功能更加关涉到诗性和智慧的层面。处在欲望都市中的我们追名逐利,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心灵的境界提升。神秀的“菩提树”和“明镜台”的比喻昭示人们必须澄明自己的心灵,需要时时地“拂拭”,不使它染上世俗的尘埃。心灵境界的提升最关键的构成就是保存和恢复华夏民族的诗性精神和审美趣味,承接祖先的人文精神。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构成之一,就是生命存在中唯美主义理念的确立,它和诗意的生存形成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推崇的“晋人之美”是一种理想境界。换言之,“晋人之美”闪烁着唯美主义的光彩。这种唯美不仅仅关乎外在物象之美,更重要的是关乎主体的心灵之美。魏晋士人寄情于自然,如“竹林七贤”的“竹之恋”、支道林“重其神骏”的“马之情”、简文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生灵之爱……在纵情于自然中强烈追求着理想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自由,使得生命涂抹上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色调,个性人格辐射着自由、通透、澄明、潇洒、浪漫、豪迈的情致。
情性自然既是诗性和智慧,也是境界。它是生命的纯粹澄明、“逍遥以游”,可以打破知识和经验,超越逻辑和意识形态,进而拯救心灵被现代物质欲望的遮蔽,复活主体的审美冲动,恢复主体的审美智慧,提升主体的生命境界。
直面技术工具理性世界中主体的危机,高扬和强调人之自由和历史责任感,是现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的共同呼声。当此历史境遇,彰显着诗性美和人格美的魏晋华夏美学对于改变经济至上和消费欲望横行,彰显自然情性进而完善主体的审美趣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由此观之,魏晋美学的自然情性论理应成为当代美学建构主体审美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
[1]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4][5][6]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8]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0][11] 陈学明:《文化工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12]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李 理)
Metaphysical Incl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al Instinct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Aesthetics
WANG Xiao-y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Wei and Jin Metaphysicians amalgamated Taoism and Confucianism,they praised highly the theory of“Nature”as the ultimate value and standard of why we are human beings,and they formed the ontology of personality aesthetics,which was the unification of natural feelings and human nature.The theory of Metaphysical incl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al instinct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personality aesthetics,that is,aimed to harmonize this tens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This was a supplement to classical Confucianism which had laid too much stress on Ethical Code.This theory remains a useful reference in spirit construction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and naturally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Wei and Jin Metaphysics;incli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al instincts;subject aesthetic
王小岩: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