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又潮落:抗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文◎尚季芳
潮起又潮落:抗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文◎尚季芳
高潮 开发西部波澜壮阔
西部工业的变身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布局极不平衡,大的工厂企业基本集中于沿海各省市,偌大的西部之地则寥若星辰,几成工业荒漠。“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决策的确定和有关政策的制订,西部的近代工业才开始崭露头角。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战时经济体制确立,西部的工业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纷纷出炉。首先是沿海工厂的内迁。到1940年底,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厂矿共达448家,机器材料为70,900吨,技工12,080人。其中,机械工业占40.4%,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教育用品工业占8.26%,电器制造工业占6.47%,食品工业占4.91%,矿业占1.78%,钢铁工业占0.24%,其它工业占3.8%。迁往地分布在四川、湖南、陕西、广西等。这些企业的内迁和工厂的兴建,为这片久久干涸的荒漠洒注甘霖,凝结为西部近代工业的生命之躯,大后方的工业基础雏形初现。并且,重庆区、川中区、广元区、川东区、桂林区、昆明区、贵阳区、沅辰区、秦宝区、宁雅区和甘青区等若干个工业区域的形成,如群星闪现,曾经黯淡的西部工业之天穹,渐渐清亮而澄澈。
其中,重庆“虽是西南诸省中一个最优越的都市,可是它在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言的。它那时所有的工业,只少量的农产加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厂而已”。但抗战后,重庆工业迅速崛起,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集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器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基地。

当时,重庆的工厂、资本、职工、工具机设备的数量在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都具有相当优势,尤其是工具机设备和动力机设备几达一半。因此,重庆的工业不仅在四川,而且在整个后方都举足轻重,难怪乎有人称重庆为战时中国的“工业之家”。
不仅是重庆,就其它地区而言,新兴工业区和各省工业数量的增长,初步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西部地区的工业近代化正徐徐起步。诚如当时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所言:“这些能源工业推动了内地的工业发展,使原来十分落后的地域有了工业,就全国来说,最终使工业配置有了一定的改变。最为显著的是,今日成为十大工业城市的重庆市,就是这时奠定基础的。”
食粮衣料求自给
近代西部地区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支柱,而农业生产却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自然灾害频繁等颇为衰敝,频仍的旱荒又如恶魔般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存。抗战时期,东部沿海主要粮棉产区相继沦陷,西迁后的国民政府便面临着农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并开始意识到后方农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要“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达到“食粮衣料力求自给”。为此,国民政府积极致力于大后方农业的开发和投入:在农业改进方面,注重优良品种的培育,棉麦病虫害的防治,化肥绿肥的推广以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水利方面,要求须设“专门之机关与人材,作精密之考察,通盘之筹划”。此时的西部不仅有了大型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一些现代化的水利思想也初见端倪。其中,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功不可没,由他主持修建的陕西水利工程,从原料、设计、施工方法等方面都采取了现代化的标准。正如学者王敬成所言:“近年来,由于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的倡导,新式的农田水利在西北各省确已首屈一指,实际上在全国中亦能占到领导的地位。”李仪祉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是为陕西现代化农田水利事业之发端,亦是此项事业在华夏之滥觞。农业技术的改进,新品种的应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一片片西部粮田延展着,丰裕着,坚实了抗战胜利的物质保障。
交通之脉带动地方经济
交通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又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尺度。西部资源虽丰,但苦于交通梗塞,以致所有资源都无从开发,这也是近代西部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因此,国民政府决定把开发西部的首要目标放在发展交通事业上,使之成为发展西部经济链条上的首要环节。
就公路而言,国民政府在西南主抓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在西北则改善了西兰公路和修建了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国际交通线,并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西部重要的公路干线,7年之间共新筑公路11 675公里,改善公路88 901.5公里。抗战时期,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最终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网和西北各省区的公路网。在铁路方面,西南除湘黔线到抗战胜利建成外,其它完成的工程量不多;在西北,陇海铁路的延展和咸阳到同官、渭南至白水等轻便铁道的修筑,大大便利了战时陕西对外交流,推动了陕西社会经济的进步。
交通一如命脉,带动起沿线各地经济的勃然跳动。1943年10月《陕行汇刊》上载文指出:“西北方面的工业,因资金人员交通种种关系,渐渐兴盛起来了。陕西在西北各省中工业较为发达,尤以陇海铁路及咸同铁路沿线各县为盛。”宝鸡由战前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发展成为秦宝工业区中举足轻重的工商业城市,被茅盾称为“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烟囱;宝鸡城外,新的市区迅速的发展,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这一切,便是今天宝鸡的‘繁荣’的指标。人们说:‘宝鸡有前途!’”而到兰州时,又见“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在西南,滇缅公路筑成后,物资输送源源不绝,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而昆明则变身为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军事要地,交通的重要枢纽。抗战时期,许多在云南建立的厂矿企业如矿业公司、煤业公司、昆明炼钢厂、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工器材厂、中央电器厂、桐油厂、制茶厂、云南纺织厂等等,都是滇缅公路建成通车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加速近代化之步伐
由于战争残酷的炮火和西部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人们纷纷抛离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西北、大西南等安全区域。受到这些外力的冲击,西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变动和瓦解。首先就是人口的激增:1936年的昆明城市人口为14万人,1937年的成都和重庆的城市人口分别约为52万人、47万人。到了1946年,重庆、成都、昆明的城市人口分别跃升至124万人、76万人和30余万人。1939年人口为217 584人的西安市,到1946年人口已达549 199人,7年之间已增加了数十万人,甚至是战前的几倍,增长之快,可见一斑。在这些外来者的耳濡目染中,西部人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居民身上,如西安市“因各方面之日趋繁荣进步,长安古城,已成一新式都市。一般市民受环境之变迁影响,旧有习惯,亦部分随之改变。现今就男子蓄辫,女子缠足二事而言,在西京城内,已绝少见矣。同时女子教育,已趋发达,尤以小学为甚。随之而来之都市向有奢侈风尚,亦与日俱进。偶行大街,红男绿女,俨若沿海各大城市。至于吸食鸦片之瘾君子,因政府例行严禁,成效显著,过去之遍地罂花,现已不见矣。”甚至在僻远的西宁市,人们追逐时髦也不亚于西安。对西装革履、礼帽旗袍等新式打扮,“西宁城镇男女纷纷仿效”,“地方政界要员、绅士也以穿西服为时尚。30年代后期,中学生几乎都是新式的装束”。另外,此时的妇女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识字率与战前相比呈数倍增长。手中针绣已不再,却留书香阵阵。
是的,西部社会渐渐浸染了一些新思想、新风气,古老僻闭的西部大地吹来了一股近代化的春风。

◎抗战爆发后,云南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人口与物资激增
潮起 上下齐心推波助澜
1938年,《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开篇就指出:“经济政策应适应时代之需要,是以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凡对于抗战有关之工作,悉当尽先举办,努力进行,以期集中物力、财力,早获成功。”其实施的具体方案是推进农业、发展工矿、筹办工垦、发展交通、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例行节约等。据此,在那战乱动荡的岁月,国民政府的西部开发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纸面,即使在内忧外困、时局艰难中,也仍然步履蹒跚。就这样,西部开发的滚滚浪潮,便在国民政府和后方人民的推波助澜中,逐渐高涨起来。
国家力量的介入
如此耀眼成绩,国家力量的介入可谓一个重要因素。
在厂矿企业的内迁中,国民政府的策划和组织,为沦陷区的企业迅速转移大后方提供了条件。同样,在西部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的建设方面,国民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开发西部重工业为例:抗战前,西部重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数量少,而且水平低。抗战开始后,要在短期内建立起西部重工业的基础,单靠地方政府或民营工业,其孱弱的肩膀很难担负。这样,资源委员会便迅速地承担起了这项重大的建设任务。据1938年公布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1.创办和管理经营基本工业;2.开发和管理重要矿业;3.创办和管理经营电力事业;4.举办政府制定之工业。
资委会将重点放在了建立重工业和电力工业上,原因何在?据原资委会副主任钱昌照回忆:“资源委员会之所以不惜冒亏本风险,乃是本着举办重工业的原则进行的。资源委员会开始从事企业活动时,曾明确规定了经营范围,其中主要的是‘为国防所必需’,‘规模宏大,私人没有力量办,或虽有力量而由于经济效益上无把握不愿意去办的事业’,‘精密制品为自给上所必需’,以及‘目前无利可图的事业’。这些原则资委会是尽力贯彻了的。”资委会主任翁文灏也说:这些企业,不论“动力之来源,燃料之生产,钢铁之制炼,重大机器及电机之制造”,还是“大量水泥、肥料、食糖及基本化学品之生产”,“实为全国经济之根本,亦为工业化必需之基础,如不确为建立,则中国经济不易独立自存”。的确,在大后方,较之于风险小、资金周转快、获利丰厚的轻工业,重工业见利慢,利润低,甚至有亏本的风险,一些企业主很少问津,而这些企业又为国防所必需。因此,资委会承担这项任务乃大势所趋。
在具体举办的方针上,实行中央和地方合营,中央出钱,地方出力;企业由资委会全权处理,地方不过问,人事全由资委会配置;年终结算,利润各半分配,而中央所得到的50%仍保证用于地方兴办工业。对此,地方自然大多持赞同态度。很快,资委会就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和青海等处建立了厂矿企业,重点又在电力、工矿和冶炼等方面,“到战争结束时,厂矿单位共有121个,其中火力发电厂26个,煤矿19个、石油矿3个(玉门和新疆独山子等)、铁矿和铜铅锌矿4个、钨锑锡汞矿11个、冶炼工业37个,等等”。这些企业对于支援抗战和发展后方经济,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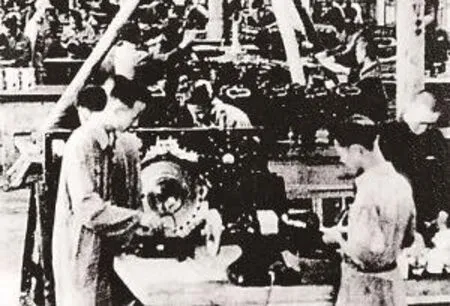
◎内迁到重庆的工厂正在加紧军用物资的生产
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持
西部画卷的铺展,自然少不了后方广大人民的心血描绘。日本侵华,群情激愤,广大人民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了。后方民众与前线士兵同仇敌忾,他们节衣缩食,努力生产,捐金捐粮,支援前线。四川省田管处处长甘绩镛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由南充到三台督粮,途中在路旁一家鸡毛店休息,遇着一个老年农民,便和他摆谈,我问他今年收成怎么样,他说,收成差一点,每天吃杂粮加苕藤,但还是吃得饱。问他上粮没有和有粮无粮。他说,该上的粮已经上了,邻居的粮都上了。再问他,你们自己口粮都有困难,那来多余的粮食交给公家?老人很质朴地说: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有命也不能拼。只要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老百姓能够过太平日子,我们暂时吃点苕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好多了。”
在四川,1941~1945年田赋实征共计8408万石。在云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滇西、滇南的一些重镇成了盟军的战略要地,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不仅大量供应盟军的食粮,还投身筑路工程。修筑滇缅公路时,民工们夜以继日,在崇山峻岭间挥洒血汗,徒手开凿,“星月风尘度新年,一段推进又一段”。据原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龙云回忆:“每天出勤的不下数十万人,轮班昼夜赶修。”众志成城,仅仅8个月时间,此路便于1938年8月全线通车了。这可是血肉筑成的中国抗战生命线啊!华夏内外无不为之一振,斗争的激情愈发高涨。
不仅如此,在抗战的硝烟中,一群务实的科技人员踏进了西部,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一丝现代科学的气息。他们深知科技发展为战争服务已成为主旋律,纷纷努力投身于生产建设和发明创造,1937年到1944年专利发明就共计423件。此时,科研主要侧重于军需民用,研制出了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棉楷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式回火管锅炉等。这些工业科技的研制开发,在学者黄立人看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锤炼和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自己的工业科技人才,也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近代科技体系与促进工业科技进步的制度。离开了战时工业科技的进步,就难以维系大后方经济和坚持抗战。智慧的珠玑涌动着,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闪耀光芒,赠缀亮泽。
潮落 西部开发再回低谷
潮起又潮落,国民政府的西部开发一度引发热潮,并在1942年达到高潮,但之后渐不如前,特别是伴随着抗战胜利几成定局,国民政府开发的热情遽减,各种开发、建设西部的活动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再回低谷。那么,是什么桎梏了国民政府的西部开发而终致流产呢?
国民政府力不从心
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届政府,财力支绌,捉襟见肘。国民政府也难以脱其窠臼。抗战爆发,不仅需要大批军费开支,而且要协助工厂内迁、复工,开辟大后方交通等等,无一不需要资金投入。财政支出在急剧上升,而财政收入却迅速递减,这种严峻的时局使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身心交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就一直处在财政赤字的漩涡中。

注:a、实收是指除债务和银行垫款之外的收入。b、现金结存除外的实际总支出。c、1938年度只包括1938年7-12月。
抗战八年中,国民政府年年都有财政赤字,并呈逐年递增之势。当然,战争不得不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这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但对西部开发而言,国民政府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势必制约其投资西部的力度。
以国民政府投资甘肃农田水利为例,1943年1月前洮惠、湟惠、溥济、汭惠四渠都100%完工,其它完工程度则由25%到80%不等。但此后情形更为悲惨,除肃丰渠外,其它都浅尝辄止。其实,水利建设一向乃国民政府西部开发的重要内容,《西北开发案》就对西北的水利作过精心统筹之规划。然而,事与愿违,处在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已无力投资,中道夭折不可避免。水利建设的投资即是如此,其它更是不言自明。
因人因时而变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开发西部颇为用心,亦对西部社会的落后面貌有所改善。然而,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西部的开发逐渐走上了穷途末路。究其因,还在于国民政府对开发西部缺乏系统的政策,总是因时因人而变,没有长远打算。由积极转向沉寂的滇缅铁路修筑正是如此。
滇缅铁路于1938年开始动工,进展速度缓慢。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华南大片国土的丧失,迫使国民政府加紧修筑滇缅铁路,以便打通西南国际交通线,保证国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进来。1940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给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电文中指出:“窃意滇缅铁路为今日唯一国际交通路线,现在公路每月运输不能达五千吨,殊觉缓不济急。近自三国成立同盟,英美双方之厉害已与我国完全一致。职意此路仍应赶紧筑通。”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极为迫切的筑路意志。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行政院抓紧了办事效率,在3月17日的行政院大会上,一致表决通过了《行政院决议通过滇缅铁路追加预算致交通部密训令》,加之宋子文在美国就修路事宜艰难交涉后,美国同意借款,这样,滇缅铁路便开工了。
然而,正当滇缅铁路的修筑大有进展之时,蒋介石却在1942年1月3日下令停止该路的修筑,提出“滇缅铁路工人可移筑中印路”。张嘉璈和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痛陈停止修筑滇缅铁路将会带来的损失和困难:“不独前功尽弃,且恐失信国际”,“又滇缅工人多为各县征工,实难移筑,中印必须另起炉灶”,“若新加坡不守,则印度海口亦成问题”等等,其言辞之诚恳,指点事实又切中肯綮,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在1月23日的复电中,态度有了改变:“滇缅铁路仍应如期赶筑,并加紧筹建”。但是1个月后,陈议上书蒋介石,指出:“滇缅铁路按目下情形,势难利用,而月需工程费六千万元,未免可惜。今日行政院会议多主张即行停工,将此项人力财力用于赶筑中印公路。”其“未免可惜”的论调,使蒋介石再次动摇了。3月9日,他在给滇缅铁路督办曾养甫的电文中说:“中印公路工程迫切规划,全线所需人力物力甚巨,滇缅铁路工程仍应迅即停工,将铁路人力物力移用于赶筑中印公路。”这样,滇缅铁路的修筑也就中途夭折了。
如此一项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工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系统的政策和长远的规划,而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胸无成竹,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使办事者无从着手。滇缅铁路沉寂的命运,亦在情理之中。
地方实力派的掣肘
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政策之所以不能完全付诸实施,与当时国内的形势息息相关。表面上,国民党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各地方实力派都集中于国民党的锦麾之下,效命于沙场。然而实质上,他们都心怀鬼胎,阳奉阴违。蒋介石与西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这种松散的政治联盟,时而凝聚,时而涣散,游移不定。与西北军阀之间,蒋介石以正统自居,时刻不忘分割、瓦解和消灭西北诸马(即以西北军阀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鸿宾为首的回族武装势力),统一国家。然而西北诸马长期以来形成的统治根深蒂固,封建势力在西北尤其在青海、宁夏极其顽固,中央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推翻其统治,无奈只得采取既打又拉的态度。
蒋介石难以有效地控制西北的青海和宁夏,中央政府的开发热潮在这些地区必然受到阻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措施大多集中在陕西、甘肃,对宁夏和青海开发的实践则寥寥无几。如截至1943年12月止,中国银行在各地举办的分支机构中,陕西14处,甘肃12处,而宁夏和青海则各有1处。同样地,1945年,交通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中,陕西12处,甘肃8处,宁夏1处,青海没有。在宁夏和青海,各银行所办的分支机构都比陕甘少,这固然有地理位置的关系,但其根本原因是,这两个省在马步芳和马鸿逵的专权独断下,他们不允许中央势力插手地方政权,唯恐蒋介石打着西北开发的旗号,向他们割据的地盘渗透,彼此都心照不宣。1940年,四联总处(即由国民政府成立的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的简称)要求中国银行西宁分行办理青海农贷,却因种种原因而停止,其根本原因是“据各方面议论,系马主席不愿骤办。其原因或系与其个人所放之高利贷冲突”。宁夏亦然,马鸿逵总揽宁夏的经济大权,“几乎把所有的存款、放款、汇兑、贴现等,统统垄断。中央派驻宁夏的其他银行,业务难以展开”。就这样,西部开发在虚虚实实、推推搡搡中时断时续。
此外,在西南,云南一直在龙云的控制下,中央势力于1946年前并未控制该省事务。西康省则在1939年建省后,其政府主席刘文辉将之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央势力很难干涉,致使境内许多事情走不上正轨。总之,抗战时期,如此不统一的局面,使中央政府的政令无法通达地方,开发政策和成效自然受到了限制。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国民政府的功利主义
国民政府的西部开发,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不仅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还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国民党政权是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始终以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为目标,并没有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反而高踞其上。
“我到了重庆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这样说,“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及兰州办的西北毛纺织厂,都有官僚资本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我并没有得到蒋政府的支援,倒为当时的大老板赚了一笔国难财。”1946年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在接见重庆中小工厂请愿代表时,一反过去提倡发展内地工业的腔调,竟声称:“现存工厂无论在资金、设备、技术各方面,都根本不算工业,不如任其倒闭。”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对迁川工厂请愿代表说:“美国机器这样便宜不买,而买你们的破破烂烂的机器,岂有此理?”“美国货种类甚多,价廉物美,而中国货又孬又贵,中小工厂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政府官员如此言论,民营工业难逃厄运便在情理之中。据1943年岁末对工业最发达的重庆一带的统计,重庆区324家大小机器厂,停工的有75家。18家铁厂有14家停炉,4家钢厂1家已停,其余3家勉强维持。国民政府在抗战的非常时期,虽然为民营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和帮助,但抗战一结束,这种有限的帮助也随之烟消云散,民营工业最终破产倒闭。正如民族资本家李烛尘所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回。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抗战时代一页伤心惨目之历史。”
抗战爆发,国府西迁。一度甚嚣尘上的西部开发如潮起又潮落——在国民政府和后方民众的齐心协力下空前高涨,却又随着抗战胜利在望,国民政府转移重心、撤人撤资而再次回落低谷……
(本文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吴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