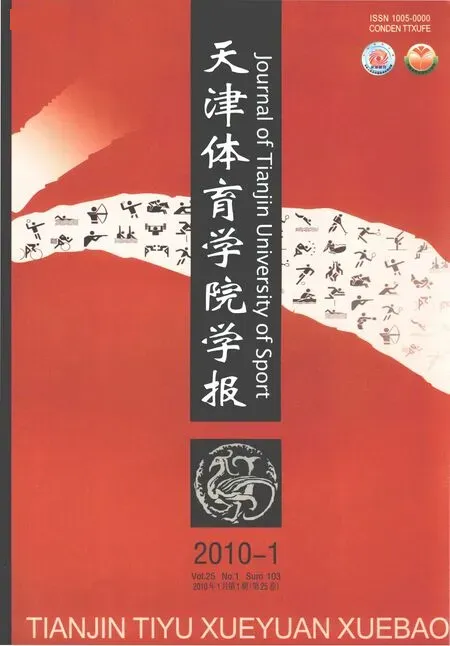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
——与布特博士的讨论提纲
袁旦
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
——与布特博士的讨论提纲
袁旦
认为体育学作为试图以理性把握人类体育整体的学科,因其目的和对象的非实体性,它应是一门人文教育理论学科,这是体育学存在价值和现代意义之所在。提出,体育学应在实践唯物论的人文主义基础上建树一种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的人文体育观,由此出发通过反思、追问、评价现实体育提出的基本问题,建构它的理论体系。并讨论了体育学的科学性以及它与人文性有机结合问题,指出作为人文学科的体育学,其研究和学习本身就是检验道德和锻炼、发展人性的过程。
人文体育观;体育学的人文性;体育学的科学性
1 体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
体育学是一门试图用理论把握人类体育的学科。这门学科19世纪20年代末就在中国出现,先后有体育原理、体育概论、体育教育理论、体育理论、体育哲学和体育基础理论等称,至今也不统一。但是,因为它们都是以人类体育作为研究对象,并且都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这个整体,所以我们把它们都视之为体育学。如此,体育学在中国构成了一个已有80年历史的理论流变过程。现在看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怎样理解或界定这门学科的性质,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左右着这门学科理论发展的方向,而且这个问题似乎还是人们并不一定自觉的问题。
我这样界定体育学的性质:体育学是以我们中国人用“体育”一词所指称的人的一种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因为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体育,实际上一个主要含义就是指我们心目中的人类体育的整体,所以也可以说体育学是以人类体育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如果我们接受对体育学性质的这种界定,则它的研究过程就应该是根据这种性质——人文学科——所规定的方向去发展它的理论,逐步实现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有的目的。因此,正确地把握这门学科的人文性,对它的研究和理论建构就具有重要意义。
把体育学界定为一门人文学科是基于人类知识现有人文学科和科学的分野,从而对其分类属性的一种判断。但是,现在也许在一些场合不论我们说体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或一门科学,都可能不一定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因为尽管有人始终把科学概念限定于自然科学,但更多时候、更多地方,科学一词在人们心目中其含义都是泛化的,它不仅把一切理性认知纳入其中,甚至把善和美的评价也囊括进去,何况现在国内外都有人把“人文学科”就称作“人文科学”的。不过,应该指出,尽管如此,所谓人文学科和科学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我们应该注意的重要区别。因此,这就使得我们明确体育学究竟是一门人文学科抑或科学的性质问题就很有必要了。
一般地说,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区别更像是一个对待研究对象的方法、态度或精神的问题。科学是把整个世界分门别类对其一个个局部进行认知的活动和由此建立的对世界的分科的理论知识体系。科学把对象(包括人文学科研究的人和人的活动)一概视为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在其外部进行“静观”意义的认知,静观其变,力求揭示作为客体的对象不受研究者主观方面干预和影响的、客观的、普遍的因果关系或规律,它主要是实证性的,回答对象“是什么”的问题。而人文学科则不然,人文学以作为主体的人为研究对象,是对人的各种主体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群,它所关注的是维护和发展关于人的权益的崇高目标、问题和价值[1]。因此,它不把也不可能把对象视为客体在其外部进行认知,而是研究者以一定知识、意志和情感或身心整体介入人的活动,对其进行内在的直接体验和认同,对它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它主要是规范性的,回答对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1]。所以,如果体育学是一门科学,则它当然是把体育这种人的活动视为客体,在其外部进行认知,揭示其客观的、普遍的规律,主要是实证性的,回答“体育是什么”的问题,是研究体育的“实然性”的学科。而如果体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则它就是把体育视为人的一种主体活动,研究者以一定知识、意志、情感或身心整体介入其中,对其进行内在的直接体验和认同,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主要是规范性的,回答“体育应该是什么”(当然也意味着要回答“体育不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研究体育的“应然性”的学科。显然,它的研究和学习就是对于研究者、学习者的道德、人性的检验、锻炼和发展过程。
2 作为技术体系的体育和作为主体活动的体育
可见,要把作为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体育学区别开来,除了两者关心和追求目的不同,主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和把握被我们视之为客体的体育和被我们视之为主体活动的体育这两者的不同。直言之,把体育视之为客体,就是把它视之为以历来人们创造的多种多样的身体运动这个集合为基础的体育技术操作活动体系。实质上,这就是把体育视之为一个无人称的技术体系。很多时候,体育就被视之为种种身体运动的集合。但是,把体育视之为人的一种主体活动则不然,它是把体育当作人们为使自己的人性臻于完善,运用上述那个无人称的体育技术体系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进行创造的活动。
这样,前者——作为科学的体育学的对象——就是一个有限的、固定的和实体性的存在,因而可以当作客体来研究的对象;后者——作为人文学科的体育学的对象——则就是一个无限的、无法纳入固定领域的非实体性的存在,因而无法当作客体来研究的对象。进一步说,如前者,尽管人们历来所创造的体育技术体系,不论是运动技术或管理技术,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内容和结构都是不断丰富、趋于复杂、处于动态之中的,但是作为既往的创造成果,总之是一个有限的、固定的实体,因而研究者就恒可以把它当作外在于自身的客体,在其外部对它进行科学认知,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或客观的、普遍的规律。而如后者,把体育视之为一种主体活动或实践,情况就不同前者了。在实践唯物论看来,人就是实践活动(人的主体活动)本身,所以体育作为人的多种多样主体活动的一种主体活动,就是人的多种多样存在形式或载体的一种存在形式或载体。并且,由于实践唯物论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所以体育当然也就是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多项规定域的一项规定域,也就是人的这种本质多种多样对象化或自我实现活动的一种对象化或自我实现活动。如是,体育便是人的一种向着未来开放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创造活动。因此,它同人的任何一种主体活动一样,根本无法回避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经由这种实践或主体活动把自己从“已是”的改造成“尚不是”的,那种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的无限可能性和主体能动选择的一面[1]。例如,人们对那个无人称的、有限的体育技术体系的运用和选择从来就是无限的,它们至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却从来没有任何两个人一样,并且这种活动越成功,其个性化程度也越高。所以,作为主体活动的体育这种向着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不固定性决定了它的非实体性。从而,研究者无法把它当作一个客体或实体性存在进行研究,而只能代之以自己一定的知识、意志、情感或身心整体介入,对它进行内在的直接体验和认同,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回答体育应该是什么,促使体育成为有效锻炼和发展人性的活动。显然,这也正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体育学的目的和对象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这门学科的人文性之所在。
3 以实践唯物论为人文体育观的基石
科学作为人的一种认知活动同一切认知活动一样,无法避免“见仁见智”的问题。所以,也可以说科学作为“实事求是”的活动,无法避免人们面对一样的“实事”(对象),却“求”(研究)出不一样的“是”(认识成果);这些不同的“是”分别以不同程度逼近着“实事”的固有之“是”,或者有的甚至谬误。因此,在科学中从来都把怎样去“求”、怎样去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视为头等重要的问题。科学尚且如此,在人文学科中,由于研究者要以自己一定的知识、意志、情感介入作为对象的一种主体活动中,进行内在的直接体验和认同,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从而回答对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究竟怎样就更加不可忽视了。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甚至完全左右了研究的方向、过程和结果。所以,作为人文学科的体育学一开始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要有一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认为,我们可以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因为,不论历史上的体育具体样态如何,人类的体育一开始和最终都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演化出来的。这是对人类体育进行研究、企图回答它究竟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绝对不能回避、始终都要重视的基本事实。其实,所谓以人类体育为对象,所谓把人类的体育视为人的一种主体活动(而不是一种技术体系),主要或者说其核心就是指的这个事实。所以,离开这个基本事实,很难想象研究结果能对人类体育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甚或根本也就没有体育学。体育学就是要找到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研究这个基本事实入手来研究人类的体育。而马克思的理论恰恰为此提供了一个坚实有力的思想理论基础。因为,马克思所提供的这个思想理论基础恰恰是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他把我们直接引导到最彻底的地方,即在人和动物相区别的地方来对人类的体育进行体验和认同,反思、追问和评价的唯物论基石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生活本身却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
这里,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了,显然体育作为人的一种活动与我们熟见的高等动物的嬉戏活动是有根本区别的。从生物生理上讲,人的体育活动和动物的嬉戏活动,都来自一种共同的本能或需要。因为,所谓需要乃是“生物体、人由于内部不平衡和与环境不平衡,为维持和恢复平衡状态而产生的一种动态依赖关系和倾向。”[3]所以,人和动物因体内营养和能量匮乏而失却平衡,就有摄取食物的需要;相反,因能量和体力的充盈而失却平衡,就必然产生以肉体活动方式耗散能量和体力来恢复平衡的动态依赖关系和心理倾向,从而引起肉体活动。这种本能需要是人类一切创造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特别是以身体运动方式来创造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身体文化,身体运动文化客观物质基础和它们产生的最原始的动力,它必然伴随人类的存在而存在[4]。但是,由于动物没有意识,所以它的这种肉体活动就只能是这种本能或需要引起的恢复平衡态的嬉戏,所以,这种嬉戏就只能是一种一再重复、世代如此、永远如此的活动,终究不过属于满足那种本能需要的与动物的生命直接同一的活动。然而,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所以当他一旦有了以肉体活动方式耗散能量恢复平衡态的需要,则由这种需要引起的肉体活动就成为他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而不再仅仅是满足那种需要的本能活动,就成为他的意志和意识借以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面向未来开放的创造自由的活动。因此,这种活动最初可能(或必定)只是动物般的嬉戏,但重要的是这种嬉戏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人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因而它最初就同动物的嬉戏活动在本质上区别开来,不能等而视之。尤其是,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在人类谋求生存的物质生产和其他种种活动的“彼岸”发展的、无止境的、不断丰富的、为生命自由进行创造的历程。人类的体育正是从这个历程中分化、产生的。这个历程相对独立于人类为谋求生存的“此岸”的活动而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挣脱必然王国桎梏奔向自由王国的伟大历程。马克思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体育的“彼岸性”。马克思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有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一个根本条件。”[2]因此,不仅让我们看到人类体育从根本上说,不是满足人和动物机体需要的本能活动,不属于人类谋求生存的活动,并且因此让我们看到体育在人类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它是内在于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的活动,是人的生命向未来开放的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创造人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活动。体育学的首要目标或任务就是要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发展出一种实践唯物论的人文主义的体育观,人文体育观。也就是说,要在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通过对人类体育的反思、追问,从而阐发出体育在人类奔向自由王国的征程中,在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或终极价值(自由全面发展)的全部实践中,所独具的为一切其他活动所不可取代的功能以及崇高的价值和意义。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让我们看到体育作为人的生命向未来开放创造自由活动的所谓“自由”的涵义,从而有可能真正逐步达到从理论上把握人类的体育。也就是说,如果以进化的观点来看世界,这个世界:从无机到有机,从有机到生命,从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直到人类的诞生,实现了一个自然进化的历程,人是自然界进化的最高产物;人类诞生后,世界又进入了一个人类文化演进的历程。在全部过程中,进化的每一新阶段的产物或物种都继承着以前阶段产物或物种的性质。但是,新的、更高级的产物或物种却只是因为具有了新的特质、属性才成为新的、更高级的;所以,只是新的特质或属性才是它之所以是它(而不是别的什么)的理由和内在根据,从过去继承的性质则都是外在于它的。可见,人之作为自然进化的最高产物的内在根据、特质或属性显然就是人之区别于动物(因而区别于一切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显然也就在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在于人的生命是向未来开放的创造自己的自由的活动。所以,如果我们不理解人的这种文化特质,不理解自由或自由自觉活动的涵义,要回答体育应该是什么,要从理论上把握人类的体育,其困难可想而知。而就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告诉我们:“……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
这里,马克思所说,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当然不能仅仅理解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为,所谓“种的尺度”就是事物(作为一个种)的一定的因果关系或规律对动物和人的活动的技术要求。而人和动物的这种区别固然十分重要,但仅此只说明“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因此,如果片面理解,则事情就如尤西林所说:“人因技术而进入远较其他自然物更为广阔的关系之中,但因此而统治万物却非人性,那只是动物性量的放大,人性的特质不在于人所能掌握的因果关系的力量,而在于利用这一力量协调、组织、照护万物,使自己成为自然界唯一不自私(超越自我)的生存者[1]。所以,人之为人的人性或人之超越动物的内在文化特质最终就在于马克思指出:“人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里,所谓“内在的尺度”当然不是外在于人的本质的那种为满足人的动物性本能的需要、禽兽欲望的功利性目的技术要求;而是人超越动物界、内在于人的本质的、无功利性目的的规定性;即按照美的规律为自由创造极致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人要追问和创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人以实现人性升华为本位的人文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因此,它不是一项可以测达的指标,而是人所追求的前赴方向;是“人的潜能现实化”(马斯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为创造生命美的极致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是促使人在美的向度上无限自由创造的力量,它使得人的主体活动或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就表现为:人在为创造生命美的极致的无限追求过程中不断“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即不断从对象返回自身来充实自己,使得人的生命过程成为他不断在人性臻于完善阶梯的新高度上自我实现的、审美的生命历程。难怪,尼采会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5]
可见,我们说人类的体育这种发端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主体活动、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或载体、一种人的本质的规定域、一种人的本质对象化或自我实现的活动,当然也是人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实际上就是人的自身),为创造生命美的极致的无限的活动,通过不断对自身的审美(从对象返回自身)来充实自己的活动。所以,它当然应该具有种种主体活动应有的性质,而不过是种种主体活动这种一般性质的一个特殊表现。体育学的研究当然应该这样从理性上来把握人类的体育应有的特殊性质,根据这种性质来发展它的理论。就是说,我们面对人类的体育,可以在这个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基本思维框架基础上,进而广泛运用哲学和现代科学的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反思、追问和评价它之对于人的生命和人性升华之所独具的、为人类各种其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功能、崇高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从而建构起一种实践唯物论人文主义的体育观,人文体育观,作为后续理论发展的前提,真正从理论上正确把握人类体育的基础。
4 生活现实要求正确的人文体育观
建立正确的人文体育观,这不仅是体育学理论内在逻辑的要求,更是生活现实的要求,现实的体育发展的要求。如果我们不以机械决定论的眼光看待社会生活中诸事间的关系,则我们一定可以发现,现实的体育是同人的生命存在以及社会生活相互决定着的:一方面,人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体育,他们便也创造了什么样体育中的自身;另一方面,人们的生命存在是怎样的,他们生命存在中的体育便也是怎样的。一方面,人们生活中有了什么样的体育,他们便也拥有了什么样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体育便也是怎样的。因此,如果我们以追问人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为旨趋的人文体育观理论来衡量体育的状态水平、它同人的生存以及社会生活状态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以一种广义的和连续的尺度看待这种关系,则我们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零相关。显然,体育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样那样的状态和相关关系进行反思、追问和评价,才有可能或有能力去分析回答和正确评价生活现实中提出的种种具体问题,并且种种具体问题不论具体内容如何,概括地说,它们不外是以下形式的基本的问题:一种体育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为什么是这样的;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中的体育为什么是那样的;为什么一种体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这样的;为什么一种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是那样的。
离开正确的人文价值观念和人文体育观,没有一种以活生生的人“为实现人性升华和自由全面发展”为本位的价值评价标准,面对这类基本问题要做出正确回答并发展出一种正确、有用的体育学理论显然是很难设想的。
5 体育学是人文教育学理论
以上这些讨论基本上是限于体育学的人文性而引起的。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源于古罗马西塞罗一种理想化教育思想humanitas(拉丁文),指古罗马时代成长为人,即公民(自由民)所必修的科目,后有人证明这种教育更早在古希腊便已存在。欧洲中世纪humanitas转为基督教服务,构成了基督教徒的基础教育,15世纪又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复活了。19世纪起,人文学科与科学严重分裂,到20世纪上半叶,人文思潮与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主流相对抗已成常态。有了人类知识的人文学科与科学的分野,人文学科也有了它在教育中不同于古代的地位和现代意义。现在人文学科的发展本身是有一系列分歧和争论的,但是正如《大英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指出,人文学科在它悠久的传统中,在一个基本点上人文学科倡导者们是完全一致的:人文学科应当为普遍教育和文科教育提供基础,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人文学科的教育是非行业、非职业性的,它关注的是促使个人成熟为人或公民(自由人),而不是使之成为某一特殊领域的工作者。因此,人文教育关心的是维护和发展那种人类权益的崇高目的、问题和价值表达艺术和表达技巧。并且,两部全书都有类似的说法:人文学科是文理学院设研究生院的学科分类之一,特别是美国高级名牌大学设有此种学科。
把体育学界定到人文学科中去,显然是意在使我们以理性把握人类体育的理论跻身于这类学科行列之中。因此,如果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则体育学在分类上便属于现代教育中人之成为人的教育——人文教育的理论,因而它与现代教育中为使人之成为各种专业劳动者的教育——职业教育相并立,属于后者即职业教育的基础。体育学这种分类属性和地位不仅决定着它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决定着它因受到的挑战而带来的机会。例如,恰恰在现代教育中国内外的情况都表明,在教育舞台上无功利性的人文教育与功利性的职业教育这两者的紧张对峙,后者对前者的挤压、排斥已成为现代教育中一种有害倾向,而且在某些地方体育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挤压和排斥,这种情况下,体育受到职业教育的挑战可说是最尖锐的,因此把体育学推到了与这种倾向交锋的前沿。显然,它直接为体育学在批判这种有害倾向中发展它的理论提供了条件,为它成为推动人文教育和整个现代教育健康发展积极力量提供了丰富的机会。
6 体育学的科学性
作为人文学科的体育学的人文性决定了它在人类知识分类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这门学科与科学无涉和它没有科学性。不仅如此,它同所有人文学科一样,都还必须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活动的科学性。因而体育学与所有人文学科一样也都具有科学性。我们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人类的体育从来就不是一种只同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目的、价值评价和选择相关联的那种“自由”的活动。换言之,体育不是可以“由着性子”蛮干的事情。这种活动必须遵从这种活动的客观的、科学的规律,即种种体育技术操作活动的客观的、科学的规律。否则,人在这种活动中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由。
从理论上讲,这一点在前面最初指出体育作为一种主体活动其实就是人们运用那个无人称体育技术体系,对自己生活和生命进行创造的活动时,就已经触及了。在讨论实践唯物论人文主义和人文体育观时,实际上已经深刻地论及了它。因为,人类的体育作为人之为人、人之超越动物的主体活动,用马克思的说法,它也是人“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活动(此处关系到了实践唯物论的人文主义体育观的核心)。人类体育与人类大多数其他实践相比较,一个显著的区别或特征就在于,它是人一方面作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把自身当作改造对象的活动,它属于实践主体与改造对象(实践客体)两者同一的那类实践活动。但总之,它还是同人类一切实践或主体活动一样,都是主体与对象(客体)两者相互作用对立统一的活动过程,而不是只有主体,没有对象的活动,不是或只凭主体的主观目的、价值评价和选择的活动。因此,在体育活动中也必须遵从两个尺度:一是,主体内在的尺度,即人的潜能现实化、自由全面发展、为创造生命美的极致的前赴方向或行动目标;一是,对象的外在尺度,即人作为一个种的存在其身体运动所必然存在的生物、心理、社会三大方面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科学规律,它们浸透在人的体育技术操作活动中成为必须遵从的外在尺度。人的体育活动必须努力遵从这两个尺度,这个努力过程就是力求使自己的这种活动与人的一切其他主体活动一样既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又是合规律性的活动。而这种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恰恰就是美的规律。而努力本身就是我们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自我实现过程。因此,离开了这种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性,人的体育活动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是什么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美的规律”。所以,体育学必须高度重视体育这种主体活动和学科自身的科学性。实现学科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两者的有机结合。否则,它就只能把体育这种促进人性健康发展的活动建基于低水平认知平台上,归于空洞的说教和妄动。
7 体育学人文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科学的巨大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深刻、全面的影响。科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东西通过物化成各种技术、通过对传统技术的改造,使人类各种领域的活动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手段从而效率大大地提高,出现了“技术科学化”甚至“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以及体育自身需要的共同作用下,人类体育也出现了一个至今不断进行的“体育科学化”趋势,导致了一系列体育科学(技术)新学科的产生,一个与现代科学体系逐渐密切联系起来的体育科学体系正在形成。
必须看到,实际上这一趋势是人类科学“分化—综合”规律在这个领域的表现,并且始终与体育学的产生、发展相关联。因为,当人类的体育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独立的实践出现时,它就成为一种研究对象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最初作为研究成果不论以何种名称或形式而展现,它们都是研究者企图用理性把握其整体的理论成果,只是一门学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体育学。而此后产生的新兴学科,其中一部分是随着体育的发展和研究从整体向其各个方面或局部扩展和深入,从原有理论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则是针对体育发展中出现的新事实、新问题的研究成果。显然,这些新学科不论与体育学原有理论是否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在性质上都是人们理性从整体到部分推进,企图全面、深刻把握人类体育所产生的成果。并且由于这些学科的分化产生更好地承担和取代了体育学在这些方面和局部的作用。因此,体育学这门企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类体育的学科,如果在这种不断变化、发展的条件下,不能不断地在新的高度、新的水平上对体育科学的新成果进行综合,达到新的高度、新的水平上把握人类体育的整体,则实际上这门学科就将寿终正寝,不论怎样修饰也不能避免人们将其归于无用之列。
但是,为了人类体育的前途,从整体上对它进行理性的把握,又始终是必要的。因此,这就需要不断进行综合,这种不断的综合就构成了体育学的发展过程。而这种综合本身就是通过这门学科的人文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合来实现:一方面,体育学提供的人类体育正确价值目标来规范和引导体育科学研究,促使体育技术体系在正确的价值取向上变得有效、更有效、丰富、更丰富,不断分化产生出新的科学成果(这不仅意味着使体育科学化不致遗忘或放弃以体育促进人性臻于完善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研究,而且还意味着体育科学技术成果不致沦为实现这种那种功利目的的工具,不致把体育科学技术这种文明成果当作对人的运动能力和社会资源实行野蛮的掠夺性开发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是体育学自身要不断地、及时地将体育科学研究揭示的科学规律、因果关系和新的技术置于有血有肉的有意识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动整体联系中、置于社会生活整体联系中(即把科学的因果关系和新技术置于更大的关系系统中),进行反思、追问来评价体育,来回答体育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从而阐发出人类体育对于促进人性健康发展、社会和谐发展之所独具的、为一切其他活动不能取代的功能、崇高价值和意义。这是今日我们所处的伟大变革时代体育发展的需要和呼唤。
[1]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6,12,26,5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96-97.
[3]李德顺.价值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848.
[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
[5]尼采.悲剧的诞生[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6.105.
Construction of Human SportView:Humanism and Scientificalness of Scienc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Discussion Outline with Dr.Bute
YUAN Dan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1,China)
Scienc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 is a subject which tries to rationally grasp the entirety of human sport.Because its aim and object are non-substance,it should be a theoretical subject of human education,and this is existed value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sport.The author proposed sport should establish human sport idea caring the ultimate value of human being based on the humanism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and to introspect,inquiry and evaluate those basic questions of practical sport,and to construct its theoretical system.In this paper,the scientificalness of scienc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humanism was discussed,the study and learning of sport as a human science is a process of examining moral and developing human being.
human sport view;humanism of scienc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scientificalness of science of physical culture and sports
G 80-05
A
1005-0000(2010)01-0001-05
2009-12-10;
2010-01-04;录用日期:2010-01-05
袁 旦(1939-),男,江苏人,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