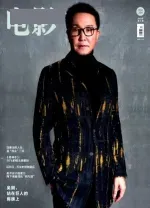关键词:性、黄色、傻子
文/谷静
性、黄色、傻子
文/谷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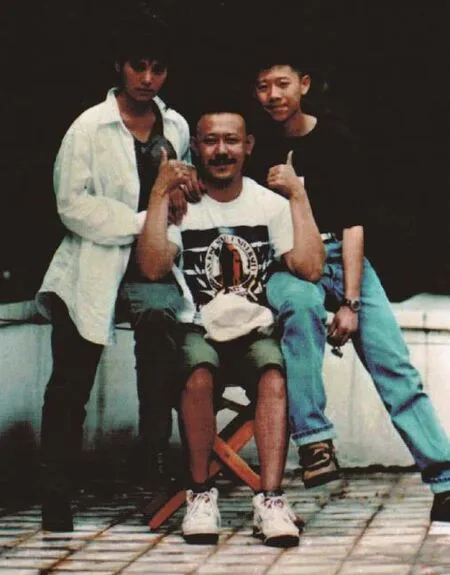
姜文和主演宁静、夏雨合影
王朔评价《阳光灿烂的日子》为“叹为观止”。
姜文评价王朔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都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是一个痞子,一个土匪两个核心组成的。不错,痞子文学以王朔为代表,土匪文学以莫言为代表。痞子目光专注城市,土匪则觊觎乡村。痞子文学形成的是有力的语言磁风暴,干扰了中国文学的思维方式,降低对自我的期望值,以抑为锋,然后以守为攻,进行此所谓的大打出手。匪气是从莫言的《红高粱》发端,其中包含着的爱我所爱的人性解放,正好迎合了八、九十年代一代“萎”中国人的精神。这里,痞子是一种解构,解构现有的秩序与传统;匪气是一种张扬,张扬一种人性的本能与原始。城与乡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殊途同归的集合,这基本可以说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特征。
中国导演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堪称是94年度全世界令人赞绝的、至今仍渴望观看的影片之一。它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全新的中国电影,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时代》周刊
王朔和莫言,都喜欢用走向青春期男孩的那种在情、性与爱中纠葛而觉醒的痛苦,来揭示出这个年龄段的复杂的欲望与冲突。比如《动物凶猛》,青春期的男孩,也就是马小军,只是一个小毛孩,但青春的荷尔蒙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肉体和灵魂,希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在这样膨胀的激奋冲击下,他渴望在“中苏战争中成为一个英雄”、渴望在群架上成为痛殴对手的骨干、成为有勇气从大烟囱跳下的好汉,更希望博得女人的青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仍旧是个男孩,一个还未完全发育好的男孩。影片里,宁静的丰腴性感成熟在言语、酮体上都衬托出马小军的孱弱,这种客观的不平衡,使他的内心产生了自己的莫名,转而诉之于武力,延伸自己的强壮,获得对世界的主宰的慰藉。所以,电影虽然改写了原作中一些残酷的场景,却选择性地保留了马小军最后强暴米兰的场景——这是一种青春期痛苦无处发泄而最无能的作为和表现。
姜文说他并没有想拍一个“文革”片,只是如果他和王朔这些人在写一个男孩变男人的过程的话,那他们只能写那个时候。6万字的小说改成了9万字的剧本,对比之下不难发现电影更侧重于表达一个青春期模糊的爱情故事。小说里爱情情节固然重要,但是着力表现的,是70年代里一群“大院里的孩子”的躁动青春。但那种红色年代里的阴暗故事,都是王朔与姜文成功表达了的艺术印象。庆幸的是,无论是王朔与姜文都没有把它归咎于时代,这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而是跳出到人性本能,以平静、反思的心态进行了正视。每一个男性导演,无论国内国外,由于这种通性,都愿意在自己表达手法成熟的时候去追忆一部在特定环境下的“马小军成长”的故事。将这两部作品的名称连读,动物凶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套用下现在大俗的网络语:你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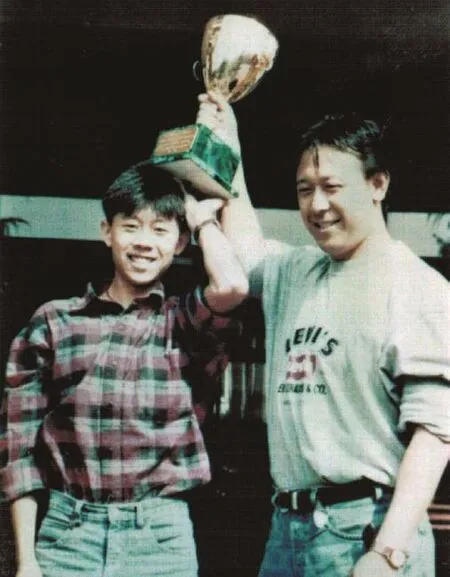
夏雨因主演《阳光灿烂的日子》而获得威尼斯、金马在内的诸多影帝
性的彻底完结
《阳光灿烂的日子》,被定义为一部有关青春,有关成长的电影,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那个无人顾及管束他们的年代里,在北京城横冲直撞的故事。而青春或者成长,无论哪个年代都离不开男生女生,对性的好奇和萌动。于是,于北蓓和米兰,这两个女性角色担当了这一任务,而她们两个将原本属于个体行为的对性的追求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
当于北蓓在其他伙伴的嬉笑声中强吻马小军,马小军极力拒绝,最终马小军脸上红红一片而于北蓓气急败坏的时候,影片对性进行了第一次嘲讽和瓦解。对于马小军这个对性略觉神圣与神秘的半大孩子来说,性竟然成了一种强迫进行的集体游戏。于是在马小军的眼里,于北蓓成了一个毫无神秘性因而毫不美丽的单调的性的对象。在她那里,马小军找不到一点他所渴望的“美丽”的东西。
米兰“干呼万唤始出来”的出场给了马小军以极大的神秘感,在他眼中,米兰成了他自视是由自己独自寻找到的美丽高贵的暗恋对象。然而最初的神秘并没有给马小军以长久的可以守候的美丽体验。由最初不敢看米兰熟睡中无意暴露出来的身体;到看着身穿大块暴露的泳衣的米兰,说她“肥”得像刚生过孩子的妇女而朝她丰脓的屁股踹上一脚:再到他最想要强暴米兰……马小军一步一步陷入对性的谜惑与失落之中,美丽的外衣一层层地被剥落,性不过就是欲望。
尤其当“彪哥”这个黑社会大哥以米兰的昔日情人身份出现时,尽管马小军仍旧毫不犹豫地拿起刀子想保卫她,但米兰的美丽与神秘已经开始破碎了,因为米兰根本就不是纯洁的;当刘忆苦公然以米兰的男友自居时,马小军终于明白,米兰从来没有和他好过,她不过是他的暗恋甚至是意淫对象。于是,“强暴”这种最拙劣最无能的满足性欲的手段被他使用,可用这种手法去获得实际上摧毁了他心理上最后那点残留的美丽:当情况变成米兰大叫“你觉得这样有劲吗?”,马小军歇斯底里的喊道“有劲!”。性,无论是美丽的还是肮脏的,都离他远去。
就像那只充满了气的、在空中像炮弹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它那么直接与无所谓,可以在空中荡来荡去而显出莫大的自由;它那么不可遏抑,由一只小小的橡皮套子膨胀成一枚横扫千军的炮弹;然而,它又是那么无意义,因为仅仅竟是一个小眼儿导致了原本觉得很宝贵很神圣的生命的诞生。
当马小军穿着米兰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条鲜红的游泳裤站在高台上的时候,与其说他是要再次向米兰证明自己以求最后的美丽,不如说他是要彻底摧毁自己的美丽的幻想。他绝望地从高台跌落入水,在池中沉浮,那一刻马小军再也没有什么美丽的念头了——他再次游向了米兰、刘忆苦、于北蓓这些他曾经拒绝过的人,他渴望再次融入他们,然而结果却又是摧毁:千万只脚一次次踏下来向他宣告他彻底的孤寂。他甚至没有能力去获得庸俗大众的认同,成了孤零零的人。
就这样,对性的瓦解完成了。马小军由拒绝庸俗的性到追求美丽的性再到美丽破灭而拒绝庸俗最终彻底绝望——这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性的摧毁的全过程。

经典台词

1影片开始,成年马小军旁白:“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她已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眼前一阵阵发黑…… ”
2成年马小军旁白:“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
3胡老师向外面的学生呵斥:“给你鞋?我给你穿上!滚!你们这些害群之马,不学无术!”教室外面的学生向胡老师说了一声“好,你等着!” 胡老师:“咳!笑话,我等什么?你还能把我怎么样?难道你会叫人打我吗?你扎我的车胎,你暗害我不成吗?(胡老师把鞋往外扔)啊!我们没人稀罕你这只破鞋。”
马小军:“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中苏开战,因为我坚信,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
4成年马小军旁白:“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构了。……我一直以为我是遵循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可我还是步入了编织和合理推导的惯性运作。……我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情不自禁地把一切擦得锃亮。”

《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疑是90年代中国影界的意外之喜。它带给观众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闲聊调侃,也不仅仅是对特殊年代的追忆与讥讽。当观众深深地为影片打动时就会发现,这部影片所展现的竟是一个意象丰富、意味深长的“社会一个人”、 “文化一心理”图景。
——影评人陆镜
黄色里的阳光
康定斯基在他的《论艺术的精神》里说暖色意味着接近黄色,暖色向观众逼近,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体会到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影片以黄色为基调,它像黄色老照片一样,呈现在眼前的一切会把人带入金黄色的回忆中,那是一种对自己青少年时光的暖洋洋的记忆。现实生活中人会有很多痛苦和忧伤,但这种温暖可以一定程度上抚平伤口。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多的是给观众增加温柔和美好的记忆,让人可以记住许多个傍晚马小军在北京近代楼群的上空游荡的情形,夕阳西下的黄色海洋把所有的忧伤和痛苦都淹没了,只留下对天真烂漫的美好回忆。
黄色如果长时间注视,会使人感到心烦意乱,刺激骚扰,让人显露出急躁粗鲁的本性。用黄色来比拟心境是一种狂躁状态,一个疯子总是漫无目的地到处袭击人,直到他筋疲力尽为止。从某种程度上讲,《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黄色主要是其主人公马小军心境的一种外射。它告诉我们主人公温柔记忆的同时还心存狂躁不安。马小军上镜头的第一句台词:“我操!”他的桀骜不逊和离经叛道表露无疑。当他和伙伴骑着老式笨重的自行车驶向暗黄的街头巷尾,那种不顾一切又不屑一顾的眼神清楚宣布了,偌大个北京城就是他的王国,他可以为所欲为不负责任且惟我独尊——他挥霍着自己那充满阳光的青春:跟伙伴一起打群架,并且拿起红砖砸向对方而面不改色、随随便便地开人家的锁……
某天打开了一扇房门后,他发现一张穿泳衣的女孩照片,从此他全心全意死缠烂打。这里充满青春期的骚动和歇斯底里的渴望,其中不乏粗鲁的强暴,但与道德无关。然而他的爱情总是遥不可及。这种苦闷与狂躁使他在阳光充足的黄色之中迷失了方向。他背离他的伙伴孤独的走向自我。他孤立伙伴,伙伴也孤立他。于是出现了游泳池那一片浅蓝浅蓝的水域。这是马小军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忧郁点缀。
蓝色是冷色。是离开观众向自身的中心收缩,在蓝色中感到一种对无限的呼唤。对纯净和超脱的渴望,蓝色是典型的天空色,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宁静,蓝色越浅,也就越淡漠,给人以遥远和淡雅的印象。显然,马小军的天空不是蓝色的,那仅仅是生命中某个时刻的停留,并且还是很浅很浅的那种。当马小军六神无主地爬向那高大无比的跳水跳台时,他顿时变得安静无比并且缠绵悱恻起来,爱情原来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情。平时天马行空的口若悬河这时候很遥远很幽深,当然,也很忧伤很悲凉。
黄色又是典型的大地色,它从来没有多大的深度,也无表达深度的能力。王朔的原作小说《动物凶猛》没有承担揭示深刻意义的义务,姜文改编的电影剧本《阳光灿烂的日子》同样也没有。所以我们也不要在马小军身上挖掘什么深度内涵和反思。
影片结尾也意味深长:现代化的北京,还是那些伙伴,却在豪华的轿车里,在一片黑白里。白色带来巨大的沉寂,像一堵冷冰冰的坚固的和绵延不断的高墙。基调是黑色的毫无希望的沉寂。黑与白之间诉说的是现实的我们,沉寂又毫无生机。只有那“阳光灿烂的日子”才是心的向往。
但黑白只是点缀,充满了亮晃晃的黄色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热情洋溢,精神焕发的,在温暖的海洋里体会到的是马小军青少年时期妙趣横生的点点滴滴。

姜文和获奖的夏雨
一群“傻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个傻子,一共只有三句台词:“古伦木”、“欧巴”和“傻B”,而他似乎无处不在——终日在有警卫站岗的部队大院门口傻笑,他呆滞可笑的脸上永远带着一些污垢,他总骑在一根木棍上面高叫。马小军在大院门口等米兰时有他;米兰约马小军晚上一起玩的时候也有他;更多的时候,傻子是在画面中闪过或作为一个远景样的道具——这种无处不在向观众暗示着,傻子必然与马小军这群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傻子经常出现在哪儿?部队大院门口,也就是马小军那帮人的家门口。还有影片结尾处,已经成人的他们路遇傻子时的兴奋甚至是亲切,不得不让人相信,他们认为傻子就像其他的哥儿们一样伴随着自己的成长,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尽管在大多数时候这个成员并不与其他成员一起活动,只是作为一个事件的旁观者,但这种群体的认同感却是不能抹杀的。
然而,马小军们却不知道,傻子其实就是自己的抽象:马小军就是傻子,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傻子的分身。每当这群小伙子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时, 那个骑着棍子的傻子就会出现,用这个符号直接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这是一部表现一群傻子的生活历程的影片。
傻子那三句台词“欧巴、古伦木和傻B”,短却意味深长。“欧巴和古伦木”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会这么问,因为语意太不明确,却又被无数次提起,仿佛是马小军他们和傻子的密语。根据考证,这可能是来自一部当时在中国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中抗击法西斯战士的接头暗号:
甲:“古伦”
乙:“欧巴”
甲:“消灭法西斯”
乙:“自由属于人民”
这样的对话不用多说,你也知道是符合少年马小军那个时代的特色。末了,到了结尾长大成人的他们开着豪华轿车在八十年代北京才有的立交桥上路遇傻子而冲傻子高呼“欧巴、古伦木”寻求一种亲切感时,傻子脱口而出的一句京骂则又是一种新的话语时代表征。
一个傻子仅有的几句语言由神圣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集体语词转变为一句市井人物的公众骂语,这种意味展现的也许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和社会中个人的历史文化变迁。而由《阳光灿烂的日子》优美情调所表现的略带滑稽的话语变向无疑就是一种由神圣到世俗,由集体到个人的摧毁与瓦解的过程。这样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欧巴、古伦木就是傻B。”
话语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傻子。建国初期他就在有战士站岗的军队大院门口傻笑着高呼“欧巴、古伦木”;几十年过去,他又穿着西装、骑着木棍在现代化的立交桥上不屑大骂。可以说这个傻子其实是导演最希望大家看到的。每一个人最终都变成了傻子。在小混混中叱诧风云的“小坏蛋”,在与马小军他们喝过酒不久便被别的小混混打了,成了生理傻子。控制马小军他们,掌管大局的刘忆苦,最后在打仗时震傻了头。马小军最终被大家孤立了,在游泳池中不断遭受着集体无情蔑视的攻击。米兰成了空有美女外型的泼妇,毫无自尊可言……
年轻的时候,这些傻子们就生活在“无”里。没有学习,没有父母,没有性,没有工作,没有勇气。长大了他们依旧生活在“无”中。当大款马小军在豪华轿车上因为一句傻子的京骂而快乐地大笑时,一切意义都消逝了:轿车,洋酒,西装革履,美丽,神圣,价值,性,集体。他们从来都是生活在“无”中的傻子。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从“傻子向傻子回归”的过程。起点与终点唯一不同的也许只是对“无”的态度:在成年的傻子看来,“无”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无”就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因为面对“无”他们已经能够放声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