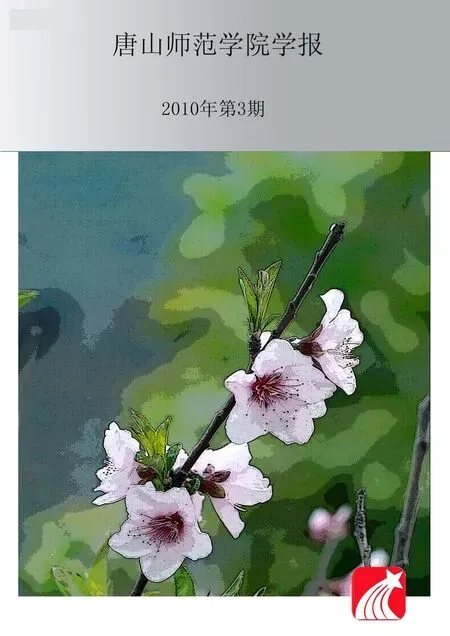认知视角下探析中国相声的制笑机制
王 龙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一、相声研究的简要回顾及评述
相声表演已经具有100多年的历史,不仅观众而且表演者和创作者们都惊叹于其魅力。就写作技巧而言,《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1]以及马季的《相声艺术漫谈》[2]具有代表性。近些年来,纵观相声研究的论文,其理论成果甚微,特别是从语言学视角的研究较少。高玉兰[3]基于格莱斯的合作原则CP研究相声,认为违反四个准则是相声幽默效果的关键。陈金中[4]从前景化视角研究相声中的幽默,认为语言偏离(linguistic deviation)是相声表演的主要技巧。向小蕊等[5]通过框架转移(frame-shifting)理论研究相声中的“包袱”(package),分析并提出了词汇误导(lexical misleading)是导致框架转移的原因。彭有明[6]从原型范畴(prototype theory)理论视角研究相声,认为相声创作充分利用了认知语境原型效应中的典型或非典型形式,使它们以及以它们为语用前提而推导出来的结论之间形成一种极大的矛盾(contradiction),或极度的不和谐(incongruity)。谢峰等[7]从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视角做了研究,认为相声中的幽默在于错误推理表面上的合理性(rationality)。
由于相声研究的历史不长,其理论成果还不十分丰硕。许多文章和专著也是局限于其类型和特征的研究,很少有研究涉及到其制笑机制,特别是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的讨论;尽管高玉兰从合作原则研究相声中“包袱”的形成,也主要限于描述层面;还有学者从关联理论视角进行研究,但并未涉及到相声中笑的动态生成过程,除此之外,对于听众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的参与在相声的互动及理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本文的研究框架描述
近年来,关联理论[8]和框架转移理论[9]被广泛应用于幽默研究。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相声表演中的双方处于不同的认知语境中(cognitive environment),他们对于双方交际话语的最终理解大相径庭,这种认知过程如何动态地发生并被听众所领会?框架转移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对于新旧信息是如何对比,听众是如何以不同于交际者意图的方式感知(perceive)话语,提供了动态的交际过程?本文正是基于这两个理论的互补视角,寻找相声制笑机制的认知过程。在交际中人的认知倾向是付出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在相声理解的第一阶段交际者受这种认知倾向的支配,在甩出一个包袱之前要做一定量的铺垫,使听众在大脑中先形成一个可以通过较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关联的初始框架(initial frame),得出对话语的显性可及理解(overt accessible interpretation),而相声交际者清楚听众的这一认知倾向故意偏离最可及的理解,直至笑料(punch line)的出现,从而得出隐性解释。究竟是什么造成前后的框架发生转移?本文认为一是交际者话语的不确定性;二是听众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反差产生前后的不一致;话语交际者利用人们认知的最大关联本能,巧妙地释放认知迷雾,诱导人们先沿着最大关联进行思考,然后再出其不意掀翻最大关联,指向最佳关联。三是交际者隐藏意图(covert intention)的成功暴露,即显性意义(explicit meaning)转为隐性意义(implicit meaning)。
三、中国相声制笑机制的认知过程
(一)交际话语的不确定性
格伦迪指出,在交际中我们很容易根据说话人所要传递的信息得出推论。我们所听到的话语通常是不明晰的,可能不止一种意义。我们所得出的推论更接近说话者所要传递的可能意义[10]。在相声表演中,说话者为了达到逗笑听众的目的,刻意改变他的话语,随之交际意图也发生变化。对于听众而言,首先他形成一个和他们当前交际话题相关的初始框架,由于交际者话语的改变(通常出现于相声表演的后半部分),听者起初形成的框架会和后面的交际信息发生冲突,以至于开怀大笑。如:
马:长这么大个子,就是不忍心看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
杨:可真是善人哪!
马:没害过一个性命,墙上有个大蜘蛛,“叭叽”一声掉地下啦,把它踩死?
杨:可以呀。
马:我马善人不忍心哪!
杨:连个蜘蛛都不踩?……
马:甭说是蜘蛛,就是打我身上翻出个大虱子来,这应当怎么样?
杨:挤死!
马:又损啦!那也是个性命啊。
杨:那怎么办哪?马:不论看见谁,往他脖子上一搁,嘿!善嘛。杨:啊?!这叫善哪?这叫缺德。(马三立,杨少华《开粥厂》)
表演一开始,双方就聚焦于一个叫“马善人”的角色,他很善良都不愿意伤害诸如鱼、蜘蛛甚至臭虫之类的动物。当提到身上的臭虫时,马说他不想要伤害它,如果把它拍打在地,它注定会死。因此杨就会质疑马将会怎么做。事实上这也是听众们所想要知道的。在马回答之前,听众们始终认可“马善人”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仍就不清楚他多么的有爱心,即使在前面部分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后来马回答他会把它放在别人的身上。当听众们听到这里时,他们起初形成的框架就会转为一个不同形象的“马善人”。
(二)听众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之间的反差
Sperber等[8,p4]认为如果话语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听众只需要付出最小的努力。在大多数相声作品当中,话语通常包括两部分:开始部分通过双方的交际,听众基于最大关联形成对当前交际话语的认知假设,进而形成初始框架;随着交际的深入,到交际的后半部分直至笑料的出现,听众得到对话语的最佳关联,从而形成了新的认知框架。因此听众对话语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理解的偏差导致前后认知框架的转移。以《找舅舅》为例:
马:那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就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第一天,我们去那个轧钢厂,去一个车间,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了两个多钟头。
唐:对了,工厂太大。
马:那天我们去那化工厂,由车间到办公室,我们骑自行车去的。
唐:工厂大嘛!
马:那天我们去那机械厂,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是没到北门。唐:这玄啦!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啊!马:啊,中间挖沟过不去啊。(马季,唐杰忠《找舅舅》)
从相声表演的前三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厂确实很大。马先生给听众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推测第三个工厂究竟有多么大,于是听众就会把当前的语境信息和前面话语联系起来,从而得到最大关联假设;基于这样的假设,听众的头脑中就会形成有关于机械厂规模的初始框架。既然马先生说到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是没到北门,听众就会在思考那也许会有更好的方式穿过工厂,最后话语却出乎大家所料。因而,听众根据交际语境的发展所形成的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对比不仅仅引起前后认知框架的转移,也反映了相声表演中制笑的动态交际过程。
(三)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间的对比
关联理论[8]认为从显性意义得出隐性意义,必须经过两个步骤:先得出隐含前提,然后再推导出隐含结论,他们都涉及语用推理。在相声表演中,说话者正好利用了交际中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的区别,使听众基于话语的显性意义建立初始框架,到后来又揭开隐性意义,听众因此而要根据新情景从新考虑调整自己的初始框架。
马:我爱人就要生产了,我赶紧跑到医院,就见值班大夫有七、八个人,都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有四个坐着围着一张桌子,其余的人站在后边看着,都是聚精会神的,我想这是干什么哪?
郭:也许是开会哪。
马:不像。手里拿着许多硬纸片儿。郭:也许是病历表。
马:不像。上边有黑点儿、红点儿。
郭:也许是病人的脉搏温度和大小便的纪录。
马:我赶忙走过去:“请问今天是那位大夫值班呀?”就见坐着的一位冲对面戴眼镜的说:“六十五!”
郭:哦,原来对面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叫刘世武。马:我说:“刘世武同志,今天您值班呀!我爱人要生产啦,请您去一趟吧。”这位同志没理我。
郭:为什么?
马:我又说:“刘世武同志,我爱人要生产啦,请您跟我走一趟吧。”
郭:他说什么?
马:刘世武向旁边梳两个大辫子的女同志一努嘴:“七十分!”
郭:原来这位女同志姓齐,叫齐淑芬。
马:我说:“齐淑芬同志,我爱人要生产啦,您值班儿请您跟我一趟吧。”
郭:齐淑芬说什么?
马:她一抬手向我说:“你瞧我这牌能叫七十分儿吗?最少也得叫八十五分。”
郭:怎么回事呀?
马:人家打百分儿哪。(马季、郭启儒《请医生》)从表1的对比中,可以看出马先生和郭先生的对话不是在双方互明的情况下进行的,马通过不断地修正郭的认识,让郭逐渐形成一个有关于医院场景的初始框架,之所以会出现郭的错误推理进而形成新的框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马的明示不够,明示手段不合理。因为这段对话是出现在相声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里,所以马肯定是故意而为之,使郭的认知框架前后不一致产生一种喜剧效果。

表1 请医生的整个交际过程
结合关联理论和框架转移理论可以这样认识相声制笑的认知机制过程:相声表演不仅是表演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相声作者与听众之间的动态交际过程。本文的研究与传统的幽默研究理论相联系,主要是幽默理论研究中的乖讹论(incongruity theory),相声中幽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相声演员一方所明示的信息不足,从而使另一方和听众所形成的初始框架和后来形成的框架出现偏差。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幽默理论的研究,推动中国相声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