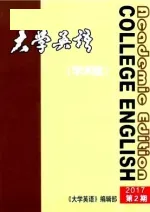悲剧意识下的乐观主义精神——《只争朝夕》主人公威尔赫姆的精神世界探析
张 艳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3)
悲剧意识下的乐观主义精神
——《只争朝夕》主人公威尔赫姆的精神世界探析
张 艳
(中国地质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3)
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在其小说《只争朝夕》中,描述小说主人公“痛苦”和“救赎”的意义。区别于同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品,小说中积极正面的结局体现了作者人道主义仁爱、乐观的人生态度,激发了读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使现代读者意识到仅仅活着就是具有价值与意义的。
痛苦;救赎;乐观态度
索尔·贝娄在美国当代被认为是与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齐名的三大犹太文学作家之一。瑞典学院因为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1]贝娄试图向读者揭示现代人的心理创伤,影射文明背景下人类生存极其窘迫的处境,经历了“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的发展过程,主人公的悲剧是在冷酷世界里普通人的悲剧,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全面的批判,体现了悲剧意识下巨大的现实意义。他更多的是希望人们认识到生活的悲剧性,并以深沉的乐观主义正视现实生活。他也向人们揭示了生活的奥秘,希望人们从痛苦中发现快乐的价值。这正是贝娄所具有的乐观的深沉、悲剧意识下的乐观。
贝娄是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对人生意义、人生本质、人类社会价值体系、道德观念等重大问题的探索。在更多的时候,贝娄实际上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通过探索摆脱人类生存困境的途径和对人类前途的忧患意识,来表现对人类深深的爱,与此同时也对人类的愚蠢和荒谬表现出极度的失望。这种正视现实也不拒绝希望的人生态度,正是贝娄文学作品透射出的深沉乐观主义倾向。人类的生存痛苦乃是人类的常态,所以用文学来表现痛苦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
“救赎”——犹太文化的不变的主题,也是贝娄文学作品中的乐观主义的根源。受难最早见于《圣经》,在《圣经》中,耶和华为了考验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圣人约伯的忠诚先后降祸于他,让他先后遭受了丧失牲畜、土地、家破人亡的灾难。“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是说:‘我在怒气,愤怒和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将从那里把他们召集回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3]因此,在犹太人看来,他们被驱逐异邦,受尽苦难是耶和华对违背戒命、道德沦丧、崇拜异神的犹太人的一种“惩罚”。只要犹太人恭顺地接受惩罚,悔过自新,最终会得到耶和华的眷顾恩免,会使之优宠于世界各民族。犹太人用“救赎”的观念把其面临亡国流散的悲惨境地解释成一种赎罪的苦行,反省忏悔必将得到救赎。
贝娄以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为主人公,是犹太古老文明与美洲新大陆智慧的结合构成了贝娄最伟大的创作动力,因此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犹太特质往往与美国文化相兼容,甚至同化。对索尔·贝娄而言,犹太经验是他永远无法摆脱掉的、根深蒂固的文化遗产,而美国经验是他无时不被浸润的文化大染缸和他文学创作的直接源泉和灵感,这两种文化在《只争朝夕》中得到了整合。从50年代开始,美国的犹太人在美国有了一定的地位,从而有了更多的自信和骄傲。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的内心的问题是“我在这儿做什么”而不再是“我是谁”。犹太文化最令人敬佩的一个本质就是对人道主义的信仰,对人性和未来总是抱有乐观主义的信念,这也许是支撑犹太民族历经两千多年饱受迫害的流散生存状态却依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之一。而贝娄全部创作的基调正是在批判否定背后潜藏的对人性和未来的肯定,他坚决摒弃以某些现代作家为代表的现代荒原意识和虚无主义哲学。
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马尔科姆·布莱德伯利称《只争朝夕》是贝娄“最平衡的作品”之一。约翰·克莱顿甚至认为《只争朝夕》是“贝娄最精致的小说”。小说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百老汇大街为创作背景,主人公是一位出生于犹太家庭的中年男子汤米·威尔赫姆,他重感情、讲信义、极具才能、光明磊落,可是命运不济,他受人排挤被迫离开自己视为生命的公司,被朋友欺骗,与妻子玛格丽特不和而分居。小说描述他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里,汤米一生的苦难达到了顶点。早上,他和父亲共进早餐,本希望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支持与鼓励,换来的却是一顿谩骂与侮辱。后来,与特莫金医生碰面,汤米为了走出自己的经济困境,拿最后的七百美金和特莫金合伙投资期货市场,但投资失败,血本无归,特莫金医生也突然失踪,父亲又袖手不管,而分居的妻子因他迟签支票不依不挠,对他的处境并未表示出任何同情。至此,感情与金钱损失殆尽的汤米在一个陌生人的送葬队伍中得到了心灵的涤荡与顿悟:仅仅活着就是具有价值与意义的。在这一天,真正死去的人赋予了“行尸走肉般”的现代人以活力。
《只争朝夕》表达了索尔·贝娄小说一贯的主题:人怎样在动荡的世界里找到生存的立足点,对生活始终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贝娄在作品中充分展示了美国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文化背后的阴影,揭示了在物质力量的极度挤压下,人的生存状态所发生的过度扭曲以致异化。主人公威尔赫姆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立足点,不断受到现实世界的嘲弄而显得荒唐可笑,他承受着精神世界的巨大磨难,然而他在奋力进行着内心的抗争,执著地寻求自我精神的立足点,试图超越生存的物化状态而建构起更为人道的价值世界。小说题目“只争朝夕”通过特莫金的嘴说出来,让读者以为是在劝人们活在当下要及时行乐,但之后,威尔赫姆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这才是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
被特莫金医生欺骗尽管是一种事实,但在与医生相处的过程中,汤米从特莫金身上获得了安慰,从特莫金口中说出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作者贝娄想要传达的主旨,在特莫金的言语中,汤米懂得要珍视自己的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孤独,苦难,以及死之欲望。特莫金告诫汤米,“只有目前才是真实的——此时此刻,只争朝夕”。[2](80)汤米意识到只有现在才是真实的,是他可以把握的。
他并没有对这个世界绝望。他不同意特莫金把人人都看作杀手、把这个世界视为“地狱”的观点,并争辩说:“总还有一些善良、平凡和有用的人吧?他们在——乡村。其实四面八方都有。”虽然威尔赫姆犯了愚蠢的错误,但他还是希望“让我后退一程,再重新开始吧!”
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一方面与时代进行抗争,这种悲剧命运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引起大家对当时社会弊端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不断追寻美好生活,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平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在诅咒命运的同时又毅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乐观地坚持生存的态度。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威尔赫姆脑海里可以不断闪现,“在片刻的宁静中,他似乎又回到了他在罗克斯巴勒的小庭院之中。他呼吸着早晨那清新甜蜜的气息。他聆听着百鸟的长鸣。”[2](96)街道市场在他看来是装满了鲜花与鲜果的象征富饶的羊角,阳光下金光闪闪的自助餐厅也变成了梦中的幻境。
威尔赫姆一直具有责任心,虽然经历痛苦,但它依然存在,这种责任感表现在虽然经济极度困难,但想到孩子,“不忍心让他们缺这少那”[2](58)他仍然愿意寄去抚养费,和妻子通电话时,他也极力劝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与你共同生活了多年的人呢?他把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你。他努力这样做过。他也爱过你。”[2](132)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一日夫妻百日恩的理念始终不被妻子认同,她要让威尔赫姆意识到离开自己后生活会变得多么窘迫。与妻子相比,威尔赫姆更加具有人情味。特莫金也劝过他抛弃妻子,可他没有那样做,他自我反省道,“现在,既无具体数字,也无对这种重担的价值做过估计。但也许威尔赫姆这个富有幻想的动物自己言过其实了。”所以暗自揣度:“我应该一辈子从事艰苦的劳动。”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挽回生活中的荣誉、幸福和无忧无虑的安宁”。他认为自己“从前是个傻瓜,但可以原谅。光阴被白白糟蹋了……事情太复杂了,但可以简化。东山再起时完全办得到的”[2](92)威尔赫姆完全可以走出虚幻,扎根现实,像父亲说的那样,做一个好士兵,履行自己的义务。经历了最后的心灵洗礼后,这种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会再次引导他的行动方向。
实际上,与父亲艾德勒、特莫金医生相比,威尔赫姆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他爱母亲,每年都会到母亲的坟墓上悼念。当特莫金问他是否爱父亲时,他的回答是“当然,我当然爱他”。“我也不希望他死……他一死,我就会丧失一切,我就再也没有父亲了。”[2](109)在经济困难,向父亲求助未果时,他虽有怨言,但也相信“不管年岁多少,父子之义是永恒不变的”。[2](55)“三番五次地劝诫自己,万万不可向他老子谈论他个人的苦恼问题,因为他父亲需要保持宁静”。威尔赫姆不仅对家人怀有一颗有慈爱之心,而且也用一颗善良的心对待他人,“威尔赫姆从来不曾故意伤害任何人的感情。”[2](40)当股市行情低迷时,他虽然心急如焚,但没有拒绝几乎双目失明的拉巴包特先生要他帮忙的“命令”。
他有一颗博大的心,他爱所有的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索尔·贝娄塑造的这位“反英雄”的真正意义。他虽然没有去教堂忏悔,祈求救赎,但是他善于思考事物的本质,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热爱身边的人。当特莫金谈到“每一个人的胸膛里——不只是一颗灵魂。有许许多多的灵魂。但是,主要的有两颗,一颗真正的和一颗伪装的。”[2](84)威尔赫姆很认真的在关注而且认同特莫金的话,人毕竟是社会的人,当人睁开双目看世界时,“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2](91)这是平凡中的伟大。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更大一些的机体,你不能脱离它而独立存在。 ”[2](98)
在小说末尾,当威尔赫姆路过泰晤士广场的地下隧道时,他忽然间感到,对身旁那些擦肩而过的行人们有了一种兄弟姐妹的情谊:
就在这黑洞洞的隧道里,就在这使人的外貌丑陋不堪并使鼻、眼和牙齿变得怪模怪样、支离破碎的闷热、昏暗和行人来去匆匆的地方,一种并非十全十美、甚至令人可怖的普遍的爱,在威尔赫姆的心坎里突然出人意料地涌现出来。他热爱他们。他热烈地爱着他们所有的人。他们是他的兄弟姐妹。他也并非十全十美,甚至可以说是丑陋不堪;但是,如果他以这种热烈的爱把自己和大家联为一体,那又会形成怎样的差别呢?他一边走一边说:“哦,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和姐妹。”他还为他们大家和他个人祈神赐福。[2](99)
这时,威尔赫姆与大家成为一个整体,不再耽于自己生活的困境中,这种普遍的爱让威尔赫姆感觉瞬间温暖。他意识到,“任何人的奥秘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真伪混淆仅仅是暂时现象”。[2](99)而且“在他沉思的日子里,他再一次地回味,思索,而且认为他必须回到那种思想境界中去。这是正确的途径,它可能使他受益良多”。[2](100)他开始剖析人的内心灵魂,这一切表明威尔赫姆终会得到救赎。
在小说结束时,威尔赫姆“湮没在崇高而幸福的泪水”之中,“藏身于人群”之中。[2](136)被淹没的意象既是威尔赫姆对受难命运的接受,又象征他精神重生的洗礼。他不仅是为个人失败的命运而哭泣,也是向过去虚假的自我告别——陌生人的尸体是他虚假自我的象征性死亡。威尔赫姆感到自己成为整个大的机体的一部分。他感受到了对所有同胞的爱,不再自怨自艾,逐渐地融入并与这个更大的灵魂联结在一起。湮没在如雨的滂沱泪水中,威尔赫姆领悟到了生命的意义、自由的可贵,终于解除了精神上的重担,找回了迷失的自我,这个被放逐的灵魂终于寻觅到了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
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卡尔·拉格纳·吉罗评价贝娄从未忽视过在咄咄逼人的现实世界里价值标准受到威胁的地位,这正是他经常描写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人类的行为举止或者科学的突飞猛进,预示着一场全球性的浩劫。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坚信人性善良的反对派领袖。
[1]Nina Bayn(1995).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W.W.Norton&Company Inc.
[2]宋兆霖 (2002).索尔·贝娄全集(第十卷).只争朝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圣经 [M].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