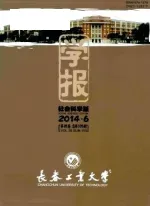陈凯歌影片文化禁锢表征的转型
王 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陈凯歌影片文化禁锢表征的转型
王 月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陈凯歌的影片历来格外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影片中人物都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中。在影片《梅兰芳》中,文化禁锢的表征已由“铁屋子”变成了“纸枷锁”,更深刻、真切地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通过对陈凯歌较有影响的三部影片《黄土地》、《霸王别姬》和《梅兰芳》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解读“铁屋子”和“纸枷锁”对人生的不同禁锢。
陈凯歌;影片;文化禁锢;铁屋子;纸枷锁;
陈凯歌从《黄土地》的一鸣惊人,《霸王别姬》向国际市场的进军,到《荆轲刺秦王》的票房“滑铁卢”,《无极》商业转型的破产,三年沉默后奉出的《梅兰芳》“创造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艺术效果的‘三重丰收’”,[1]也实现了陈式影片文化禁锢表征的改写。
陈凯歌历来都对中国传统社会语境格外关注,影片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浓郁的中国气息和特有的文化禁锢中,为广大西方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异国风情的视觉感官符码。而在艺术和商业何去何从中挣扎了三年的陈凯歌,影片中文化禁锢的表征已由“铁屋子”变成了“纸枷锁”,更深刻、真切地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铁屋子坚不可摧,想冲却冲不出去;纸枷锁很容易撕破,却不敢撕破。铁屋子中的清醒者企图唤醒沉睡者,而一切都是徒劳,即便醒来也是死在冲不出去的铁屋中;带着纸枷锁的人是清醒的,并清醒地给周围人也带上纸做的枷锁,然后大家一起带着枷锁起舞。
一、唤醒他者/给他者带上纸枷锁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出了“铁屋子”的生存困境:“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2](P3)在铁屋子中清醒者总想唤醒那些熟睡的人,不让他们闷死在铁屋子中。《黄土地》中为了展现这个“铁屋子”,不惜浓墨重彩地渲染铺陈。首先,影片中大部分黄土地的外景取自早晨或黄昏,使得土地的色调更为浓重,给人以沉重压抑之感。其次,影片中起伏绵延的黄土地常常占据了整个画面,只看到一点儿蔚蓝色的天空,让人感觉到挣扎的无望。八路军干部顾青就奉命来到了这个“铁屋子”——国统区陕西中北部农村,收集民歌,给部队文工团提供演出素材。顾青住进了村里最贫苦农民的窑洞家,与农家同耕、同食、同住,向不多言语的鳏夫和他的一儿、一女灌输革命道理,企图唤醒“铁屋子”中的沉睡者。
到了《梅兰芳》,影片一开头,闪现的不是梅兰芳舞台上的妙曼身姿,而是一张苍老的面容和一副纸枷锁,这也成为贯穿全片的文化禁锢的表征。梅兰芳轻易就打破了旧有枷锁对京剧的束缚,细微情绪的流露,文化内涵的融入,让所有人为京剧疯狂,可纸做的枷锁却从此紧紧套住了他,“只要你一天戴着它就一天不许撕破”。他想撕破纸枷锁,实现对心爱女人的承诺——去看一场电影,面对救场的请求,邱如白提起了纸枷锁,“知道它可怕在哪吗?就在它是薄薄的纸做的,不用丁点力气就能把它撕开。可要真能撕开,你大伯、你爷爷早就撕开了,既然他们都撕不开,那到了你这儿——”。哪怕撕开一天,撕开看一场电影的时间,邱如白也是不许可的,圈里的规则也是不许可的。福芝芳也跑去找孟小冬,让她离开梅兰芳,告诉她“梅兰芳不是谁的,他是座儿的”。邱如白和福芝芳都看到了这副纸枷锁,却又活生生地协助所谓的社会规则把纸枷锁套在了梅兰芳头上。
二、冲不出的铁屋子/不敢撕破的纸枷锁
鲁迅在提出了铁屋子的生存困境后,又否认了唤醒的必要性,他看到了铁屋子的坚不可摧:“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2](P3)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铁屋子’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象征’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3](P97-98)在文化原型的意义上,中国文化对人的基本欲望情感的禁锢,正如一个‘铁屋子’那样牢固和结实”,[3](P97)对中国的女性更是如此。《黄土地》中的翠巧就是在“铁屋子”中呐喊却冲不出去的女性。顾青对延安的描绘启发了13岁的翠巧,可是当意欲逃婚的翠巧哀求顾青带她到延安时,顾青却以纪律不允许为由拒绝了她。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她们的命运被男权和男性话语所主宰。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翠巧在顾青的呼唤下醒来,这时顾青却突然收回了伸出去的手,失去了顾青的协助,翠巧是绝冲不出这铁屋子的,只能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摆脱铁屋之困。
到了《霸王别姬》中年幼的小豆子已有了清醒的意识,不需要被他人唤醒,可他却在他者的强制下走进了铁屋子,从此便再也冲不出去。他被母亲剁了第六根手指,这样才有资格学戏。当他被安排学旦角,他总是念错《思凡》中小尼姑的道白,把“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说成是“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一次又一次地出错,一次又一次地挨打。当师兄把师傅的烟袋插进他的嘴里时,鲜血从嘴角渗出,从此他便能很自如地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待小豆子在堂会演出后,被前清太监倪公公召到后宫玩弄了一夜。这些经历都在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程蝶衣已经被阉割、被压迫、被女性化。他冲不出去他被女性化的铁屋子,只能在铁屋子中以畸形的方式恋着他的霸王,不满霸王和其她女人结婚,不满霸王和其他旦角唱他们的《霸王别姬》。然而这也只是他一厢情愿的不满,他的霸王还是和菊仙成了亲,还是和小四唱了他们的《霸王别姬》,一切的抗争都是徒劳,他走不出想把他型塑成女人的男人构造的铁屋子。
从铁屋子里醒来的人想冲出去,也敢冲出去,但却冲不出去;而纸枷锁下的人不想撕破,也不敢撕破它。到了陈凯歌倾尽心血的《梅兰芳》里,每个人在时代浪潮前都看得到象征所谓规范的纸枷锁,但却没人敢撕破它。十三燕是旧时代京剧艺人的缩影,这位过去的伶界大王并非不懂得创新——他的薛平贵面对梅兰芳扮演的王宝钏在表演上的变化,轻轻巧巧地便接了过来,得了个大彩。他看到了纸枷锁却不敢撕破,固执地不肯改戏,并一再申明自己不守旧,什么老规矩都不在乎,在乎的是在戏上一会儿一改,怕人家说自己是朝三暮四靠不住。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他对于戏子低下地位——下九流——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为了避开舆论的纸枷锁,便选择一意坚守地戴着它。
福芝芳曾是当时梨园行最早的一代坤旦之一,自嫁与梅兰芳,便退出舞台。在孟小冬家两个女人的对峙中福芝芳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不如你,过去也唱过,自打跟畹华结了婚,就把戏给扔了。”福芝芳还是渴望站在戏台上的,为了成全丈夫,她作了伶王身后最坚实的后盾。她去求孟小冬离开,不是因为这个女人夺走了丈夫对自己的爱,而是怕她分了梅兰芳唱戏的心。因为她看到了“他是座儿的”。她在梅兰芳有钱的时候替他管家,在梅兰芳需要钱的时候为他典当首饰养家。她希望梅兰芳事业成功,更希望他生活安稳。在梅兰芳访美前的筹款中,福芝芳起初坚持典当家产凑钱,钱凑不够时,无奈才签了抵押房子的文书。她带着自己看得清清楚楚的纸枷锁牺牲自己的一切,掩住自身的光芒,成全了梅兰芳的一生。孟小冬作为一代坤角之后,在面对持枪戏迷要她“立即、马上离开梅兰芳”的威胁时,她能够坦然地说“你可以现在就打死我”,但面对邱如白“谁毁了梅兰芳的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的忠告时,她选择了离开。两个女人为了所爱男人事业发展的一纸枷锁,一个为了爱而放弃,一个为了爱而坚守,没有人敢撕破纸枷锁。
三、在铁屋中死去/戴着纸枷锁起舞
困在铁屋中的人或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闷死,或者是被唤醒,可醒来也冲不出去,又不甘待在铁屋中,只好以死亡的方式来告别铁屋。而戴着纸枷锁则不同,人们逃不过纸枷锁,就小心翼翼地戴着它,只要不让它撕破,就可以戴着它起舞。《黄土地》中翠巧哀求顾青带她离开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于婚后不久,便独自泛舟横渡波涛汹涌的黄河,丧身于黄河的巨浪中。她似乎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临别时唱给顾青的是诀别之词,而她选择独自强渡本身就是一种自杀行为,她以生命的结束摆脱了铁屋的型塑。
《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一次次的遭遇迫使他转变了性别意识,他为了彻底实现女性的身份认构,于现实生活中也恋上了戏里的“霸王”,迷失于戏里戏外的铁屋子中。当菊仙出现时,一声“师弟”向他展示了周转于柴米油盐、养家糊口中的现实版的段小楼。然而,铁屋中的他只能不停地为自己的霸王义无反顾地去付出,他牺牲自己的色相为换回段小楼心爱的宝剑;段小楼被日本人抓去,他又不惜损害个人的声名去为日本人唱戏。文革时菊仙的暗示使段小楼对戏曲艺术的坚守做出了现实的妥协;批斗时段小楼的揭发背叛,使蝶衣发出了“你们都在骗我”的绝望悲鸣。在铁屋中醒来,但却冲不出去,只能以死的方式离开铁屋。当获得平反的程蝶衣和段小楼再次粉墨登场时,虞姬从霸王腰间抽出宝剑,自刎倒在台上,又一个生命告别了铁屋。
《梅兰芳》本是一部传记影片,即便影片中的其他人再出彩,主角仍是梅兰芳,纸枷锁下套得最严实的还是梅兰芳,但纸枷锁下舞动精彩人生的也是梅兰芳。影片以大伯的信为叙事框架,这封信的间断叙述和重复叙述的画外音始终伴随着梅兰芳的每一步成长,每一个艺术和人生的紧要关节。梅兰芳的成功离不开艺界、商界、政界和座儿的帮助,但他正是被他所帮助的人绑架而戴上了纸枷锁。十三燕引领他面对人生苦难逆境,告诫他捍卫梨园人的尊严,使他得到了座儿的认可,但十三燕不允许他改革京戏。邱如白是梅兰芳一生事业成功的策划人,引领他实现京剧变革,帮助他步入艺术巅峰的辉煌之境,但却在他追逐真爱的过程中给他套上了纸枷锁。另外,邱如白在一意坚持梅兰芳复出时,冒名给电台打电话,使梅兰芳陷入了丧失民族大义的误解中。这一切福芝芳都看得清楚,当听到电台播出梅兰芳将于近期复出的消息时,福芝芳说“自从畹华认识了他,就让他给绑了架了”。
梅兰芳在纸枷锁下面临着太多次唱与不唱的选择。小时候就知道大伯在信中说“不想让你再戴上那纸枷锁”,在年幼第一次唱与不唱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唱,主动戴上了纸枷锁。和十三爷争辩改戏的打擂赛中,在要不要唱新时装戏《一缕麻》时,“以前我不敢唱,今我输了,反倒敢唱了”,他依旧选择了唱。梅兰芳不断进行着戏曲革新,戴着纸枷锁推进了京剧的改革。当他要和心爱的女人去看电影时,三哥提起了纸枷锁,在纸枷锁的束缚下,他放弃了爱情,选择了事业。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面对要不要去美国的抉择时,福芝芳再次看到了梅兰芳的纸枷锁。她对六爷和三哥说“从我进了梅家,我就没见过畹华干什么事是自由自便的”。此时梅兰芳又想到了大伯的信“大伯想让你不唱,可兴许你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那你就好好唱,千忍万忍带着你的纸枷锁甭回头,一股劲儿地走到底吧。”他在纸枷锁下一直向前走着,他选择了去,他走红了美国,他把京剧带出了国门,让世界认识了京剧,认识了中国。在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在要求他复出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提起十三爷要他帮个忙“把咱们唱戏的地位提拔下好不好?让人家把咱们当人看好不好?”答应老人家的事,他做到了,他选择了不唱。
梅兰芳在纸枷锁下一次次放弃“规矩”、放弃爱情,成就了他京剧艺术的辉煌。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放弃了代价重重换来的事业,实现了民族大义的超越。抗战胜利后,片中又出现了戴着纸枷锁的大伯,梅兰芳又置下大伯的劝告,主动戴上了纸枷锁走上了戏台。梅兰芳的一生都没有挣脱纸枷锁,也未被纸枷锁束缚住,他让纸枷锁熨贴了每一寸肌肤,戴着纸枷锁舞出了人生、艺术的辉煌!
“纸枷锁”较“铁屋子”多了对人性束缚的残忍与无奈,“铁屋子”里人们要么无知地死去,要么在反抗中永生;“纸枷锁”下人们已放弃了反抗的冲动,甚至心甘情愿地为自己、为身边的人套上纸质的枷锁,并小心翼翼地在没有“铁屋子”的空间里“自由”行动以维护“纸枷锁”的完好无损。这种文化禁锢表征的改写更加深刻、残忍、绝望,更加暴露了人性面对自由的无能。
[1]杨新贵,等.评电影《梅兰芳》[J].当代电影,2009,(1).
[2]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长沙:岳麓书社,1999.
王月(1982-),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